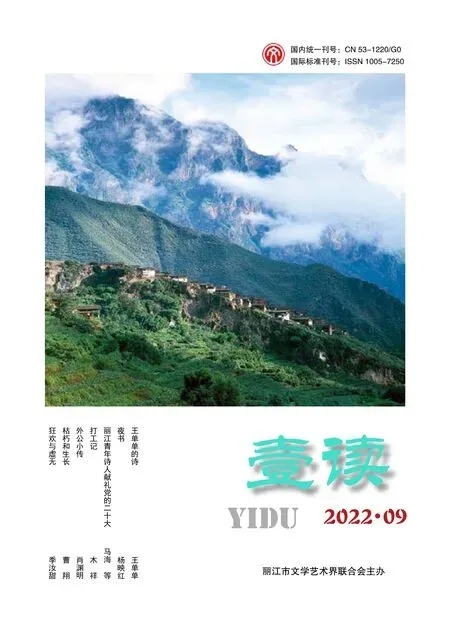外公小傳
◆肖淵明
1
故事須得從外公的爺爺講起。
老一輩還處在三妻四妾的年代,家中擁有一座山頭,身為“莊園主”的爺爺卻對奶奶沒有二心。
可惜啊,奶奶雖然得了愛人的心,卻沒法為他生兒育女。和爺爺不同,奶奶總覺著爺爺家的香火可不能斷在爺爺這里,她整日里就琢磨,該去哪個地方給爺爺再物色一個能生的小媳婦兒。
挑選了許久,最后奶奶將目光放在了一個在親戚家里做長工的江邊姑娘身上。
爺爺本不想再娶,可奶奶卻堅決不在這件事上讓步妥協,就連夜里都不準爺爺上床睡覺,除非爺爺愿意去見那個姑娘。兩人就此事僵持不下,最終還是爺爺選擇妥協,同意了奶奶的要求,去見了那姑娘一面,并直接將她“拐”回家中。
這之后奶奶總算喜笑顏開,就盼著姑娘早日給爺爺生個大胖小子出來。
可惜事情仍有變數。
那個年代,家中的女兒都是用來“賣”的,那姑娘的父母早早收了別人家的禮金把姑娘給賣了。而那戶買姑娘的人家在江對岸的寧蒗也是大戶人家,禮金都下了,總得去把媳婦娶回來吧。
于是有一天,那戶人家便闖進了爺爺的山頭,說是來領媳婦兒回去。
可是這個時候姑娘早跟了爺爺,是爺爺家名副其實的二奶奶,現在突然要讓別人領走,別說爺爺不依,早把姑娘當自家人的奶奶也不可能同意。
兩家爭吵了許久都未能得出姑娘到底該歸哪家的結論,無奈之下,只好去保長家里請保長幫忙評理。
可這樣一來,爺爺家可不是理虧嗎?那人家先下了禮金買下的媳婦兒,突然就被人半路截胡了,這換誰來判不都得將姑娘判給先下禮金的那家。眼見兩家又有要掐架的趨勢,保長一錘定音,直接把姑娘判給了寧蒗人家。
寧蒗人家將評判的證書收好之后,就準備帶著媳婦離開。
然而此時天色漸晚,寧蒗人家沒辦法披星戴月趕路將姑娘帶走。一心想著如何解決問題的奶奶望著漫天星光之下若隱若現的銀河,心中再生一計。她邀請寧蒗人家在爺爺家歇息一晚,待到明日清晨再趕路也不遲。
奶奶好言好語相勸,也算是微微放低了姿態,看起來似乎也沒有因為媳婦被搶走而感到氣惱。
寧蒗人家自然也是在幾句交談之中緩解了方才爭吵不休而產生的隔閡,他們商議之后,決定聽從奶奶的安排,在家中休息一晚,明日再出發也不遲。
當天,爺爺家里又是殺雞又是宰鵝,給客人們準備了一桌豐盛的晚餐。
奶奶知道寧蒗人喜歡喝酒,便打開一罐陳年的蘇里瑪酒,給他們倒上。酒香四溢,將整間屋子都染上一層濃郁的香氣,幾人不過是聞著香味都隱隱覺得醉了,不自覺地深吸一口氣又咽咽口水。
眼前盡是美酒佳肴,如何能苦了自己的胃?幾番暢飲下來,便醉得不省人事了。
火塘里還在燃著旺旺的火,他們卻倒在了火塘邊的床上呼嚕呼嚕睡著了。
而這正是奶奶想看到的。等到幾人酣睡不醒,奶奶才湊上前去,從他們的貼身小腰包里翻找出那張被小心翼翼收起來的評判文書并將其藏了起來。
待到屋外晨光熹微,奶奶已然笑瞇瞇做好了早飯準備送幾人離開。
尚未完全清醒的幾人對奶奶表示感謝,并連聲稱贊爺爺家的飯菜美味、美酒可口。不過等到他們想帶著“他們家的媳婦兒”離開的時候,他們再也笑不出來了。
奶奶拉著姑娘的手,神情嚴肅。
她一臉正色告訴他們,須得有東西能證明這是他們家的媳婦兒才能讓他們把姑娘給帶走。
幾人只覺得奶奶是糊涂了,昨日在保長家可是拿到了評判的文書,上頭寫得清清楚楚這媳婦兒就是他家的。幾人未曾在意,笑著伸手掏腰包,準備把文書拿出來讓奶奶好好回憶一下昨日對峙的情形。只不過……伸手一摸,文書不在腰包里;伸手二摸,文書還是不見蹤影;伸手再摸,腰包里仍舊空空如也。
手還搭在腰上,余光一瞥,又見奶奶笑瞇瞇的模樣,如何還能不明白發生了什么。
可昨夜又見爺爺家的財力物力,現如今他們可不像昨天那么強勢了。
幾個人面面相覷,愣了許久。最后只能吃下這個啞巴虧,拱手將已經買回來的媳婦兒送給了爺爺。
雖說幾人吃了個啞巴虧,可爺爺還是將姑娘父母收下的禮金代為歸還,總不好讓人家賠了夫人又折兵。
也正是因為奶奶的精明能干,爺爺后來才會有三個孩子——才會有我的外公,才會有現在的我。
可惜二奶奶命不好,在生第四胎時難產,沒能救回來,和她那尚未出世的孩子一起離開了。
2
都說了解一個人要從他的爺爺輩開始,外公的爺爺奶奶精明能干,外公自幼受其熏陶,自然也從奶奶身上學到了堅韌不拔的精神。不過外公的性子更像他的母親——寬厚、仁慈。
外公的父親在家中排行老二,是個祭天的大東巴,村里以及鄰村祭天都要請他前去主持。不過外公未能繼承其大東巴的身份,而是干起了馬幫,成為了充滿傳奇色彩的馬鍋頭。
3
下午六點,屋子里還很熱。
天色還沒有暗下來,暖陽透過窗口落進屋內,光線下除了柴火燃燒產生的煙霧外,還飄浮著塵埃。
屋子和正在窗邊翻找東西的老人一樣,看起來飽經風霜。
老人從某個角落找到他所需的東西——那是一個顯眼的紅色塑料袋,被老人攥在手里,在夕陽的照射下成了屋內唯一一件搶眼的物品。
老人名為和汝典,是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曾是馬幫的馬鍋頭——馬鍋頭是馬幫首領的尊稱——他所講述的故事在我這代人眼中聽起來總是覺得新奇。在那個沒有汽車沒有飛機的年代,靠著一隊騾馬于各個城市中往返的馬幫充滿了神秘感,便是如今再聽他講述以往,也能夠從他的言語中體會行路的艱辛以及馬幫那不可動搖的堅韌意志。
正對著窗口,光線略微刺眼,我瞇著眼看著外公用自家種出的小梨將塑料袋填滿。外公總是這樣,不論我什么時候來,來的時候有沒有帶禮物,他總是不忘將自己有的分我一些,讓我帶回家里。
小鑼鍋剛架到火上,外公緩緩在火塘邊炕上坐下。他的手里拿著獐子皮制成的煙袋和黃櫻木做成的煙鍋,點燃煙吸了一口,就著滿堂縹緲,又開始講述他的故事。
還沒造橋時,馬幫渡河有兩種方法:其一便是坐船,其二則是使用溜索。
坐船當然是首選,可總有些時候需要用到危險性較高的溜索。外公口中的溜索是麻質的,比人的大拇指還要粗不少,人坐在第一根繩上,第二根繩則在腰、背、肩等部位打上活結連接到嚴實的鐵環之上。
溜索從高往低滑,快滑到地方的時候,有人在兩側牽著繩子綁住坐溜索的人緩沖,而緩沖之后,坐溜索的人雙腳蹬在擺放在前面的草堆上停住。
據說若是在晚上滑溜索,能看見溜索上劃過一串火花。
雖說外公很堅定地告訴我,坐溜索的時候很安全,人就算在溜索上面掛上兩天也沒什么問題,可我未曾親眼見過,聽著只覺得呼嘯的風已從耳畔掠過,帶來的全是未知的危險。
外公突然停頓了一下,他凝神靜聽從鑼鍋內傳出的輕微沸騰聲,眼神略微飄忽。他安靜了幾分鐘,緩緩將目光轉向我的方向,透過他那飽經風霜的雙眸,我隱隱看到了一段抹不去的記憶。
1958年,正值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
那年外公不過十五歲,前往寧蒗參與修建麗華公路。大東人民公社說要供給他們一頭牛,需要他們回到麗江將牛肉運輸到寧蒗,于是外公與另一個同伴伍三共同承擔起將牛肉運回寧蒗的重任。
渡口正在造船,但是還未完工。無奈之下只能選擇溜索,可即便是溜索都只有單邊——自麗江往寧蒗方向滑的單邊溜索。若是想要從寧蒗回到麗江,那第一選擇就是順著溜索從寧蒗反方向爬回金沙江對岸。可惜伍三身體單薄,沒辦法自行爬過溜索,只能選擇較為危險的下水渡江。
渡江自然要選擇水流平緩的地帶,于是兩人簡單告別,準備各自用不同的方法渡江。
外公來到溜索旁,率先往身上套麻繩,他在“擺渡人”的幫助下利用兩個滑輪將自己牢牢吊在溜索上,背對著江水開始了自己的攀爬之旅。
也不知道雙手抓住溜索爬了多久。他感受到身上掠過的風越來越緊,知道自己離地面已愈發遙遠。
耳畔除卻疾風之外,還響著自背后傳來的疾馳而過的江水聲。
烈日高照,火辣辣地照在他的身上。不斷頂著烈日順著溜索奮力向上攀爬,他的全身都開始冒汗。
他抓著溜索,仰起頭,順著溜索向上看去,試圖從視線所及之處看見江對岸的終點。可他再怎么努力仰頭,也只能看見那條吊住他的溜索筆直地向上延伸,最后超出了他的視野。
根本望不到頭。
他收回目光之后,又想低頭,順著溜索找尋起點。可是這么一個固定不動的姿勢,他最多能從雙臂的縫隙間看見自己休息時扣在溜索上支撐全身的雙腿。
他深呼幾口氣,放松著已經開始發酸的雙臂。
身體還有些力氣,但是他準備休息一會兒。在刺目的陽光下他只能瞇著眼,微微偏過頭,讓自己能更舒服一些。偶爾有幾只飛鳥自他一側路過,嘰嘰喳喳,等到飛遠了,那幾聲悅耳的鳴叫又混入奔騰的江水聲中,再也聽不見。
他休息夠了,又開始向上爬。他在心中默默數著雙手向上挪動的次數——一個五十、兩個五十、三個五十……重復的動作讓他雙臂酸痛不已,手心也早因為和溜索摩擦而感到火辣辣的疼。
他想得很好,每五個五十,他就休息一次。可身上出現的異樣讓他休息的間隔不斷縮短,休息的時間卻越來越長。
已經記不清是第幾個五十了,也記不清休息了多少次。
身后的江水滔滔不絕,翻滾著,呼嘯著,奔流而下。不會停歇的水流早已穿透了渺小的他。他的腦海中充斥著江水奔涌的聲音,恍惚間讓他生出自己已經掉下溜索被滾滾而來的金沙江吞沒的錯覺。
抓著溜索,他心中滿是悲涼。
奔騰的金沙江上,有一條橫跨而過的溜索,有一個人吊在溜索上,除卻江水而外再聽不到任何聲音,仿佛天地間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渺小得讓人心生絕望。
絕望感逐漸將他包裹,他甚至開始想象自己真的掉進江水,淹沒在急流中。只覺得心底止不住地冷,連著后背都感到冰涼。
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微微顫抖的手往后背上摸去,竟摸到滿手涼意——原來他的衣服早已被汗液浸濕,一陣涼風竄過,整個脊背都是冷的。
可一想到連隊的兄弟們還等著吃牛肉,一想到只要他能渡過這個江,就能見到思念已久的父母,他只覺得身上又有了力量!他又開始不斷努力著向上爬去。
太陽暴曬著,他的身上一直在出汗。身體因為缺水有些無力,喉嚨更是干澀難耐,嘴唇也干裂出血,又被鮮血染得濕潤,連帶著他的意識都有些模糊。
可是等到那雙已經布滿了傷痕的手再次緊緊握住溜索,他那模糊的意識又會被疼痛刺激著,恢復短暫的清醒。
他強忍著能灼傷人的疼痛,逼著自己將脫離溜索的雙手再次放上去。碰觸到溜索的時候,還是因為痛意忍不住縮了下手,那已經不是他能控制的,是身體保護自己的本能反應。
他一點一點向上爬著,爬向根本看不見終點的江對岸。
太陽逐漸偏移,尋了一塊軟糯的云朵歇腳,偷懶打個盹兒。
可他的身體早已僵硬,神智早已模糊。哪怕沒有了烈日,他的前行依舊艱難——全靠著那驚人的意志力才能重復向上攀爬的動作。
等他到達對岸的時候,他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邁過了成功的門檻,他僅存的意識驅使著他抓緊繩索向上攀爬。
江對岸也是有“擺渡人”的,他們解開他身上的繩子,想將他放下來時,他反而將溜索抓得更緊。似乎他還在那條隨時都能將他徹底吞噬的江水上。
下來之后,哪怕休息了很久,他的神情依然木訥,他還沒能從噩夢中蘇醒,他渾身都在顫抖。他的嘴唇就像連年大旱時的土地,他的手沾滿了已經干枯又碎裂開的黑色血塊。
話音戛然而止,外公低垂著眼眸,用粗糙的指腹摸著手上的老繭,“就算以后我忘了,這雙手也不會忘。”外公手上的老繭,至少有一半要歸功于這次的爬溜索事件。
手腕酸痛持續了將近半個月,甚至可能還要更久,似乎一直沒有恢復,睡覺都能夢到自己吊在半空中,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沖走。
那雙手也慘不忍睹,連著冒了一排的泡,哪怕不小心碰觸一下都能讓人感覺到疼痛。水泡的那層皮也會因為不小心碰到而炸開,炸開之后水泡里還沒長新皮的肉直接接觸外界,一個不小心又是細密的疼痛,接連不斷地從手心傳來。
回去自然是不能告訴老爹攀爬渡江實情,只能想辦法把一雙手藏起來。外公的老爹對外公這個長子一向寄予厚望,要求也非常嚴格,做事都要按規矩來。外公自然也是對老爹敬重,不敢有絲毫差錯。不過在家中總把雙手藏起來,怎么可能不被懷疑?面對老爹嚴肅的神情,他最后還是只能將此事全盤托出。然后啊,自然免不了一番語重心長的教導。自己出門在外,安全永遠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下次就別這么冒險了……
忽然,外公的眼神突然亮了,他說他爹也有帶他一起去冒險的時候,其中有一次就是帶他去獵熊。
4
與今日不同,那時的村中還能見到手持獵槍與弓弩深入山林的獵戶;而今天村莊里已經鮮少見到上山打獵的農戶了,許多野生動物也都被列入了保護名單……
此刻,外公叼著煙鍋,深深吸了一口,慢慢講起那個獵熊的故事。
雪山甘海子,千年冰川的方向,云霧繚繞——那正是當年外公和他父親一起獵熊的地方。
秋收過后,村里的男人都開始集中打獵,從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
這一行,他們總共來了九個人,其中有個名為伍之的人知曉熊洞的位置,所以便由他前去探查熊洞里有沒有他們此行的目標,剩余的人則原地休息,等候他的消息。
沒過多久,伍之已經探明情況,他那神情中掩藏不住的興奮已經告知了大伙一切——獵物就在洞里!
于是眾人開始商討如何下手。伍之不僅知道熊洞的位置,他還是九個人當中射箭技術最好的一個,幾個人商量后決定讓伍之先出手,等他把熊趕出熊洞之后再集中火力。
幾人攜帶的唯一一把長火槍正是外公父親的,據說比一般的短火槍更猛,于是外公的父親與隊伍中另一人帶著獵狗遠遠觀望。
等到幾人說定之后準備動手,為了方便集中射殺,他們要砍掉洞口一棵手腕粗的樹。然而樹砍了一半便有意外情況發生,有一塊木屑飛進了洞穴中,片刻間眾人便聽見了從洞穴中傳來的低吼。
所幸熊只是哼了幾聲,并沒有在他們準備就緒之前先給他們來一波意想不到的突襲。
等到幾人各就各位,伍之對著熊洞開出了第一槍。
頃刻間,那頭熊便從洞穴中飛奔而出,兄弟幾人按照先前制定好的計劃快速招呼著手里的家伙伺候這頭倉皇逃離的熊。可是熊并沒有倒下,大聲哼著直奔草坪而去。
大伙看到圍堵失敗,熊成功逃出生天,多少有些氣餒與沮喪。一個個的,都蹲在洞口,點燃一桿煙,互相問有沒有射箭。都是沖著這頭熊來的,哪里會有人偷奸耍滑?大伙都卯足了勁,準備讓自己的獵物清單上再多一頭熊的身影。可惜啊……
就在眾人唉聲嘆氣時,外公的父親卻獨自一人站起身,朝著那頭熊消失的方向摸了過去。順著那個方向走了一段距離,那頭熊的腳印也逐漸清晰——上面沾滿了斑斑血跡——再跟蹤著腳印向前尋找,又能看見石頭上多了些被熊爪抓過的痕跡。他小心翼翼地四下探查,最終在不遠處發現了已經躺倒在地的熊。
那頭熊沒有發出什么動靜,外公的父親在原地看了一會兒,還是覺得先把眾人喊過來。等大家伙一起來到這邊,觀察一段時間后得出結論:這頭熊已經徹底咽氣了。
至于那些石頭上的抓痕,是因為他們射的箭都在箭頭上涂抹了草烏劇毒,這頭熊雖然從他們的圍追堵截中成功逃出生天,可那些已經刺入它身體的箭,卻已經足以致它于死地,等毒性發作,這頭熊苦苦掙扎,這才留下了石頭上的數道爪痕。
他們慢慢打開熊皮,看到了眾人各自射中的部位。伍之的箭射在熊胸口的硬骨上,外公的父親用那把長火槍直接穿透了它的肺……他們在熊的身上找到了各自的箭頭,方才的郁悶早已一掃而空,都在為自己精湛的箭法而贊嘆,為成功拿下大熊而高興。
他們燒火烤肉,等到飽餐一頓后再背上熊肉來到城里,天色都沒黑下來,熊肉已經賣完了。可惜熊皮在賣出之后皮匠鋪不收,又退回到了幾個人手中,在城中輾轉了三天才成功出手。一行九個人,每人都分到銀元三塊半。
“等等。”我忍不住出聲了,剛才要是沒聽錯的話,是不是說那箭頭上是涂了毒的,那怎么這肉又能吃又能賣?就不怕毒死了買肉吃的人?
我對此提出疑問,外公搖搖頭,糾正我錯誤的想法。
并非只要箭上涂抹了劇毒之后整頭熊的肉都會作廢,他們只需要挖掉箭頭周圍的那一圈肉,剩下的熊肉都是可以吃的。外公告訴我,過去都是這樣打獵的,他還說獵物最多的是他姨爹家。
在姨爹二樓陽臺上掛滿了獵物的頭骨,都是姨爹的父親獵到的。獵物的頭都歸他,這些頭骨會在他離開人世時燒掉,還要祭奠獵神。
故事到此為止,外公手上的煙也只剩下最后一口。
5
水蒸氣與柴火燃燒的煙霧混合在一起,徐徐向上飄去。
一打開小鑼鍋,整間屋子里都彌漫著濃郁的飯香。
外公抽完了煙,將煙鍋擺在火塘邊,我將碗筷遞到外公手里,目光不經意間自他瘦削的臉龐上掃過。視線所及,除卻暮年的滄桑而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那雙深邃的雙眼。
我只覺得外公的眼里仿佛還留存著往昔的光景,在搖曳的火光之下熠熠生輝。
外公夾起一塊排骨送到我的碗邊后又拿起擺在他手邊的那小碗酥油茶,他看著酥油茶,似乎又被帶進回憶之中。
馬幫一般由四個人組成,每人分別負責自己的騾馬。
外公當時是馬幫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夜幕降臨的時候,整個馬幫隊伍里只有我外公一人能夠翻越叢山,也只有他一人能夠趕上藏族的馬幫“雄霸”一起夜宿山上。
大抵是因為總能趕上藏族馬幫一起露宿,外公如今也能說出些藏族馬幫的習俗。
酥油茶正是藏族馬幫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菜品——即便身處山林之中,也無法阻擋他們對酥油茶的喜愛;但凡生火做飯,他們總會打酥油茶的。
外公告訴我,當初和藏族馬幫“雄霸”一起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總是帶著一個專門祭神用的小碗。他們會先往這個小碗里倒上一碗酥油茶,擺放到灶臺面前,然后才會用自己的專用碗喝酥油茶。不過在喝酥油茶之前,他們會用中指沾上一點酥油茶朝著自己的頭頂彈三彈。
外公喝了兩口酥油茶,又夾起一片肉,繼續和我說他所了解的事情。
他說藏族的馬幫在吃晚飯的時候有一個很特別的習俗,他們會根據馬幫的人數切肉,馬幫里有幾個人就切成幾片肉。隨后會讓其中一個人背對著他們回答今晚有幾個人吃飯,回答的人可以隨意說出任何數字,然后他們就會根據這個數字算出哪個人該吃到哪片肉。
假設吃到了最好的那一片肉,這個人第二天在路上便會很順利,一路暢通無阻。
假設吃到了最差的那一片肉,那他第二天在路上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不過正是因為在前一晚就有算過運氣如何,第二天行路的時候,馬幫的幾個人都會自覺幫助這個運氣不太好的人度過難關。
我聽到這,剛剛夾起排骨的筷子在半空中頓住了,微微扭過頭,往菜板上剩下的完整的那塊肉上看了兩眼。
外公順著我的目光看去,顯然明白我這是想做什么了,不過外公卻對著我搖搖頭,他并不知道藏族馬幫是如何算出哪個人該吃哪片肉的。
心底略微有些失望,不過這也不妨礙我繼續聽故事。
只聽外公繼續道:“還記不記得剛才說藏族馬幫吃飯前會先倒出一小碗酥油茶祭神?”
看我點頭,外公又接著往下講:等到馬幫準備離開的時候,會把熬酥油茶用的茶葉分開倒在安灶的灶石上,再抓三把青稞面撒在茶葉上,最后把那小碗酥油茶倒上去。而這么做的原因,卻是為了讓后來趕路的人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也能拿這些東西墊墊肚子。
外公說到這里,突然又想到了方才遺漏的細節,轉而扭過頭和我追溯藏族馬幫做飯之前的一個小準備。
外公說他們不會殺生,所以每次做飯之前,都會先查看地面上是否有螞蟻一類小動物的蹤跡,只有在見不到它們的情況下,才會把開水倒上去。
我咽下嘴里的飯,感覺這次外公講述的場景十分有畫面感:
外公之前曾經說過藏族馬幫的裝扮——藏族馬幫所有人都會攜帶兩把長刀,一把掛在后腰上,一把斜掛在腰前的腰帶上,以防路上碰到搶劫的。
此時我腦子里飄過的場景便如這般模樣:一幫斜挎大刀的五大三粗的漢子,微微佝僂著腰,小心翼翼地探查腳底以及四周有無小螞蟻的蹤跡。
雖說想象中的畫面略微有些違和,可聽過外公的講述,只覺得這便是藏族馬幫那魁梧的外表之下有如涓涓細流般不斷溢出的別樣溫柔。不論是身處何方都不忘了信仰,亦或是那塊留放在灶臺上的青稞面餅,再或者是對待渺小的螞蟻……都能夠讓人感受到一種無法被粗獷的外形所掩蓋的,從骨子里流淌出、透露出的溫柔。
提到這一點,外公又忍不住給我講了個小故事。
外公的馬幫隊伍里有一個人,從路邊撿了許多雞縱蟲吃了,還不慎被藏族人達瓦給發現了。被發現之后,達瓦拎起一把藏刀過來,說他這是吃了千千萬萬條命,要償命的。周圍的人怎能任由事態發展,一個個都拼命阻攔,甚至還有人直接從后攔腰抱住達瓦。再三阻攔之下,達瓦總算冷哼一聲,放下了刀。
我接過外公遞過來的空碗,以為這個故事就到這了。
但故事仍有后續:在勸阻之后,達瓦走到了那個吃雞縱蟲的人面前,周圍的人心有余悸,見達瓦又有往腰上摸刀的意圖,連休息都來不及,差點再沖過來按他一次。幾人沖到面前,都做好摁住他的準備了,可余光一瞥,達瓦沒有摸刀,而是摸出了一張百元鈔票丟到了那個人的面前,鄭重地吐出一句話——想吃什么就拿去買!
6
達瓦最后的處理方法著實讓人感覺出乎意料。
我仍在回味剛剛故事的尾聲,母親卻突然轉了話題,原來是想告訴我外公和雄霸的兄弟情誼是從哪開始的——一切都要從外公釘馬掌這件事說起。
都說人靠衣裝馬靠鞍,可是身為馬幫的騾馬,整日跟著這群漢子馱著重物風里來雨里去,沒有一雙“好鞋子”怎么能翻山越嶺?
釘馬掌可是一個技術活,而雄霸最佩服的就是我外公釘馬掌的一手好本事。
所有跟著馬幫混的騾馬都要釘馬掌,一般工匠師傅釘的馬掌能夠支撐兩個月多,而外公釘的馬掌,足足能支撐三月之久。
他伸出雙手給我比劃,模仿著用偏錘敲打的動作。這是外公最拿手的本事,他給我演示的時候眼底帶著一抹別樣的光彩,那是許多年后的今天也無法磨滅的,由內而外透露出的自信。
釘馬掌之前,還是有準備工作要做的。首先要把陷進它腳底的泥土弄出來,再把馬蹄底部削平。說來這便和人剪指甲是一樣的,騾馬被工匠師傅修整馬蹄底部的時候是不會疼的。
只有把馬蹄底部修平整了,釘上去的馬掌才會是平的,不會妨礙到它活動的。
準備工作就緒之后,便要把燒紅的蹄鐵用鐵鉗夾著擺到馬蹄上觀察大小以及形狀是否合適。每一匹騾馬的馬蹄形狀都有細微的差別,在經過對比之后才能進行微調,再將燒紅的蹄鐵放到水中進行冷卻定型。
我前些時日也因為好奇去觀察過景區的馬匹,可惜那里的負責人告訴我,現在景區帶人上山的馬匹都是不釘馬掌的,它們的工作量還不需要用蹄鐵來支撐。
很遺憾,沒能親眼觀察到。
不過我也會翻找一些網絡上的視頻。通過與視頻對比發現,其實當年釘馬掌的步驟和現在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或許只是工具更加便捷了。
而視頻中將蹄鐵放到馬蹄上的畫面,看著讓人覺得疼痛難耐。于是許多人對此提出疑問,難道這騾馬被滾燙的蹄鐵碰到,一點兒也不會疼嗎?
我曾經也好奇過這樣的問題,不過那條視頻底下有一條評論讓我印象深刻——就這么說吧,假如馬疼的話,那么師傅的臉上就有一個燒紅的蹄鐵。仔細想想,也確實是這么一回事,馬如果真的疼的話,它一定會有所表示的。
便是馬兒也知道哪個工匠師傅的技術好,若是有人讓外公幫忙釘馬掌,那外公只要雙手碰到馬腿,馬兒就已經自覺抬起了蹄子。
等到蹄鐵冷卻之后,便要用釘子將蹄鐵固定。
外公伸出五根手指,告訴我每個蹄鐵需要用五個釘子來固定。用圓錘敲打,將釘子從蹄甲表面敲出來。若是釘子不小心放歪了,就會被打到肉里,那時別說拉貨了,走路都困難。這一類的,當天釘好馬掌被拉回去,不出兩天,又得重新再釘一次。
把釘子從蹄甲表面敲出來之后,工匠師傅會把釘子壓彎,貼合在蹄甲上,以免騾馬刮傷自己。
這便和視頻中略有出入,我猜這是因為工具的原因。現在的視頻中,敲出釘子以后,工匠師傅會將多出來的那截釘子直接弄斷,然后再把斷層壓彎打磨光滑,最后給馬兒刷上一層護甲油。
外公拿著鍋鏟當道具給我講完釘馬掌的全過程,又忍不住嘆了口氣,似乎在感嘆滄海桑田,時光易逝。
7
我回過神來,抬頭望向窗外。
原來夜色早已降臨,是我沉浸在故事中,錯把搖曳的火光當作黃昏的霞光。我還貪戀火塘,念著外公的傳奇故事,屋外的滿天星光卻已催我踏往歸途。
外公站起身,挺直了他的脊背,朦朧煙火中,我隱約透過年邁的外公看到了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馬幫少年。
我看見他將裝滿了小梨的塑料袋提起,似乎覺得還裝少了,又從一旁拿起梨子往里裝。可是啊,看著那個袋子,都隱約覺得袋子承受了太多,已經快被滿滿當當的梨子撐爆了。
載著一車的故事,我與母親終于披著星光,沐浴著皎潔的月光,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望著窗外,被夜幕吞沒的黑色群山中,隱約有一群人,圍繞著火堆坐下,吃著肉、喝著酥油茶,說說笑笑;勞累了一整日的騾馬則慢步踏入夜色,開始了它們的“夜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