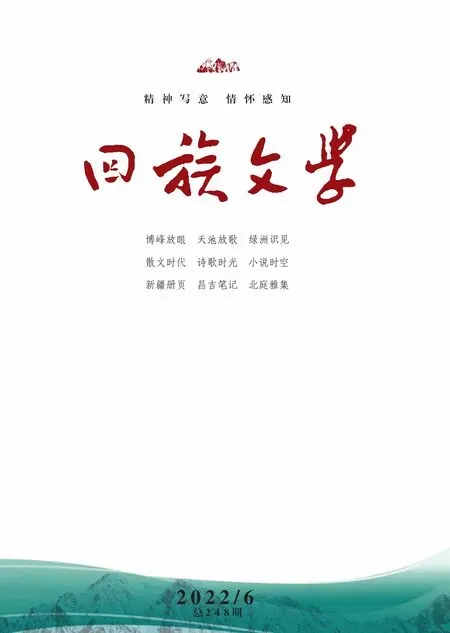你就是文學環境(三題)
劉誠龍
你就是文學環境
這是一個文學傻子與文學騙子的故事。傻子與騙子,說他干嗎?兄弟有所不知,文壇傻子進出,自然不是文壇好事;文壇騙子出入,確定是文學盛世。都說上世紀80年代,全民皆文學,傻子、才子、娘子、妹子、嫂子、嬸子、騙子、童子、公子、孫子、兒子、老爺子、知識分子,都來文壇里結對子,扎堆子,燒腦子,找路子,撩妹子,搭臺子,過日子,文學盛矣哉。如今諸子百家,高智力者玩其他去了,都不太來弄文學了,留下我們這等人喝五吆六的,搞起蠻大勁,胸脯挺得大蚱蜢跳高,黃尿射得拋物線飆高,想來真不算么子,要是高智商的,沒去經商辦企業,我等弄文學,弄不成什么勁兒。
傻子進出文壇,真非文學好事;騙子出入文壇,可算文壇盛世。這年頭,騙子還惠顧文學領域,一者可見,文壇傻子多,傻子魚貫而入,絡繹不絕;二者可見,文人日子過得不錯,指定是腰有十文錢在振衣作響。
好啦,我要說故事了。要說故事,先遇到了麻煩事,如何稱呼故事主人公,直接呼其名吧,一者,他是咱老鄉,湘人,我素來不為尊者隱,卻鄉土情懷深深深幾許;二者,也怕老鄉萬一找上我來,那可不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很大概率是,老鄉見老鄉,背后打老槍。然則,某君昆仲,若今隱其名,閣下又疑我弄虛作假。好吧,我把其題目列此,閣下百度去。題目有主題,《中國詩人文人的切骨之痛》,副題是《最佳詩詞獎評選大賽紀實》。好吧,還是隱其真名,給他起個筆名,叫文公吧。
故事里主人公文公,自詡是文壇獲獎專業戶,年近花甲。“一生中我拿過許多文學和詩歌獎項,有市級、省級、國家級和世界級獎,且在2006年被評為湖南省首批青年文化名人。”世界級獎啊,諾貝爾?青年名人啊,沒花錢的吧?其他國家級與世界級獎,花沒花錢,破沒破費,文公沒說,不妄猜。下面這個獎啊,可是花了大價錢,錢花了,獎沒得,惹得文公憤怒出文章,跳起來罵娘。
說的是一個詩歌賽,冠名是“詩詞中華·常老師”,文公說,“出于對文學和詩歌的虔誠與敬畏,我未假思索按要求寫好200字內作者簡歷,與詩作4首發給了‘常老師’,很快,對方發來了我的參賽編號(2992)和參賽鏈接。”文公說這個大賽“看不出任何破綻”。呵呵,下面這個參賽規則,不是破綻啊?智力下降到文公,破綻都綻放文學芳華呢。這文學大賽,要玩點贊的,點贊是要付錢的,“還會出點錢買贊支持”,規則是:“令牌5元25贊,毛筆10元50贊,竹簡20元100贊,硯臺50元290贊,折扇100元595贊,香爐200元1220贊,揚琴500元3125贊,翡翠750元4800贊,玉璽999元6500贊。”
什么令牌,什么翡翠,啥香爐與玉璽,搞不懂,搞得懂的是錢。大賽與點贊掛鉤,點贊與銀子掛鉤,文公自己被掛起來不算,全家都被鉤上了,“我的妻女和近80歲的老母親更是沒日沒夜點贊,其興奮程度高出作者我本人”。花錢點啊點,躥點,“我的排名已沖在前11名”,非常不容易呢,參賽的有5000多人,文壇傻子真扎堆哪。文公沖進11名,所有錢加起來是,“僅騙走我的親朋好友點贊現金就高達130905元”。文公啊,花這筆巨款,可以去操作魯獎了呢。這些都是什么錢?“老母親自己支付了她的養老積蓄13000多元,妻子支付了17600元,女兒更是把要裝修房子的錢花在點贊上達35000元,還有兩位好友,點贊也近萬元……”
文學傻子哈得死?文學騙子更是惡得很,貪了那么多,居然“作者的結果是作品金獎,卻無分文現金獎勵”。好一個文公啊,人家就是要弄你的現金,你以為他會搞回扣啊。
文公傻不?好像是傻的。文學老人家到這會兒,還沒完全鬧明白這是文學騙子與文學傻子合作搞文學之事。文公傻不?好像是不傻的。文學老人家,還會呼吁,還會發議論呢:“他們在利用文人、詩人的善良、自尊和脆弱行賄賂骯臟之事,斂不義之財;更可鄙的是,敗壞了文人和詩人的形象,嚴重擾亂了社會、文化和經濟秩序,這些人不是文人、詩人,而是社會的敗類,應該受到法律的譴責和制裁,還社會一個公道、祥和、健康的生活環境,還文人一點尊嚴,讓中國詩人少一些切骨之痛……”
議論得很不錯嘛,義正詞嚴,慷慨激昂,理直氣壯,正氣凜然,文公,繼續發動您妻子、孩子與80歲老母親,去翻《古代漢語詞典》與《現代漢語詞典》,多多找些古今吉利好辭,來夸夸您啊。文公議論是好議論,卻有一二處不好解,比如“賄賂骯臟”,文學騙子骯臟確乎骯臟,賄賂何言哉?善良兩字,用在這里,貌似不準確,哪是文人善良,是文人愚蠢吧。嗯,這些人指定不是“文人與詩人”,確乎是“社會的敗類”,敗類所以在,是因有這般蠢類在。若說80年代,很多人要發表文章,要得文學獎,花老婆嫁奩資、花女兒裝修費、花老母親養老金,去購買隆譽,或還可想,那時節文學可浪得虛名,可以騙取妹子做妻子。如今這時代了,還有好多文青文老,付費發文章,花錢買野雞文學獎,蠢得非一般。花一分錢去買版面,都是蠢。
文公要尊嚴,文人尊嚴何來?要文學騙子給你啊,騙子給不了你尊嚴,你自己給自己尊嚴好不好?文公嚴肅說笑話,去跟郭德綱說相聲,指定名師出高徒。疑惑的是,文公那么會思考會思想,何故不思思自己?這個文學獎盛事,不是騙子智力有多高,而是文學傻子智商有多低。怪什么“社會敗類”,怪什么社會環境呢?
文公自暴其丑,意在立此存照,還是思在警世通言?皆不是,石頭不說自己說,他不說自己,他要罪他人。多把罪責推與社會,推與政局,推與外界,是一大人性奇觀。因為從來不想是自己出問題,所以自己永遠都在出問題。文公名欲熏心,不是一個蠢字了得,是欲字害死了他。文公怪人怨世,固文化環境出大問題,更是文人智商與心態出大事了。
新詩何日成高精尖科技
與曹丞相煮茶論文藝門檻。使君可知甚文體無須門檻?
散文可是沒門檻?小女子做散文,小男子做散文,可知散文無門檻。非也,散文形散神不散,別說小男小女,便是大男大女,形難散開,神更難聚攏。
歌唱可是沒門檻,黃髫小兒唱得幾首,白發老翁哼得兩句,可知歌曲無門檻。非也,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他不唱我還落座為好,他一唱我就提腳開跑,不為藝也。
新詩可無門檻?隔壁老王夜半見阿嫂手持黃瓜,作了一首《黃瓜詩》,對門小嫂嫂見小寶寶拱臀出恭,作了一首《我的媽》,可知新詩無門檻。詩乃語言存在之最高形式,古之為詩,皆智商最高者,君幾時見過阿斗劉禪寫過詩?君指定不曾見弱智晉惠帝留下過詩,詩家說了呢:你還停留在唐詩宋詞階段嗎?可見新詩,唐詩人宋詞人,都玩不動的。
何藝術可當無門檻也?曹丞相曰:攝影也。人人拿著一部手機,咔嚓,拍個風景;咔嚓咔嚓,照個人影;咔嚓咔嚓咔嚓,風景與人影,拍照一個“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之翩鴻照影。按個甚鍵,小鴨變天鵝;美個甚顏,鳳姐變嫦娥。是噠是噠,自從嫁了人,她就成了女人家;自從娶了妻,我就成了男人公;自從有了手機,男人公與女人家,便都成了攝影藝術家。
婚禮讓男女不再是少男少女,手機使老少立轉為藝人藝家。曹丞相說得真對。
對個鬼。若說文藝無門檻,劉某我,還是覺得新詩無門檻。手機拍照,俺劉某固然大大地會,美顏卻是一竅沒通也;城里三尺小兒與鄉里七十老頭,多不會拍照的嘛。不會拍照者多多,不會流口水、吐口水、分泌口水的,有沒有?沒有。吐口唾沫,歇口氣,便是詩。吐口水,是摛句子,歇口氣,是分個行。新詩成矣。
新詩,讓人最難見到詩,新詩,卻讓人最容易見到詩人。去個茶館,聽得啊啊啊,便是詩人在吟詩;去個廁所,聽得唵唵唵,便是詩人在憋詩;去個微信群,聽得滴滴滴,便是詩人在敲詩;去個衛生間,聽得噗噗噗,便是詩人在作口水詩。
新詩,不就吐個口水嘛,不就是分個行嘛,不就是一句話截成三截,一截遺尿,一截增屎,一截還黃瓜嘛。我承認,曾經特別不懂新詩。當年朦朧詩,我左看右看,上讀下讀,硬是沒弄明白,詩人把朦朧詩,當奧數題,當天文學,我是相信的。而新詩從三皇五帝到如今,多得是三歲小兒牙牙學語,多得是八十老太奄奄說話,或者是油膩男、生猛女俏皮一樂。太多新詩,小情小趣當了大智大慧,小兒小科當了大志大觀,一節腦筋急轉彎,當成新詩大奇觀,一個小笑話,當成新詩大絕唱。
新詩,越寫越淺白;新詩人卻越來越自詡深奧。小說、散文、戲劇,貌似都沒把讀者與作者當成敵我,貌似都不曾把文藝精英與普通大眾劃界開去,唯有新詩人,卻把世界分為兩端:新詩人與非新詩人。若對新詩批評一句,詩人便高聲號叫:你是外行;不能讓不懂新詩的人來評判新詩,不能讓新詩門外漢來破壞新詩意境與文藝環境。
赫魯曉夫說:以前我不懂文藝,現在當了總經理,我還不懂文藝嗎?普羅大眾因此也可以說:以前我不懂新詩,現在讀了幼兒園,我還不懂新詩嗎?讀了幼兒園的,都是能夠讀懂新詩的,新詩者,是新詩叔叔,新詩姑姑,吐個口水,歇口氣,寫句新詩,分個行,有甚不懂的?新詩人豪氣沖天,牛皮哄哄,自我標榜,高自標譽,把他人當文藝外行,把自己當文藝天才。動不動便訓讀者:不寫詩的,請不要來論詩。
新詩,是原子彈制造,還是基帶芯片制作?是量子物理,還是神經科學?新詩人貌似把持了人類最高藝術,直把分行式句子當了高精尖科技。
新詩人真那么高端?也不是的。一位詩人,寫了一首驢尾巴詩,兄弟我講友情,高贊其語妙天下,可為傳世。這位新詩兄弟,引我為知己,三番五次喊我去喝酒;喝酒的不行,那喝茶。他反正要高山流水,結我為知音。后來又讀了這兄弟一詩,此時,我是半個出家人,不太打誑語,實話實說,說兄弟,你這般三五短句,缺想象,無文采,欠詩意,少內涵。新詩兄弟頓時大怒,大叱:你不懂詩,沒資格評詩。然后,刪除我,拉黑我,割袍斷義,壯士斷我,老死不相往來了。
諸位從此處,可知新詩人評定新詩讀者內行與外行的標準了吧,很簡單的:批評新詩的,是外行;歌頌新詩的,是內行。這標準,跟人情標準是一樣的:對我好的,你是好人;對我壞的,你是壞人。
讀者越來越覺得,新詩不是詩,作者越來越覺得,新詩最是詩。讀者與作者,天天干仗,這是文藝界大奇觀焉。散文讀者與作者,不對立;小說讀者與作者,不對立;哪怕是神劇,讀者與編劇者,偶爾對立,多半不對立:坐沙發上的大媽大嬸看電視多,坐在書桌上讀新詩的作手作家,沒幾個。
是新詩讀者不知道詩,還是新詩作者不知道詩?把新詩搞明白,新詩才能有明天。新詩人最應該是:知道什么叫詩,才能寫出好詩;知道什么不叫詩,才能不寫爛詩。最惱火的是,現在新詩人,既不知道什么是詩,也不知道什么不是詩。故,好詩真沒有,爛詩到處是。詩人把自己玩壞了,便把一腔怒火噴向讀者。
作者怒,讀者更怒,詩壇內外就熱鬧得很:作者寫口水詩,讀者含口水斥。口水來口水去,詩壇天空沒有星星,滿地都是唾沫星子。
癡文人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這說的是一般情形,并不合特殊物種。文人就屬于別科:謙虛使文人落滿灰,驕傲使文人跑大紅。文人謙虛,無聲無色到無名;文人驕傲,爆炒爆笑到爆鳴。文人謙虛是雅量?文人驕傲是流量。陽春雪輸與下里巴,正三觀輸與惡三俗,高大上輸與下半身,風雅頌輸與屎尿屁。
諸位曉得王爾烈者誰?不曉得吧。登起文人三百萬,若論名氣寒徹。縣市級作協會員不計,省級以上登花名冊上的,三百萬是有的,難得幾人蓋棺后,還有人論。王爾烈是清朝遼陽作協會員,若這一級會員,想留下名來,是:上邪,我欲讓人知名,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但人家硬是以一個市級作協會員,到底至今名氣有流傳。考其留名法,便是:謙虛使人落滿灰,驕傲使人跑大紅;天下文章屬三江,三江文章屬遼陽,遼陽文章屬我兄,我為我兄改文章。
夠驕傲吧。這么一驕傲啊,王會員便三百年后,有人還記得他,要舉文人吹牛皮,可能還繞不過他。不過,兄弟看他吹得蠻猛,到底自吹有限,還只是自吹為賈府里的屈原,不曾自吹為宰相府里的要員。若是這么寫,估計名氣會大到四海翻騰五洲震蕩:遼陽文章勝三江,三江文章勝天下,我兄文章勝天下,我為我兄改文章。如此,則真個將是:一不小心作了一個黃粱夢,二不小心作了一段春秋夢,三不小心作了一部《紅樓夢》。
明朝汪道昆,才氣算可以,加入大明朝作協,沒問題。可他沒加入。噢噢,不是他加入不了,而是明朝沒有專門領導作家的機構。有領導文學的機構當然出文學家,至少可以出文學獎;沒領導文學的機構當然也出文學家,但難以出文學獎,李白杜甫白居易,屈原蘇軾韓退之,都沒文學獎,都有文學千年以降。不扯遠了,說汪文人吧,汪文人寫了一些詩,編了一些劇,還摛了一些賦,便文學在群里漫自嗟呀:屈原算啥?文章平平,所以叫屈平;李白是甚?詩歌白開水,所以叫李太白,“圣主若論封禪事,老臣才力勝相如”。文壇若也來搞個墳山,哦,不,文山封禪,汪哥我指定是:恥居王后,愧在盧前。恥,狂妄得很,愧,謙虛得很。一半是驕傲,一半是謙虛?一半加一半,等于是一全,等于獨一個。
一半謙虛,謙虛一半。南朝有個柳信言者,活得一直不開心,要去黃鶴題詩,黃鶴題詩在上頭哪。他說他文章,南朝第一,別人不認噠,說你第一,這征文,那征文,沒見你一等獎第一名,有之,也是與梁安城王蕭佽并列過一次第一,柳大作家在各個群里訴衷腸:恥居第一,愧居第一。第一非唯一,也是文壇搞亂了阿拉伯數字與“說文解字”。柳作家郁悶死了,郁悶將死而未死,王作家先他死,他與賓客前去吊唁,高興死了,金雞獨立,單腳翹立,獨腳跳立,孤腳飛立。兄弟你見過公雞在母雞那里繞走模樣不,一只腳甩爪子,一只腳跳步子,翅膀扇,金步搖,柳作家正是那樣子。“及聞佽卒,(柳信言)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腳跳。”
大家好奇怪,忙問這是什么款何造型,柳作家喜滋滋:“獨步來獨步來。”從此搞征文啥的,不會再有甚并列第一的了,指定是我獨步天下,老子天下第一。于是,甲在群里@柳作家:柳公文壇是一哥,獨領文壇在南朝;乙于群里發紅包,紅包封單上寫,五百年文壇前三名:柳部長,柳部長,柳部長。還有其他作家抬轎子,此處不引了(眾賓皆舞,以為笑樂)。
柳作家獨步來獨步來,癲狂不,狂則狂矣,癲或未癲,精神則精神矣,貌似不曾到精神病五級,有人不尿他,他怎么著,也只是單見他主席臺惡罵人,沒見他線下面狠打人,若前往醫院鑒定,頂多精神病一級(一級是:患者會有口頭威脅與喊叫,但并無肢體行為)。柳作家也只是認定自己在散文上傲視群雄,并沒說自己包攬詩詞歌賦、子史經集、琴棋書畫、文教衛體、理化生醫之鰲頭。
晚明王逢年,自費出版了一本詩集《海岱集》。“少為諸生,試以義多入古文奇字,為有司所黜。”文章不行,便文字搞怪;作品欠佳,便題材弄奇。技止此耳。自出了一本詩集,那可不得了了,原來腦殼勾著走,尾巴夾著走,現在是脖子后仰三十度,尾巴上翹九十度,到街頭,到巷尾,高喊:安靜,肅靜,寂靜。“每出其詩示人,以手按紙,手顫口吟。”
沒誰組織王大作家,他搞文化下村,他搞文學上墻,他搞散文之鄉,他搞詩詞碑林,他搞小說創作基地,廁門、墻頭、碑面、田埂,都是他一個人的,人或訝異之,他冷笑曰:“慢世敵嵇康,綴文敵馬遷,賦詩敵阮籍,述騷敵屈宋,書法敵二王。”
某君昆仲說:“我很牛的。”牛在何處?牛在:“我在大群,敢鄙視散文作家才華,因為我的才華,很可以的。”(摘自某散文群,某文論教授言。下同。)更牛在:“我的才華,一半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半在群里發言,我的群發言,甩第二名幾萬分。”嘻嘻,“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幾萬分是何概念?不懂。不是幾萬分何概念,而是教授何人?十四億人中,有十四萬人知他不?滿打滿算,加他文學圈,加他家人圈,加他馬仔圈,難超一千四百人。
文人太可憐太可悲了。有兄弟有姐妹由此慨嘆。文人吹牛皮,千古如此,無甚嘆息。不然,文人這般自吹,也太悲涼是不,馬仔的有,貼心馬仔的沒有。吹牛皮,若有馬仔幫著捧,或許貴;要自己披掛上陣,指定賤。
馮夢龍在《古今笑史》里,描述過好些“癡畜生”,癡得可憐又可悲:“螳螂,嗔癡也。鵝與鱖,驕癡也。烏鲗,愚癡也。錦雞,愛癡也。半翅、蚺蛇,愛癡亦貪癡也。故癡趣非人不能領,若惡癡,則畜生之不若矣!”
其中愛癡錦雞,便是自吹自戀之癡也:“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我漂亮,天下第一靚麗;我太有能耐了,能力上頂破了九重天,下踩穿了十八獄;我好才華,天下第一才子,我不是第一,第一不算啥,我是第一得遠遠超過第二幾萬分。
錦雞自以為其羽毛蓋世無雙,天天岸上“自照水”,結果是,“有溺死者”;文人自以為國士第一,天天群里“吹牛皮”,溺死倒沒溺死,人家唾沫沒把他淹死,卻是當他是笑話存在,被人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