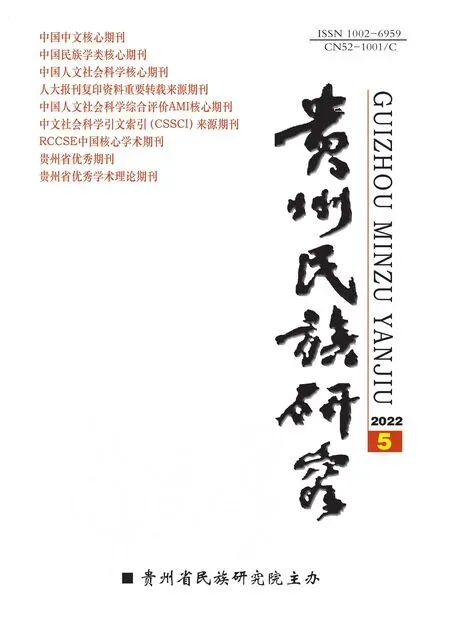基于活態傳承模式的苗族非遺手工藝產品的“再設計”探討
趙 蕾
(貴州財經大學 藝術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在漫長的社會演化過程中積累的勞動和經驗智慧,其表現形式多樣,內涵質樸。苗族傳統手工技藝品類很多,是苗族精神文化的生動體現,其中蠟染、刺繡、銀飾等多項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國2005年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指導的基本方針“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1],可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是第一位的,“合理利用、傳承發展”是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通過非遺手工藝品的“再設計”,使形成于特定傳統社區、民俗中的非遺手工藝獲得再生能力,適應當代生活環境,在助力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非遺的文化性、地域性和民族特色,增強文化多樣性和非遺人群的文化認同,對實現非遺的活態化傳承有重要意義。
一、當前貴州苗族非遺手工藝品產業化面臨的問題
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國家保護和扶持傳統工藝美術行業生產,保護了一大批傳統工藝品種,民族工藝美術曾經作為我國出口創匯的支柱產業一度得到蓬勃發展,其中包括不少后來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苗族手工技藝。20世紀80年代,貴州安順的苗族蠟染就由傳統的家庭手工生產轉化為產業化發展模式,出現了大量分工協作,標準化、流程化的蠟染工廠,出現了我國第一家生產民族蠟染的國有企業安順蠟染總廠,產值一度達1500 多萬。黔東南臺江、雷山等地的苗族銀飾、刺繡等傳統手工技藝產品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大規模合作社模式的產業化面貌。以往的情形可以看出貴州苗族手工藝品產業化過程一度取得過繁榮發展,無論是蠟染、銀飾還是刺繡,在傳統技術和題材的基礎上,均不同程度積極開發新工藝,新產品,主要針對旅游商品市場和國內外工藝品愛好者,產銷國內外多個地區。然而,隨著當地產業結構多元化發展,加上不良競爭帶來的影響,上述地區苗族手工藝產品逐漸出現同質化嚴重、材料、工藝水平下降,設計創新乏力等問題。
以銀飾鍛制技藝來說,銀飾作為苗族同胞彰顯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智慧的代表,在幾百年的傳承發展歷史中始終植根于廣大民眾之中,融入他們的日常審美和民俗文化,雷山麻料、控拜、烏高、白高、烏殺被稱為“中國苗族銀飾之鄉”。隨著近20年來苗族銀飾鍛制技藝的保護如火如荼地展開,以雷山縣為中心的西江和臺江縣展開了銀飾加工線,呈現出較為復雜的狀況。首先,大部分民族村寨經濟落后,屬于外出務工人員輸出地,隨著老一代傳承人的逐漸逝去,年青一代外出打工,由于受到外部文化的影響,對于自身民族文化缺乏認同感和自信心,不愿再從事銀飾鍛制工作和技藝傳承,銀飾技藝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危險。其次,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使得村寨傳統民俗文化正逐漸逝去,苗族特有的儀式和節日逐漸消失,銀飾逝去了其參與民俗生活和展示的場合。旅游產業的發展使得純正苗銀的傳統審美被因經濟利益所驅動的旅游商品設計而同化,政府牽頭的銀飾文化產業園注重經濟政治效益而忽略了銀飾技藝的自然傳承狀態,迅猛發展的銀飾產業存在以單一經濟價值為導向,非遺傳承的“原真性”缺失等問題。再次,村寨中的銀匠制作銀飾時也出現產品分化,銀飾產品分流為兩大類,一類針對以本土文化同質性消費為主的當地人,當地苗族同胞依然維持著定制銀飾的傳統,并遵循著鄉村鄰里口碑相傳的習俗,要定制重要的銀飾部件時會選擇區域內出名的銀匠,大家一致認可的“老手藝”師傅。這些本地人定制的款式一般遵循苗族傳統的審美和文化,題材來源于他們的傳統文化和傳說,鍛制技巧、構圖和意向表達也充滿著原始拙樸的質感。另一類產品針對流行文化審美為主體的外來游客,在西江旅游景區開設銀飾店鋪,研發新產品,這部分產品要求現代感強,滿足游客的審美,“老手藝”師傅及其傳承人往往囿于自身設計學科系統訓練的缺乏,脫離傳統之外創作能力極為弱勢,只能簡單模仿一些流行樣式,這就使得他們的創新產品同質化嚴重,缺乏內在生命力,極易被市場淘汰[2](P24-30)。
二、貴州苗族非遺手工藝產品“再設計”存在的問題分析
非遺傳承的生態性和活態性決定了傳承的前提是維持其“本真性”,即非遺最核心的文化基因,外在形態、材料、功能組合的變化為文化基因的表達提供媒介,因此,“再設計”方法顯得尤為重要。“再設計”是以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基礎衍生出的文化創意產品的二度設計,將傳統工藝美術的精神和圖式注入到現代設計中,使用設計方法的合理性、原則和思路的清晰性,決定了是否能充分發揮傳承人、設計師、市場和傳承主體的多重合力,平衡開發與保護之間的關系,在取得有效的產業化成果的同時保持非遺自身的文化特性。手工藝需要在當代社會獲得能夠支撐其自身發展的內在生命力,這是維持一成不變的傳統技藝和生產模式無法產生出來的。當下對于苗族非遺手工技藝產品“再設計”開發呈現出多種方法與策略,以苗族非遺手工技藝為基礎開發的創意產品大量涌入市場,從各個角度對產品進行“二度設計”。有從材料和工藝上進行改進的,有從審美傳承角度進行設計的,有從載體變更的角度考慮的。總體來說,大部分產品在設計上缺乏深層次的文化自覺,設計師對傳承問題缺乏深入的思考,停留在元素的拼接,轉嫁上,流于粗淺的形式主義。
(一) 注重形式探索,忽略歷史文脈傳承
設計形式與內容脫節,缺少對設計對象深層次的情感共鳴和理解。一般意義上,非遺手工技藝傳承的關鍵是傳承人,而產品設計的開發創新則由產品設計師來完成。然而實際情況是,更多時候傳承與創新的工作并非如此涇渭分明,傳承人在熟練掌握技藝的基礎上,也會進行一定程度的藝術表達和工藝技巧上的創新。傳承人的“再設計”往往因缺乏系統的造型能力與設計思維訓練,對于現代設計方法的欠缺,顯得難以跳出傳統的思維慣性,產品也難以符合現代消費者的需要。而產品設計師的工作建立在現代設計理論和實踐體系的基礎上,對傳統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理解,對民族性的內容不能加以正確的解讀,未能充分尊重民族特性,不能切入非遺的核心,形式上慣于模仿西方,視覺元素的運用也往往留于簡單的嫁接,拼貼,作品呈現更注重形式表達,忽略了歷史文脈的傳承。
(二) 現代設計體系與傳統手工藝文化體系之間的差異未能調和
傳統手工藝是自發性設計,承襲于經驗和直覺,是隨機的、直覺的,與現代設計的專業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有著根本的差異和明顯的不同。在臺江縣的苗族刺繡合作社中,設計公司向合作社下單收購,用繡娘們批量制作的手工繡片作為設計師在產品“再設計”創作時使用的元素,我們看到在這里設計體系的分工合作、專業化制度化中嵌入了手工制作,使得繡娘的刺繡作品從原本自發性的、直覺的生產,在合作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轉變為為了謀求利益的機械化運作。在此模式下,很多繡娘對于自己刺繡圖案內容的來源已經說不清楚了,技藝水平也顯得參差不齊,所用的材料,按收購方的要求分為了三六九等,其中不乏劣質原料。這就是現代設計介入傳統手工藝生產容易出現“剝奪性”,由于現代設計體系與傳統手工藝文化體系之間的差異難以調和,出現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制,失去平衡點,傳統手工藝文化因為各方面的弱勢而變成以現代設計體系為中心,喪失自身的獨立性。而另一種相對應的情況是以傳承人為重心發展起來的刺繡產業,產品變得作品化,出自各種對非遺傳承人大師的炒作,以消費情懷為賣點,使手工藝變為奢侈品,審美價值過分掩蓋其功用,顯示出現代設計體系與傳統手工藝文化體系之間的矛盾。
(三) 缺乏系統的設計價值衡量體系
“再設計”產品的評價標準不一,設計價值衡量缺乏系統的標準。雖然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非遺保護的“原真性”原則,認為在非遺保護性開發中在堅持“本真性”原則的基礎上外在形態的變化是合理的。但是對于具體設計中遇到的非遺手工技藝種類,決定“本真性”的外在因素各有不同,如苗族傳統蠟染中采用染料為本地生長的植物“藍靛”熬制成的天然植物性染料,如果改變了染料的來源,當前市場上出現的化工染料浸染的蠟染產品,就丟失了苗族蠟染的“原真性”,變為拙劣的仿制品。苗族傳統剪紙技藝,如果將手工制作的方式轉變為機器切割,則徹底失去了剪紙這一手工技藝的“原真性”。類似的,對于“再設計”和非遺傳承的目標和價值衡量出現偏差,有的側重于物質產品,有的側重于手工藝本身,有的側重于文化價值,有的側重于市場效益,造成當前產品設計價值衡量混亂。
(四) 設計合作模式的精英式主導
傳統手工藝人缺少足夠的話語權,設計師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觀念占據主導,未能給予手工藝人應有的尊重。“再設計”創意產品與非遺手工技藝的共生,兩者本是互惠的關系,但在設計師與手工藝人合作的模式中,設計師常常作為主流文化精英的代表,掌握著主流話語權,手工藝人被視為民間文化的代表,成為被主導者。造成了在產品開發設計上設計師代替當地手工藝人,成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產品之中發生了許多歪曲、誤讀和嫁接。事實上,傳承人才是民族文化實質上的主人,設計師有自身的局限性,應當給予手工藝人充分的尊重。不能要求設計師對非遺手工技藝及其后的文化背景具有相當于傳承人的熟練程度,也不能苛求傳承人的創造力和系統開發設計能力能與設計師匹敵,兩者需要緊密合作才能在非遺文化的傳承中各司其職,相得益彰。
三、基于活態傳承模式的苗族非遺手工藝產品“再設計”原則
相較于普通文化創意產品而言,苗族非遺手工藝產品源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更多文化傳承上的深度需求,對于設計師的文化素養、理解和領悟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其手工藝特征要求設計師熟知并了解傳統手工技藝的技巧,或者至少具備對傳統手工技藝的基礎認知。相較于傳統的產業化開發,它要求設計師具備較強的創新創意能力,對產品的“當代性”“流行性”有較為敏銳的感知,相較于形式上的創新,更重要的是非遺手工藝產品文化基因和“原真性”的保持。
(一) 傳統“人”“技”“器”角度下的“再設計”原則
當前,傳統手工藝文化在當代社會的作用與價值正在重新被發掘和探討。手工藝在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發生了轉變,荊雷認為:“伴隨著傳統手工藝的價值觀念的顛覆,西方當代手工藝及中國當代藝術在觀念與形式語言探索方面的影響,使手工藝的價值觀念產生了轉變,催生了在學院領域的實驗性、學術性手工藝藝術創作形態的形成與發展,并直面當今社會問題和生活現實的感召力,對處于社會不同層面的手工藝形態產生的積極影響,獲得了具有‘當代’意義的價值轉換。”[3]民族手工藝在當代社會的作用產生了變化,傳統手工藝人在苗族生活中扮演物質生產者,造物者的角色,轉變為當代生存空間中,為工業化背景下技術化生存的人,提供了逃避與安頓精神的家園,變為一種“鄉愁”語境下具有豐富文化標志性意義和內涵的造物活動。除了價值的轉變,手工藝自身也在努力尋求發展、突破藩籬,努力融入到純藝術或設計藝術的主流活動中,其作用在發生變化。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就興起過“工作室手工藝運動”,運動中,手工藝人積極加入純藝術家、設計師的活動,積極參與各類藝術院校的教育,加入各種藝術流派,融入現代藝術、現代設計的范疇,許多手工藝人努力實踐了從“工匠”到藝術家、設計師的轉變。在西方后現代主義設計的實踐活動中,手工藝與設計的界限劃分越來越模糊,在以意大利“孟菲斯集團”為代表后現代設計中,追求個性化、趣味性、小批量或獨立定制,設計風格上的雜糅、提倡文化多元化,從世界各地古老而邊緣的民族文化中吸收養分,又呈現出設計向手工藝的某種程度的回歸,尋求手工藝與設計融合共同發展的探索,尊重傳統手工體系的價值本體是關鍵。
傳統手工藝作為一種生產生活方式,其創造和作用主體是“人”,“人”通過實踐手段“技”,創造客體“器”或“物”,“人”“技”“器”構成了傳統手工藝的三個價值本體。首先,“人”是民族傳統手工技藝的價值主體,“人是萬物的尺度”,在民族非遺手工藝活動中,其造物活動的出發點和最終針對目標都是人,甚至非遺手工技藝的活態傳承也是通過“人”來傳遞和完成,這與設計學中“以人為本”的考量不謀而合。產品設計當中對于使用者的多角度研究發展出了人體工學、心理學、人機交互設計等學科,只不過,設計學考量下的“人”被從技藝中分割出來,而在民族傳統手工技藝中,人與技藝是不可分割的,應當充分吸取手工技藝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照,包括生理和心理層面,為技術化背景下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提供慰藉。其次,“技藝”是傳統手工藝價值主體“人”與客體“器物”溝通的橋梁和中介,“人”通過某項技藝的熟練掌握和勞作,達到與自然界的溝通[4],在雙手勞動過程中使自身和所創造的事物融于一體,透過技巧性的勞作,“人”獲得的成果是物質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因此,“再設計”對于器物的生產改造是否考慮了“技藝”的傳承,是否尊重傳統工藝流程與程序,保留傳統的方法技巧,直接決定了非遺的活態傳承特性是否得到保證。最后,“器物”是傳統手工藝的價值客體,是主體理念與意志的外化,傳統手工藝中“器物”除了是由物質材料轉化而來,具有物質性,又能為主體提供使用價值,還具有精神和文化屬性。傳統手工藝產品使用價值可能與當代生活發生不適,“再設計”過程中必須遵循可以對于“器物”的結構與形式進行多樣化改變,使其使用價值適應當代生活,但對于“器物”的精神作用和文化屬性等內涵必須進行保持和傳遞的原則,以保持傳統手工技藝的價值本體得以繼承。
(二) “原真性”與“當代性”保持下的“再設計”原則
非遺手工藝產品的“再設計”,堅持“原真性”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則,在非遺產品從傳統向現代轉化的過程中,“原真性”是兩者之間溝通的橋梁。而“當代性”,是非遺從民族技藝遺產轉化為可在當代生活中發揮功能作用的產品時必須具備的特性。日本的《奈良原真性文件》 中對“原真性”的表述為:“使認識文化遺產的性質、特性、涵義和歷史成為可能的,一切物質型、文字型、口頭型和圖像型來源。包括形式與設計,材料與質地,利用與功能,傳統與技術,位置與環境,精神與情感,以及其它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5]。
非遺的“原真性”可能是不可見的,也可能由某些可見的物質材料所決定。二度設計要根據所設計改造的非遺手工技藝的具體情況作出分析。譬如在黔東南苗族蠟染產品的設計開發中,就有蠟染企業為了追求高效和降低成本,把蠟染當中采用的天然植物染料替換為化學染料,在旅游商品市場上進行售賣,外行人無法分辨其中的差異,但對于非遺的活態性傳承來說,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對非遺“原真性”的不負責任的篡改和侵犯,這些產品雖售價低廉,但從工藝材料上已經不能稱之為真正的蠟染產品,此時蠟染中的天然染料,就成為蠟染技藝“原真性”的重要物質保證。同樣是設計師,對于苗族刺繡蠟染和銀飾中經常出現的蝴蝶媽媽、苗龍等傳統形象進行再創作,有的設計師將這些形象按照苗族傳統圖案的構圖法則在新的載體中加以應用,雖沒有遵循傳統圖案固有的程式化應用方式,但卻繼承了苗族裝飾圖案的視覺審美特征,組合方式,使得圖案雖然脫離傳統載體,在新的載體上獲得了“當代性”與“原真性”的共存。
(三) 傳承人與設計師:市場條件下的合作與依附
基于活態傳承模式的非遺手工藝產品“再設計”,要依靠傳承人+設計師的合作模式,以針對市場作出合理的配合與調整。
傳統手工藝的傳承主體手工藝人,主要從事技藝性的勞作,而“再設計”的主體是設計師,從事的“設計”只是工業化生產中的一個環節,手工匠人具有設計師不具備的某一手藝的技藝和經驗,從設計、選材到加工、雕琢、工藝步驟到成品,一體化的掌握。設計師所接受的現代設計教育,建立在西方現代設計理論體系的基礎上,注重創造力的培養,具備手工藝人所缺乏的系統設計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造型能力、美學熏陶、創意技巧。非遺手工藝產品的再開發設計,對設計師的要求是比較高的,除了掌握傳統設計課程中的構成基礎、人體工學、產品設計等課程外,還需要設計師對傳統文化具有深入的領悟能力,較熟悉的掌握程度,如對傳統圖案、民間美術、工藝美術等學科有較為深入地了解。
傳統手工藝的傳習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大部分采用家傳或師徒制,口傳心授,言傳身教,現代設計師的培養,大多在高校中進行,教學模式沿襲西方以德國包豪斯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現代設計教育體系,對于視覺傳達、環境設計等較為立竿見影的學科,辦學規模和普及范圍都比較大,而針對非遺開發和保護的產品設計專業,則進展緩慢。究其原因,非遺的傳習時間相對漫長,技藝和經驗的積累要經過大量實踐獲得,并且需要將傳承人引進高校日常教學當中,擔任技藝導師,手把手教學生學習傳統技藝,而我國現階段的設計教育對這一塊的投入還十分欠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高校引入傳承人進課堂,但也只是針對短期的交流,從學習的深入程度、學生的接受度、實際對技藝的掌握程度方面,都難以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因此,在當前的情勢下,加大設計師與傳承人之間的整合,增強他們之間的緊密合作,是應對市場需求的最有效做法。
四、基于活態傳承模式的苗族非遺手工藝產品“再設計”方法
(一) 堅持傳統材料與工藝下的分工協作
傳統手工藝生產的特征之一是生產過程一體化,手工藝人從設計構思到制作成型對器物制作進行全方位的把握,以作坊式小規模或家庭生產為基本單位。而現代設計對應著工業化生產方式,分工更為精細明確。但手工藝與分工協作之間并不是完全對立,在傳統非遺手工技藝中,也很早就出現了分工協作模式,譬如在民間年畫制作過程中,根據繪畫、雕刻、印刷、裝裱等流程分為畫師、雕版師、印刷工、裱工,各司其職分工明確,專門人員各有所長,作品完成后精細雅致,比起一人全攬的手工藝品種,某些特定的工藝非常適合高效分工。因此,非遺手工藝產品在一定規模的產業化生產中,堅持使用傳統材料與工藝的條件下,適當采用分工協作的方式,讓不同的人員專注于不同生產步驟,既堅持非遺產品的“本真性”,又提高工作效能,提升產品品質。如在苗族傳統蠟染工藝中,包含了布面制作、蠟液制作、藍靛制作、上蠟(葉城畫蠟)、浸染、脫蠟、縫合等步驟,在貴陽及黔東南、安順、黔西北地區蠟染產業較為發達的地方,有小型蠟染工坊或工作室采用分工協作的模式來制作蠟染產品。與安順蠟染總廠這一類規模化生產的工廠相比,小型工作室和作坊更大程度地保留了蠟染作為非遺的“原真性”,從材料選擇、制作到工藝流程完全保留了蠟染最本真的風味,避免了因大批量生產帶來的粗制濫造和原材料質量下降引起的整體品質的下降。
(二) 基于傳統材料,對工藝的改進與創新
工藝是對材料的處理手段,傳統工藝根據行業的差別各有不同,往往經過長期的積累與改進,有著悠久的歷史,對于手工藝人來說,沿襲和磨練傳統的工藝技術很重要,乃至于值得花一輩子的時間去打磨。如今經過官方認證的一系列苗族非遺手工藝傳承人,民間工藝大師,學藝都從青少年時代開始,持續時間長,如控拜銀匠村的楊光賓、穆天才,千戶苗寨的李光雄,臺江縣的吳國祥,吳水根等人,最長的從藝時間達到40多年,伴隨著熟練技藝的,是對本民族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經驗的掌握,而對民族傳統文化和技藝知之甚少的設計師,在對工藝的改進與創新的“再設計”過程中,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當傳統工藝不足以支撐新產品時,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第一種情況,由設計師來掌握整個創新工藝流程,要求設計師接受過深入的傳統技藝的訓練,并且對工藝有足夠的認識,具備敏銳的洞察力,以發現工藝中存在的漏洞,或新產品需要何種工藝的配合,同時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第二種情況,在設計師掌握一定程度的傳統技藝的情況下,設計師與手工藝人各司其職,密切配合,但深入的工藝探索,需要手工藝人的協助。最后一種情況,手工藝人掌握了較強的系統設計方法和創新能力,能在自身熟練技藝的基礎上,開創新的工藝。第一種和最后一種情況都是非常難得的,對設計師和手工藝人要求較高,比較難以實現,而第二種則比較現實可行。如黔東南州丹寨縣的寧航蠟染基地,訂單生產模式有兩種,一種是由設計師決定產品造型和圖案,由蠟染基地內的婦女按照傳統工藝模式進行蠟染制作加工,另一種由客戶提出需要產品的大致形態,其余由婦女們自由發揮加工,她們會將自己熟悉的傳統圖案運用到產品上,最大程度保證了工藝的純正。
(三) 堅持傳統工藝,對新材料的探索
“再設計”是對非遺物質形態產品的二度改造,是對前述手工技藝中“人”“技”“器”價值本體中“器物”的改設,在傳統手工藝中,制作原料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通過技藝的加工,具有了不同于自然物的特征,“化材為器”,使得物質材料具備了使用功能。工匠在設計制作一件器物時首要考慮取材的質地、密度、紋理、顏色等,充分理解和把握材料,“因材施技”直接反映出工匠的技藝水平,決定最終器物的呈現效果。苗族傳統手工藝產品的材料通常取材于自然,如蠟染、織錦使用的線或布料來源于苗族同胞親手種植的植物,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對天然材料的依賴性可能會受到影響,但對材料要求的某些屬性不會輕易改變。苗族傳統手工藝使用到的材料種類繁多,品種豐富,主要包括棉花、麻、絲及其他以農作物為基礎的織物用品,各種竹、木、藤、草等植物材料,如以板藍根為代表的各種植物染料,古法造紙中所使用的構皮麻、杉根等,以及來自動物的原料,如動物毛、皮、骨、牙,蠟染所使用的蜂蠟,還有以銀為代表的金、銀、銅等基礎材料,和一些非金屬礦、石、玉、陶土。在苗族傳統手工技藝中,材料、技藝和器物三者在漫長的發展歲月中達到了高度的融合,共同構成了器物之美。
現代設計學對材料的研究,與傳統手工藝有諸多相似之處,使用了更系統化的梳理,著重材料的顏色、質感、肌理、物理特性和化學特性,材料帶給人的情感體驗、心理特征。相較于傳統材料取材于自然,與手工藝人身處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現代材料來自工業生產,化學合成,有著更多復雜的分類和屬性,“再設計”應從材料的角度對非遺產品進行設計創新,豐富非遺手工藝產品的品種。在2019年貴州民間工藝品文化產品博會上,黔藝寶公司設計的苗繡新產品,沿用苗繡傳統圖案,手工刺繡的方式,將原本刺繡用的布料上替換為人造皮革制品,再將其制作為手袋,背包等皮具,增強了苗繡在現代生活中出現的實用性,又豐富了它在材料方面的表現力。除此之外,許多刺繡、蠟染、銀飾相關文創產品,也不局限于傳統載體,出現了塑料、亞克力、玻璃、化工纖維等多元化的現代工業材料。對材料的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簡單替換,創新的基礎是對傳統的認真研習,研究傳統材料的屬性,熟練掌握其使用,當傳統轉化為自己的技能時,才有可能談適當的創新。
(四) 基于“原真性”的創新產品設計
基于非遺手工藝對“原真性”的規定,是“使認識文化遺產的性質、特性、涵義和歷史成為可能的,一切物質型、文字型、口頭型和圖像型來源,”包括“形式與設計,材料與質地,利用與功能,傳統與技術,位置與環境,精神與情感,以及其它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本真”是不具有形態和標準的一種文化基因,據此,苗族文化中的裝飾題材源于其古老傳說,民間流傳的故事,以及民族歷史和記憶,這些記憶和題材經過世代相傳依然不變且貫穿始終,也是“本真性”的一種基質,可以在保持基質不變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多種形態的周邊產品開發,衍生出更多樣化的物質形態。當前非遺手工藝“再設計”產品中使用圖形圖案提煉運用最為普遍,設計師從苗繡、蠟染、銀飾等中的傳統圖形里面提煉出具有民族代表性的、視覺效果較強的圖形圖案,將其運用到手機殼、明信片、貼紙、書簽等創意產品上。此類產品采用批量生產,并不使用傳統的技藝,只是將圖案造型通過矢量化處理或者重新繪制轉嫁到新的產品之上,由于版權保護方面的相對空白,設計師或設計機構通常不用向相關人員或機構申請版權授權,使用也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從技藝的角度,這類產品剔除了傳統手工藝品中技藝性勞作的因素,對手工藝傳承人本身并沒有直接的益處,對于非遺傳承起到的作用極其有限。另一類設計,來源于苗族民族中口頭相傳的歷史記憶或民間傳說,從內核上保證了產品創意來源的“原真性”,同時,在繼承用傳統圖形圖案的基礎上,對材料和技藝有更進一步的探索,如以苗族蝴蝶媽媽與12個蛋的古老傳說為原型設計的現代燈具,其中的造型設計來源于誕生蝴蝶媽媽的楓樹及12個蛋的造型,裝飾紋樣上選取了傳統蠟畫中蝴蝶媽媽相關的圖案,材質上保留了蠟染所使用的白麻布料,以及一些古法制造的花草紙,從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從創意到形態再到材質工藝設計的“原真性”,作為現代家居生活的裝飾,頗具民族特色,也非常切合實際應用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