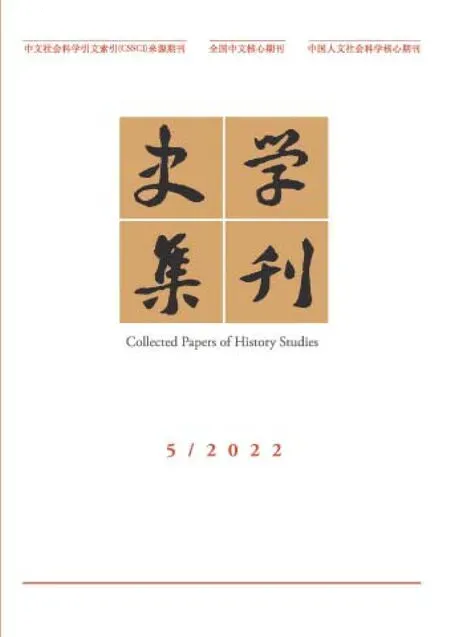南宋明州砂岸買撲制與沿海社會秩序的重構
張宏利
(渤海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遼寧 錦州 121013)
南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完成南北大轉移,受此影響,東南地區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同時,受惠于國家積極開放的海洋政策,宋朝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達到了新的高度。伴隨而來的是,沿海地方政府面臨著以何種方式管理沿海居民的新問題。彼時,明州(1)慶元元年(1195),宋寧宗將明州升為慶元府。為便于行文,本文主要以“明州”概稱,或根據語境而以“慶元府”具稱。宋代之時,明州領有鄞縣、奉化縣、慈溪縣、定海縣、象山縣、昌國縣,其域相當于今浙江省寧波市的鎮海區、北侖區、江北區、海曙區、鄞州區、奉化區,以及慈溪市、象山縣、舟山市。地方官府對此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在所屬海濱之地創設砂岸(2)宋代時通行寫法為“砂岸”,有時也寫作“沙岸”。入元后,通行寫法變為“沙岸”,“砂岸”亦在使用。買撲制,以此將海物資源的所有權納為官有,進以強化對瀕海民眾的管理。于是,砂岸這一場域匯聚了明州及所屬沿海諸縣官吏、私占承佃砂岸地方精英、賴砂岸為生的沿海民眾三方相關利益主體。他們之間的頻繁互動,導致沿海社會秩序處于破壞—重構過程之中。透過砂岸買撲制,不僅能夠呈現古代中國海洋資源的所屬權變動和海洋管理方式的轉變,而且還可以考察南宋及以后朝代沿海地方社會的發展走向。
目前所及,學界尚無以砂岸買撲制作為研究對象的論著。但是,關于砂岸的研究,已有諸多先行研究成果可資參考。就研究主旨而言,大多論著僅是在論述貨幣地租、學田、海洋捕撈、漁業稅等時附帶提及,(3)漆俠 :《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367頁;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頁;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頁;白斌、張偉:《古代浙江海洋漁業稅收研究》,崔鳳主編:《中國海洋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頁;徐世康:《宋代沿海漁民日常活動及政府管理》,《中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近來研究有進一步深化的趨勢,有學者對其做專題性研究;(4)倪濃水、程繼紅: 《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論》,《浙江學刊》,2018年第1期。但以研究視角觀之,主要基于經濟史視域。
據上述先行研究之檢討可知,學者們主要把砂岸作為海物采捕場所來研究,僅有少數研究者視其為一種海洋租稅制度。既有研究雖已注意到砂岸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但未認識到兩者皆由砂岸買撲制衍生而來。據此可以講,現有研究還存在諸多尚需解決的問題,諸如怎樣定義砂岸買撲制?砂岸買撲制產生于何時?承佃砂岸地方豪族上戶如何憑借砂岸買撲制破壞明州沿海社會秩序?地方官員又是怎樣重構明州沿海社會秩序,重構過程中是否遇到阻力,其結果如何?有鑒于此,本文擬以歷史學、社會學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解讀南宋明州的砂岸買撲制,并回答上述問題。
一、砂岸買撲制釋義
從目前所掌握的文獻來看,砂岸僅見于明州,且集中載述于地方志中。關于砂岸的含義,寶慶《四明志》稱:“所謂砂岸者,即其眾其(共)漁業之地也。”(5)(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5頁。開慶《四明續志》的記載與此相類,“砂岸者,瀕海細民業漁之地也”。(6)(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頁。對此,學界的解讀尚存分歧,主要有兩種看法:其一,砂岸即民眾近海捕魚之場所。漆俠、徐世康、白斌、張偉等學者均持此觀點。(7)漆俠:《宋代經濟史》,第172頁;徐世康:《宋代沿海漁民日常活動及政府管理》,《中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白斌、張偉:《古代浙江海洋漁業稅收研究》,崔鳳主編:《中國海洋社會學研究》,第170頁。其二,砂岸不僅包括漁民近海打魚之地,而且海島上的田地、海島周圍的海涂亦屬其組成部分。倪濃水、程繼紅首倡此說。(8)倪濃水、程繼紅:《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論》,《浙江學刊》,2018年第1期。兩位學者之所以如此定義砂岸,乃是源于他們對“洋山岙隸昌國州(今浙江省舟山市),山七百余畝,地四十九畝三十八步,海濱漲涂不可畝計”的解讀。(9)章國慶:《元〈慶元儒學洋山砂岸復業公據〉碑考辨》,《東方博物》,2008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洋山岙與洋山岙砂岸實屬兩個相異的概念,不可等量觀之,此處的山地、海涂地系指洋山岙。另據文獻所載“昌國縣洋山岙砂岸一所”,“昌國州洋山砂岸系本岙住人丁德誠”所佃,(10)章國慶:《元〈慶元儒學洋山砂岸復業公據〉碑考辨》,《東方博物》,2008年第3期。更是言明洋山岙砂岸為洋山岙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在定義砂岸之時,不宜將海島上的田地、海島周圍的海涂歸入砂岸范圍。
那么,砂岸是如何變為一個專有名詞的呢?在此,我們擬根據地方志的相關記載,勾勒出其大致演變過程。檢索文獻可知,成書于乾道五年(1169)的《四明圖經》尚無砂岸的記載,而撰成于紹定元年(1228)的寶慶《四明志》已經有多處關于砂岸的載述,并詳敘砂岸的產生情形。其文稱:宋孝宗之子魏惠憲王趙愷判明州時,奏請朝廷將石弄山砂岸撥賜明州州學養士,令其自擇砂主,并定其租錢額為5200貫文。(11)(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4-3135頁。開慶《四明續志》則將“砂主”稱作“砂首”“主砂者”,并記載“以砂首煩擾,復奏請馳以予民”。(12)(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612、3715頁。此處的“砂主”,知慶元府事顏頤仲在奏疏中用其來指代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13)(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對于“自擇”之意,據“浦嶼窮民無常產,操網罟資以卒歲,巨室輸租于官,官則即其地龍斷而征之,或興或廢”,(14)(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頁。則指稱的是招佃。結合上述所載,趙愷此舉意在解決州學經費不足的問題,而“令其自擇砂主”意指明州州學將石弄山砂岸向當地居民招佃,富家豪民向其繳納規定額度的租稅后,地方政府賦予承佃地方勢豪壟斷砂岸,并賦予他們向使用砂岸的瀕海細民征稅的權力。這便是砂岸買撲制的雛形,其法是將通行于宋境的買撲制度移植于海洋經濟管理的一種新舉措。所謂買撲,系指私人通過類似現代流行的招標競標的方式,向官府交納一定數額錢物后,承包或承買官府的商稅場、酒坊、田地、鹽井等特定時空內的經營權。(15)方寶璋:《略論宋代政府經濟管理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基于市場性政策工具的視角》,《中國經濟史研究》,2014年第3期。因此,知慶元府事吳潛稱砂岸買撲制實施的場域為砂岸稅場,又稱其為團局。(16)(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3717頁;(宋)吳潛:《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三《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頁。政府此舉不僅可以節省設務差官的開支,而且能假借豪民之手實得商稅,實屬有益無弊之舉。(17)冷輯林:《略論宋朝的商稅網及其管理制度》,《江西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細考之,趙愷于淳熙元年(1174)徙判明州,(18)《宋史》卷二四六《趙愷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733頁。宋廷于淳熙四年(1177)頒布除罷續置砂岸的詔令,(19)(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573頁。因此明州地方政府當于此間創建砂岸買撲制。其后,砂岸數量逐漸增多,故明州新設砂岸局統轄各處砂岸,專門負責砂岸的招佃,并向承佃者收取租稅。(20)(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612頁。在此背景下,明州沿海官民逐漸使用“砂岸”一詞來指稱近海采捕場所。
隨著砂岸買撲制的推行,明州地方官府財政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同時,依海而生的當地民眾經濟生活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首先,明州地方政府憑借政治權力將海濱人戶共漁之地強行納為官有,進而以強制性手段剝奪了瀕海居民共同享有的海物捕撈場域的所有權,由此完成了物產權的轉移。其次,沿海細民捕撈海物由免稅變為納稅。北宋時期,明州地方政府“以海鄉散漫,止產魚鹽,商賈之所不至,故無征禁”,(21)(元)馮福京修,(元)郭薦纂:大德《昌國州圖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冊,第4758頁。官府此舉乃是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的習海之人。(22)(宋)吳潛:《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三《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第177頁。降至南宋,明州地方官府曾短暫向海民捕獲鮮魚、蚶、蛤、蝦等征稅,不久即以明州乃瀕海之地、田業既少、其民興販鮮魚為生理宜優恤的名義,免除了上述稅項。(23)(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94頁。但是,這種情況在淳熙元年至四年(1174—1177)伴隨著砂岸買撲制的實行而發生根本性變化,其后整個明州沿海地區業海人的采捕活動均被征收租稅。明州地方政府向使用砂岸的習海人群征收的賦稅,寶慶《四明志》稱作砂岸租,有學者稱之為“砂岸海租”制度。(24)倪濃水、程繼紅:《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論》,《浙江學刊》,2018年第1期。此外,漁船出海捕魚前后,需要在沿海灘涂晾曬漁網、海產品等,地方政府亦會對占用沿海灘涂的海民進行征稅。(25)白斌、張偉:《古代浙江海洋漁業稅收研究》,崔鳳主編:《中國海洋社會學研究》,第170頁。
綜合上述,明州地方官府將海物采捕水域強行納為官有后,創建砂岸買撲制,通過買撲形式讓渡該水域使用權予地方權勢之家,瀕海人群享有的無償采捕海物之權隨即被剝奪。明州地方政府由此獲取巨額砂岸租收入,有效地緩解了地方財政的困窘局面。與此同時,包佃砂岸的地方豪民大族取得了向瀕海細民征收海洋漁業稅的權力,他們因勢而壟斷海物資源,致使賴此為生的沿海鄉民只有交納一定賦稅方可繼續使用砂岸。承佃砂岸的富家大族正是憑借征稅之權恣意侵害海濱人戶的利益,導致兩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明州沿海社會秩序因此遭到破壞。
二、承佃砂岸地方勢家豪民對沿海社會秩序的破壞
由于明州地方財政日益趨緊,砂岸買撲制得以推廣,尤其是在寶慶年間(1225—1227)得到普及。(26)倪濃水、程繼紅:《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論》,《浙江學刊》,2018年第1期。因砂岸買撲制引起的明州沿海區域社會關系的變化,成為考察沿海社會秩序破壞—重構的邏輯起點。正所謂權力與所控配置性資源成正比關系,(27)[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7-8頁。強族豪民取得砂岸這一配置性資源后,意味著他們同時獲得了官府的授權,堂而皇之地壟斷砂岸之利,并能夠合法地向海捕人群進行征稅。在此情形下,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與瀕海居民由平等的關系轉變為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邊海之人因此受到明州地方政府、承佃砂岸地方富民大家的雙重剝削。易言之,正是因為明州地方官府強勢介入砂岸場域,改變了沿海地方原本利益關聯度不強的社會關系,進而生成充滿利益糾葛與沖突的新型區域社會關系。
在資源依存性極強的古代社會,海物捕撈場所對于瀕海細民生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砂岸是明州海濱之人的重要生計來源,其民“素無資產,以漁為生”。(28)(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在缺乏利益均衡機制的古代中國,資源配置有利于強者,更易于使強者以侵犯他人利益邊界的方式使自己獲得最大的利益,弱者愈益處于被剝奪的境地。(29)李瓊:《沖突的構成及其邊界——以湖南省S縣某事件研究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上海大學,2005年,第25頁。承佃砂岸地方精英正是以壟斷砂岸獲利,“海鄉細民,資砂岸營口腹,龍斷者以抱納微入啖官司,而擅眾利”。(30)(宋)劉克莊著,辛更儒校注:《劉克莊集箋校》卷一四三《寶學顏尚書神道碑》,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703頁。知慶元府事顏頤仲更是指出:“數十年來,壟斷之夫,假抱田(佃)以為名,啖有司以微利,挾趁辦官課之說,為漁取細民之謀”,并稱承佃砂岸地方豪民對瀕海民眾橫征行為乃是“奪小民衣食之源”。(31)(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史籍雖未明確記載承佃砂岸地方豪民巨族何時借砂岸擾亂瀕海生民,但寶慶《四明志》載:“淳熙四年有旨,續置砂岸并除罷。”(32)(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573頁。這說明砂岸買撲制創建不久后,租佃砂岸地方豪民巨族欺凌使用砂岸的海濱民眾,對明州沿海社會秩序造成了較大的破壞,從而引起宋廷的關注并詔令廢除。
然而,宋廷此詔并未能遏制明州砂岸的續置,明州反而不遺余力地續增之,石壇、蝦辣、鱟涂、大嵩、雙岙、淫口、沙角頭、穿山等處均屬新置砂岸。(33)(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4-3137頁;(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612頁。在此種情勢下,官員、地方豪強趁機私占了少部分砂岸,“在外官民戶砂岸”,秀山砂岸為徐榮等物產,然其所占比重較少,且砂岸規模亦不大。(34)(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4-3135頁。以此之故,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一直是剝削瀕海細民、破壞沿海社會秩序的主體,私占砂岸者在其中所起作用非常有限。對瀕海細民來說,一旦其生存手段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意味著其生活與過去有了根本的不同。(35)[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顯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隨著承佃砂岸勢家豪民掠奪幅度的增大,砂岸變為民害的場域,海民因此陷于困苦的境地。文獻記載瀕海民眾為求生存而上訴明州地方官府的情形為,“砂岸之為民害,見于詞訴者愈多”,“爭佃之訟紛如”,“人又謂主砂者苛征而相吞噬者,則滋訟”,“沿海細民又且詞訴迭興”。(36)(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6頁;(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612、3715-3717頁。換言之,承佃砂岸地方大家上戶的逐利行為,業已侵害了賴海為生的民眾利益,并使他們的生存陷于困境。
逐利屬于人的天性,在政府約束力不強的情況下,逐利的天性更是得到彰顯。正是由于明州地方官府的縱容,使得砂岸成為包佃砂岸地方精英營私的空間,進而導致砂岸承佃者將征稅之權發揮至極致,沿海鄉民利益因而被肆意侵害。寶慶《四明志》載述地方勢家富民借壟斷砂岸之便大肆侵漁瀕海細民的行為有如下諸端:
其一,借辦課官租,肆意征稅于民,為己大肆斂財。壟斷砂岸之人,挾趁辦官課之說,為漁取細民之謀,名為抽解,實則攫拿。始焉照給文憑,久則視同己業,或立狀投獻于府第,或立契典賣于豪家。以此倚勢作威,恣行刻剝,表現在:一是肆意擴大征稅范圍,竹木薪炭、豆麥果蔬莫不有征;二是征稅名目繁多,有艚頭錢、下莆錢、曬地錢等;三是對官府免稅的醫卜工匠,亦創名色以苛取。(37)(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當然,包佃砂岸地方大族富民的上述行為,既受到自身利益的驅使,又因明州諸司不斷增多的砂岸租稅額壓力所迫。唯有更大規模地斂取于民,他們方可完納官府的課額,進而為己謀利。由此可見,承佃砂岸地方精英的所作所為業已超出了明州地方官府讓渡的權力范圍。他們為追逐私利、完納官府砂岸租稅而聚斂錢財,對沿海民眾進行高強度的經濟掠奪,加重了民眾負擔。
其二,民眾生業艱難,民怨歸于公。地方富戶豪民借砂岸大肆掠奪普通民眾,導致后者陷入生存困境,卻將民怨引之于官府。時有議者謂:“公家利益甚少,而稅場為民害者不貲。”(38)(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7頁。時人對此而嘆:“凡海民生生一孔之利,竟不得以自有。輸之官者幾何,誅之民者無藝。利入私室,怨歸公家,已非一日。”(39)(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此段引文說明,涉海民眾將其生活艱辛的原因歸咎于明州地方官府倡行的砂岸買撲制,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承佃砂岸地方勢家富民正是憑借明州地方政府賦予的征稅權力任意盤剝于己,故民眾將所怨歸于地方官府。
其三,擴充勢力,酷虐百姓。承佃砂岸之人不僅在經濟上嚴酷剝掠瀕海民戶,而且憑借其權勢和財富大肆干預地方政務。他們在當地廣布爪牙并大張聲勢,所屬砂主、專柜、牙秤、攔腳等數十人結為群,四處為害,具體行徑有:一是“邀截沖要,強買物貨,挜托私鹽,受亡狀而詐欺,抑農民而采捕”;二是民眾“稍或不從,便行羅織,私置停房,甚于囹圄,拷掠苦楚,非法厲民,含冤吞聲,無所赴訴,斗歐(毆)殺傷,時或有之”。(40)(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3136頁。據此可知,承佃砂岸地方豪強已然成為當地的惡勢力,不僅恣意擾亂當地民眾的經濟活動,對地方經濟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而且還任意迫害或殘害邊海之人,地方政治秩序不斷受到沖擊。受其影響,明州沿海社會秩序持續地遭受破壞。
在砂岸包佃者持久且愈來愈重的經濟盤剝與政治欺壓之下,海邦之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越來越難以維系。在這種情況下,瀕臨生存邊緣的沿海民眾迫于生計壓力轉而為盜,用以拓展其生存空間,“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置團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免淪而為盜”,(41)(宋)吳潛:《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三《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第177頁。“近年海寇披猖,如三山、小榭等處,有登岸焚劫之事”。(42)(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6頁。正是由于承佃砂岸地方精英對瀕海細民侵剝強度的不斷增大,導致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呈現出加劇的態勢,由此引發了地方社會的動蕩,對沿海社會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部分承佃砂岸地方豪強變作海寇四處劫掠,更是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社會秩序。他們羅織惡少、招納昔為犯罪之人,揭府第之榜旗,為逋逃之淵藪,操戈挾矢,撾鼓鳴鉦,焂方出沒于波濤,俄復伏藏于窟穴。其所為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強者日以滋熾,聚而為奸;弱者迫于侵漁,淪而為盜。由此薄人于險而靡所不為:他人之舟,即己之舟;他人之物,即己之物。其強悍的程度,以致兵卒不得而呵、官府不得而詰。(43)(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6頁。這說明以地方豪族為首的海盜勢力,不僅規模大,而且異常兇悍,以致陸地、海上民眾均遭其肆虐,而官府對其亦無可奈何。在上述兩股勢力的破壞下,沿海社會失序問題漸顯并呈現出擴大的趨勢。
綜合上文,明州地方官府創建砂岸買撲制的目的在于解決日常經費不足的問題,以實際效果來看,明州地方官府經費困乏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緩解。但是,宋朝朝廷、明州地方官府未曾預料到的是,承佃砂岸的地方權勢之家取得向使用砂岸的沿海民眾征稅之權后,其所作所為卻逐漸擺脫了明州地方官府的控制。承租砂岸的地方精英不僅對沿海居民苛取暴利,而且他們隨意干涉地方政事,儼然成為危害一方的惡勢力。在此種情形之下討生活的沿海之人,在承佃砂岸者經濟剝削之下,生活業已困苦不堪;在承佃砂岸者插手地方事務后,沿海居民更是時刻面臨著失去生命、財貨的危險。可以說,砂岸承佃者的弄權行為,不僅加劇了其與涉海群體之間的矛盾,而且也引發了明州沿海地方社會的動蕩。為維持地方社會的穩定,明州有見識的官員以行政命令形式罷除砂岸買撲制,旨在消除造成明州沿海社會動亂的根源,重整沿海社會秩序。
三、地方官員重構沿海社會秩序的努力
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侵損瀕海民戶利益以及破壞沿海社會秩序的行為,已經引起宋廷的重視,并從國家層面發布廢除砂岸買撲制的詔命,“淳熙四年(1177)有旨,續置砂岸并除罷”,(44)(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573頁。后令近海“眾戶舟楫往來,縱便漁業,勿有所問,不得容令巨室妄作指占,仍舊勒取租錢”。(45)(清)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52頁。需要強調的是,宋廷僅是下詔要求明州地方政府禁罷砂岸買撲制,而廢除砂岸買撲制的實際行動則有賴于明州有作為的官員。鑒于承佃砂岸地方大家上戶的行為對濱海居民利益侵損越來越大,并嚴重影響了沿海社會的穩定,破壞了沿海地方社會秩序,有見識的地方官員屢有廢砂岸買撲制之舉。寶慶《四明志》對此有詳細的描述,“慶元二年(1196),陳景愈于爵溪、赤坎、后陳、東門等處創置稅貌。縣令趙善與以擾民,白府罷之。提刑李大性攝府,與除免所抱之錢。嘉定二年(1209),楊圭冒置,分布樊益、樊昌等為海次爪牙。鄭宥等訴之主簿趙善瀚,歷陳其害。五年,守王介申朝廷除罷,毀其五都團屋,版榜示民。寶慶元年(1225),胡遜、柳椿假府第買魚鮮之名,私置魚團。鄭宥等又有詞,倉使齊碩攝府,杖其人而罷之”。(46)(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573頁。除此之外,明州沿海制置使司屬官胡叔恬亦有勸罷砂岸買撲制之舉,“唱言巨室而沙岸為徹局”。(47)(宋)物初大觀:《物初剩語》,許紅霞:《珍本宋集五種——日藏宋僧詩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62頁。尚需注意的是,這些官員罷除砂岸買撲制之舉,僅是于一定時期在明州局部地區施行。
因砂岸買撲制造成的惡劣影響日趨嚴重,最終引起了知慶元府事的重視,并以政治權力強行廢罷砂岸買撲制。淳祐六年(1246),知慶元府事顏頤仲到任之初,訪聞砂岸買撲制為當地之害,“乃撙節浮費,先措置錢五百(萬)余貫,代納砂岸租錢,而一害先去”,(48)(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204頁。并申奏尚書省:“州郡既率先捐以子民,則形勢之家亦何忍肆虐以專利。應是砂岸屬之府第,豪家者皆日下,聽令民戶從便漁業,不得妄作名色,復行占據。其有占據年深,腕給不照,或請到承佃榜據,因而立契典賣者,并不許行用。欲乞公朝特為敷奏,頒降指揮,著為定令。或有違戾,許民越訴,不以蔭贖,悉坐違制之罪”,宋廷下旨依其所請。(49)(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6頁。在顏頤仲的努力下,明州官有及官民私占砂岸一例蠲除。(50)(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顏頤仲此舉旨在恢復原本穩定、有序的沿海社會秩序,在吳潛的奏言中已明確言明:“庶幾海島之民可以安生樂業,府第、豪戶不得倚勢為奸,非唯為圣朝推廣惠下之仁,亦不至異日激成為盜之患。”(51)(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6頁。然而,砂岸買撲制雖在顏頤仲四年任期內被禁行,但其后又得以復置。
寶祐四年(1256)知慶元府事吳潛到任后,獲悉砂岸買撲制為當地民害而奏言:“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團局,聽令民間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并稱永行禁斷砂岸買撲制是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52)(宋)吳潛: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三《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第177頁。在吳潛的推動之下,曾一度廢除砂岸買撲制,但之后“因民之欲而奏復之。越一年,人又謂主砂者苛征而相吞噬者,則滋訟。公知其擾民也,亟奏寢之,或止或行,悉因民欲”。(53)(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頁。此后的寶祐五年(1257)吳潛奏請將贍學砂岸“復歸于學。繼而爭佃之訟紛如,準制札仍撥歸制司,卻于砂岸局照元額發錢養士。六年五月,以砂首煩擾,復奏請馳以予民”。(54)(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612頁。在吳潛四年任職期內,砂岸買撲制除罷與復置時或有之的原因,乃是吳潛將沿海盜賊盛行的原因歸為罷砂岸買撲制而致砂民無所統率,(55)(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頁。為維持地方穩定而復置之;其后鑒于復置砂岸買撲制致擾民不息又罷之。這說明,吳潛雖欲根除砂岸買撲制,但受當地實際情形所迫,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協。
與此同時,為消弭海盜對沿海社會的沖擊,顏頤仲、吳潛力推保甲之法,并增加沿海地區的屯兵數量,力圖恢復沿海地方的穩定。淳祐六年,顏頤仲已將當地民船團結保伍。(56)(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吳潛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保甲之法。吳潛對該法實行的緣由、具體做法、預期效果等有詳盡的闡述,“始者之興復砂岸稅場,不過欲為清海道絕寇攘之計,今已將應干砂岸諸岙并行團結,具有規繩,本土之盜不可藏,往來之盜則可捕”,“則前所謂砂民無所統率而盜賊縱橫之事,不必慮矣。又于浹港置立小屯,則前所謂數十里之內官司并無纂節,而莽為盜賊出沒之區者,不必慮矣”。(57)(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6-3717頁。慶元府“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強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置立頭目,部勒隊伍……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58)(宋)吳潛:《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四《條奏海道備御六事》,第184頁。明州地方政府此舉,是以政治手段強力推行保甲制,借此強化對沿海居民的人身控制,進而達到穩定地方社會的目的。應當說,明州以強制性力量彈壓沿海群盜的不法行為,僅可暫時實現地方社會的穩定,卻無法維持該局面的常態化。因此,地方官府應當構建穩定有序的沿海社會秩序,穩定是外在表象、是初級狀態,而有序才是內在的、本質的高層次的理想狀態,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根本基礎。(59)宋寶安:《論實現社會從穩定到有序的戰略抉擇》,《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第2期。
總的來看,明州自上而下皆有官員竭盡所能除罷砂岸買撲制,確實在一定時期的局部地區或短時期于全境住罷砂岸買撲制,海濱居民因此能夠無償、自由地采捕海物,使得明州沿海社會秩序得以短暫恢復。但是,相對于砂岸買撲制存續時間而言,地方官員維持無砂岸買撲制的時間畢竟為期不長,故其重構沿海社會秩序的努力只能在短期內有效。這足以表明,明州沿海社會秩序的重構遇到了極為強勁的阻力。觀其所遭阻力,主要源自兩個方面:一是明州地方官府;二是私占、承佃砂岸的既得利益集團。
其一,明州地方財政收入窘乏,官府日常經費對砂岸租依賴性極強。明州所在的兩浙地區,一直是北宋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60)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頁。伴隨著宋代經濟重心的南移東傾,江南地區步入宋廷重賦征斂時期。(61)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27頁。受此影響,兩浙地區于北宋后期已屢屢出現財政虧匱情況。(62)(清)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九》,第7107頁;(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七《國用考五》,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795頁。迨至南宋時期,明州成為畿輔之地,宋廷對其財賦的索取愈益增重,致使明州出現“稅重田輕,終歲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的現象。(63)(宋)李心傳著,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八○,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456頁。更為嚴重的是,明州同時進入自然災害頻發期,多個年份發生規模較大的水旱蟲災害,臺風、海嘯時有發生,甚至出現人食草木之現象。(64)《宋史》卷六七《五行五》,第1463-1477頁。因此,朱熹言:“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臺、明號為最熟,亦不能無少損”。(65)(宋)朱熹著,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六《奏救荒事宜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62頁。不唯如此,明州還需承擔日本、高麗使者居留其間費用,對兩國漂流人出錢糧施以救濟。尤其是開禧用兵后,南宋進入與蒙古軍事對抗期,中央財政壓力驟增,無疑加重了明州地方財賦的負荷。綜合上述,宋廷的重賦索取、自然災害造成的收入減損以及地方支給增多,共同導致明州地方財政陷于困境。
緣于此,明州地方官府不得不另辟新的財源,以求緩解愈來愈重的財政壓力。對邊海的明州及所屬縣來講,向采捕海物的濱海居民征取賦稅成為解決財政困境的重要方式。于是,魏惠憲王趙愷創砂岸買撲制,以解決明州州學經費不足問題。難得的是,文獻載述了明州贍學砂岸租稅額度的變化情形。從淳熙初年至淳祐六年(1174—1246)的70余年間,明州贍學砂岸就由初始稅額的5200貫文猛增至30 779.4貫文,十一年后的寶祐五年(1257)更是達到37 478.75貫文。(66)(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3136頁;(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612頁。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明州地方政府所定砂岸租額度亦呈現遞增之勢,某一年歲收砂岸錢共計53 182.6貫文,(67)(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6頁。之后更是達到驚人的368 700貫文。(68)(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3716頁。深究明州地方政府征收砂岸租額度越來越多的原因,乃是在于所轄諸司以及屬縣日常支給愈來愈依賴砂岸租所致。明州地方官府征取的砂岸租稅,不僅用來撥助昌國縣官俸,甚至郡庠養士貼廚、水軍將佐供給、新創諸屯與出海巡逴、探望、把港軍士生券及慶元府六局衙番鹽菜錢之費亦需由其支付。(69)(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頁;(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3716頁。
正是基于此,導致砂岸買撲制能夠長時間存續。顏頤仲推求砂岸買撲制不能禁絕的原因在于州縣財賦收入依賴于砂岸租,為此他建議欲廢除砂岸買撲制應先自有司始。(70)(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6頁。雖然如此,顏頤仲甫至慶元府即意識到廢除砂岸買撲制牽扯多方利益,除罷之事必須慎之又慎,因此他說:“竊計所管課額,散在他司,用度所關,未易除罷。”(71)(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204頁。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顏頤仲、吳潛雖盡罷砂岸所入課利,但并不意味著明州諸司依賴砂岸租收入的現象立即消失。對于昌國縣官俸及養士、餉軍之需,他們僅是截撥版帳錢、慶元府醅酒庫息錢及翁山等坊、慈溪酒務每歲息錢給予支遣而已。(72)(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5-3137頁;(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6頁。由此可見,兩位官員所舉皆屬應急之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明州財賦窘乏的困境,這也導致砂岸買撲制被廢除后,復有興之。更為重要的是,為年入數萬緡砂岸租,坐視海民困苦而不救的明州官員甚多。(73)(宋)劉克莊著,辛更儒校注:《劉克莊集箋校》卷一四三《寶學顏尚書神道碑》,第5703頁。據此可以講,明州地方官府所屬諸司日常辦公經費依賴于砂岸租所得,由此明州地方官府成為住罷砂岸買撲制的主要阻礙力量。
其二,私占、承佃砂岸既得利益集團竭力阻擾廢除砂岸買撲制。私占、承佃砂岸者“由其恃有憑依,所以肆無忌憚”,其開抱砂岸者部分為品官與貴勢之家,致使奸宄日出、遺禍無窮,從而導致砂岸買撲制屢不能禁。(74)(宋)胡榘修,(宋)方萬里、(宋)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冊,第3136頁。因此,包佃砂岸的地方豪強憑借明州地方政府讓渡的砂岸征稅之權以及自身具有的權勢、財富,能夠統率瀕海細民,后者對前者具有較強的依附性。史籍對此有明確的記載:“人謂砂岸廢而民無統,寇職以肆”,“適當海寇披猖之余,遂行考究本末,多謂因沿海砂岸之罷,海民無大家以為之據依”,“皆起于罷砂岸,而砂民無所統率之故”。(75)(宋)吳潛修,(宋)梅應發、(宋)劉錫等纂:開慶《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冊,第3715-3716頁。正是由于承佃砂岸地方形勢之家具有的強大勢力,他們能夠對濱海之民形成威懾之勢,從而任意剝掠沿海民眾。在這種情勢下,吳潛雖強行罷除砂岸買撲制,但仍憂慮地方豪民勾結官府而復之,“一方奸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創砂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76)(宋)吳潛:《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三《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第177頁。從文獻明確記載遲至咸淳三年(1267)砂岸買撲制得以復置來看,(77)章國慶:《元〈慶元儒學洋山砂岸復業公據〉碑考辨》,《東方博物》,2008年第3期。他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上述事實,充分凸顯了明州致力廢除砂岸買撲制的官員與私占、承佃砂岸之人博弈過程的復雜性和持久性。
綜上可知,明州地方官府日常經費困乏的局面始終未得到實質性改善,故對砂岸租有著強烈的依賴性,得以保障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私占、承租砂岸的地方大家上戶基于經濟利益考量,也希望維持砂岸買撲制,進而獲取巨額收入。在這種情形下,明州地方政府與私占、承佃砂岸地方豪強之間存在著同樣的利益需求,故為實現彼此間的利益最大化,結成了既得利益共同體。地方官府有意容縱承佃砂岸地方精英的不法行為,任由其欺壓瀕海居民,沿海社會秩序不斷遭到破壞。在這種形勢下,明州有作為的官員罷除砂岸買撲制、重構沿海社會秩序的努力,雖可短期內取得預期效果,但卻難以扭轉整個發展態勢。值得注意的是,砂岸買撲制并未隨著朝代的更迭戛然而止。元代之時,不僅出現官屬砂岸被官員、豪民據為己有的新現象,(78)(元)王元恭修,(元)王厚孫纂:至正《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冊,第4614、4628頁。而且將其所占官屬砂岸轉售他人的情況亦有之。(79)章國慶:《元〈慶元儒學洋山砂岸復業公據〉碑考辨》,《東方博物》,2008年第3期。據此可斷言,砂岸買撲制產生的破壞力在元朝依舊發揮著作用。降至明代,受官方海洋政策日趨保守的影響,海物采捕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砂岸買撲制最終伴隨著明朝的嚴厲海禁政策不復存在。(80)倪濃水、程繼紅:《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論》,《浙江學刊》,2018年第1期。
結 語
明州邊海地區有著豐富的海洋物產,這為田業較少的瀕海民眾提供了賴以生存的資源。北宋及南宋前期,宋廷、地方財政壓力較小,故明州地方官府任由瀕海居民無償采捕海物,沿海民眾得以平等地享有海洋捕撈之權。降至南宋中后期,中央政府的財政需求不斷增多,對地方財政的索取隨之增強,尤其是地處畿內之地的明州成為宋廷重點征取對象。這直接加劇了明州地方政府的財稅負荷,為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明州地方官府將行之于宋境的買撲制度引入海洋采捕活動中,是為砂岸買撲制。至此,砂岸買撲制作為一種新的機制被創立出來。
明州地方政府通過砂岸買撲制將地方政治權力滲透至海物采捕場域中,剝奪了沿海民眾自由和無需交納租稅即可使用海洋資源的權利,并將獨占砂岸的權力賦予承佃的地方勢家豪民,于是砂岸承佃者與瀕海細民之間形成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在明州地方官府賦稅壓力和自身經濟利益驅動之下,承佃砂岸地方精英不斷突破明州地方政府的規限,肆意擴充稅項并任意侵漁沿海民眾,兩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沿海社會秩序受其影響不斷被破壞。有鑒于此,明州有識見的官員屢有除罷砂岸買撲制之舉,并在短時期內取得了預期效果,明州沿海社會秩序因此得以重構。然而,由于明州州學養士、屯戍水軍所需及部分縣官俸祿主要仰給于砂岸租,截撥他處收入支給僅可暫時應之,卻無力改變明州地方財政的窘困局面。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明州相關官員欲永久住罷砂岸買撲制,并借此重構沿海社會秩序的努力,勢必難以取得一勞永逸的效果。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嚴重依賴砂岸租的明州諸司,以及私占、承佃砂岸地方勢家富民結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明州有作為官員廢除砂岸買撲制、重構沿海社會秩序的主要阻力。因此,宋廷、明州地方政府雖皆有罷砂岸買撲制之舉,但均遭到賴砂岸租維持日常用度諸司,以及私占、承佃砂岸既得利益集團的百端阻擾,其結果便是由砂岸買撲制引起的沿海社會秩序的破壞活動,終南宋一代未能得到消除。
砂岸買撲制的影響并不限于此,由砂岸買撲引起的承佃砂岸地方勢豪破壞明州沿海社會秩序的活動,更是對元明清三朝海洋經營活動產生了影響。雖然,明州地方政府以砂岸買撲制為媒介,將政府力量逐步滲透至沿海居民海物采捕活動中,并不斷擠壓沿海地方社會的自主空間,意圖嚴格管控涉海群體,進而維持沿海社會秩序的穩定。但是,明州沿海社會的動蕩局面并未因此而被有效控制,官員重構沿海社會秩序的努力最終沒有成功。受其影響,元明清官府非常忌憚沿海居民的破壞性活動,對濱海民眾的防范意識日漸增強,進而不斷強化對海邦之民的管理。此舉更是直接導致明清官方海洋政策日益保守,對民間海洋活動的限制日趨嚴格,以致海禁政策屢有實施。
——張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