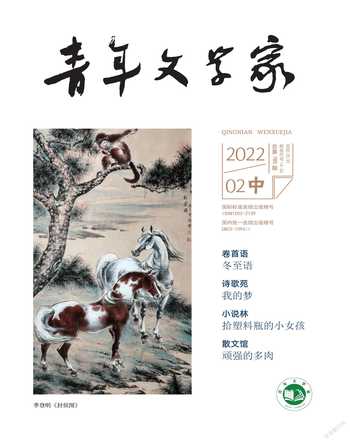飄過雪花的記憶
張雅娜

深冬,已好久不見姨媽了,突然地想念。
給表姐電話,才知姨媽的阿爾茲海默病愈發嚴重了,已住院。
姨媽是漢劇演員,年輕時是紅遍江城的漢劇大青衣。舞臺上,鳳冠霞帔的她,纖指輕捻,聲音穿在鋼絲上一般,婉轉唱著《二度梅》。后臺,卸妝的她,露出精致洋氣的面容,長長的睫毛上仿佛凝著薄薄的冷霜,眼里透著距離感。記憶里,姨媽是這樣耀眼而遙遠的存在。
被無數漢劇迷崇拜著、寵愛著,難免膨脹出極度的自我。然而,所有人都那么包容,仿佛漂亮的名伶天生就該擁有這樣的特權。包括我,以及姨媽的獨生女軍軍,也都這么以為。
表姐帶我去醫院的那天,天空飄著雪。走在去往病房的雪地,樹枝上墜下的冰晶落在臉上,瞬間冰涼地滑落,像無聲的淚珠。讓眼前白茫茫的世界平添一份空落感,這感覺在心頭縈繞,一點點蔓延成無邊際的雪白,直至與姨媽白色的病床融在一起。
兩個護工一左一右幫姨媽洗漱著,小心翼翼的樣子。姨媽皺著眉,一臉不滿。“病成這樣了,還是和原先一樣挑剔。”表姐低聲嘀咕著,像告訴我,又像是對護工表達著歉意。
曾經的姨媽活得有多精致講究,也只有我們知道。我定睛細看姨媽,面容蒼老,眼神空洞,灰白的短發隨意攏在耳后。一瞬間,心里像有千軍萬馬踏過。命運曾賦予這張臉多少燦爛輝煌,而今的剝離就有多徹底殘忍。唯眼底宛在的那抹淡漠,依稀能喚起曾經的記憶。
表姐拉我上前,在姨媽耳邊重復著:“娜娜來看你了。”迎著兩眼空洞,我靠近她:“姨媽,我是娜娜。”
姨媽呆滯的目光終于落在我臉上,仿佛記起了什么似的,忽然綻出快樂的笑容,連聲說:“娜娜呀,長漂亮了。”那嫵媚歡快的表情竟讓我的心為之一動。記憶深處有一抹明媚在閃耀,那是我曾經的仰望。我轉頭望著表姐,眼里有一絲責備,姨媽哪里就糊涂到不認識人了呢。
表姐看我一眼,俯身叫了聲“媽”。姨媽轉過臉,表情木然。我不甘心,拉著表姐:“姨媽,這是軍軍啊,你不認識了嗎?”姨媽望向我,眼里有說不出的漠然氣息:“軍軍是什么人啊?”她反問我。表姐看著我,臉上滿是悲戚與受傷。
是我心存僥幸了。阿爾茲海默病,真的雁過寒塘,了無痕跡。我低下了頭。
彼時,姨媽患同樣病癥的弟弟,我的表舅剛去世。他們姐弟倆有一張極為相像的臉,眉宇間都透著一股驕傲和貴氣。表舅一直待我如女兒般,最后的時光里,失憶的他像個無助的困獸,在全然陌生的環境里做著無謂的抵抗。他已不認得我,但我的陪伴偶能換得他短暫的安靜。像個聽話的孩子,總是默默吃完我帶去的“小桃園”雞湯,然后一起靜靜坐在陽光里。院長說:“雖記不起你了,但你存在于他的潛意識里。”如此,亦聊以自慰了。
仿佛一道微光,穿過了漫長的黑暗,我忍不住要抓住那道光:“姨媽,你還記得悶子嗎?”
“悶子五歲了,長得幾帥哦。”姨媽的聲音突然柔下來,眼里蓄滿了柔情,“姆媽喜歡悶子,什么好東西都給他,我沒有。”言語里尚有孩子般的委屈。
我和表姐驚奇地對視。太意外了!一時間,百感交集。怎能想到,在被抹掉的無盡虛空里,牢牢占據她腦海的,是她曾滿心幽怨的姆媽和多年來少有往來的弟弟。
窗外雪花飛舞,像極了零落的柳絮。在這冬天,煙水縹緲的光陰里,我就這么跌進了清澈無塵的回憶里。
那該是姨媽深藏于心的一段時光,一段在心底重復千回的述說。
終于逃出不幸婚姻的姆媽,帶著十歲的她再嫁,繼父是一個英俊的黃埔軍官。郎才女貌的神仙眷侶,次年便有了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弟弟,弟弟自小不愛說話,小名便喚作悶子。姆媽身著旗袍,一頭卷發,身后站著貼身警衛,在璇宮飯店大宴賓客的日子,是一家人最富足無憂的時光。可好景不長,不久繼父隨部隊離開,再無音訊,是死是活至今成謎。一家三口的生活自此拮據。
即便成了萬眾矚目的名人,我們仍常聽到姨媽念叨心中的遺憾:“若不是環境所逼,我可以上清華的。離校那天的雪,像蘆花一般的雪啊,像蒲公英一樣的雪啊,在空中舞,在隨風飛。我,畢生難忘。”這是她心里最深的憾,亦是對姆媽最深的怨。
青春逼人的女孩,憑著老天爺賞飯吃的優越條件順利考上了戲校,擔起了養家的重任。后來,拜漢劇大師陳伯華為師,成了漢劇院的臺柱子,名噪一時。
星光熠熠的日子,各種演出應接不暇。姨媽無暇顧及癱瘓在床的姆媽,以及伺候母親長達七年的弟弟。她一個人,兀自盛開,盛大而隆重地綻放,把血濃于水的光陰全都席卷而去了。
疏離,隔膜,遙遠,似毫無關聯的季節,沒有過渡,沒有連接。
無法責備,無法要求。我們站在這親情之外,待時光流轉,看紅塵落寂。
晚年的姨媽開始嘗試走近唯一的弟弟。可時光久遠,親情早已疏淡。隨著阿爾茲海默病的一天天加重,表舅已不再認得這個姐姐。失去太久,彌補的路是那么遙遠,且來不及。
“悶子五歲了,長得幾俏皮呢,他最喜歡和我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姨媽一遍遍重復著,“姆媽只喜歡悶子……”
冬天的雪,漫天紛揚,終于凝結成最溫暖潔白的一朵,深種在了姨媽荒蕪的記憶里。屬于她的冰雪世界,在無聲無息中消融,但至親仍在,何嘗不是她最后的幸運呢?
伴著呼呼的北風,我看到了雪花飄過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