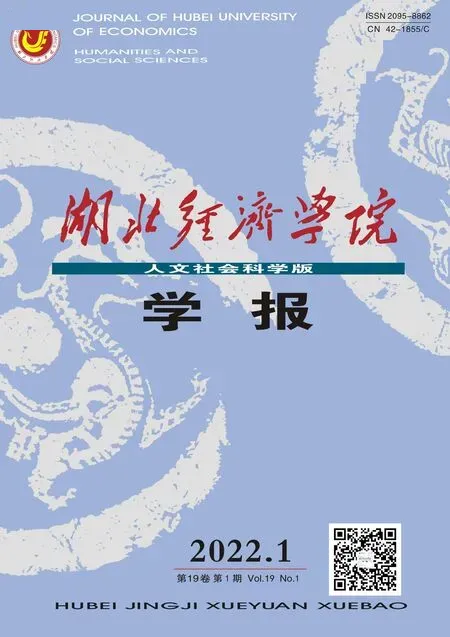外語教育史的成就與挑戰: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為中心的考察
盧鈺婷(湖北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一、引言
如果以1682年京師同文館的誕生標志中國近代外語教育的開端,到2019年中國教育部考試中心與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所聯合發布的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的對接結果來看,我國的外語教育已然走過了三個多世紀的漫長歷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外語教育歷經了各種變化、發展以及挑戰。可以說,這一承載著中國“主體性”意識的歷史進程,既建基于國人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逐漸自覺,也呈現出我們對自身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發展的深刻認識。而在今天,中國英語語言能力標準與國際的接軌更顯示出中國的文化自信。回顧和總結建黨百年來我國外語教育發展歷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未來挑戰,將進一步加速中國未來的發展,使其更深入地嵌入世界秩序的體系之中,并實現文明需求的新的可能。
二、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教育改革呼聲的高漲,外語學科(尤其是英語教育)的教學改革也被推向了討論前沿。一方面,英語作為涵蓋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基礎學科已是既定事實;但另一方面,英語課程設置的必要性卻受到了來自學界內外的各種質疑。例如在今年3月份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許進就建議改革義務教育階段英語的必修課地位。換言之,英語在義務教育階段的主科地位是值得商榷的。而針對高等教育中的英語教學,取消英語專業以及四六級考試的呼聲更是不絕于耳。究其原因,在很多教育工作者看來,英語作為一種言語的交流媒介,并無助益小學素質階段學生在思考、實踐以及創新能力的增長。而從現實角度出發,隨著人工智能在現代社會的廣泛應用,英語交際活動(比如翻譯)的實現逐漸呈現出機器替代人工的趨勢。
鑒于此,外語教育界也逐漸意識到教育過程中曾出現的各式痼疾:如語言知識的淺表化、教學模式的單一化、學術理論的滯后化等確實對外語教學產生過負向影響。但如梁啟超所言,“變法不變本源,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故此,近年來外語學界涌現出大量具有針對性的改革舉措:例如,除了在“新文科”的宏觀背景下外語課程建設的系列研討,連續五年在京舉辦的全國高等學校外語教育改革與發展高端論壇則更加從本位聚焦高等外語教育本身。尤其在第五屆論壇(2021年3月20-21日)上,不僅教育司司長、教指委專家及高等外語教育百余位學者親自蒞臨,全國外語教育同仁更是通過直播線上參會(例如百余所院校組織外語院系教師集體觀看)。據統計,此次論壇直播累計觀看人次達37萬。總而言之,以當代視角回溯中國建黨百年來外語教育發展征程中的問題與成就,無異于溯本求源,以期求得新時期下外語教育高質量的創新發展之路以及共謀時代變局下高等外語教育鑄魂育人的新格局。
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外語教育:認知和實踐
對外語教育史的研究,學界歷來采用歷時研究模式,即將外語教育劃分為若干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例如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外語教育史》(1986)就以溯源的理路將中國的外語教育劃分為中國早期階段(1840年以前);中國近代階段(1840年至1919年);新中國建立前出國留學及外國人在華辦學階段(1870年至1949年)以及新中國的發展階段(1949年以后)。相較之下,《新中國外語教育史》(2009)則更加條分縷析地呈現了新中國成立后外語教育的六個關鍵時期及三次發展高潮。而《民族復興的強音——新中國外語教育70年》(2019)則在系統梳理、探究史實的同時,精心遴選了數十位新中國外語教育的親歷者、見證者、引領者和拔萃者的真實故事,以史為綱,以外語為旨回眸了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外語教育的發展歷程。客觀地說,這些史料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外語教育史的成長脈絡,
但另一方面,以共產黨建黨百年歷程為中心的考察卻相對被掩蓋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下,而當我們站在新時代起點,回顧中國共產黨走過的百年歷程,便會深刻感受到這是用鮮血、汗水、勇氣、智慧和力量寫就的百年。故此,筆者試圖厘清共產黨在建黨歷程對外語教育的認知和實踐,并據此認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外語教育實質上建構并凸顯出具有“中國主體性”話語體系的實踐意圖。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立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共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在1920年,同樣也是在上海,由俞秀松、李震瀛等創辦的外國語學社,則是我黨開辦的第一所外國語專門學校。彼時,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蘇聯成功的革命經驗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使我黨早期的革命先驅認為“走俄國人的路”乃是當時正確的歷史選擇。因此,外國語學社最初旨在培養一批懂俄語的黨員干部。但隨后,該學社也面向社會招生,并開辦了英、法、日等其他語種。然而,學社的開辦時間不足一年。更為遺憾的是,當時的相關教學內容和教學記錄也并未得到妥善保存。但是,外國語學社的確為我黨輸送了一批革命干部,正式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1]46。
其后在1922年10月,在原東南專科師范學校基礎上改組而成的上海大學則真正成了我黨誕生后的首個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許多知名的共產黨員都曾在上海大學任教,如李大釗主講歷史和社會主義;瞿秋白主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陳望道講授漢語語法和修辭學;惲代英主講心理學等。而在外語教學方面,上海大學所開設的德文、英文、俄文和日文也都由黨內外的著名專家學者擔任教學。如茅盾、周越然、王登云、朱湘等教師對民族復興和共產主義發展培養了大批重要人才,雖然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迫使上海大學終止教學,但其在我國外語教育史上劃下的濃墨重彩的一筆是極具開創性意義的。
而當整個中國進入抗戰歷史階段,我國主要的革命目標則出現了重大轉變:即由蘇聯社會主義及馬克思思想的傳播轉移到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對抗之中。因此在根據地,日語的簡單教學成了我黨了解敵方以及勸降日本士兵的主要方式。而在后期,隨著蘇聯與延安根據地建立了聯系,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新華社、陜北公學等機構的主導下,俄語教學重新回到外語教學視野之中。此后,1941年建立的延安大學以及延安外國語學校應運而生。可以看出,在歷史的至暗時刻,我黨在全力抗戰的同時,依舊沒有放棄外語教育事業,這充分顯示出我黨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砥礪前行的一貫風格。隨著日本人的投降,抗戰進入尾聲,人民解放區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除了人民群眾的俄語教學外,此階段的英語教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其中最為著名的事件就是1948年到1949年間在華北大學二部外文系基礎上創辦的北京外國語學校,也就是后來的北京外國語學院[1]54。
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國的外語教育以歷史背景為綱,中國共產黨正是在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的劇烈沖突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在各種革命環境的風云變幻中適時地調整著外語教育的對象和路徑的。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49年10月1日,隨著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的一聲歷史性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立于世界之林。
20世紀50年代的中蘇友好使得知識界再度掀起學習俄語的熱潮。因此從全國范圍來看,俄語成了當時外語學習的主流。例如,發布于1954年4月3日的《政務院關于全國俄文教學工作的指示》就明確表示要加強全國俄文教學工作,并旨在培養和提高俄文干部對于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知識和經驗的水平。這份文件除了對當時國內的俄語教學現狀進行了客觀有效的分析之外,還規定了各大教學單位(如高校)對俄語專業設置的具體要求、年限等。可以說,1949年到1956年是我國俄語教育高速發展的7年。在這7年間,畢業學生人數達到13000之多,基本上已經滿足當時國家的建設需求。“經過這7年的努力,在蘇聯專家的協助下,俄語教學工作走上正軌。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已經配套,形成了系統的教學體系。”[2]89
但也正是因為這樣,其他外語學科的教育發展在這一階段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擠壓和忽視。造成這種歷史現狀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還未和多數西方國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因而相對于俄語,其他外語如英語、德語并沒有很大的實際需求。但另一方面,由于“當時的教育部門尚缺乏全面和長遠的觀點,忽略了部署其他語種的必要性,這也不得不說是當時外語教育工作中的一種失誤”[1]71。值得慶幸的是,這種情況1956年得到了改善。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從當年起,高中英語課的教學得以全面擴大,高中英語教學大綱也于同年頒布。不僅如此,各大高等院校也開始逐步增設和恢復英語教學。截至1956年底,全國共有23所高校設有英語系科,英語專業學生達到2500余人。
實際上,作為共產黨人,毛主席在很早的時候就以戰略家和革命家的高度意識到英語作為一門國際通用語言的重要性。據史料記載,毛澤東在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就表達了自己對各種不同科學進行研究的迫切愿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國范圍內的俄語熱潮下,毛主席還是選擇了英語學習。從1954年10月開始,在新華社林克的教授下,毛主席學習英語并長達十二年之久。可見,毛主席對英語所展現出的學習熱情不僅是我國共產黨人對彼時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需要的一種深刻自覺,更是對國際革命形勢和國內外環境的一種審時度勢和高度敏感。
到了60年代,學習并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并進一步使其服務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求成了我黨在制定外語教育方針政策的主要目標。1964年10月,教育部同中央部門于在周恩來總理的有關指示下制定了《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綱要》不僅從新的歷史視野客觀地分析并總結了當時國內外語教育的缺憾和不足:“目前高等外語院系培養起來的學生,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遠不能滿足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事工作的需要”;同時又高屋建瓴地修正了之后外語教育的發展方向及行動方針:“這次《綱要》既需要大力改變學習俄語和其他外語人數的比例,又需要擴大外語教育的規模。這樣才能把外語教育的發展納入國家長遠需要相適應的軌道,由被動轉為主動。”[2]130
然而,后來1966-1976年的十年動亂不僅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給整個中國的文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尤其在外語教育方面,由于林彪、“四人幫”篡改黨的教育方針,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致使外語教育處于崩潰邊緣。在關鍵的歷史時刻,還是共產黨站了出來。他們撥亂反正,主導廣大師生與其進行斗爭。因此從1971年到1972年,根據中央指示,陸續有學校恢復了外語教學和招生。隨著1976年“四人幫”的粉碎以及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使命與加強英語外語教育形成了深厚的現實與理論的關聯。可以說,《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的出現,體現的是我黨在面對變動不居的歷史環境下以發展辯證的眼光看待分析問題的一貫思想作風;而對十年動亂的浩劫,我黨的撥亂反正則彰顯共產黨對問題不回避、不遮掩的歷史擔當與思想自信。
(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教育部從1978年連續五年在外語教育領域完成了五件具有相當重大意義的事件:1978年召開的全國外語教育座談會;1979年頒布的一批高等院校外語專業教學計劃的試行草案和教學大綱;1980年成立的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此機構旨在對外語教材和教學方面的指導和咨詢工作;1981年召開的全國高校外語師資培訓工作會議以及1982年的加強中學外語教育方針[2]180。毫不夸張地說,這一系列事件為我國外語教育走向新時代和新高度奠定了有力的現實支撐和理論基礎。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從1978年起,所有高考考生都可參加外語考試。而1980年11月在青島發布的《高等教學英語專業基礎階段英語課教學大綱》可以說是首次以條分縷析、事無巨細的方式將英語教學的相關細則呈現在公眾面前。仰賴于國內外語專家、學者的專業性建議以及經驗總結,這份大綱除了明確規定英語專業對新生入學的最低要求,到經過基礎訓練以及畢業時應達到的要求,再到教學內容、方法、原則以及考察方式外,還列舉了各個不同年級英語教學的要求以及安排。可以說,這樣一份文件的出現使得我國英語教育不再混同在其他語種泛化趨同的教學模式中,英語教育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應有關注。
次年5月,中美代表團在華盛頓簽署了“托福入華”協議。同年12月11日,即協議簽署7個月后,托福在中國的首次考試于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同時舉行。據統計,當年參加托福首考的中國考生共有615名,其中教育部公派考生453名、自費考生162名。隨著托福考試進入中國,國人漸漸打開了通往國際教育的大門。從此,中國教育考試開始引進、研究和應用一系列國際教育界的先進理念和手段,逐步推進了中國各項國家教育考試的現代化和標準化。
伴隨著改革開放浪潮的進一步深化,社會各界對外語,尤其是英語表現出更多更高的需求。針對這種情況,各大高校開始陸續開展以招收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層級、不同形式的外語教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生的外語教育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的。同時,為了加強研究生培養工作的規模和教學質量,從1986年起,國家教委還組織力量研究和制定了研究生的學科和專業目錄。而在1987年,國家正式開啟了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這一舉措更進一步強化了英語在全國范圍的普及。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不僅有效調動了師生對外語學習的積極性,還有力地推動了大學英語教學大綱的貫徹實施,促進了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水平的提高。不僅如此,由于其信度和效度的科學性,四、六級考試完全符合大規模標準化考試的質量要求,并能真實反映出我國大學生的英語水平。故此,這一全國范圍性的英語考試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盡管如前所述,近些年取消英語四、六級考試的呼聲不絕于耳,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是一項規模性的標準化考試,這種考試屬于尺度相關常模參照性考試,即以教學大綱為考試依據,是完全可以科學客觀地反映出考生總體的正態分布情況[3]。
而當英語教育邁入21世紀,伴隨著媒體的多元化和信息技術的豐富化,英語教育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加速發展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的語言實驗室到90年代的多媒體,21世紀的英語教育呈現出課堂人工授課和計算機教學輔助相結合的模式。對于外語人才的培養,也出現了觀念上的轉變,即從以往的單一性語言人才到復合型人才的轉化體現出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英語專業的新的時代需求。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2012年11月至今
從2012到2021的近10個年頭里,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被譽為“教育元年”的2013年,在我黨主導的教育方針下,教育部開始有意識地規范對高等學校本科人才培養質量工作。本著這一精神,高等學校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立即開展《大學英語教學指南》的制定工作。《指南》和以往的指導性文件的不同在于,它是從國家戰略需求層面強調英語的重要性,即通過英語教學,使學習者能夠直接學習和了解國外的文化進展,同時也幫助國人增強國家語言實力,傳播中華文化。同一年,英語教育在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階段的常態化發展,英語語言培訓也成了另一重要陣地。根據相關統計,獲得投資的在線英語教育企業數量約占教育行業總投資事件數的五分之一[4]。
而從宏觀方面來看,2017年8月,國家外語人才資源動態數據庫建成的重要意義在于從現代化數據了解國家各類外語人才的狀況和分布情況,并借此優化政府對外語人才資源的管理和有效使用,以改進和提升我國的國家語言能力。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思想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推進國際能力傳播建設,講好中國故事”的立場[5]。可見,外語教育在新的世紀正朝著數據化、宏觀化以及國際化的方向發展。
而當2019年末至2020年的新冠疫情給世界范圍帶來巨大沖擊的時刻,是黨中央果斷決策、統攬全局。在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的社會生活、生產秩序逐步恢復,經濟社會發展重上正軌。尤其是線上教育,為疫情之下的正常學習秩序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外語教學方面,慕課、微課、翻轉課堂、學習通、騰訊課堂等一系列數字化網絡教學平臺為廣大師生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提供了極大的便捷,也為我們打贏這場攻堅戰贏得了信心。新的時代,新的使命,這場疫情更讓世界見識了中國共產黨超凡和卓越的領導力,同時也讓我們清楚認清到,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不可動搖的。
四、結語:百年成就與時代挑戰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近百年來所建立的世界認知圖景,是在中國由過去的落后挨打到當今對世界事務的深度參與和發展需求中逐步形成的。而外語,尤其是英語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樣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依舊起到了語言交流以及文化交融的重要作用。回顧百年外語教育的成就,我們看到的是國運興衰對教育枯榮的深刻影響。在成就方面,不同歷史時期的外語學界優秀專家學者承前啟后、砥礪前行,從語言種類的專業化、人才培養的復合化、課程目標的素質化、教學內容的本土化、教學手段的互動化等幾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6]。
但另一方面,于中國而言,被動挨打的歷史曾一度造就了我們學習西方的急切心態和實用主義方法。從整體上看這也容易導致了兩種明顯弊端:其一是照搬西方模式,這容易演化出各種形態的“食洋不化”;其二則正好相反,即排斥西方文化的“本位主義”,而這則有損于中國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啟示性的深刻洞見。因此,伴隨著中國崛起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盛行,外語教育如何與中國的話語體系達成一致就成了首要問題。
首先必須承認,西方國家因其工業化勢能建構了龐大且復雜的世界話語體系如哲學史、宗教史、科學史等,并以語言為載體對其他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在重新認識世界的中國時代,學習了解西方文化仍然是中國知識界以及認知體系無法回避的一環。而外語教育,尤其是在將中西交融方面,如何凸顯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傳統文化以及思想體系既建基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人對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交融發展的深刻認識,也建基于國人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深刻自覺。其次,西方社會的認知模式在世界認知圖景中曾占據著優勢,但我們也應當看到,隨著近年來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嬗變,當代西方社會也必然浮現出新探索和新思潮:如歐洲各種形式的政治立場及探索;西方傳統宗教的衰微及世俗化引發的精神危機。所有這些新興出現的問題,既是中國“主體性”對西方認知危機的一種折射,也是外語教育在面對認知困境時所要解決的主要內容。再次,我國的未來發展必將更深入地嵌入世界秩序的體系之中,“一帶一路”倡議已經開啟了中國與世界相關聯的序幕。因此,以外語教育與中國文化的互動性建立起知識與話語體系顯得更加緊迫。而如何在外語教育中凸顯“中國主體性”既是對中國人完整世界觀的建構,也是人類文明新的可能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