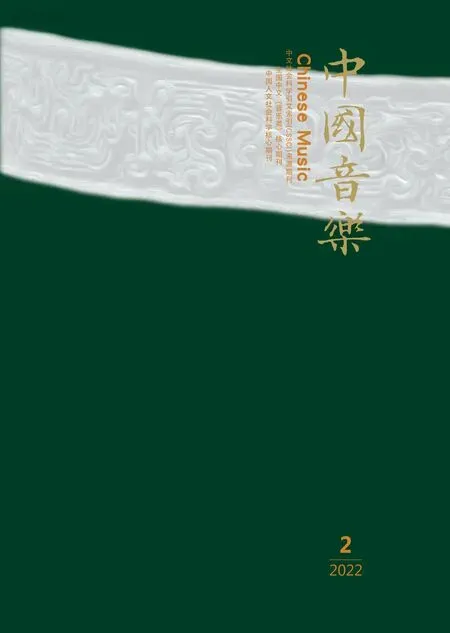死音活曲
——河北撫寧鼓吹樂單家班儀式行為解讀
○ 臧 穎
這是開篇的第一個故事,也是某種意義上最后一個故事。
農歷臘月廿九,對于河北省秦皇島市撫寧區留守營鎮的鄉民們來說,是猶如為新春這道“錦”上又添“花”的一天。作為地道的秦皇島人,生于斯長于斯的我,在2017年這一天,領略了一場濃縮了家鄉風土人情的盛會。
清晨,一聲嗩吶劃破寂靜,喚醒沉睡的村莊,傳承人單洪彬帶著單家班為即將到來的吹吹打打做準備,同時,一輛載著昌黎縣秧歌隊的大巴車開到大隊部門前與眾人匯合。與過去二十多年一樣,操持這一切的,是住在村北街的一位老執賓,在老先生的協調下,每年的迎春儀式都如期舉行。儀式開始,單家班在大隊部門前與秧歌隊你來我往,交相輝映,鄉民們提前約好一般,搓著雙手,呵著白氣,一大早就圍聚在一起,欣享著企盼了一年的歡慶時刻。嗩吶聲聲如旺盛的火苗,映紅了大隊部,還將遍染整個村莊。儀式進行至高潮,單家班帶著秧歌隊走街串巷,詢家問戶,吹吹打打,好不熱鬧!
每當提及撫寧鼓吹樂,這幅迎春畫卷便浮現眼前,聲聲嗩吶便縈繞我心,當我次年想繼續參加迎春儀式時,單洪彬遺憾地告訴我,操持儀式的老執賓不久前已經過世,沒有老先生忙前跑后,便沒有了往年的儀式,就算今后再有,意義也是不同的。
“死音活曲”予以民族音樂文化極為恰當的詮釋,在老先生身上,也可以讀出另一層含義。先生的葬禮是單家班吹的,他生前操持、掛念著的那些鮮活的曲調,在他身后亦為他而鳴,坐落于葬禮中的樂曲,是單洪彬把控下對音樂的活態傳承。雖然老先生已然辭世,但是鼓吹樂的血脈卻在單家班得以延續,音樂的傳遞,亦是生命的傳遞。由于我無意間參加的儀式遺憾成為最后一次,所以我希望忠實地記錄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撫寧鼓吹樂。這是由一個故事引發的研究,研究中又貫穿了一場場儀式,正是這樣一個個故事,一場場儀式,實現了撫寧鼓吹樂的傳與承。
一、儀式場域中的人
“人類學把儀式分為‘生命禮儀’(rites of passage)和‘強化禮儀’(rites of intensification)”①張振濤:《冀中鄉村禮俗中的鼓吹樂社—音樂會》,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61頁。,對于歲時節日具有聚合功能的強化禮儀來說,屬于生命禮儀的喪葬儀式為本節論述的重點。無論哪種儀式,最終目的都是服務于“人”,而“人”也是儀式場域中的行為主體,觀照“人”的行為方式,是剖析儀式音聲運行軌跡最直接的途徑。
葬禮是民間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人們共同的價值取向,在儒家尊祖敬宗思想的影響下,其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儀式。葬禮的舉行代表著一個家庭進入特殊時段,在儀式的時空坐落中,不同身份的人具有不同的行為方式,所有行為皆以音聲為指令,分析人與樂的互動關系,便能理解音樂在喪葬禮俗中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
田野調查期間,會明顯感受到,同是作為通過儀式的葬禮,其外在呈現并非完全一致,是何原因導致在儀程有所差異的情況下依舊保持儀式的相對穩定性?這些表象下是否蘊含著儀式運行的內在規律?為此,本文選取了兩場具有明顯差異的葬禮進行描述與分析。
(一)崔李莊村喪葬儀式
這場葬禮同時請了單家班和小朱嗩吶藝術團,按照習俗在第二天下午開始吹奏。下午4點,我與單家班一行人到達東家,門前是一條窄窄的村路,門口已經支好一張圓桌,放置嗩吶等器具。樂聲吸引了不少村民,由于東家沒有選定樂曲,所以樂手自行吹奏,既有烘托葬禮氣氛的傳統曲牌,也有吸引鄉民的流行歌曲。
5點20分,東家在門前支起幾張桌子張羅晚飯。正值夏季,晚飯后的吹奏直到10點才停止。
次日〔出靈〕,我們一行人于早晨6點到達東家,小朱嗩吶藝術團的人已經到達,東家在張羅早飯,此時還沒有其他村民。單洪彬與徒弟董相一以一首《北調子》開始吹奏,這首曲子原叫《悲調子》,長達15分鐘,是單洪彬的啟蒙老師程萬林從盧龍傳到撫寧的,顧名思義,曲目烘托了葬禮悲傷的氣氛。
7點20分,小朱嗩吶藝術團的人撤走座椅,拿出話筒,連接電子琴和音響,一切都預示著之前哀傷的氛圍將被沖淡。一首吹唱相間的《大出旗》拉開了葬禮熱火朝天的序幕,繼而,《真的好想你》《想念爸爸》《父親》等一首首鄉間傳唱頗廣的曲目將氣氛推向高潮,單洪彬的兒子單奇偉由于太過投入而大汗淋漓,索性脫掉上衣,在演奏《擁抱你離去》時,氣氛最為高漲。
8點46分,一直沒有間斷的嗩吶聲終于停歇,小朱嗩吶藝術團的楊闖拿出薩克斯吹奏《愛你在心口難開》。由于當天有陣雨,東家擔心影響〔出靈〕,所以楊闖吹奏結束后,準備其他事宜。
9點,舉行〔上香〕儀式,單家班兩位成員進入院內吹【小開門】,9點15分入殮,不奏樂。
9點35分,在墳地舉行〔燒車〕儀式,前往墳地走街時吹奏《梁祝》《花池》《八板》。
10點〔出靈〕,抬棺時所有嗩吶吹長音,當地稱之為筒音超吹。到達墳地〔下葬〕時吹【四六句】。
在這場現代氣息頗濃的葬禮中,雖然有單家班和小朱嗩吶藝術團共同參與,但兩者風格不同,性質不同,“對棚”意味并不明顯,往往是你方唱罷我登場。
(二)丁義莊村喪葬儀式
由于東家與單洪彬熟識,所以這場葬禮沒有中間人,按東家要求,只在〔出靈〕當天吹奏。早晨5點40分從班社出發,驅車15分鐘到達東家,一下車,東家便向單洪彬遞煙并親切握手,希望將葬禮吹得熱鬧一些。
東家同樣沒有選定曲目,樂手們吹了【冬來】【比正宮】【趕舟】【柳青娘】等傳統曲牌,每首時長15到20分鐘,八個樂手四人一輪換。值得一提的是,這場以莊重嚴肅為基調的葬禮中,突然一首悲切與歡脫交相呼應的樂曲敲擊著我的耳膜,詢問后得知曲牌名為【滿堂紅】,那一白一紅、一悲一喜的強烈反差沖擊著我的心靈,也在心底埋下一絲疑問。
8點30分〔出靈〕,火葬后骨灰盒放置于東家院內,準備〔出靈〕時所有樂手圍在東家門前,骨灰盒被抬起的瞬間,八桿嗩吶筒音超吹,原本安靜的空間充斥著驚天動地的哀鳴,悲傷氛圍到達頂點。
走街開始,東家抬一張桌子于隊伍最前方,其上擺有白酒、杯子、貢品和香爐,用于〔下葬〕前的〔上香〕儀式,其后跟著樂手們,東家抬著骨灰盒走在隊伍最后。為了表達對逝去長輩的尊敬,東家所有人倒退著走,樂手們在行進途中也頻頻回望,以示對逝者的不舍。
看似東家出殯,實則由樂手掌握進程,在路口或者街道拐角處,樂手們會停止行進,聚成一圈吹奏,在近40分鐘的走街中,隊伍暫停四次,最后一次停在墳地附近舉行〔上香〕儀式,吹固定曲牌【小開門】。
通過對兩場葬俗的描述,可以發現其間具有一定差異。對于作為“過渡禮儀”的葬禮,如果用維克多·W.特納(Victor W.Turner)提出的閾限理論②〔英〕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4-98頁。來解釋,或許會有一個更為清晰的把控。(見表1)

表1 儀式過程對比
(三)行為主體分析
根據葬禮實錄可以看出,儀式參與者有東家、傳承人單洪彬、單家班及非班社成員。現對儀式場域中的人由核心到外圍逐一剝離,分析其行為方式及起到的作用。
1.東家
東家是儀式的發起人和主要參與者,既指逝者所屬家庭,也指家庭中的個體。
筆者從單洪彬處了解到,與舊時葬俗不同的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東家對音樂的要求并不嚴格,只圖熱鬧風光,對于不甚了解音樂的鄉民來說,熱鬧風光就代表著聲音大,聲音大就意味著用力吹,正如我記錄葬禮時遇到的情形,東家握住單洪彬的手,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使勁吹。
2.傳承人
在葬禮中,鼓吹手必不可少,但傳承人并不是經常遇到,只要單洪彬出現,必定是儀式音聲的核心。
畜牧業的發展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著基礎保障,所以相關部門應加強對其重視度。同時基層動物防疫監管部門是實行畜牧業管理的重要環節,所以其工作的實踐與創新是十分重要的,應加強對監管意識、機制及隊伍等方面進行加強,使基層動物防疫監管工作的實踐與創新得到保障。
單洪彬在儀式中時常閉起眼睛吹奏,他用音樂去表達,用嗩吶去言說,大多數人用耳朵感受音樂,單洪彬則是用心。一次葬禮結束后,無意間聽到東家由衷夸贊單洪彬,這贊賞不僅是對技藝的肯定,更是對單洪彬儀式解讀的認同。
傳承人一直起到引領眾人的作用,儀式中不用語言交流,所以單洪彬扮演的角色顯得尤為重要,一曲吹罷,下一曲吹什么,走街中何時停止何時行進,班社成員參照的都是他的行為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當音樂作為儀式的內在推動力,傳承人無疑是儀式的主導,由音聲核心轉化為儀式某一環節的核心。
3.班社成員
民間樂器的特點注定了合奏才更能體現其特色。在喪葬儀式中,單家班的樂手以單洪彬為核心,曲目的變換往往依靠成員間的默契,這是單洪彬采取此種方式教授徒弟的效果,也是單家班活躍于鄉土間,頻繁參與葬禮的結果。
通過儀式可以發現,成員們起到的作用是逐漸增強的。閾限前,單洪彬帶領單家班一同吹奏,在閾限期〔上香〕或〔下葬〕這些關鍵節點,他們觀察著進程,到了固定環節不需提醒,便由兩名成員自行齊奏,一切看起來水到渠成,但得益于單洪彬對成員們日積月累的培養。
閾限期是班社成員展示技巧、體驗儀式的最好機會,每一個集中演奏的時段都是儀式氛圍的高峰,他們用聲音代表東家宣泄哀思,用曲調抒發對儀式的理解,單家班每一位樂手用音聲之凝聚體現了儀式的精神內核。
4.非班社成員
在儀式音樂的考察中,往往容易忽略前來憑吊的親友、被樂聲吸引的村民和殯儀人員。
親友們在樂聲的環繞下到達東家,音聲營造的氛圍影響著他們的情緒,悲傷的情感又烘托著葬禮的氣氛,被樂聲吸引的村民更是將東家置于人們關注的焦點,突出了東家和樂手的地位。
殯儀人員是與音樂相關的比較特殊的一個群體,除了安排葬禮的一應用品之外,其特殊之處在于有樂手加入儀式,這些既會吹奏又熟知殯葬事宜的人們在葬禮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雙重角色。
(四)儀式分析
本文選取的兩場葬禮雖有差異,但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儀式中主體的行為方式及音聲運行的內在規律。
其一,樂手構成不同。崔李莊村的樂手來自單家班和小朱嗩吶藝術團,丁義莊村的樂手全部來自單家班。當單家班和小朱嗩吶藝術團同處于葬禮時,雖沒有“對臺”的場景出現,但兩者你來我往,音樂風格不斷變換,為東家掙足了臉面;丁義莊村葬禮只聯系了單洪彬,單家班成員也是輪番上陣,可見無論儀式只請了單家班還是與其他團體并行,樂手們都會使出渾身解數,以求更好地服務于東家。
其二,儀式氛圍不同。樂手身份的差別造成了儀式氛圍的鮮明對比,崔李莊村的喪儀中,單家班雖然也吹流行歌曲,但比起小朱嗩吶藝術團的電子琴和薩克斯等現代樂器,其代表的依舊是傳統的一面,隨著村民越來越多,流行歌曲和現代樂器反而沖淡了葬禮悲傷的氛圍,使鄉民們可以一同熱鬧一下;丁義莊村的葬禮中,單家班吹的全部是傳統曲牌,音樂風格與崔李莊村一新一舊,截然不同。解讀音樂在儀式中的作用可以發現,樂手們總是習慣用傳統曲目烘托哀傷氣氛,通過音聲宣告葬禮的開始,待聚集的人多了,便會轉換相對歡脫喜慶的樂曲以娛鄉民,即便吹奏的全部是傳統曲牌,樂手們也會選擇相對歡快的秧歌曲。
其三,儀式過程不同。在喪葬儀式中,預示著〔出靈〕的筒音超吹代表著儀式由“喪”進入“葬”,也昭示著閾限期的開始。崔李莊村的葬禮中,〔上香〕儀式是〔出靈〕前在院內舉行的;丁義莊村的〔上香〕儀式是〔出靈〕后在墳地附近舉行,這就表示兩場儀式在閾限期是不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抬棺時的筒音超吹、〔上香〕時吹的【小開門】、〔下葬〕時吹的【四六句】,都是儀式環節的固定曲目。走街時,樂手們在隊伍最前方,哪里行走,哪里駐足演奏,都會選擇合適的位置,以樂聲為東家漲聲勢,當東家伴著音聲抒發了對逝者的不舍之情,待圍觀眾人稍感乏味之時,樂手們便很有眼色地繼續走街,到下一個人流稍多的街口再停駐。
兩場葬禮閾限期及前后的不同表現,根本原因是鄉土社會賦予了儀式和音聲相對的靈活性,這并不妨礙喪葬儀式尊祖敬宗核心內涵的表達,而閾限后是否返回東家,也以樂手是否方便返程為前提,在儀式中,鼓吹手不只是樂人,更是表達者。
通過兩場看似存在差異的葬禮可以發現,無論樂手構成、儀式氛圍或是儀式過程有何不同,音樂在儀式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始終是一致的,都是服務于東家,服務于儀式甚至在某些時候主導儀式進程。
二、儀式場域中的樂
對儀式用樂的考察中,我疑惑于本該莊嚴肅穆的葬禮為何會用到【滿堂紅】這樣喜慶的曲牌,帶著這個問題,我記錄了單家班對于秧歌曲倍調【滿堂紅】的教習情況并結合儀式進行分析。
在第一天唱譜的過程中,每一遍附點節奏和個別音都有稍許變化,單洪彬在講吹奏技巧的時候也說,曲子是變化多端的。為求客觀性,我的記譜以單洪彬第一次示范為標準。
“滿堂紅”一詞出自《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③〔明〕洪楩:《清平山堂話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8年,第45頁。和清代《通俗編·器用》④〔清〕翟灝:《通俗編》下,陳志明編校,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496頁。,冠為燈名,有全面勝利和到處興旺之意,遼西、甘肅等地均有相同曲牌的嗩吶曲,但對于曲牌【滿堂紅】的由來,文獻中并沒有詳細記載。【滿堂紅】常用于葬禮,可見對此曲的學習是服務于儀式不可跨越的過程。
用單洪彬的話說,【滿堂紅】分為“四個身子一個尾巴”,在樂曲中,“四個身子”之前還有一個樂句。根據劉正維老師《中國民族音樂形態學》中關于傳統音樂結構特征的論述⑤劉正維:《中國民族音樂形態學》,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15頁。可以得出,“四個身子一個尾巴”是指第一樂句后加入了四個長大插句,“四個身子”就是四個插句,“一個尾巴”指進入快板的第二樂段,全曲由主句加四個插句組成的第一樂段和快板的第二樂段構成,共140個小節,1至10小節為主句,11至72小節為四個插句,73至140小節為第二樂段。
主句由弱起小節開始,結束至第10小節板拍,速度由慢板過渡為中板,樂句猶如緩緩的訴說,渲染出悲傷的氛圍。為避免有僵硬之感,第3小節和第5小節的長倚音要偏高不到半音,具體音高的掌握要靠氣息把控,第6小節板拍的顫音要注意對嘴唇的控制。(見譜例1)
譜例1 【滿堂紅】(倍調)節選;單洪彬演奏;臧穎記譜

第一插句從第10小節眼拍至第38小節板拍。第16小節板拍用到了撫寧鼓吹樂特有的“嘟嚕”技巧,這種技巧常用于音程關系較遠的大跳中,上滑音與花舌相結合使音色更加清透嘹亮,音符刺破長空,凸顯喪禮的悲切氛圍更加濃重。第18和19小節的7音要吹奏出婉轉的感覺,如泣如訴,傳達出東家對親人離去的悲痛之情。(見譜例2)
譜例2 【滿堂紅】(倍調)節選;單洪彬演奏;臧穎記譜

第30、31小節與第32、33小節重復,一來一去間,頗有秧歌逗趣的意味,稍稍沖淡了之前的哀傷,令東家的情緒予以緩和。在由高到低跨度較大的音程中,吹奏要圓滑,仿佛后一個音從前一個音直接滑落下來,音符的顆粒性使樂曲更加靈動。(見譜例3)
譜例3 【滿堂紅】(倍調)節選;單洪彬演奏;臧穎記譜

由于倍調【滿堂紅】四個插句只有后半句各不相同,因此不再重復列出前半句譜例,只舉例后三個插句不同的部分。(見譜例4)
譜例4 【滿堂紅】(倍調)節選;單洪彬演奏;臧穎記譜

第四插句的后半句由主句發展變化而來,樂曲悲傷的基調再次凸顯,這一句結束后,直接進入由“減字”手法而來的第二樂段,氣氛變得較為歡快,手指的靈敏度和唇齒舌喉的配合更為重要。(見譜例5)
譜例5 【滿堂紅】(倍調)節選;單洪彬演奏;臧穎記譜

樂曲最后這段“尾巴”速度極快,由于倍調【滿堂紅】是一首秧歌曲,需要配合舞步,當秧歌越扭越歡快時,樂人們只吹主干音,中間不加花,以求速度越來越快,這種手法稱之為“減字”,所謂“減字”,實質上是樂曲的節拍寬放,旋律節奏緊縮。
教學中,單洪彬經常強調下滑音的把握及樂句間的連貫性,技巧的使用是為了更好地詮釋音樂蘊含的情感,加之嗩吶曲的歌唱性,使葬禮中的悲悲切切,得以聲聲入耳,亦使娛樂賓客的歡歡鬧鬧,能夠句句傾心。【滿堂紅】作為秧歌曲,一方面,年歲節慶時與秧歌隊一道,紅紅火火,吹打唱跳;另一方面,明艷熱鬧的曲牌名及曲風使其坐落于喜喪中并不顯突兀。第一樂段的悲切之情與第二樂段的歡脫之感對比強烈,相映成趣,明暗交加,悲喜一堂,足以使人領略到喪葬儀式音樂中深厚的文化意蘊。
三、儀式音樂內涵探析
(一)死音活曲:一個名稱 兩種含義
“‘死音活曲’代表了中國傳統音樂中‘為人奏樂’部分的人文精神”⑥項陽:《傳統的回歸與“舊調重彈”》,《人民音樂》,2003年,第8期,第25頁。,記錄葬禮用樂更加說明了這一點。與單洪彬交談中,每當問及音樂本體時,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模糊的,“都可以”“都行”“也對”經常貫穿于我們的對話。
隨著田野調查的不斷深入可以體會,這種模棱兩可的答案對解釋本體是恰到好處的。就樂器方面來說,葬禮中使用的二喇叭不定調,音高由簧片大小決定,所有嗩吶要根據頭喇叭的音高進行調整;從樂隊方面而言,也是較為靈活的,過去葬禮中只有兩桿嗩吶,當下若雙親都已過世樂手為雙數,一位在世樂手為單數,此外沒有其他要求,由于樂手們一專多能,所以葬禮中經常出現同一樂手演奏不同樂器的情況。
最能體現“死音活曲”的要數樂曲部分,一個“變”字最能體現其深意,雖然目前收錄的樂曲共224首,但這些曲目不代表有這么多曲牌,單洪彬告訴我,很多同名曲牌都是由老母曲通過“減字”和“加手法子”等方法發展出不同調門而來的。
單洪彬教授倍調【滿堂紅】時,讓徒弟們記錄的雖是簡譜,但在學習中,為了突出曲調的韻味,會在需要注意的音上強調偏高或偏低一些,在示范時還會隨機在某些小節中臨時加入幾個音以增添色彩,用他的話說就是,“每一遍都不一樣”。
曲目靈活的方面不只是“變”,還有“遍”。在記錄的倍調【滿堂紅】中,單洪彬傳授的第二樂段是根據第一樂段的四個插句進行兩遍“減字”而來,當我進而求證記錄與分析的曲譜正確與否時,他又為我演奏了三遍“減字”手法的“尾巴”。不管是秧歌曲、漢吹曲還是大牌子曲,每一類曲子都會進行不同程度的反復,這些反復是通過“遍”而達到曲調上的變化。以上便是“死音活曲”包含的第一層含義。
田野調查的兩年間,單洪彬沒有吹奏過任何一場婚禮,所參與的儀式都是葬俗,秋冬兩季經常會一天內到兩個東家出活,可見,鼓吹樂存活的土壤皆是白事。日常接觸中發現,單家班對白事沒有任何避諱,平日里習得的樂曲,在葬禮中更能加深記憶,單家班日日面對葬禮,面對死亡,除了日常教學,徒弟們習得的技能都是在葬禮中得以加強,出徒后也將一直參與喪葬禮俗,鼓吹樂因其不斷面對死亡,而得以在這片土地上生機勃勃地存活下去。
對于音樂本身而言,與所處的文化語境是共生共存的,土地滋養著音樂,音樂回饋于土地。在后期田野調查的階段,我時常憶起操持迎春儀式的老執賓,他雖然已經辭世,但這個村莊鮮活的文化血液得以保持溫度,也是他生命的延續。人好似曲,曲亦如人,當嗩吶聲每每在葬禮中鳴響,內心的萬般情懷總會被這份“向死而活”的文化意蘊所觸動。
(二)“縮影”與“全貌”:從音樂出發對儀式產生的思考
社會學研究領域中,對單一社區的考察分析能否代表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焦點,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臺三村五論》一書中,對閩臺三村的考察與反思亦對本文的落腳點予以極大啟發。王銘銘老師認為,雖然社區不是中國社會的“縮影”,但對閩南山區美法村的調查有益于窺視中國整個社會⑦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臺三村五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97-98頁。。從此視角出發,我開始思考我所考察的葬禮用樂能否窺見中國喪葬儀式音樂及其文化內涵。
以往研究可以總結出,葬禮是一個家庭由安定進入特殊狀態又回歸平靜的轉折點,當親人離世,這個家庭無疑會陷入巨大悲傷從而進入一個特殊的、不平衡的反結構狀態,葬禮的順利進行代表著每個家庭的訴求與企盼。
喪葬儀式中,音樂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始終是維持儀式環節有序推進的關鍵。吊唁的親友們在或歡脫或悲戚的樂聲中對東家報以關懷,致以問候,接踵而至的人們和遠擴的音聲使東家暫時成為村民們關注的中心,樂聲提醒人們需要給予這個家庭比平日更多的溫情與善意。音樂不只是通過其本身的色彩為東家淡化悲傷,還通過外延作用平衡了東家因親人離世而導致的特殊狀態。
在調查中可以發現,人們吊唁時遞出禮金或其他互利互惠的行為都受到音樂的影響,在社區個體的記憶里,葬禮中的行為與音聲是相伴而行的,這種意識會伴隨著社區生活的經驗保持下去,可以說,音樂強化了葬俗中人們固定的行為模式,這一作用在具體儀程中更為凸顯。
閾限前,樂手們皆在東家門外吹奏,作為東家非語言形式的代言人,音聲以獨特的方式傳遞東家舉行葬禮的訊息,長期出活的經驗賦予樂手們靈活的行為方式,多根據儀式現場環境及情緒選定樂曲。葬禮中濃厚的尊祖敬宗意味決定著這終究是一個嚴肅場合,為了突出莊重的色彩,樂手們通常會吹奏一兩首悲切傷感的傳統曲牌,用音聲為東家表達哀思。傳統曲牌因為多慢板、多反復,所以用時較長,為了平衡氛圍,也為了吸引更多鄉親鄰里以突出東家的地位,樂手們會選擇一些歡脫的曲目或流行歌曲,一些年輕的樂手甚至會用演唱的方式沖淡悲傷的氣氛,以達到娛人的作用。
至于樂手們為何會想盡辦法為東家爭取臉面,在考察的儀式中或許可以得到答案。兩場葬禮雖同在撫寧區,但行為主體、儀式氛圍及過程皆有不同,就算鄰近的兩個村莊,儀式也會存在差別。面對閾限期的交融狀態,樂手們始終應變自如,大量實踐告訴他們遇見不同場合該如何應對,但這并不足以解釋樂手們為何會對葬禮如此重視,歸根結底,原因在樂手與東家的關系上。葬禮中,東家與單家班親近的行為很容易使人們忽略二者間的本質關系—雇傭關系。調查中了解到,樂手們對于鼓吹樂極其熱愛,在葬禮中吹嗩吶不僅從事了自己喜愛的行業,而且也保全了飯碗,這就不難理解樂手們為何會在葬禮中如此賣力。此外,單洪彬告訴我,撫寧境內鼓吹手四百多人,雖然農村地區葬禮較多,也基本不會出現兩個樂班打對臺的情況,但是葬禮辦得風不風光、熱不熱鬧,都會成為村民們茶余飯后的閑談,而最能體現風光與熱鬧的,當屬儀式中嗩吶發出的音聲了。葬禮是每個家庭不可避免的儀式,一個樂班把葬禮吹得好,村民們自然會口耳相傳,反之,在樂手如此眾多的地區,班社必定會逐漸淘汰,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秋冬兩季單洪彬會如此忙碌。除我的田野調查外,許多儀式音樂研究也可以總結出如此結論。
如果說閾限前樂手們的活動范圍僅在東家,那么閾限期便是以東家為原點輻射至整個村莊。鄉村地區老年人居多,過世的老人通常身患疾病,所以東家對長輩的離世已有心理準備,葬禮中情緒并沒有太大起伏,但日常奔波忙碌的生活中,親人的離世也會造成東家的措手不及,葬禮一應安排已經令人手足無措,所以偶爾抱頭痛哭的僅是女性或至親。作為葬禮嚴肅氛圍最濃的一天,樂手們便用手中的嗩吶代替東家表達不舍與哀思。
蕭梅老師認為,在閾限當中,音聲的作用是整理“路”,使“路”能夠走下去⑧此觀點為蕭梅老師在“儀式音樂—信仰存在的一種方式”線上講座中提出,2020年9月4日。。換一種說法,閾限的交融狀態是為了使反結構順利進行到結構。〔出靈〕當天,筒音超吹的悲切伴隨親人們的哭聲拉開了走街的序幕,葬禮的哀傷氛圍至此達到頂點,樂手們走在最前方引領東家送葬的隊伍,一路上吹吹打打,走走停停,不僅是為了讓逝者風風光光地走完這一程,也是向整個村落中的人們告知葬禮已進入最后階段,平日里不好意思說出的話語,日常生活中偶爾產生的摩擦,都可以抓住最后的時機,跟隨東家和村民們的送葬隊伍得以化解。
走街過程中,隊伍經過村中主要街道到達墳地,除了東家及為逝者送最后一程的社區鄉民們,其他村民如何知道東家的送葬隊伍經過了呢?靠的自然是樂聲,聲音穿透房屋,穿越阻隔,傳到每一位鄉民耳中,聲音不僅傳遞東家〔出靈〕的訊息,而且起到了劃分邊境的象征性作用,使人們得知〔出靈〕的是自己村落中的一分子,從而也起到了凝聚鄉鄰的作用。在以往對喪葬儀式乃至祭祖儀式的研究中,也有樂手們引領隊伍環村走街的情況,可見音聲在儀式當中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
在調查儀式用樂時,不可避免地會將音樂與當地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文化聯系起來,往往容易忽略鼓吹樂作為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樂種,雖然分散在全國各地,但蘊含著相同的精神內核,葬禮中多用鼓吹樂的情況也可以體現這一點。雖然同一地區的儀式存在差異,全國的葬禮根據當地的發展與變化,所用曲目和儀式過程也各有不同,但對單一地區儀式音樂的深入考察,可以洞悉喪葬禮俗中音樂起到的作用及普遍規律。
結 語
文化的歷久彌新關鍵在于能夠找到適合生存發展的土壤。在一望無際的冀東平原上,撫寧鼓吹樂扎根于葬禮,孕育了一批技藝高超的樂人,將目光聚焦于這些個體的行為方式,通過人類學的視角觀照其在葬禮中扮演的角色,或許能夠找到解讀其意義的有效途徑。
調研中能夠體會,單洪彬面臨著與其他傳承人相似的困境,“現代”語境的沖擊令其對傳承與發展充滿擔憂,但鄉土的長期滋養并沒有令傳統賦予的特色完全消失,記譜時田野與文本不能完全契合,這種不對稱性體現了“死音活曲”的一個方面;在直面死亡的葬禮中,鼓吹樂根植于土壤的頑強生命力又體現了“死音活曲”的另一方面。是音樂賦予單洪彬對土地不同的解讀,單家班扎根于喪葬禮俗,猶如一個“縮影”,將其作為個案深入研究,便可以投射出喪葬儀式音樂的“全貌”。
如果說“死音活曲”代表了傳統音樂的特性,那么“和而不同”便恰如其分地詮釋了“縮影”與“全貌”的含義。應當承認每一個“縮影”都是獨一無二的,同樣,在“縮影”與“全貌”的交互關系中,可以洞悉出個性中存在的共性。將思維發散,宏觀地思考音樂在儀式中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作用,便會鋪開一幅儀式音樂的宏偉畫卷,每一筆精描細摹都是傳統音樂的具體呈現。在寫作即將結束時,我感到橋墩下的嗩吶聲逐漸遠去,但我知道,它始終不曾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