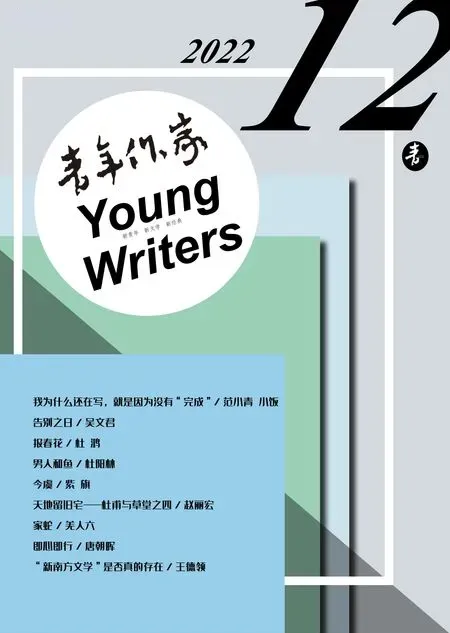評論者說無以冰炭置我腸
——紫旗小說印象
李穎
紫旗的短篇小說《今虞》和《小園》寫了兩個孩子的生活,同時也是以孩子的眼去看父輩的故事。名為向小園和向今虞的兩個人,命運互相關聯,內外交織。《今虞》寫母親,《小園》則寫父親,《小園》可以看作是《今虞》的前篇。這兩篇既是孩子和父母、也是孩子和孩子之間的隔空對話。
兩個故事都不是發生在一個溫暖的家庭,字里行間充斥著孩子的不安、憂懼和恐慌。《小園》講述了向小園幼年的故事。父親的暴力、母親的忽視、群體的冷漠間接造成了弟弟的死亡,向小園對此念念不忘,弟弟之死也成了她再未解開的心結。向小園是在不安中長大的女孩,作為長女,她時時刻刻遭受著父母的暴力和冷漠帶來的精神上的壓力和恐懼。這種創傷影響到了之后向小園的成長。長大成人的向小園會無意識地壓抑自己的情緒,并將這份傷害延續下去,在數十年后再一次施加給自己的女兒。《今虞》寫的是向今虞幼年的成長故事,也是作為母親的向小園的故事,抱著近乎執念的“女孩一定要比男孩更強”想法,嚴苛地要求女兒向今虞。我們不難發現,在未被講述的故事留白處,向小園幼年的創傷并未在她后來的成長過程中得到治愈,可以說,她童年時代遭遇的不幸和她此后在婚姻里遭遇的不幸都是緊密相連的。弟弟之死勾連起了兩個故事,向小園一直堅信是自己的過錯,才沒能讓自己的父母滿意。向小園父輩造成的這份傷害跨過時間和空間,延續到了下一代的向今虞身上,向今虞在成長過程中更是充滿了惶惑和創痛。
然而這兩個故事不是單純的關于原生家庭創傷的書寫,而是對兩代人關系的一種思考,是受過傷害的兩代人之間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可以說,紫旗的寫作不是純粹的傷痛性寫作,她的寫作真實而飽有力量,質感粗糲又帶有溫度。她的寫作也是一次尋本溯源,是根植于現實和生命的寫作:在面對真實的生活時,生活在中國式家庭里的孩子到底是如何形成自我,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到底承受著怎樣的痛苦。
從《今虞》的寫作可以看出來,紫旗非常擅長氛圍的塑造。她使用了許多精準的比喻來塑造環境的壓抑,尤其對孩子的情緒,處處書寫得惟妙惟肖。幼年在心理上寄人籬下的小孩子,早早地開始面對成人世界,而孩子心中的秘密是最為沉重的,生活細節在孩子心中不斷被放大,留下陰影。比如說她寫母親說話的樣子,小孩子在面對不可撼動的權威時戰戰兢兢的形象一下就躍然而出:“她憤怒時,眉頭聚成層疊的山巒,窗外吹進的熱風不能把它拂平,我更不能。屋里的光線很暗,我必須更加仔細地分辨母親的表情,才能揣摩她是什么樣的心情。”“每次母親升高了語調說話,我都感覺像是銅爐里燒開了水,再多一秒就要迸裂。”母親對孩子嚴苛的鎮壓,則通過刻畫孩子的動作來體現。向今虞的靜默是一種無聲的反抗。她經常處于一種失語狀態。從小在和母親共同居住的生活里,她一直在學習說什么話才能讓母親好過一些,她嘗試理解母親的痛苦,無法拒絕母親的請求,于是迫使自己習慣性地壓抑自我需求。雖然今虞和母親血脈相連,但母親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今虞的頭頂揮之不去,令她時刻活在膽戰心驚的環境中,哪怕是在景色描寫中,都能使人感受到無處不在的母親和隱隱的威脅——“我好像總讓母親生氣。”母親也不是一個單薄的角色,她有著復雜的精神世界,在無堅不摧的強硬下,隱藏的是她與生活的對抗。貧窮是母親的枷鎖,她必須以兇悍和堅強才能為自己和女兒撐起一個家。正因如此,她無暇顧及女兒的心情,只能一次次逼迫女兒去向她的父親要錢,以此維系搖搖欲墜的生活。法庭一場,更是顯示出母女二人各自的重負。文中的父親則是一個懦弱的形象,吝嗇刻薄,還經常逃避為人父的責任,在這場失敗的婚姻中,他以受害者自居,卻在面對女兒時,試圖顯露自己早已不復存在的威嚴。母親和女兒只有表面上的對話,很少有實質性的深入內心的對話。明明二人是最親密的家人,同住一個屋檐下,彼此卻顯得十足陌生,唯一一次向今虞得以窺見母親的脆弱,是母親給尚未長大成人就早早夭折的弟弟燒紙,請求弟弟亡靈的保佑。弟弟之死始終是母親的心結,她認為“如果你舅舅還在,我們是不會這么被人欺負”。不禁讓人想要去探尋,母親的童年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故事,于是故事來到了《小園》中。
在《小園》中,紫旗換了一種書寫方式,她不作判斷,只是摹寫父親的動作和父親的神態,寥寥幾筆,寫出父親作為父權制大家長的時刻緊繃和嚴苛。向小園的父親是一個色厲內荏的角色,他生氣的時候是“一只受驚的金魚”,會“扯起嗓子吼叫”制造一種大家長的威嚴感,對孩子們沒有真正的關心。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順從且聽話,以維持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在這樣的家庭里,危險時時刻刻都會降臨,父親會動手打孩子,比如揚起高高的手打向小園,讓她謹記自己的錯誤。向小園也因為貧窮和長姐的身份,不得不在這個家庭中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即便弟弟想要幫助姐姐,但在悍然無匹的父親面前,姐弟二人的反抗只是屢次證明了暴力的無可撼動。母親以養大兒子作為目標,和小園的父親不同,母親總想表現出一種毫不費力的感覺以維系自己的體面。如果說向小園的父親給孩子帶來的是實質性傷害,是粗暴的吼叫和肉體上的暴力,那么向小園的母親帶給孩子們的則是精神上的漠視:“父親的拳腳雖然有力,像火焰一樣傷害我們的身體,但母親壓根兒不需要拳腳,她用冰涼的目光和言語。”母親的做法是一種更深層的傷害,無時無刻地否定侵入孩子內心的情緒,便是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漸消磨掉了孩子對母親的信任,“它是不易察覺的”,且“因為毫無防備,所以出奇地燙人”。弟弟的意外死亡給家庭帶來了巨大沖擊,年幼的向小園嘗試安慰父母,但在父母的質問下,她從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她無意間說出的“媽,你為啥子不帶弟弟拜保保”是第一次表達出對母親的指責,但父母沒有接納她的情緒。“你曉不曉得你在說啥子話,你還想把責任推給你媽?”父母的控訴讓向小園恍惚是自己殺死了弟弟,即便弟弟的死亡并不是向小園造成,卻給她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愧疚。
讀完兩則故事,可以看出生活始終沒有給向小園伸出援手,不斷地給予她苦難,卻沒有給予她應得的愛護,她只能拼命維護自己和女兒的生活,無力去管姿態好不好看,在生活的一地雞毛之下,不斷地進攻和防御。上一代人不可承受的生命重量,延續到了下一代。沒有人教會上一代人如何正確地去表達以及如何去愛,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教育自己的后代,在面對生活時,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這樣家庭之下成長的孩子,她們的人生都用在了什么地方,或者說浪費在了什么地方?紫旗在這里寫得很明晰,即和父輩的斗爭上。兩代人之間始終無法真正地對話,從來都是或隱或顯的斗爭。偶有片刻的溫情,但也稍縱即逝,孩子無法改變偏執的父母,只能盡力去改變自己。但矛盾的地方也在于,她們不是不能理解父母。她們理解父母身為家庭支柱的壓力,理解她們面對生活瑣屑難以控制的情緒,但她們也難以忘懷,自己也不過是個孩子,卻承受了父輩的沉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壓抑自己,將問題歸結在自我身上,變得越發敏感脆弱,用外殼偽裝起自己。難以原諒父母帶給自己的傷害,又始終無法理直氣壯地指責,隨著積怨,隨著她們越發了解父母,這種自我矛盾感愈深,最終不可避免地深陷生活和心理雙重的水深火熱。
紫旗的寫作或許會給同樣遭遇的孩子提供一種共情和理解,她真實地看見了那群面對傷害卻無力反抗的少年們。父母和孩子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二者之間埋下的矛盾是否會得到解決,彼此之間是否能夠得到和解,這些文中未曾解答的困惑,使人更加期待紫旗之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