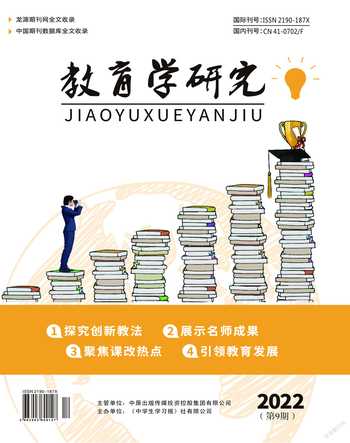“酋長”張叔叔
賀譯萱
有人總嫌這世界太乏味,有人我行我素,唯我獨尊。
窗外,銀杏葉一樹樹地落,有一個人在那里站了很久。
想起了張叔叔,一個渴望在雪線之上有一箭之地的人。他說他是那里的酋長,壘雪建寨,在雪地上寫字,以雪化水,抄經書,種一院梅,扶著一山的寂靜。他是一個很憂郁的人,也許只有半山寺小和尚向他打招呼時偶爾能讓他笑一笑。頭發比眉毛還短,緊蹙的川字似久干的河床,鼻如塌掉的荒墳,從兩片嘴唇蹦出來的聲音和一截溪水落在深潭里一樣,倒是一雙眼睛埋了很多黑夜,不見盡頭。他偶爾寫詩,說每一首詩是一條去遠方的路,他卻沒有在一條路上,遇見過歸鄉的自已。
他喜歡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帶,每次見面時總帶一些書給我。不講大道理,聽人說話時神態柔和,對別人掉下去的尾音表現出懷里的陽光有一點點減少的感傷。適時的沉默也不打破,有時候長得感覺在九月的田野里走過,影子跟在后面,垂向土地的稻穗沉甸甸地,有人在田那頭喊我們,恍惚如麻雀飛過天空。聽我選了文科,建議我多讀一些史書,領悟歷史有三個層次:真相,教訓,人性。他贈給我圣保羅寫給提摩多的一句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張叔叔一次次走向高原,說在氧氣越少的地方,才知道心里放哪一個人。江水浩蕩,佛號聲聲如滾雷,他愛一個人是那樣,恨一個人也是那樣。有一次從色達回來,同回的有一個藏族小女孩,在眾人疑惑的指指點點里,我行我素,教她說漢話,寫漢字,一筆一劃的寫一個女人的名字,白的紙,像厚雪,我生怕一場雪崩,埋了他倆。
有次聚餐后,窗外驟雨,閑來無事,都慫恿張叔吹一曲。燈熄后,先是一陣長低音,簫聲嗚咽,像是一個夜行人走在草原上,火把微弱,黑夜把他吞了又吐出。接著蕭聲緩和輕快起來,同村上春樹寫的在春天的原野,抱著毛絨絨的小熊從長滿三葉草的坡上滾下來差不多。突然簫聲急促,陡上陡落,像奔涌的大海上的孤舟,就在大家都絕望地等待撕碎的命運時。簫聲卻如水過灘涂,在一個拐彎處,楓樹長滿的地方,匯成了一面湖,你坐在那里,靜靜地,給你無數個黃昏都不愿換的時刻。燈亮后,張叔叔全身濕透,剛從湖水里走出來。
也許是突然或者是必然,張叔叔就從青藏高原的源頭看向了黃河,在一個月夜,張叔叔出發去探放黃河,從此杳無音信數月,直到滿身黃土滿目滄桑的歸來。
踏上黃土地,天高地廓,昊天,洪水和一線麥田,好似砂紙上粗獷勾勒的凸出線條,是來不及修改的雕塑,一旦塵埃落定便沒有改變的余地。山西與別處是不同的,就算你昂首挺胸決不左顧右盼,五彩繽紛的古塑、攝人心魄的琉璃的光韻也會撲面而來。炎黃古帝、堯舜禹三圣這些閃光的名字,表里河山、炎黃之根這些充滿敬意的稱呼,都凝結在飽經滄桑的一椽一檁,一磚一瓦之中,并且在那片與厚厚煤層緊密相聯的遼闊黃土地中慢慢沉淀。
逼近黃河,觸目皆空闊寂寥,靜默地敬畏著為黃河的出現蓄勢。峰回路轉,滾滾滔滔,只見那赭色的浪濤從天際而來,為萬物都調出一絲蒼涼的色彩,混沌不分明,湍急的水流在白楊樹林里翻騰,在漠漠蒼穹中摩擦,在河床堅硬之上沖蕩。碰撞,相擊,但越過天穹之后卻是按部就班的流向。抬頭望去,天很高,兩岸的黃沙很遠,黃河的氣壯山河也并未讓周遭有絲毫的動搖。平地延伸得分外遠,白楊挺拔多年不變的禮贊,這讓黃河的出現氣場安閑,天地間格局太大,大到萬物的存在都與情理之中。
張叔叔說他仿佛看見了黃河流過華夏身體里的每一個角落,她從《二十四史》的扉頁流過,跨越大唐盛世的夜夜笙歌,橫穿黃土縱橫的牽絆。不知她飲過多少次華夏的熱血和淚水,不知她伴隨了多少位文人雅士,度過多少書齋里的不眠之夜?她從巴顏喀拉流到腳下,上億年的沉淀,留下的不僅是輝煌壯闊的黃沙滾滾,更是永不冷卻的中華歷史。當她擁有一切榮譽的前綴,她依然熱情不減,她依然牽著華夏兒女的手,不舍晝夜向前奔去。
旅途是一條路,歷史,更是一條千年不平的波折之路。
天地山河的智慧正在于此。用寬廣平靜的胸懷接受天地間的萬物,燦爛如奇跡的,或是平庸不值一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越是壯闊的,便越是平靜淡泊,越是滄桑古老的,便越是生意盎然。因此華夏文明本身就是一個內向自足的氣場,將自己和周遭環境的身份看得渺小平淡些,因為縱使黃河一般的存在,在這里都成為了沉默不語的小小的一份子,你,又有什么必要為自身的喜悲而身處牢籠?走出那一片局限的地界,山河壯哉,大美無言,對周圍的一切形成泛化,形成內心淡然處之的神韻,保持高貴的姿態,融入人潮,就此上路。
世界的魅力沉穩內斂,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永遠在路上,在山河面前,換內心的須臾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