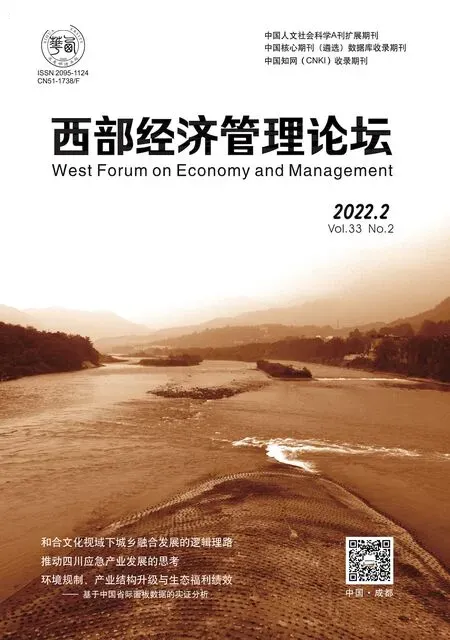外部壓力和信心支持對新共享經濟的雙元驅動
——基于廣州付費自習室的實證研究
柒永芳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 北京 102249)
近兩年,付費自習室在我國一二線城市悄然興起,成為一種消費時尚。艾媒咨詢的數據顯示,2019 年全國新增付費自習室達上千家,到2020 年付費自習室用戶規模已突破700 萬人,預計2022 年達1900 萬人[1]。付費自習室源于日韓,后傳入中國,逐漸形成“去K 書”“時不我待”等幾家連鎖店獨大的行業局面。付費自習室的盈利模式并不復雜,即將營業空間劃分為數個獨立的區域,用戶在付費后可以得到某個獨立區域在一定時間內的使用權。共享自習室既有獨立的個人空間,也有公共空間(或稱共有空間)[2]。艾媒咨詢將付費自習室歸類為新型共享經濟,認為其本質是一種“氛圍付費”。同時,付費自習室也是互聯網經濟的衍生產物之一。隨著移動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型升級[3],以空間或載體為內容的功能、氛圍消費成為時下都市青年的消費熱潮[4]。付費自習室搭建APP 平臺,嵌入無人監管系統,既可以進行座位預約,還能整合付費自習室的其他資源,如用APP 平臺購買茶飲、小食等[5]。
目前,學界主要從四個方面解讀付費自習室的市場熱情。第一,經濟下行和失業壓力說。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 年年末全國城鎮失業率達5.2%[6]。此外,新冠疫情也可能使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同時,隨著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高精尖人才門檻不斷上升。在經濟壓力和就業形勢的雙重影響下,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學習提升的道路,而檢驗提升效果的硬性標準就是考研、考證等各類考試,進而引發了對學習空間(如付費自習室)需求的上漲。第二,心理素質說。在網絡信息爆炸的時代,青年群體的心理承受力、自律性均易受到學習環境的影響。付費自習室是青年在壓力、風險情境下適應與抗爭的一種外在呈現,即自我嵌入城市生活努力的儀式化[4]。付費自習室消費行為折射出的是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群體在面對逼仄的居住空間、激烈的就業競爭等壓力時所產生的普遍焦慮[7]。第三,公共資源短缺說。付費自習室暴露了公共學習場所的供給還存在短板與缺口[8],而付費自要習室為有需要的群體提供了一個高質量的學習環境,消費者則為合理使用高質量的學習環境付費,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公共資源的壓力,這也是其誕生的重要原因之一[9]。第四,產業借鑒說。付費自習室的盈利模式在日韓等國家已相當成熟,是一個具有可行性和巨大潛力的行業,而非短暫的網紅經濟[5]。不算高昂的進入成本、較短的回收周期及輕松的退出機制,讓這種新型經營業態成為創業者爭相追捧的對象。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是在觀察的基礎上進行總結,缺乏實證分析。本文在研究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對廣州市主城區范圍內的26 家付費自習室的消費者進行了訪談,篩選出了“內卷”環境、公共資源、消費觀念與平臺效益四個要素,對這四個要素如何推動付費自習室的消費規模上升進行了研究。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本文首先對兩個關系進行初步分析,即:“內卷”環境(IE)和公共資源(PR)與付費自習室消除外部環境壓力之間的關系;消費觀念(CC)和平臺效益(PB)對消費者的信心支持作用與付費自習室消費驅動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構建假設和量表,引入訪談數據來探究這四個要素如何影響付費自習室消費規模。
(一)“內卷”環境要素(IE)
經濟下行和失業壓力是驅動自習室消費規模擴展的外部因素,對于正值考學階段的青年群體來說,一個重要的內部驅動因素是人口紅利導致的“內卷”——即“過度競爭、無增長的競爭”。“內卷”(involution)又稱“過密化”,源于拉丁語 involutum,最先被美國人類學家Alexander Goldenweiser 用以指社會或文化形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難以突破或轉化,只有通過使內部更加復雜化而繼續下去。“內卷”一詞在20 世紀90 年代開始被國內學者用于研究我國華北平原、長三角地區的農業經濟[10-12],進而引起廣泛關注。近年來,內卷被用于解釋新經濟形態下“996 式加班”“績點為王”“小學軍備競賽”等社會現象[13-15]。“內卷”本質上是一種競爭文化,跟土地資源和資本一樣,勞動力也是一種生產要素,當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群體涌入北上廣,他們便喪失了議價能力[14]。“內卷”是競爭文化發展到晚期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家都在搶跑[14]。可見,“內卷”使就業壓力增加、職業競爭加劇,同時,“內卷”環境也激發了青年群體自我提升的需求,越來越多的準畢業生或社會在職人士選擇了考研、考證、考公等學習方式,以求持續提升個人競爭力,而付費自習室顯然是一個理想的考學復習場所。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a:“內卷”認知增加了消費者對“內卷”環境的焦慮。
H1b:“內卷”經歷增加了消費者對“內卷”環境的焦慮。
(二)公共資源要素(PR)
公共資源數量短缺以及配置不合理也是促使年輕人轉向付費自習室的一個原因。本文根據公開資料及實地調研,整理出廣州主城區(不含南沙區等新設區)截至 2020 年底的城市公共圖書館資源供給情況(見表1)。表1 顯示,廣州主城區規模以上圖書館一共有10 個,總建筑面積約29.7 萬平方米,開放座位約12500 個,日均開放時長約8.95 小時。而廣州市主城區常住人口達 1400 多萬(截至 2020 年底),主城區各行政區均超百萬,其中天河區、海珠區、白云區人口最多[16]。表1 顯示,這10 個圖書館存在開放位置數量少、日均開放時長較短(中午閉館、下午閉館時間早、多數晚間不開放)、需提前預約搶座且預約時長受限等問題。此外,非主城區圖書館街區分館共約120 個,經實地調研走訪發現,街區分館大多存在面積狹小、環境氛圍差、不設座位、開放時間短、與老年兒童活動場所或居委會場所混用等問題。

表1 廣州主城區范圍規模以上圖書館開放情況表
實地走訪還發現,城市圖書館存在配置地理區域集中、交通時間過長、不可存放書籍物品、預約手續不便等問題。此外,高校圖書館因近年高校強化安全管理、疫情封鎖等原因,對外開放程度下降。上述原因推動著青年群體轉而為“省心、省時、方便”的付費自習室買單。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a:公共圖書館資源數量少、獲取困難增加了消費者的資源獲取壓力;
H2b:公共圖書館資源的環境和氛圍差增加了消費者的資源獲取壓力。
(三)消費觀念要素(CC)
共享經濟和網絡經濟的日益繁盛使青年群體的消費觀念發生了改變,進而推動了付費自習室消費。學界將付費自習室歸類為“新型共享經濟”。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將共享經濟按分享對象劃分為產品分享、空間分享、知識技能分享等六大類,區別于共享單車等租用實物的交易,付費自習室的本質是租用“空間、氛圍”,本文據此將其歸類為“共享經濟”中的“空間分享”。由于互聯網技術的沖擊,許多消費者已逐漸習慣并可借助網絡實現自己的消費需求[17],而習慣于“租”、愿意為“空間氛圍”等虛擬價值買單,正是共享經濟和網絡經濟下年輕一代消費者日益形成的觀念和習慣。此外,隨著消費者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更加注重綠色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使用權消費理念逐漸取代了強調所有權的消費理念,同時互聯網技術的興起也讓共享成本變得更低[18],這些都推動著共享經濟飛速發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對新共享經濟的認同有助于消費者觀念轉變。
從消費自信的角度,本文在調研中發現,消費者的親友對付費自習室的認同感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消費者信心,從而促進消費規模。一方面,消費者的親友認同感給予消費者消費信心,另一方面,這種認同感也帶動更多人消費這種新共享經濟,形成一種循環上升的趨勢。消費結果自信是影響決策的核心成分,它包含個人結果自信和社會結果自信兩個因素,前者表示消費者對自己的決策使自己滿意的程度,后者表示消費者的決策能受到他人肯定和稱贊的自信程度[19-20]。社會結果自信側重反映在大眾對自己消費決策能力的評價,由個體通過周圍的社會關系給予自己的反饋和自己的反思形成;擁有較高社會結果自信的消費者通常認為自己眼光獨到,做出的消費決策能得到包括朋友、家人等在內的社會大眾的正向評價反應[20]。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b:親友對付費自習室的觀念認同有助于消費者觀念轉變。
(四)平臺效益要素(PB)
學界在分析驅動因素時,側重于研究青年群體在面對居住空間壓力、生活競爭壓力等產生的焦慮問題。然而本文調研發現,上述壓力遠比不上受到排擠質疑的精神壓力。考研、考證等“充電”行為仍然面臨著“不合群”“用處不大”“學歷貶值”等或質疑或打擊貶損的聲音。考學青年群體除了應對搶占資源的煩惱,還要應對排擠質疑帶來的壓力,他們迫切需要得到信念的支持、價值觀的認同和經驗的傳遞。相較于城市公共圖書館的高流動性、住宅環境的高緊張性,付費自習室能為考學青年群體提供一種歸屬感和“安全支持”——即一種平臺效益。根據走訪調研發現,相當一部分付費自習室的創始人是考學過來的青年人,他們本身就是一種精神信念和經驗的先導。并且,付費自習室的“考友”之間,大多數相處融洽,交流互動輕松愉悅,互相勉勵鼓舞,許多“考友”即使考試結束不再需要付費自習室,也會跟以前的“考友”互動,或者回訪付費自習室給后來的“考友”傳遞經驗。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4a:平臺產生的精神支持有助于消費者獲得平臺效益;
H4b:平臺提供的經驗交流有助于消費者獲得平臺效益。
(五)綜合假設及概念模型
上述“內卷”環境(IE)、公共資源(PR)要素可歸結為外部壓力,本文調研認為,付費自習室為消除考學青年群體的外部壓力提供了途徑,一方面為他們實現提升自我的轉變提供學習高質量的空間,一方面免除了他們獲取公共資源的煩惱。而消費觀念(CC)的轉變與平臺效益(PB)的獲得則讓青年群體獲得信心支持——這種付費模式被認為是正常的、值得的、有效的。通過消除外部壓力、增加信心支持,最終驅動了消費者對付費自習室的消費。因此,提出假設:
H5:付費自習室通過消除“內卷”環境壓力和公共資源獲取壓力而消除了消費者的外部壓力;
H6:付費自習室通過消費觀念轉變和平臺效益獲取而使消費者獲得信心支持;
H7:消費者通過消除外部壓力和獲得信心支持而提升付費自習室的消費規模。
結合以上假設,構建以下結構模型(圖1)。

圖1 結構模型
二、變量設計和樣本數據
(一)變量設計
本文主要研究消費驅動因素,四個要素即“內卷”環境(IE)、公共資源(PR)、消費觀念(CC)和平臺效益(PB),均需要調查消費者的主觀評價,因此,本文采用成熟的量表體系——Likert scale(李科特7 級量化表)[21-22]對消費者的內心想法進行研究。四個要素均設置相關測項(見表2),并對所有的測項賦值,1 至7 依次表示“非常不認同”“不認同”“較不認同”“中立”“較為認同”“認同”“非常認同”。本文量表各要素的測項均參考前人的成熟量表,語言組織上請專家潤色及反復驗證,在正式發放問卷調查前也請10 名測試者進行預先測試,確保測題的意思表達準確性。

表2 量表測項設置及信度檢驗結果

表2(續)
對“內卷”的認知設置3 個測項(IE1、IE2、IE3)、對“內卷”的經歷設置3 個測項(IE4、IE5、IE6);對于公共資源數量少、獲取困難設置3 個測項(PR1、PR2、PR3),對于公共資源環境、氛圍差設置3 個測項(PR4、PR5、PR6);對認同新共享經濟設置3 個測項(CC1、CC2、CC3),對親友觀念認同設置3 個測項(CC4、CC5、CC6);對平臺產生的精神支持效益設置3 個測項(PB1、PB2、PB3),對平臺的經驗交流效益設置3 個測項(PB4、PB5、PB6)。對于假設H5,設置3 個測項Eep1、Eep2、Eep3;對于H6,設置3 個測項Gcs1、Gcs2、Gcs3。所有自變量的量表設置見表2。
對于因變量設置,由于付費自習室興起不過兩三年,如果僅從過去的消費規模進行判斷可能和實際情況相差甚遠,為此,本文加入對未來的消費需求調查數據進行調整,最終用“過去一年累計對付費自習室的消費規模”(W1)以及“未來一年或者更久遠的時間已經預定或者預計需要使用付費自習室的時間累計”(W2)對付費自習室消費規模進行測量。為剔除各家自習室之間由于裝修、地理位置、投資者對回報率的要求等因素的影響,本文選用消費時長作為規模測量值(事實上,大多數付費自習室都是按消費時長計費,并設置有日封頂額、月卡、年卡等消費方式,用時長來反映付費自習室消費者的消費規模,更貼近于實際)。對過去的消費規模,本文以更細致的“小時”計量時長,從低到高劃分為“500 小時及以下”“501~1000 小時”“1001~1500 小時”“1501~2000 小時”等 7 個等級,從低到高分別賦予1 至7 的分值。對于未來預計的消費規模,本文以較模糊的“月”“年”計量時長,從低到高劃分為“一個月以下”“一個月~三個月”“三個月~六個月”“六個月~一年”“一年~一年半”等7 個等級,從低到高分別賦予1 至7 的分值。
(二)樣本屬性
本文通過線上調研平臺對廣州市區范圍內26 家付費自習室的消費者發放問卷,歷時半月,共回收問卷455 份,剔除無效問卷71 份,得到有效問卷384 份,問卷有效率約84%。調研問卷設置了3 個關于被訪者屬性的測項,分別是“年齡”“身份”和“使用付費自習室的目的”。年齡劃分為“15~18 歲”“19~22 歲”“23~26 歲”“27~30 歲”和“30 歲及以上”5 個段,占比分別為14.1%、36.7%、25.8%、15.1%和8.3%。身份劃分為“高中生”“大專、中專學生”“本科院校大學生(大一到大三)”“準本科畢業生(大四)”“研究生”“待業備考人員”“在職人士(進入職場三年以內)”和“在職人士(進入職場四年及以上)”等8 個類別,占比分別為13.7%、11.2%、17.4%、8.9%、3.9%、12.0%、20.1%和12.8%。使用目的劃分為“備考高考”“備考專升本”“備考研究生”“備考雅思托福、GRE 等出國留學相關考試”“備考執業證書或職業相關證書”“備考公務員”和“備考其他類型的考試”等7 個類別,占比分別為13.5%、8.1%、23.2%、17.2%、17.7%、5.2%和15.1%。樣本基本能覆蓋廣州市使用付費自習室的各個年齡段和各種身份的人群,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檢驗
為了檢驗量表測項設置的合理性,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數進行同質信度檢驗,采用CR(composite reliability)系數進行組合信度檢驗(見表2)。根據SPSS25.0 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Cronbach's α 系數最低為0.778,高于臨界值0.7;所有變量的CR 系數最低為0.786,高于臨界值0.7。此外,各測項的標準因子載荷系數(Factor loading)均大于或接近0.7,說明因子(潛變量)與測項(顯變量)之間的關系密切,本文量表沒有需要剔除的測項。由此可知,本文量表信度質量較高,可用于進一步分析。
本文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進行效度檢驗。效度檢驗包括聚合效度檢驗和區分效度檢驗。本文的調查樣本容量N=384,超過200 個樣本,根據AMOS25.0 結果顯示,本文量表擬合指數:卡方值χ2為540.936,自由度df為360,p值0.000,卡方自由度比χ2/df=1.503 <3,GFI=0.914 > 0.9,RMSEA=0.036<0.07,SRMR=0.039 <0.8,CFI=0.977>0.9,NFI=0.934 >0.9,NNFI=0.972 >0.9,所以本文量表模型的擬合度較高(參考hair 臨界值)。同時,所有變量的CR 系數高于臨界值0.7,所有變量的AVE 值均高于0.5,且所有變量的AVE 的平方根值均大于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的Pearson 相關系數(見表3),說明本文量表聚合效度和區分效度都較高,可用于進一步分析。

表3 區分效度:Pearson 相關與AVE 平方根值
(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共同方法偏差(又稱同源方差,簡稱CMV)是指測量環境、項目語境等造成的人為共變所帶來的誤差,通常情況下使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方法進行檢驗。本文對所有測項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大的因子的方差解釋率(旋轉前)為 23.807%,遠低于 50% 的臨界值,且各變量的 AVE 的平方根值均大于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的 Pearson 相關系數,說明本文量表的效度不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可用于進一步分析(見表3)。
(三)結構方程模型與路徑分析
本文采用AMOS25.0 對結構方程模型(SEM)擬合度和路徑系數進行檢驗,以驗證文本假設。本文將因變量設置為“過去一年累計對付費自習室的消費規模”(W1)以及“未來一年或者更久遠的時間已經預定或者預計需要使用付費自習室的時間累計”(W2)。對因變量同樣賦予1 至7 的分值。
首先對本文提出的結構模型擬合度進行檢驗。根據AMOS25.0 結果顯示,本文結構模型擬合指數:卡方值χ2為671.908,自由度df為444,p值0.000,卡方自由度比χ2/df=1.513 <3,GFI=0.902 >0.9,RMSEA=0.053<0.07,SRMR=0.037<0.8,CFI=0.972>0.9,NFI=0.921>0.9,NNFI=0.968 >0.9,本調查樣本容量N=384,超過200 個樣本,所以本文結構模型的擬合度較高(參考hair 臨界值)。
下一步進行路徑檢驗,根據AMOS25.0 結果顯示,本文提出的假設均得到支持,自變量與中介變量、因變量間的路徑系數均大于0.5,呈顯著相關性(見表4)。

表4 假設檢驗結果:路徑系數
從表中可以看到,“內卷認知”“內卷經歷”與“內卷環境焦慮”之間呈現積極的相關關系(p<0.01,路徑系數0.735、0.646 均大于0.5),說明假設H1a、H1b檢驗通過;“數量少、獲取困難”“環境、氛圍差”與“資源獲取壓力”之間也呈現積極的相關關系(p<0.01,路徑系數0.543、0.627 均大于0.5)。說明假設H2a、H2b檢驗通過;“認同新共享經濟”“親友觀念認同”與“消費觀念轉變”之間呈現顯著的相關關系(p<0.01,路徑系數0.845、0.757 均大于0.7),說明假設H3a、H3b檢驗通過;“精神支持”“經驗交流”與“平臺效益獲得”之間呈現顯著的相關關系(p<0.01,路徑系數0.836、0.743 均大于0.7),說明假設H4a、H4b檢驗通過。
此外,存在“內卷環境焦慮”“資源獲取壓力”的消費者通過付費自習室得以“消除外部壓力”,三者之間呈現積極的相關關系(p<0.01,路徑系數0.587、0.548 均大于0.5);由于“消費觀念轉變”“平臺效益獲得”,消費者通過付費自習室“獲得信心支持”,三者之間呈現積極的相關關系(p<0.01,路徑系數0.567、0.640 均大于0.5),說明假設H5、H6檢驗通過。
最后,由于“消除外部壓力”“獲得信心支持”,消費者愿意為付費自習室買單,前兩者與“消費規模”之間呈現出積極的相關關系(p<0.01,路徑系數0.536、0.512,均大于0.5),H7檢驗通過。
四、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通過收集大量數據、構建結構方程模型與路徑分析后得出結論:(1)“內卷”的外部環境導致青年群體產生焦慮,城市公共圖書館資源短缺、質量不佳導致青年群體產生資源獲取壓力。(2)付費自習室對消除青年群體的環境焦慮和資源獲取壓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通過消除焦慮和壓力提升了付費自習室消費規模。(3)消費者及親友對新共享經濟的認同導致消費者對付費自習室的觀念發生改變,付費自習室提供的精神支持和經驗交流作用使消費者獲得了平臺效益。(4)消費觀念的改變和付費自習室的平臺效益對消費者產生信心支持作用,進而顯著推動消費規模擴大。(5)消費觀念轉變和付費自習室平臺效益的驅動效果最為顯著,說明消費者更在乎付費自習室所帶來的心理影響。
上述結論對付費自習室甚至是新型共享經濟的生存與發展都有參考意義。一方面,公共管理者應致力于消除消費者的外部壓力,通過投資建設、引進社會資金或挖掘城市的“金邊銀角”,加快提供更多、更優質的公共資源。這與付費自習室的發展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雙贏的關系。另一方面,付費自習室經營者應致力于強化信心支持,通過實現信心支持對新共享經濟的驅動效應而獲得經濟利益。
(二)建議
首先,政府應加快引導創新型社會建設。在人口密度極高的中國,眾多領域都存在提量而不提質的現象,這一機制常見于以應試為主的教育界[15]。面對逐年新增的競爭對手和有限且不均衡的資源,青年群體不得不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來應試[23]。不少學者研究了“去內卷化”并提出建議:一是加大對創新的關注和投入。除了政府對創新的投入和引導之外,還要更多地依賴人民群眾的創新能力,政府應該更大范圍地進行賦權和賦能。此外,政府應更多地關注和完善有利于培養創新人才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以激發更多的創新[15]。二是轉變思維,創造不同的賽道,打破一體化的競爭結構[14]。綜上,各級政府應不斷完善與職業應用相匹配的教育體系,如在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等核心尖端技術培育方面給予資源傾斜、在補貼和投入等方面拓展政企合作和校企合作空間等。對于青年群體,政府及學校應幫助他們進行職業規劃,引導形成正確的擇業觀,青年群體應結合自身興趣、經濟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做好規劃,切勿因“內卷”而產生盲從行為。
其次,政府應打破與企業、社區的壁壘,加大公共資源投入力度。付費自習室與城市公共圖書館、社區學習室不應該是互斥的圈層。公共文化空間供給不足是付費自習室成為新消費熱點的一個重要背景,說明單獨依靠財政仍難以滿足學習型社會發展的需要[24]。政府應鼓勵相關城市利益群體積極參與,例如,付費自習室與城市公共圖書館實現相互通融,與政府合作盤活城市閑置公共空間,實現公共文化空間多點化、分散化、便捷化,實現圖書資源通借通還等。此外,付費自習室還可與實體書店、培訓機構聯合,降低場地租用成本,實現客源互通。付費自習室還可與社區合作,在社區開設專屬青年群體自修區,解決場地問題的同時方便青年群體高效、便捷地獲取學習空間資源。
再次,付費自習室應抓住消費觀念的轉變和養成進行營銷。由于青年群體及其親友對新共享經濟的消費觀念呈現向好的趨勢,付費自習室的經營者應抓住此點進行營銷,如開設親友卡、共享卡等消費類型,重點推出會員推薦優惠制、親友組團優惠制等。筆者在調研走訪中發現,廣州市內的付費自習室質量參差不齊,與此同時,付費自習室帶來的精神支持效益和經驗交流效益是消費者關注的重點。因此,經營者應通過店長、管理員的引導和管理,重點打造付費自習室的文化氛圍,形成付費自習室所獨有的、強大的競爭力。自習室的服務和環境是會員消費的根本動力,提供更專業更優質服務的自習室才會脫穎而出[25]。而高質量的環境不僅包括硬件設施,還包括軟性環境,因此,付費自習室應結合消費觀念的轉變,除進行文化氛圍營造外,還可考慮消費者更高層次的需求進行精神文化港灣概念等打造,給受眾足夠的“安全支持”和“信心支持”。
最后,付費自習室應拓寬未來的盈利點。付費自習室這一經營模式應經濟發展而生,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付費自習室集中了一群有著基本相同理念、價值觀和目標的青年群體,平臺產生的精神支持和經驗支持效益對受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付費自習室應有效利用這些平臺效應,對產品、服務進行細分或進行跨界合作,開拓職業規劃咨詢、教育培訓一站式服務、會議場地租用和餐飲供給等新的盈利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