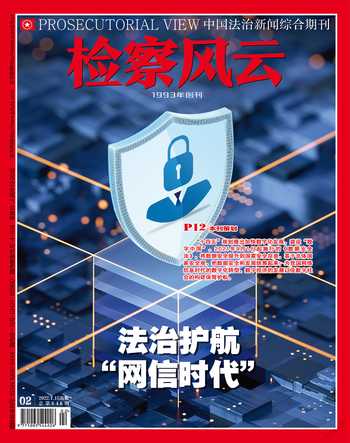繁花似錦:中歐陶瓷貿易
天禧
16世紀開始,得益于新航路的開辟與成熟,中歐貿易與交流日漸頻繁,瓷器作為最具中國特色的商品之一,源源不斷地輸入歐美地區。遠渡重洋的中國瓷器不僅見證了明清時期中國與歐洲的貿易發展,也記錄了當時圖像、設計、技術與觀念的交流,是東西文化間對話與互動的載體。2021年10月,上海博物館與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合作,聯合來自7個國家的12家知名博物館及收藏機構舉辦了“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這是疫情發生以來國際博物館界參與地區極廣,參展規格極高的展覽項目,匯聚了總共206件(組)重量級中外陶瓷與油畫作品,展覽以陶瓷為媒介,探究當時的世界貿易和跨文化交流。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表示:“展覽的主題是早期全球化中的東西融匯,而展覽本身則是全球博物館力量的融匯在疫情之下,以文化沖破阻隔,用藝術聯結世界,共同譜寫這一東西融匯的傳奇。”
大航海時代之前,中國與歐洲的交往及貿易需經中東地區中轉,東西方之間的商貿由阿拉伯商人主導,貨品自中東地區的大馬士革等貿易樞紐,經威尼斯或熱那亞輸入歐洲。輾轉到達歐洲的東方貨品數量稀少、價格高昂,是僅供權貴階層消費的奢侈品。中國瓷器在其中備受推崇,成為王室、貴族間的外交贈禮,埃及蘇丹曾以之饋贈威尼斯總督等歐洲貴胄。
當時,中東地區是東方貨品輸入歐洲的重要路徑。只有極少數的中國瓷器能夠到達歐洲,其中有一部分便來自中東的轉贈,而接收者亦為王室貴胄。1447年,埃及馬穆魯克王朝蘇丹曾將三件瓷盤贈送給法國國王查理七世。1487年,埃及蘇丹亦以瓷器饋贈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中國瓷器在當時的珍稀程度及其流通路徑,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器物通過外交、旅行、貿易等不同渠道輸入歐洲,其中有三件珍品瓷器。第一件是中國景德鎮燒制的明永樂青花纏枝牡丹紋執壺。1547年,弗朗索瓦·德·菲梅勒男爵將來自中國宮廷的珍貴青花瓷執壺攜至法國。當時,他受命于法王亨利二世,作為臨時外交使節前往君士坦丁堡,覲見奧斯曼帝國的蘇萊曼一世。作為外交禮物,這件執壺曾經見證中國與中東的交往,又經外交使節之手,聯結中東與歐洲,極具傳奇色彩。第二件是由前往耶路撒冷的埃伯哈特·馮·曼德沙伊德伯爵攜至歐洲的中國瓷器。第三件中國瓷器,出現在意大利畫家喬瓦尼·貝利尼1514年的油畫《諸神之宴》中。這些精美的器物,不僅見證了這段特殊的流通歷史,也開啟了此后東方瓷器風行歐洲的先聲。
15世紀中期,經由中東聯結東西方的傳統商路頗受阻滯,歐洲船隊于海上不斷擴張,探尋新領地與貿易路線,席卷世界的大航海時代自此開啟。葡萄牙人最先東來,1498年達·伽馬船隊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卡利卡特,開辟了歐亞交通的新路線,此后持續東進,到達中國沿海,揭開近世東西方交流的新篇章,深刻改變了歐亞貿易格局。在各貿易階段,葡萄牙都訂制了特殊的紋章瓷器。作為最早的歐洲訂制瓷,它們還記錄了東西方早期圖像交流中的誤讀,以及當時貿易和宗教文化傳播的關系,彌足珍貴。西班牙、荷蘭緊隨其后,接踵而至,東方貨品自此源源不斷地輸入歐洲,深刻改變了歐亞貿易格局。
16世紀中期以前,中國瓷器最重要的海外市場在東南亞及中東區域。澳門開埠以后,中葡貿易迅猛增長,瓷器外銷的重心逐漸轉向歐洲。在16世紀晚期出現了一種標志性的貿易瓷,稱作克拉克瓷。克拉克瓷在17世紀前期都是最流行的外銷品種。

? 明嘉靖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紋碗碗口邊沿有一圈銘文,意為萬福瑪利亞。外壁有圓形開光四枚,分別繪葡萄牙王室紋章、渾天儀標記、“IHS”標記及風景花鳥,底部書“大明宣德年制”偽托款。葡萄牙梅德羅·阿爾梅達博物館藏。(Photo ? Medeiros e Almeida Museum, Lisbon, Ave Maria bowl-side, Portuguese Arms FMA 814-Photo Christopher Allerton)

? 明萬歷五彩暗花八寶紋碗鑲嵌黃金與紅寶石這件碗是16世紀晚期由奧斯曼帝國鑲嵌。這類設計巧妙地利用了碗外壁原有的圓形開光,將奧斯曼的本地裝飾風格重映在中國瓷碗上。1877年,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將這件碗贈予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喬治·索爾廷捐贈。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文字:霍小騫 Photo ?2021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明末景德鎮官窯停燒,大量優秀工匠轉而為民窯服務,與此同時,歐洲市場上的克拉克瓷器數量已頗為可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瓷器的質量、器型與紋飾提出更高要求。1634年,公司發往臺灣地區的備忘錄中提到,希望瓷器紋樣“細致精巧地繪制步行或騎馬的中國人物、水景、風景”。1635年以后,公司開始大量使用木樣,訂制更符合歐洲需求的器型,駐臺灣地區長官在信件中提及:“我給中國商人大盤、大碗、瓶、水罐、寬邊餐具……這些模型都是木質的”,這些木樣上“畫了各式各樣的中國人物”。1638年,荷屬東印度總督范·迪門寫信給荷蘭總部:“由于普通的瓷器已充斥歐洲,今后我們會限制類似產品的數量,根據需要訂購更精美優質的器物。”制作精美,繪有大量人物故事圖的“轉變期”風格器物開始逐步取代克拉克瓷器。到18世紀,貿易瓷已多按歐洲市場需求制作,訂制瓷、紋章瓷更為普遍。

? 靜物:水果、玻璃杯與瓷蓋碗威廉·卡爾夫? 約1662年威廉·卡爾夫是巴洛克時期的荷蘭畫家,出生于鹿特丹,是荷蘭黃金時代最杰出的靜物畫家之一。威廉·卡爾夫熱衷于將中國瓷器畫入靜物作品。在畫中出現了地毯、銀盤、玻璃杯、檸檬、瑪瑙柄小刀等物。法國瓦朗謝訥美術館藏。(文字:霍小騫 Photo ?RMN-Grand Palais / René-Gabriel Ojeda)
此時,貿易船隊在大洋中穿梭如織,偶爾沉沒的船只如同凝固的時空膠囊,封存其中的瓷器是追索貿易流通軌跡的重要材料。陶瓷不易朽壞,是沉船中最易保存的物品,研究者可以據此了解當時貿易規模、流通軌跡,進而彌補文獻的缺失或不足。在利納號、圣迭戈號、白獅號、班達號、萬歷號、哈徹號、格里芬號等沉船中出水的瓷器,分屬東南亞地區,西班牙、荷蘭、葡萄牙、英國等,它們來自不同水域,共同勾勒出15世紀末至18世紀中歐貿易航線、轉運網絡的時空發展。
伴隨著中西貿易的展開,輸入歐洲的中國瓷器不斷增加,從最初的異國奇珍,到17、18世紀成為日用餐具、裝飾陳設,使用階層持續擴展。中國瓷器也同時被改裝、組合,以適應西方審美與需求,這一過程激發出源源不斷的創意與靈感。
在歐洲的油畫中時常能看到中國瓷器的身影。這是因為早期到達歐洲的中國瓷器是王侯貴胄千金難求的收藏,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中被描繪成諸神與圣徒使用的器皿,帶有神圣的色彩。17世紀流行的靜物畫再現了當時富裕家庭的室內陳設和藝術喜好,墻面、壁爐、櫥柜上裝飾著來自中國的瓷器,桌面的青花瓷、金銀器與豐富的海味果蔬共同構成象征財富與地位的符號。展覽現場將油畫與畫中瓷器并陳,透過畫作可以步入瓷器在西方的使用情境,體會中國器物對歐洲審美趣味與生活方式的影響。
中國瓷器輸出歐洲后,有時會被歐洲工匠重新裝飾,加飾手法豐富多樣,最常見的是添加彩繪。
此外,中東與歐洲都有鑲嵌珍貴器物的傳統,為瓷器加裝配件可以保護易損部位,彰顯尊貴。早期歐洲鑲嵌集中在德國、英國等地。17世紀以后,東方物品逐漸融入歐洲的室內裝飾,誕生了許多瓷器宮室。大約1667年至1687年間修葺的葡萄牙桑托斯宮瓷廳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例,以令人驚嘆的方式將瓷器用于室內裝飾。18世紀開始,鑲嵌中心轉移至法國。奢侈品商人將東方瓷器與不同材質的物品組合,通過鑲嵌改變其功能與外觀,碗、瓶變身香熏,宗教塑像化身燭臺。貴族家裝更將這些極富裝飾性的器物成組擺放,搭配金碧輝煌的家具、繪畫及墻面,營造融洽和諧的裝飾體系,構成室內設計中的點睛之筆。
投稿郵箱: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