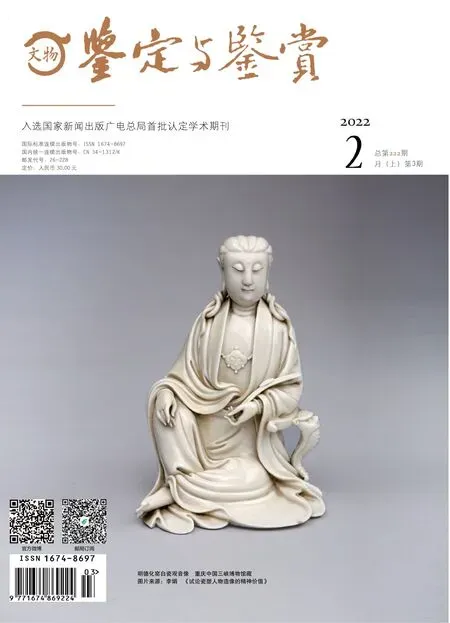西夏昊王渠考證
王飛



摘 要:通過歷史文獻的挖掘、水利工程建設資料的收集整理、文物保護檔案的查閱,結合田野實地調查的方法,對昊王渠的開挖背景、渠線走向、作用和沿革、現狀及廢棄原因等方面進行研究考證,厘清昊王渠的歷史脈絡、全面解讀昊王渠開挖的歷史背景、價值及作用,實地調查昊王渠遺址保存狀態,最后通過對比西干渠的現狀全面分析探討昊王渠廢棄的原因,進而補全開展昊王渠相關學術研究的背景資料,重建昊王渠歷史檔案,為古渠道的學術研究提供參考范式。
關鍵詞:昊王渠;遺址;文物保護檔案;考證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3.037
0 前言
黃河自黑山峽小觀音入寧夏境,過青銅峽,至石嘴山三道坎出境,流經寧夏397千米,其間沖淤形成寧夏平原。青銅峽以上為衛寧平原,青銅峽以下為銀川平原,具有引黃河水灌溉的優越條件,習稱寧夏引黃灌區。是中國最古老的大型灌區之一,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塞北江南”的美譽。通過舊渠改造、除險加固、實施續建配套和節水改造等水利工程,目前灌區共有古渠14條,長1292千米,控制灌溉面積3620平方千米。經過對寧夏引黃灌區主要古渠存續情況(表1)進行梳理研究,發現有的渠道被沖毀廢棄,有的被重修合并后更換名稱,有的至今仍在使用。翻閱《元史》《元和郡縣圖志》、嘉靖《寧夏新志》、乾隆《寧夏府志》、嘉慶《平羅縣志》等歷史文獻資料,發現記載有寧夏引黃灌區主要古渠如唐徠、漢延、七星、惠農等渠道,包括渠道長度、灌溉面積、流經縣域及堡莊、支渠概況、主要附屬閘橋、歲修人夫、所需物料等內容,分門別類,記錄翔實。同時亦發現,少部分著名古渠道如光祿渠、艾山渠、昊王渠等已廢棄并湮滅在歷史中,文獻記載寥寥數語,以致開展相關學術研究的背景缺失,無法確定有關渠道的歷史價值及其作用。本文以入選寧夏回族自治區第三批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昊王渠遺址為例,通過歷史文獻的挖掘、水利工程建設資料的整理、文物保護檔案,結合田野實地調查的方法,對昊王渠的開挖背景、渠線走向、作用及沿革、現狀和廢棄原因等進行研究考證,以期厘清昊王渠的歷史脈絡,梳理歷史價值,彌補文獻記載的缺失,重建昊王渠歷史檔案,從而為古渠道的學術研究提供參考范式。
1 西夏時期開挖昊王渠的歷史背景
“西夏是11世紀至13世紀,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割據政權,因其處于宋朝西北,別于十六國時之‘夏,故史稱‘西夏。”①西夏割據政權建立之后,轄境面積雖然廣闊,但多為荒漠和草原地帶,得益于自流引黃河水灌溉的便利優勢,只有寧夏引黃灌區最適宜發展農業,因此寧夏引黃灌區遂成為黨項割據政權“賴以為生”的“膏腴之地”,水利建設既是民命所系,又與黨項割據政權鞏固攸關。②為了保護水利設施,保障農田灌溉的正常秩序,西夏割據政權通過水利立法、實行水利分級管理、新渠開挖審批、完善灌溉用水方式、明確渠道歲修責任部門等制度,使寧夏引黃灌區“其地饒五谷,尤宜稻麥”③,進而成為漢唐以來寧夏平原農業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水利灌溉事業十分發達,“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徠),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余頃”④。李元昊時期是西夏割據政權國力最為鼎盛的時期,為持續保持對北宋、遼形成三足鼎立的有利局面,李元昊采取一系列措施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西夏社會進行了改革。從經濟環境方面看,興慶府周圍地區農業比較發達,相對穩定的引黃灌溉農業可以保證城市的軍需民食。除了原有的唐徠、漢延古渠等灌溉之利外,李元昊時期舉全國之力修建了賀蘭山東麓洪積沖積平原上由青銅峽至平羅縣境的昊王渠,使興慶府四郊的農業生產有了更大發展,成為西夏境內的糧食基地。⑤
2 歷史文獻及水利建設資料中昊王渠的記載
回顧寧夏引黃灌區兩千多年的水利開發建設歷程,從統治者重視層次、開挖規模、渠道長度、戰略意義等因素綜合來看,西夏時期開挖的昊王渠是寧夏古代水利開發歷史長河中一顆璀璨的明珠。遺憾的是,歷史文獻中有關昊王渠的記載寥寥無幾,無形中增加了開展昊王渠相關學術研究的難度。昊王渠之名最早見于明嘉靖《寧夏新志》一書,其載“靖虜渠,元昊廢渠也,舊名李王渠。南北長三百余里。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王珣奏開之,以更今名:一以絕虜寇,一以興水利。但石堅不可鑿,沙深不可浚,財耗力困,竟不能成,仍為廢渠”⑥。清乾隆《銀川小志》又載“靖虜渠,乃元昊時廢渠。舊名李王渠,疑即古之艾渠。弘治中,巡撫王珣奏開,更名靖虜。石堅沙深,竟不能成,仍為廢渠”⑦。由上述僅有可查的記載昊王渠史料的歷史文獻可知,西夏時期開鑿的昊王渠(又名李王渠)南北長150多千米,為當時重要的引黃灌溉渠道,后被廢棄,至明弘治十三年(1500),寧夏巡撫王珣經過實地綜合勘查,奏請朝廷勅撥帑金在西夏昊王廢渠的基礎上重新開鑿一條新的引黃灌溉渠道,命名為靖虜渠,然因石堅沙深,終未能重新開鑿成功,仍為廢渠,至此王珣發出“此日勞民非我愿,千年樂土為誰開”⑧的無限感慨,則更加凸顯出西夏開鑿昊王渠的艱難。
通過收集整理寧夏水利工程建設檔案資料,發現20世紀60年代末在興建西干渠的過程中,部分渠段或借用昊王渠故道,同時西干渠水利工程建設資料中對昊王渠遺址有較為詳細的記載。西干渠是青銅峽河西灌區自流部位海拔最高的一條新干渠,于1959年冬興建,1960年春通水,由河西總干渠引水。干渠沿賀蘭山東麓洪積扇邊緣北行,橫貫青銅峽、銀川、賀蘭等市縣,止于平羅縣崇崗鎮暖泉村,尾水入第二農場渠。西干渠開挖過程中,在稍里橋、二旗溝、吳家灣、橫溝和寧化橋北的羅家圈等處都發現或借用了昊王渠的故道,而且其顯在的遺跡辨認和實測1/10000地形圖證實,渠長近180千米,渠線與西干渠約略平行而稍高,由上而下以1/9000~1/6000的比降依地形高低半挖半填。⑨從西干渠水利工程建設資料相關記載來看,可以明確以下幾點:西干渠部分渠道或借用昊王渠故道,經實地辨認昊王渠遺跡走向并結合實測地形圖可以證實,昊王渠整體渠線與西干渠基本平行并稍高一點,渠道整體流向與西干渠基本一致,沿賀蘭山東麓洪積扇邊緣北行,昊王渠渠道長約180千米。gzslib2022040518403 文物保護檔案中昊王渠的記載
昊王渠遺址于2005年被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三批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并于2017年公布了遺址保護范圍(表2),從公布的昊王渠遺址保護范圍來看,現存遺址主要分布于青銅峽市、西夏區、賀蘭縣和平羅縣境內,這與昊王渠的渠線走向是吻合的。筆者查閱昊王渠遺址所在縣區文物管理部門建立的昊王渠遺址“四有”文物檔案資料,發現昊王渠青銅峽段遺址一處位于大壩鎮高橋村南,廢渠寬50米、深3米,一處位于邵崗鎮甘城子,殘渠約長300米,渠底寬約30米,渠口寬約50米,渠深2米左右;永寧段遺址在李俊鎮西邵村西殘存羅家洼一段,殘存長約4千米,渠寬35米,深1~2米,堤高1~2米,整體形制尚存,但淤塞情況嚴重;銀川段遺址在西夏區平吉堡農場三隊殘存1千米,南邊的一段僅存留渠底,寬約52米,北邊的一段僅存寬約26米的北側渠壩;賀蘭段遺址在暖泉農場六隊殘存一段,長約1千米,渠寬約35米,深1~2米,渠堤高1~2米;平羅段遺址在崇崗鎮殘存35千米,經常青村、長勝村、九泉村、潮湖村等地,其中以崇崗村的一段保存較好,渠底寬30米,渠堤黃土夯筑,上寬15米,下寬25米,堤高3.5米,部分地段已被開墾成農田。通過上述縣區文物管理部門昊王渠遺址文物保護檔案的記載,可以明確昊王渠遺址的保存現狀及位置分布情況,便于開展田野調查工作。
4 田野調查中昊王渠遺址現狀
筆者在昊王渠相關文獻記載較為缺失的情況下,根據寧夏水利工程建設檔案及有關縣區文物保護檔案資料,結合1945年實測1/200000寧夏青銅峽河西灌區圖k和1985年實測1/250000寧夏引黃灌區現狀圖(青銅峽灌區)l中標注的昊王渠遺址的位置和走向,對現存昊王渠遺址重新進行了田野實地調查。調查確定昊王渠開口于青銅峽峽口地區,沿賀蘭山東麓地帶逶迤北行,依次經過青銅峽市、永寧縣、西夏區、賀蘭縣、平羅縣、惠農區,渠道整體長200余千米,其遺址渠線基本與現西干渠渠線并行,且略高于西干渠。通過實地踏勘,昊王渠比降合乎現代渠道建設要求,現有渠道遺址基本按照地形高低行走在半挖半填地帶,既節省了土方工作量,又簡化了工程布設,反映出昊王渠開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現存昊王渠遺址較少,大多渠段已遭到毀滅性破壞,多數被改造為農田,少部分或在開挖西干渠過程中變為西干渠渠道的一部分,剩余極少部分或因渠線位置較高,周圍土質較差無法改造為農田,或因處于山洪溝口邊緣地帶,得以保存下來。整體看,昊王渠遺址保存現狀不容樂觀,殘損情況較為嚴重,多以殘存狀態存續,大多僅依稀可見渠道形狀,其中以賀蘭縣暖泉農場段遺址(圖1)和青銅峽甘城子段遺址(圖2)保存狀態較為完好,渠道形制較為完備,渠底、渠堤部分清晰可見。經實地測量,兩段遺址殘存渠道寬約35米、深約2米,渠堤上寬約15米、下寬約25米。從建設規模看,昊王渠與今天寧夏引黃灌區的主干渠道唐徠渠、惠農渠等相比體量規格相差不遠,由此更能反映出一千多年前西夏對寧夏引黃灌區水利開發和建設的重視,受制于當時極度低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修筑南北貫通銀川平原的昊王渠,反映出西夏深刻認識到寧夏引黃灌區的重要性和發展農業的必要性。
5 昊王渠廢棄原因探析
昊王渠的開挖增加了西夏農田開發的面積,因其位于唐徠渠西北、賀蘭山東麓地帶,使唐徠渠灌溉不到的旱田變為沃壤,同時大量的荒田被開發出來,進而增加了糧食產量,保證了西夏軍民糧食儲備。這樣一條具有重要農田灌溉作用和軍事戰略意義的引黃主干渠道在西夏割據政權滅亡之后,相關史料記載基本空白,這和西夏沒有獨立的專門史有關,也與蒙古軍隊多次征討西夏時的破壞相關。昊王渠至遲到元代也被廢棄,沒有如唐徠、漢延等古渠一樣被繼續使用,我們不禁疑問為什么如此一條極為重要的引黃干渠會被廢棄?筆者根據田野實地調查結合西干渠水利工程建設檔案資料,經過考證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黃河河床下切,河岸不時崩塌,導致黃河主流搖擺不定,無法保證昊王渠渠口引水量的穩定性,尤其是在春夏之際農田灌溉需水量較大的時刻,這種需供水矛盾更加凸顯。同時由于黃河自身含沙量較大,引黃渠道泥沙淤積現象嚴重,致使自流引水的昊王渠渠口及渠道逐年抬高,出現引水困難的情況,以致渠道清淤工程量逐年大增,人力、財力、物力難以維系,遂造成昊王渠的廢棄。昊王渠渠線基本與西干渠渠線并行且稍高于西干渠,因1958年青銅峽水利樞紐的興建,抬高了黃河水位,才為西干渠的開挖創造了條件,從而保證了穩定的引水量,西夏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和科學技術,無法支撐其在黃河主河道上筑壩引水以抬高水位進而保證引水量,因此高渠線的昊王渠廢棄在當時也是必然的。二是賀蘭山東麓山洪危害,觀察1985年實測1/250000寧夏引黃灌區現狀圖(青銅峽灌區)中昊王渠遺址跨越的地形,結合實地查勘,發現昊王渠沿賀蘭山東麓由南向北,穿越榆樹溝、馬圈溝、紅柳溝、插旗溝、大水溝等山洪溝近20條,每有山洪暴發勢必沖毀渠道。經過踏勘,發現凡山洪溝口處的昊王古渠遺址蕩然無存,現存遺址段基本位于山洪溝口邊緣或渠線較高地帶。20世紀60年代至今,為解除西干渠遭受賀蘭山山洪的威脅,沿西干渠靠賀蘭山東麓山洪溝口附近區域建造了20余處滯洪區,從而保證了西干渠渠道的安全。西夏時期幾無能力建造如此龐大的系列滯洪工程,昊王渠經過賀蘭山東麓多處山洪溝口地帶,直面山洪破壞是必然且常規的。三是戰爭破壞,寧夏經歷蒙古軍隊多次征討西夏的戰爭,對當地社會的破壞尤為嚴重,經濟蕭瑟,人口大量銳減,寧夏引黃灌區水利灌溉事業衰敗,縱橫交錯的干支渠道遭到嚴重毀壞,農業一片荒蕪,繁榮富庶的寧夏平原幾成一片廢墟,在這種情況下,無人管護,渠道常年失修而遭到廢棄。
6 結語
本文通過挖掘歷史文獻和水利工程建設檔案,參閱文物保護檔案,結合田野實地調查的方法,對昊王渠這一個案進行學術考證,厘清了昊王渠的歷史脈絡,全面解讀了昊王渠的開挖背景、價值及作用,實地調查了遺址保存現狀,最后通過對比西干渠的現狀全面分析探討了昊王渠廢棄的原因,進而補全開展昊王渠相關學術研究的背景資料。寧夏引黃灌區2000多年的農田水利灌溉歷史中,大量留存文獻的古渠道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成為水利史研究的盲點,希冀通過昊王渠案例的學術考證為古渠道的學術研究提供參考范式,助推寧夏水利史研究的深度和寬度。
注釋
①吳忠禮,盧德明,吳曉紅.塞上江南:寧夏引黃灌溉今昔[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21.
②楊新才.寧夏農業史[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113-117.
③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10831.
④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2568.
⑤陳育寧.寧夏通史[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130.
⑥胡汝礪.嘉靖寧夏新志[M].管律,重修.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15.
⑦汪繹辰.銀川小志[M].張鐘和,許懷然,校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36.
⑧胡汝礪.嘉靖寧夏新志[M].管律,重修.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383.
⑨《寧夏水利志》編纂委員會.寧夏水利志[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177.
⑩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公布第一至第四批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的通知[J].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報,2017(16):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