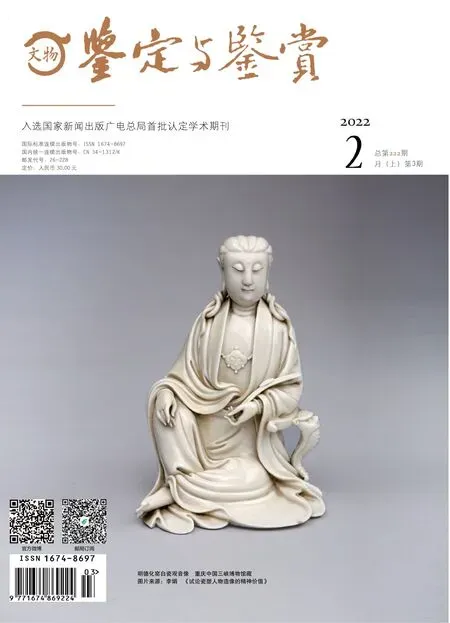北魏平城墓葬壁畫制作工藝研究
尹剛



摘 要:作為中古時期壁畫藝術的重要表現形式,墓葬壁畫因其載體的特殊性,繪制范式與傳統地上建筑壁畫有所差異。文章以北魏時期平城地區的壁畫墓葬為研究對象,主要通過兩方面內容對其進行了研究:首先,從工藝上對現有的平城墓葬壁畫進行分類,明確其制作流程;其次,具體分析它們在繪制過程中的技法,包括選用材料、繪畫技術、構圖等。
關鍵詞:北魏;平城時代;壁畫墓;壁畫工藝;地仗層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3.044
一般來說,壁畫是指在人工建筑物壁面上繪制的圖畫,可以分為寺觀殿堂壁畫、石窟壁畫和墓葬壁畫三種類型。北魏平城墓葬壁畫的物質形態主要表現在壁畫結構、繪制技法和位置分布等三個方面,它們也共同反映了北魏時期平城時代大同墓葬壁畫的制作工藝狀況。大同北魏時期墓葬壁畫在中國繪畫史、考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它們的物質狀態既表現出其制作情況的時代特點,又集中代表了中國古代壁畫發展史上北魏時期墓葬壁畫制作的總體水平。
1 墓葬壁畫的工藝結構
從山西大同現已發現的北魏平城時代墓葬壁畫的結構來看,可以將它們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的壁畫結構只由支撐體和顏料層兩部分構成,這是中國古代壁畫結構的最小組成形式,如以北魏宋紹祖墓為代表的6座石槨壁畫墓的壁畫結構以及以大同陳莊北魏墓前室四壁為代表的1處墓室壁畫結構。前者的壁畫結構只有兩部分,分別為石質材料構成的板壁支撐體和紅、黑、白等幾種顏料構成的顏料層;后者的壁畫結構也是由兩部分構成,分別為條磚壘砌而成的磚壁支撐體和紅色顏料構成的顏料層,如大同陳莊北魏墓中前室四壁角落處的仿木結構建筑壁畫(圖1)。
第二種情況的壁畫結構由支撐體、底色層和顏料層三部分組成,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只在大同陳莊北魏墓中前室北壁甬道門框處的壁畫結構中得以發現,它以磚構墻體為支撐體,以涂抹其上的白色石灰層為底色層,然后以紅色顏料繪制的交龍圖案為顏料層。
第三種情況的壁畫結構由支撐體、地仗層和顏料層三部分構成,這種結構是中國古代壁畫最基本的構成形式,因此被普遍應用于大同8座北魏壁畫墓(陳莊北魏墓前室四壁的仿木結構建筑壁畫除外)的壁畫制作中。具體來說,由于地仗層的材質不同,這種壁畫結構又可以進一步細分成三種情況:
其一,以磚構墻體為支撐體,于其上先涂抹一層厚度不等的黃泥作為地仗層的粗泥層,然后在粗泥層上涂抹厚度為0.5厘米左右的石灰層作為地仗層的細泥層(當然,這種白色的細泥層同時也是底色層),最后在白色細泥層布置紅、黑色的顏料層。此種壁畫結構形式僅僅為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畫墓所采用(圖2),大同其他7座北魏壁畫墓沒有發現,如簡報所說“壁畫地仗層分為兩層:第一層為草拌泥直接涂抹在磚上,厚0.3~0.5厘米;第二層為白灰,涂抹在草拌泥之上,厚0.2厘米”①。
其二,以磚構墻體為支撐體,其上涂抹1厘米左右厚度黃泥作為地仗層的細泥層(這種黃色的細泥層同時也是底色層),然后其上覆蓋紅、黑、白三種顏色的顏料層。這種形式的壁畫結構也只僅僅于梁拔胡壁畫墓中得以發現,如簡報所說“其制作方法是先在磚墻上抹厚約1厘米的黃泥,然后直接在黃泥上彩繪”②。
其三,以磚構墻體為支撐體,以一層厚度不等的石灰層作為地仗層,它同時也是底色層,再在其上繪制最多由紅、黑、藍三色構成的顏料層。這種形式的壁畫結構使用最多,如迎賓大道、沙嶺、云波路、華宇二期、懷仁丹揚王等5處壁畫墓以及大同陳莊后室墓頂壁畫都是如此結構。
除去其他諸如環境、工藝、外力等因素影響外,以上三種類型的壁畫結構對墓葬壁畫保存過程中穩定性程度具有重要的影響。從大同北魏墓葬壁畫出土時的保存情況來看,不同結構的壁畫出土時保存情況實在是天差地別:
第一種壁畫結構,由于石質板壁支撐體的粗糙壁面和帶膠顏料層之間具有較好的粘結力,壁畫一般保存較好,但是由于壁面光滑處顏料層的吸附力較弱,或者顏料層中膠性物質的膠結力喪失,極易形成顏料層脫落病害,導致畫面模糊不清。保存情況較差的例子如北魏宋紹祖石槨壁畫,顏料層幾乎脫落殆盡。相對來說,保存較好的如大同陳莊北魏壁畫墓前室四壁交界處的仿木結構建筑壁畫,由于作為支撐體的磚構墻壁表面比石板表面更為粗糙,紅色顏料層與支撐體之間膠結良好,故畫面特別完整和清晰。
第二種情況的壁畫結構,盡管制作時石灰底色層與磚構墻壁表面之間能良好吸附,顏料層與底色層也能緊密膠結,但如果底色層過厚,則由于石灰底色層非常容易鈣化而成片脫落,從而引起顏料層脫落,故而會造成壁畫畫面缺失,如大同陳莊北魏壁畫墓前室北壁甬道邊緣的交龍壁畫就是如此。
第三種情況的壁畫結構,由于地仗層的材質不同,其壁畫保存情況更是千差萬別。以黃泥和石灰作為地仗層中粗、細泥層的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畫墓壁畫,由于水的作用,黃泥極易軟化并進而形成空鼓病害,從而造成壁畫大面積脫落;以黃泥作為地仗層中粗泥層和底色層的大同北魏梁拔胡墓壁畫,由于黃泥遇水容易脫落、受潮則容易粉狀脫落,從而造成壁畫脫落。同上述情況相比,盡管也有由于外力、環境和工藝等因素造成的壁畫大面積脫落,但是以磚構墻體為支撐體、以石灰層為地仗層和底色層的墓室壁畫,由于支撐體和地仗層、地仗層和顏料層之間吸附良好,且石灰層比較不易變軟脫落,因而保存狀況比較理想,大都具有畫面比較完整、色彩比較清晰的特點。因此,采用這種壁畫結構的墓室壁畫墓就比較多,如大同迎賓大道、沙嶺、懷仁丹揚王、陳莊、云波路、華宇二期等北魏壁畫墓,而且這種結構技術一定也是當時匠人在繪畫實踐中不斷摸索的成果。
2 墓葬壁畫的繪制技法
對于魏晉南北朝繪畫的歷史定位,陳綬祥先生在《魏晉南北朝繪畫》一書中做出了恰如其分的總體判斷,其文曰:“在中國美術史上,由于出土遺物的不斷增加,一般把秦漢時期確定為中國繪畫取得長足發展的時代,而魏晉南北朝則是繼其后極富變革意義的時期。這種變革除了因精神領域個性自覺而導致的士人參與繪畫,從而開始出現了繪畫的文人化以外,匠工繪畫及民間繪畫也因外來美術樣式的大量傳入,從而在繪畫題材、造型觀念以至描繪技法等方面都在進行著一場模擬、容納、吸收、同化等的變革過程。”③gzslib202204051940基于陳氏上述定位,從大同發現的北魏壁畫墓的繪制技法來看,作為當時平城匠工畫家的代表作品,對比此前歷史上繪畫的描繪技法,可以發現其在繪畫材料、繪畫技法和繪畫構圖等方面更多的是對歷史描繪技法的繼承或模擬、容納,似乎很少有對外來美術樣式的吸收或同化。
首先,從繪畫材料來看,大同北魏墓葬壁畫幾乎同漢代墓葬壁畫的繪制一樣,“都以毛筆為工具,以墨為主要材料,使用化學性質穩定的朱、綠、黃、橙、紫、青、白等色礦物質顏料”④。只不過,集中大同北魏墓葬壁畫的顏色來看,其在壁畫用色上遠遠沒有漢代墓葬壁畫所采用的顏料豐富。大同北魏墓葬壁畫中,墓室壁畫的顏色基本局限于紅、黑、白三系之內,如云波路墓室壁畫墓、云波路華宇二期壁畫墓和文瀛北路壁畫墓(圖2),即使細分其顏料也最多不過為朱、黑、橙、白四種,如沙嶺北魏壁畫墓(圖3)、和仝家灣梁拔胡墓室壁畫墓;石槨壁畫的色系同墓葬壁畫一樣,幾乎也逃不出紅、黑、白三系,如宋紹祖石槨壁畫墓、張智朗石槨壁畫墓、智家堡石槨壁畫墓和富喬發電廠石槨壁畫墓。但是,在解興石槨壁畫墓中似乎在紅、黑、白三色之外還發現了粉色。
其次,就繪畫技法來看,大同北魏墓葬壁畫絕大多數繼承了秦漢時期墨線勾勒輪廓再平涂色彩的手法⑤,這在大同北魏墓葬壁畫中幾乎處處可見。此外,東漢晚期那種大筆揮灑的寫意法以及不勾輪廓而直接施色的沒骨法、單色線勾和白描法⑥在大同北魏墓葬壁畫中也屢次發現,如云波路華宇二期墓室壁畫墓西壁、云波路墓室壁畫墓中人形忍冬紋,再如云波路墓室壁畫墓南壁的主畫面以及文瀛北路墓室壁畫墓北壁和東壁上的幄幔、星斗等,都是采用漢代畫史上已經存在的寫意法和沒骨法繪制而成;文瀛北路墓室壁畫墓北側棺床臺階上的蓮花、棺床側面上的胡人牽馱和力士,則完全是繼承漢代的單色線勾和白描法進行繪制的。
最后,以繪畫構圖來看,大同北魏墓葬壁畫基本上承接漢代墓葬壁畫的構圖模式,即“在構圖上,擺脫了周秦以來呆板的圖案式橫向排列的形式,開始講究比例和透視關系。有的鋪天蓋地,滿壁飛動,極力表現廣闊的時空和盛大的場面(圖4、圖5);有的則均衡疏朗,無須背景,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精細描繪復雜而微妙的性格特征”⑦。大同北魏墓葬壁畫無論是墓室壁畫還是石槨壁畫,以墓室壁畫而言,通常在墓室的穹隆頂壁、墓室四壁和甬道壁面上布滿壁畫(圖6),而石槨壁畫通常在石槨外壁和內壁也是滿壁壁畫,都體現了漢代墓葬壁畫的構圖模式。
總體來看,北魏平城時代墓葬壁畫的繪制技法基本是漢代墓葬壁畫描繪技法的繼承,此時期體現在石窟壁畫和文人繪畫中的佛教美術樣式以及由此產生的諸如游絲描、鐵線描、張家樣、曹家樣及所謂凹凸暈染法,在大同北魏墓葬壁畫中都沒有得到體現,這說明北魏平城時代繪制墓葬壁畫的匠工繪畫與同時期的文人繪畫在藝術風格上存在巨大的差異性。
注釋
①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1(12):27.
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灣北魏墓(M7、M9)發掘簡報[J].文物,2015(12):12.
③陳綬祥.中國繪畫斷代史:魏晉南北朝繪畫[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