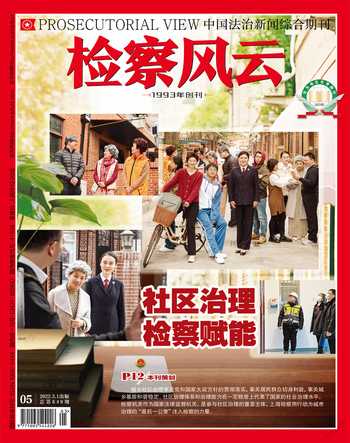秋笳余韻:流放生涯的詩和遠方
宋偉哲

流刑完全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之中 (圖/網絡)
“流放寧古塔,永世不得入關”,這是清宮劇中常能看到的一句臺詞。觀眾們雖能大致曉得劇中臺詞的含義,卻也不免有些云里霧里。被流放到那里的人命運最終如何?隋唐以來,流刑與死刑、徒刑、杖刑、笞刑一并組成了一套完整的刑罰體系,也就是耳熟能詳的“五刑”。五刑之中,死刑、徒刑被沿用至今。杖刑、笞刑雖被廢除,但也不難理解。唯有流刑完全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之中,充滿神秘色彩。清朝時期,位于東北邊疆的寧古塔的確曾長期作為重刑犯的流放地。順治年間,江南才子吳兆騫蒙冤獲刑,流放寧古塔,一去就是二十三個春秋。在這期間,他筆耕不輟,寫下了大量壯麗的詩篇。這些激揚文字既奠定了吳氏在清初文壇的地位,也為后世了解流放寧古塔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在中國歷史上,許多賢臣名士都曾遭受流放之刑,屈原、蘇武、李白、蘇軾、紀曉嵐、林則徐……不可勝數。有趣的是,正是這段悲情歲月的磨礪,鍛造出了流人們堅毅的品格。今人津津樂道的千古名句,有許多都是出自流放的遠方。但流刑畢竟是一種僅次于死刑的殘酷刑罰,在名句背后更多的是淚水、無奈與辛酸。早在先秦時期,流刑就已經成為一種刑罰措施。《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楚國詩人屈原,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流人。楚王不聽他的忠言苦諫,還聽信讒言將屈原流放。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寫下了不朽詩篇《離騷》。
秦漢時期,流刑制度有了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時期,居于徒刑之上、死刑之下的刑罰是肉刑。但是在法律實踐中,不少犯人被送到邊疆,從事戍邊工作,這又與一般意義上的流刑十分類似。漢朝南征北戰,使用了許多流刑犯人作為戰士。比如《漢書·武帝紀》載,“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流刑不同于后世的流刑,它并沒有成為刑罰中的主刑,故而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有“秦漢以降,未有流刑”的論斷,也有一定道理。隨著法律文明的演進,立法者愈發認識到肉刑的殘酷,于是在南北朝時期,流刑再次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逐漸取代肉刑成為僅次于死刑的法定刑。
隋唐時期,中華法系日臻成熟,朝廷確立起了五刑二十等的刑罰體系。唐太宗即位后,制定《貞觀律》,這次修律把隋代舊律中的九十二條死罪降為流刑。與此同時,唐太宗還廢除了此前“斷趾”肉刑,改為“加役流”。上述流刑立法是貞觀之治仁政的重要體現,受到后世高度贊揚。根據《唐律疏議》所確立的刑罰體系,流刑一共分為三種,分別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史稱“三流”,俱于流放地服勞役一年。丈夫流放,妻妾必須一同前往,不得以“七出”為由逃避。前文所提的“加役流”,則需服役三年。服役期滿或者遇到朝廷大赦,流人即可在流放地申報戶口定居,不得返回本鄉。這套流刑體系確立之后,宋、明、清等朝基本沿用,還增加了部分閏刑(輔助刑)。清朝乾隆年間,為了規范流刑的實施,糾正“趨避揀擇”之弊,朝廷制定了《三流道里表》《五軍道里表》,詳細列明了全國各府罪犯的流放地,保證了執法公平。
縱覽各朝流刑,因為疆域面積大小不同,流放地也大不相同。宋朝疆域面積很小,因此許多犯人只能流放到南方海島。清軍入關之后,東北地區的滿族人口大量南遷,當地變得更加荒涼。作為苦寒之地,又是滿族故鄉,因此清初統治者非常愿意把漢族罪犯,特別是知識分子罪犯流放到這里來。當時,東北地區的流放地有很多,比如盛京(沈陽)、尚陽堡、卜魁(齊齊哈爾),最負盛名的當屬寧古塔。清朝平定準格爾部叛亂之后,新疆又成為新的熱門流放地,一代才子紀曉嵐、民族英雄林則徐就都曾流放新疆。本文的主人公吳兆騫,就是較早一批流放寧古塔的文人“罪犯”。
吳兆騫(1631—1684),字漢槎,號季子,江蘇吳江人。順治十四年(1657),吳兆騫參加江南鄉試,高中舉人。對常人而言,金榜題名意味著可以改變命運,吳兆騫也的確因為這場考試改變了命運。不過這次命運的改變帶來的卻是厄運。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就在鄉試放榜之后,突然傳出主考官方猶、錢開宗等人舞弊受賄的訊息,導致物議沸騰。其中中舉人方章鉞乃主考方猶同宗,又系四品京官少詹事方拱乾之子。順治帝聞之大怒,命人將方氏逮捕進京審訊,同時要求中舉士子一并來京復試。
第二年初,吳兆騫抵京,幾天后便被投入駭人聽聞的刑部大獄。原來,江南總督郎廷佐將吳兆騫列入了“顯有情弊”的八名舉子名單。審訊時,吳兆騫等人拒絕承認舞弊,清廷一時也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此案年代久遠、史料缺失,但是從有限的資料并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綜合分析,此次科場案件,的確有舞弊應受懲者。但是對吳兆騫而言,應系冤案無疑。一方面,吳兆騫在江南之時,曾加入吳江的文社慎交社。當時吳江有慎交、同聲兩大文社,雙方的矛盾十分尖銳。吳兆騫身為慎交社的風云人物,同聲社的人對他恨之入骨。據吳兆騫日后家書自述,此案很有可能是同聲社的章素文、王發等人陷害。
就在吳兆騫被關入刑部大獄后不久,順治帝即親自面試此次江南鄉試中榜的舉人。這場考試可謂非比尋常。史載,“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堂上命題,二書、一賦、一詩,試官羅列偵視。堂下列武士,鋃鐺而外,黃銅之夾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在這種氛圍下,士子們內心感到極大的屈辱與恐懼,大多兩股戰栗,毫無文思。吳兆騫也奉命參加了這次考試。可能是因為過于緊張,加之此前在刑部大獄飽受折磨,導致其狀態奇差,最終竟然交了白卷。接下來他的命運可想而知。順治十五年十一月,皇帝欽定此案,正副主考方猶、錢開宗等人被處以絞刑,妻子家產沒官。吳兆騫、方章鉞等八名舉子僥幸逃過一劫,在挨了四十大板后,被判流放寧古塔。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初三日,吳兆騫等人踏上了流放寧古塔之路。所謂寧古塔,即今天黑龍江省寧安市。路過山海關時,吳兆騫被雄偉壯麗的關門所震撼。關門向東大路旁有一山嶺,出關者謂之凄惶嶺,入關者謂之歡喜嶺,令人百感交集。不到一個月,吳兆騫一行即抵達沈陽。在這里,吳兆騫見到了許多流放遼東之人,互訴衷腸,留下了大量詩篇。當時的東北人煙稀少,山嶺之間常有野獸出沒,路程極為艱辛。路途之中,獄友吳蘭友不堪顛簸折磨而逝,吳兆騫也曾大病一場。七月中旬,一行人終于抵達寧古塔。寧古塔主管巴海對這些漢族知識分子非常尊重,盡量予以妥善安置。寧古塔土壤肥沃,物產豐富,山肴野蔌極佳,任人自取。一般流刑犯人至此,大多從事耕種等業,勞役甚苦。當時,這一地區的漢人非常稀少,而當地少數民族人民耕作技術比較落后。隨著大量漢人流放至此,不但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技術,還繁榮了當地的商業。吳兆騫一介書生,不善耕種,便以教書為生,流人子弟們成了他最初的學生。后來,巴海將軍聘吳兆騫為書記官,為自己出謀劃策,同時教授自己的兒子讀書。就這樣,中原文明在冰天雪地的關外開花結果。不久,妻子葛氏從江南萬里來伴,又給吳兆騫生下一兒兩女,他們開始了新的生活。
寧古塔的歲月充滿凄涼,但邊疆的大好河山也激發了吳兆騫的無限詩性,使他留下了大量佳作名句。吳兆騫流放之時,恰逢沙俄侵犯我國黑龍江區域。清廷下令反擊,寧古塔軍民同侵略者展開了英勇搏斗。身為流人的吳兆騫也不例外,他不但積極參與備戰,還寫下了大量的抗俄詩篇。雖然身處邊關,吳兆騫卻同中原故友保持著密切的書信聯系,他的詩作也得以傳播海內,名滿京師。不但著名詞人、同時也是當朝重臣納蘭明珠之子的納蘭性德對其詩作欽佩萬分,就連康熙皇帝也被他那長達千言的《長白山賦》所深深震撼。康熙二十年(1681),在納蘭性德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已經五十歲的吳兆騫終于得以贖金赦歸,并在納蘭性德家教書為生。三年之后,吳兆騫在北京去世,留下一部《秋笳集》,向后人訴說著流放寧古塔歲月的詩和遠方。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