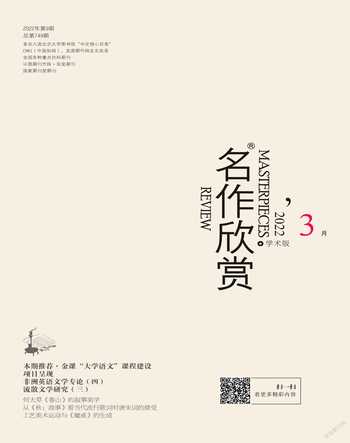《中庸》天命思想淺析
摘要:本文通過對《中庸》中原文進行分析,得出其中所蘊含的天命思想。在此基礎上試圖對其進行解釋,進而與當今生活展開聯系進行討論。
關鍵詞:《中庸》天命自然
一、概述
《中庸》作為四書之一,是中國儒學正統思想的集中體現。誠然,儒家經典當中不乏真知灼見,確有許多值得我們今人學習的地方。筆者認為其中也有許多有歷史局限性的糟粕,隱藏在傳統文化之中而得以一直以流傳至今,在《中庸》篇中體現為天命觀念。
在《中庸》中,天命規定了人應當所是。每個人都有一個應該成為的樣本,其曰“圣賢”。圣賢之所以為圣賢,是因其順承天命,因天命而動,自己的意識行為通過在世的修行,完美地迎合了天命道德的所有要求,孔子所謂“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便是這種境界。但從人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的觀點看,這無疑是一種對人生可能性的拒絕,是一種對先天道德理性的過度強調。通過天命對人的規定,人失去了他的可能性,他要么一生效仿圣賢,要么“棄圣絕智,絕仁棄義”。這樣先天的預設性,使得儒家中的人不再是一個有待完成之物,他的終點不再是死亡,而是內圣外王,成為一代圣賢。
當然,不能否定的是天命觀念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本文以朱熹編著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文本,從朱熹的解讀以及子思所闡述的天命觀點出發,結合《論語》所體現出來的儒家經典的鬼神觀,對儒家的天命觀念進行淺析,以求對其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與認識。
二、天命觀念
(一)朱熹序中所體現的天命觀念
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朱子為子思所作《中庸》作序,開篇明義: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朱子認為,人自出生便有“道心”,即所謂對世間人倫物理的判斷,是一種天賦觀念,一種先天映射,其不待學而知,不待行而能。同時,世間萬物紛雜,縱使人生來澄明,如菩提之樹、明鏡之臺,一旦與世界產生聯系,總會沾染世俗煙火之塵埃,即所謂原初的“道心”被所謂“人心”所遮蔽和掩蓋。以至于當我們被“道心”所呼喚的時候,由于不同的“人心”,便會有不同的反應,或淡然處之,或憂慮不安。然而,“人心”“道心”的矛盾時時刻刻在我們身上體現著,為了達乎“道心”,朱子指出:
靜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于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由此可見,在朱子看來,“道心”恒常,“人心”各異,而人生的終極目標便應為去“人心”,存“道心”,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不斷追求人們內心本然之物,而竭力洗去世俗之塵埃,以求“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
同時朱熹又強調道:“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
這里的“理”,可以理解為“道心”,即統籌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理。事無巨細,皆離不開其中,在需要時它自會顯現,是每一個人的良知良能;而不用時它自會收歸內心,人們沒有意識到“道心”的存在,實際上確已經完成了“道心”的要求,是一種合目的的目的性。
(二)《禮記·中庸》中的天命觀念
《禮記·中庸》一篇中對天命的討論夾雜著許多關于現世、人生的討論,以及如何達到天命的方法探討,但從天命這一關鍵詞來看,并不能很好地概括《禮記·中庸》篇中的全部天命觀念,故下文將從幾個方面分別對天命進行闡述。
1.天命思想概述
子思開篇便提綱挈領地提出了天命的具體觀點:“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朱子解為命令,是一種先天的制約萬物運行的規則,是萬物之所以為萬物的基本道理。人之所以成為人,離不開天命的規定,人的所有本性也全部來自天。人之性,也就是天命之性,由此,人得到了自身的基本規定。
在第二十一章中,子思又一次提出了“性”:“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這里的“誠”,可以理解為誠心。從心中明了天命,是一種悟性,是一種人內在的天性,有的人天性使然,出生便能明白天命的要求,這種悟性便叫作人的性。在《中庸》全篇中都將先天對天命的悟性以及通過后天理性而對天命產生判斷的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進行比較。即使先天存在差異,但在實現天命的層面上,是可以通過后天的修行來彌補的。正所謂:“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離開人的視角,天命的具體內容也是在天運行的內在規律中所體現出來,這是一種生生不息、化育萬物的意志。“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這當中的“天地之道”“天”,皆是天道生生不息、四時運作的結果,而天道正是天周而復始、永不停歇的體現。日月星辰的運行,萬物的生死興亡也都依賴于天。
至此,從人與天兩個角度對天命進行分析可知,對人與天來說,他們共同的本質就是“誠”。天道所謂至誠不息,人性也即是如此。為了符合天命,人應當在人生中不斷進行修行,在物我關系中展開自己,從而不斷地向天命靠近,以求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使得自己內在本能的要求與外在天命的要求達乎一致。
2.天命思想的體現
《中庸》中也有對天命的具體描寫,勾勒出了一些天命觀念的特征。
首先是天命無處不在的特征:“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天命的規定海納百川,包容萬物,至廣袤無邊而不能為之所破,至渺小細微也不能窮極之盡。簡而言之,就是天命的體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它是萬物的規定,是一種終極的原因。然而它也不是什么虛無縹緲之物,總是能在平常之中得到體現,即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或者天命總是離不開人世的。這里的遠人,應當理解為不離開人的日常而存在。從天命的體現不難看出,《中庸》中的天命并不是與此世對立而在的,它不是一種彼岸世界以求的對此生的超越。它是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是一種積極入世之學。
3.時中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天命有如上種種規定,廣泛存在于人世的各個角落,但不能將其理解為機械的、一對一的,是一成不變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所謂“時中”,便是雖時而中,根據不同的場合可以有不一樣的體現,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以一種動態的、不斷變化的態度看待問題的觀念。
三、儒家的鬼神觀
與許多宗教所相信的彼岸世界不同,儒家在理性認識上堅持將目光放在此世上,主張關注此世日常生活,這在《論語》中有許多體現,如:“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極力避免有關鬼神的討論,可能與康德對上帝的態度有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即鬼神并不是一個理論層面上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不需要在這一層面上對其進行過多討論,而應當把對鬼神的態度轉移到現實中來,考察其對現世的效用,所謂鬼神在實踐中的意義。這便離不開儒家所極力倡導的禮與教化:“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鬼神在儒家學說那里,更多是起到一種道德上的教化作用,是為禮而必要的觀念。“慎終追遠”,即是喪禮,其最終的目的,便是教化民眾,達到儒家對人民的要求。孔子之所以如此,離不開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周朝“禮崩樂壞”,諸侯禮法混亂,在孔子看來是導致時局動蕩的原因。“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孔子便借鬼神之名,以達到重建周禮的目的,所謂“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四、《禮記·中庸》天命思想淺析
與荀子所謂“制天命”中將天命作為一種手段不同,《中庸》所體現出來的天命觀更多是作為一種目的,是一種人生的終極目標。天命具有一種無限的特性,它統攝萬物,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它又是實踐理性的最高要求,是一種社會對道義的基本要求。天命的這兩個特點使人對其產生敬畏的“崇高感”,但這種敬畏的“崇高感”與康德的“崇高感”不同,可能與康德所論“美”更為接近。
康德所謂“崇高”,是由于主體想象力對客體的“無形式”的失敗重現,而導致轉向理性,使得想象力與理性中的理念形式相和諧。而《中庸》中的天命觀念,顯然不是一種對“無形式”的判斷。當我們在討論天命的時候,首先是一種秩序,是一種貫徹社會的道德觀念,是一種對社會公義的追求。這種觀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早已成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儒家所倡導的順天命而為,即是一種無意識中的合目的性,這是一種審美的判斷,而非崇高的判斷。這種對無意識的合目性的敬畏與對客體的“無形式”的敬畏不同,前者是現成的、既定的;而后者是外化的、無限的、不定的。前者是一種漫長的社會教化過程,所謂天規定人所應是,應該糾正為社會規定人所應是。而這種社會思想,也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或多或少會帶有個人偏好,在以前便是為封建統治服務,如今便是扼殺了人其他的可能性。
《中庸》第十七章有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定其壽。”這是一種對人的規定性。大德之人何必一定為官?幸福又是否一定要建立在物質基礎上呢?這種敬畏之情一旦被確定下來,就會通過教育得以傳承。在以前是八股取士,現在則是教育的目的化。韓軍將這歸結為對個性的絕禁,制定特定的公共話語體系,以及永遠的升華等幾個方面。
除其偽圣化的一面外,目的化的一面更是對馬克思所言“人的全面發展”的完全背離。要試圖解釋該目的性對人的背離,不得不從人的精神狀況開始分析。對此,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中有著精彩而又帶有溫情的論述:“實際上,神經錯亂的人就是那種完全無法同他者建立任何聯系的人……與其他有生命之物結合在一起,與他們相關聯,這是人的迫切需要,人的精神健全有賴于這種需要的滿足。”我們由于覺醒而與自然分離,便意識到了此生在世的孤獨之感,因此便迫切地想要與外界建立聯系。因我們無法“回到子宮”,退回到精神產生之前的狀態,而只得被迫與他者展開聯系。弗洛姆給出了幾種可能的與他者結合的方式:“順從(如信仰宗教、加入團體組織)或者統治(順從者的對立面)。”而對這些種種途徑進行分析,弗洛姆指出:“人只有一種感情能夠完美地滿足與任何世界結合的需要,同時保持人自身的完整性和個性,這便是愛。”他總結道:“愛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獨立與完整的情況下與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結合在一起。愛是一種參與和交流的體驗,它促使人充分發揮自己的內在能動性。愛的經驗使人不再需要幻想,人無須抬高他人或自己的形象,因為主動與人共享和互愛的現實使人超越了個體性的存在,同時也使人體驗到自己也會主動地產生愛的力量。”
而弗洛姆所言的“愛的能力”在帶有目的性的教育中被弱化以及扭曲了。在目的性如此強烈的今天,我們不再是為了愛的能力而接受教育,更多的是為了在物質交換中占領優勢地位。本該服務于我們的物質,用來提升我們幸福的金錢,在整個社會的文化心理上卻成為成功的唯一依據,這不正是馬克思所言“人的異化”嗎?
由此看來,我們在感慨天命所闡發的關于自然、宇宙奧秘的同時,也應該時刻保持一顆警惕之心,防止其滲入我們思想深處,產生種種不利的后果。
參考文獻: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 王世巍.孔子“天命”論的人格教育啟示——以西方崇高理論為鑒[J].大學教育科學,2017(3).
[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4] 韓軍.限制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關于中國現代語文教學的思考[J].語文學習,1993(1).
[5] 韓軍.反對“偽圣化”[J].教師博覽,2000(2).
[6] 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作??? 者:?????? 周子龍,同濟大學在讀本科生。
編??? 輯:?????? 曹曉花E-mail: 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