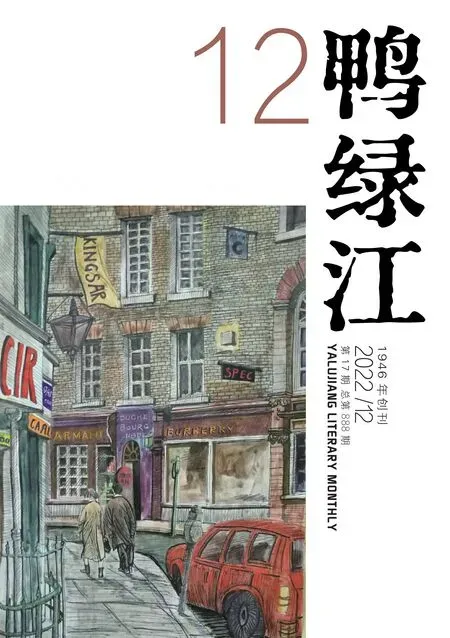師骨(短篇)
海東升
1
正如馬老師的烏鴉嘴所說,劉老師掉進了自己講的馬里亞納海溝。
但此時的劉老師并沒有意識到,所以他對自己辦公桌上的那張A4 打印紙,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直到張陽在他背后一喊,他才摸出衣服口袋里的花鏡,仔細看看,是國家工作人員登記表。
劉老師回身,對張陽說,你說啥?
張陽最近很怕劉老師的眼睛,簡直是兩個滾成團的刺猬,針尖一抖一抖地往外翻。在她的記憶里,劉老師的眼睛里只有馴鹿。但現在,溫情的馴鹿遠遁了,搖身一變,成了看著溫順但隨時可能出槍的刺猬。盡管她是年級組長,也不敢對劉老師造次。距離劉老師退休的日子還有一個星期,劉老師眼睛里的刺,抖動的頻率越來越密。張陽生怕這些刺扎到自己,就把聲音盡量壓到劉老師舒服的量級。
我說,就差您了,今天三點鐘之前必須交,否則,后果自負。
劉老師站在張陽的旁邊,一個左轉身,把右耳朵對著張陽。
比劉老師小兩歲的馬老師笑了。這是啥造型啊,鬼步舞?
沒工夫跟你閑扯,張陽她們跟我待的時間短,咱倆都是一輩子的老哥們兒了,你不知道我的左耳朵背嗎?
我哪兒知道你耳朵背。
劉老師又一個右轉身,正面對著馬老師,嘿嘿一笑,我說老馬,我原以為你只是膝蓋疼,我這出去上了三節課,咋的,你的記憶也瘸了?
幾個女老師都偷偷地抿嘴笑。在這個辦公室里,劉老師比馬老師大兩歲,在一起三十多年,兩個人的關系好,總是說笑話。另外幾個歲數小的,不好意思接話茬,但他倆的笑點太多,不能不笑,只能不出聲地笑。
馬老師說,你咋也上三節課?我以為就我命苦呢,原來咱們兩個難兄難弟,是同病相憐。咋的,你這副科(婦科)也去學習呀?
劉老師說,我這地理是副科(婦科),你那生物是前列腺科,是大縣的科唄?
辦公室里,年輕人都很少開玩笑,只有劉老師和馬老師在閑暇時偶爾開點玩笑,但只是聽的人笑,他們兩個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一點不笑。但今天倆人卻不謀而合地笑了。因為跟語文、數學、外語、物理、化學這幾科主課相比,地理和生物都趕不上思想品德、歷史受學生重視。思想品德和歷史,背背就能拿高分。而地理和生物就不同了,說是文科,你光背是白扯的;說是理科的基礎,想回頭好好學學,卻到八年級結業了。所以在老師和學生的心里,這兩個雞肋一樣的學科當然屬于副科中的副科,而劉老師和馬老師也是弱勢里的弱勢,別的科都是一二三齊步走,從七年走到九年,可他們兩個只能是一二一踏步走,從來沒在九年級的辦公室里坐過。兩個副科老師在主科老師面前相互戲謔,苦中作樂,真是沒誰了。
你去嗎?馬老師問。
劉老師說,想不去,我怕補聽。
我怕補聽還行,你就差一個星期退休了,還怕個啥?
劉老師眼睛里的刺猬又活了,但馬老師不怕,多年的較量,身上早磨出了一層鎧甲。
我怕個啥?我是怕晚節不保。
馬老師還想說你有啥節可保呀?但一看劉老師是來真的了,就和往常一樣,來了個急轉身,和顏悅色地說,也對,善始善終。正經一輩子了,最后來個不正經,也不是您的性格。
張陽也在偷偷地笑,她偶爾也能在劉老師和馬老師開玩笑的時候,添點油鹽撒點醬醋。我說兩位大師,那我也說點正經的。你們手里有沒有二寸照片?
馬老師翻翻抽屜,說,我有。
您呢?張陽問劉老師。劉老師在四個抽屜里翻了一遍,只有幾張師生畢業照。我家里有,劉老師說,可我還有第四節課。
馬老師說,你可真是的,你對我們是不放心啊還是咋的?連個照片都往家里拿,也不嫌費事。這回好,反正你的腿也不值錢。
我就當鍛煉。咋的吧?憋氣?老馬,你給我上第四節課,咱倆換一下。
馬老師看看自己的課程表,不好意思,咱倆犯相,撞車。
真的假的?劉老師過來看馬老師的課程表。
我騙你干啥?要不換一節課能咋的?
一個剛上班不久的年輕老師對劉老師說,咱倆換吧。但劉老師,我想要,不還。
那不行。劉老師認真地說,缺一節,我兩個班就進度不平了,你必須還。
那我不要了。
張陽說,都別爭了,劉老師,我和您換,您這還有一個星期就退休的人了,咋還這么認真?
藏在劉老師眼睛里的刺猬說,一輩子的習慣,改不了了。
2
劉老師和主管副校長請假,還要去教導處拿假條。
劉老師走到教導處門前,不愿進入,他怕那七八個主任的眼光砸他。中小學合并,變成九年一貫制學校,老師增加了,劉老師他們以為課節會變少,但卻想錯了,他們想著來幫忙的妯娌,卻盼來了四個管理他們的婆婆。那些分散的小學負責人將近十個,小學部放不下,分給初中部一半,加上初中部原來的兩個主任,現在初中部教導處有七八個主任,坐在一個大辦公室里。這些主任里有劉老師熟悉的老同事,也有他教過的兩個學生。老同事不打緊,劉老師最不愿意見的就是自己的學生,好像坐在衙門里的縣令,表情嚴肅得很,讓人不知道是先落左腳還是右腳。劉老師有時候在想,他們做學生的時候,進辦公室見老師會不會也是自己現在的心情?
好在劉老師今天運氣不錯,剛要敲門,管假條的主任從里面出來,劉老師順利地拿到了假條。走出校門,劉老師感覺輕松多了。他家離學校不遠,有十分鐘的路,劉老師總是走來走去的,幾乎不開車。
從飯店門前走過,一股煎魚的香味隨風飄過來,劉老師的肚子咕嚕嚕響了起來,他才感覺到快中午了,早上喝的粥、吃的饅頭雞蛋已經消化沒了。劉老師加快了腳步,想趕緊拿回照片,還趕得上學校的午餐。
撲棱棱,一只公雞在追趕三個母雞中的一只,母雞蹲下,公雞踩到母雞的脊背上。這是相約美食這家飯店老板的父親養的幾只雞,自己不吃,也不讓客人吃。
一只小狗跑過去,它穿的紅衣服和腳上的粉色小皮鞋,打亮了劉老師昏花的雙眼。小狗可能以為公雞是在欺侮它的同類,張牙舞爪地趕跑了還沒完成任務的公雞。
過來,凈管閑事。
一個中年婦女從柏油路的另一邊跑過來,訓斥那只打抱不平的小狗。從飯店里走出來的兩男一女笑了,那個女人在和小狗的主人打招呼。小狗的主人,是一個小診所醫生的老婆。那個從飯店里出來的女人,劉老師也熟悉,是幾年前畢業學生的家長,劉老師教她兒子的時候,她總是和“偶遇”的劉老師說上一陣,但自從她的兒子上了高中,即使真正遇上,也幾乎沒有什么話。像今天,劉老師和她相差幾米,她都好像沒有看見,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從柏油路對面跑過來的醫生老婆身上。其實,那個診所醫生的手藝也不怎么樣,劉老師也知道兩個女人也不是關系特別熟,但那兩個同行的男人也在和醫生老婆套近乎,這就讓劉老師納悶。老百姓雖然都不想得病,但他們就是覺得醫生總是比老師有用。老師的作用是短暫的,但誰也保不準一輩子用不到醫生。按照劉老師這個歲數,如果是醫生,正是坐在專家門診里等著患者排大隊的年齡。但在學校正好相反。領導不想跟你說話,同事們不得不跟你說話,學生們看見你審美疲勞。去年,兩個不學習、一心談戀愛的學生,背靠墻,四條腿搭橋,坐在走廊里。劉老師下課回來,走在他前面的年輕女老師路過,兩個學生撤橋,放行。等劉老師走到跟前,橋,又搭上了。老頭,不讓過。劉老師真想踢飛他們。但現在,劉老師不敢。
好在家里真有幾張二寸照片。劉老師輕松取,輕松回。進校門,去門衛,簽回校時間,進到三樓的辦公室,還沒到吃午飯的時間。
劉老師進來,看見馬老師正在打印紙上往下撕照片。張陽下課回來,說,劉老師,向后轉!繼續往家走。
劉老師眼睛里的刺猬抖了一下,說,你也學壞了,也和老馬一樣沒正形?
張陽不敢面對針刺,對著墻上的石英鐘說,劉大師,我真不逗您,第一副校又發精神了。他又仔細看了一下教育信息網的通知,今天五點鐘截止,必須貼一寸照片。寫完表格、貼二寸照片的老師全都作廢,管考核的六主任給我打電話,等吃完午飯,讓我重新去取表。
馬老師把貼上去不久的二寸照片撕下來,問劉老師,你有一寸照片嗎?
沒有。好像家里有。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啊?
一較真兒,劉老師還真懷疑自己的記憶了。他反問老馬,你有嗎?
馬老師堅定地回答,我有。
3
在食堂扒拉幾口飯,趁著午休時間,劉老師趕緊回家。其實,從打馬老師問他有沒有一寸照片的時候開始,他就感覺家里裝照片的紙袋里好像沒有一寸照片,只有二寸照片。但他沒仔細翻看,也許是自己記錯了,以前的一寸照片不見得沒有吧?
劉老師急匆匆地走回家里,中午的太陽還真是狠毒,進到樓道時,臉上熱辣辣地疼。現在的臉,也沒有年輕時那樣耐曬了,除了臉皮松弛,還容易過敏。
他要開門。右手習慣地去摸腰帶上的鑰匙。平時連想都不用想的地方,現在卻摸空了。他緊張起來。
不會丟了吧?
他先看腳下,腳下除了地板磚,連一個煙頭都沒有。他又翻身上的幾個口袋,口袋里什么都有,就是沒有他要找的鑰匙。難道是丟在了路上?按他的習慣,頂多扔在辦公桌上。他給張陽打電話,鑰匙果然在自己的桌子上。
讓午休的學生送來?二十多年前還行,現在,連想想都是犯錯誤。讓張陽和老馬送來?他們還要和校長請假簽假條。另外,他們出來跑一趟,和自己再回去跑一趟,又有什么區別?
下樓,他才想起,自己的老婆在政府上班,離家很近。劉老師給老婆打電話,老婆雖然現在沒事,但在等著迎接檢查組,頭頭兒嚴令,誰也不許離崗。
現在看來,關鍵時刻,還是要靠自己,離下午上課還有半個小時,時間還寬裕,畢竟來去有二十多分鐘就夠了。
趁著午休時間還沒過,劉老師順利地拿到鑰匙,回家拽開裝照片的抽屜,仔細翻出來十多張二寸照片,下面,除了幾張過去的一寸二寸黑白底片,連一張一寸近照都沒有,你總不能用那些高中畢業的照片來代替現在的自己吧?
照片用時方恨少。但現在不是少的問題,是一張照片都沒有。
走到樓下,劉老師看看手機上的時間,是十二點半,距離第五節課還有十分鐘,明天學習換來的三節課怎么辦?他給張陽打電話,讓他把第五節課找個人換一下,課只要有人上,學習回來還可以補,但這張表格在下午三點鐘之前就要完成,否則后果自負。這也許是自己職業生涯中填的最后一張表格了,這個責任比天還大。
學校是不能回了,反正領導也知道自己回家找照片,那就索性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去照相館照幾張一寸照片,管他今后還用上用不上呢?
走到街上,太陽比剛才還毒。行人不多,很多單位還在午休,飯店里都挺熱鬧,都說這個小地方經濟不行,但餐飲業卻始終在為這個小城裝點門面。
劉老師此時的心情全在一寸照片上。烈日當空,連跑帶顛,他恨不得一步就能趕到照相館,所以街邊挪出的井蓋,他根本沒注意到,差點踢到旁邊站著的一個人腳上。
這不是劉老師嗎?井蓋邊站著的那個男人吹出一口煙,陰陽怪氣地說。劉老師在這個小城生活了三十多年,很多人認識他。
他抬頭看看和他說話的那個人,不但認識,還是一個村出來的老鄉。
井里又探出一個花白的腦袋,抬眼看著劉老師,說,這不是大侄子嗎?
劉老師一看,這個老頭兒也很熟悉,也是自己的老鄉,他們兩個都在自來水公司打工,刨溝、修井、接管路,樣樣精通。
老鄉見老鄉,自然應該親切,但劉老師對他們親近不起來。從村子里輩分上論,劉老師應該小一輩,叫他們孫叔、趙叔。但這兩個人沒有當叔叔的樣子,說話不受聽,所以,劉老師也沒有當侄子的樣兒,從來不說正經話。記得劉老師剛上班的時候,地方上開不出工資,趙叔在磚廠打泥脫坯,看著劉老師,問,一個月掙多少錢?劉老師說一百二。趙叔笑了,還念大學呢,還不如我這苦大力,干脆跟我上磚廠打泥、脫大坯得了。當時,劉老師年輕氣盛,根本不拿他的笑話當笑話,只當是對自己的貶損,真想撿一塊石頭削他,但劉老師的眼睛尋遍周圍,也沒有一塊可用的東西。
從井里爬上來的孫叔說,看你來來回回好幾趟了,你們老師可真清閑。
劉老師來來回回走得急,還真沒注意到井里的兩個人。面對孫叔的話,劉老師眼睛里的刺猬笑了,我上課的時候,你咋沒看見呢?老師就不許有事,老師就不喝水吃飯?
大侄子說話挺硬啊,現在是不是開五六千了?趙叔扔掉手里的煙頭兒,在地上一碾。
劉老師抖動針刺,笑而不答。
你們兩口子一個月過萬吧?
劉老師還是笑而不語。
孫叔說,你們老師多好啊,寒暑假,星期禮拜,一年才上幾天班?給你們三千都多。
劉老師如今已經不是二十多歲的時候,耳順之年的他,除了對方罵自己的父母,其余的奚落,什么都不生氣,也不想爭辯。
趙叔拿出煙,給孫叔,又給劉老師。劉老師說,不會。他抽回手,問,自己在家喝酒嗎?劉老師說,不喝。兩個人都笑了,對劉老師這種無趣的生活感到悲哀。
趙叔說,錢這東西,多了,喂驢,都不吃。
劉老師想走,他沒時間和他們磨嘴皮子。他的心里只有那一寸照片。
待一會兒,忙啥?
我還有事。
你都快退了吧?能有啥事?
兩個人以為劉老師是在敷衍他們,就一邊拽他,一邊說,哎,你這么些年,教了多少學生?
桃李滿天下。劉老師的針刺閃著光芒。
說你胖,你還喘上了。趙叔的老毛病又犯了。那我問你,你教出幾個大干部?
劉老師其實是不想和他們較真的,尤其是今天,真的沒心情和他們消磨時間,如果是平時下班,他倒可以跟他們斗一陣。但多年的社會經驗,讓劉老師學會了很多東西,嫉妒你的,都是和你熟悉的人,他們見不得你的好。他也教過這兩個人的孩子,但他們從來沒說過他的好,這樣的熟人,看著和你說笑話,但實際上這些話都是他們的心里話。這樣的人,給他們臉,就是對邪惡的奉迎。劉老師不可能像年輕的時候那樣想削他們,現在,井蓋旁邊就有管鉗子,但劉老師懶得去拿,用語言回應他們就夠了。所以,劉老師面對他們,就像面對不懂事的學生,他看著眼前這兩個快七十歲的人,說,一個都沒有。你們都這么大歲數了,還在打工,連個村主任都沒當上,你們的兒子、孫子,還能是大干部?
4
劉老師到了照相館,卻大門緊閉。
門上寫著電話號碼,劉老師打過去,沒人接。說實話,這個手機幾乎代替了相機的時代,照相館如果沒有婚慶之類的活兒支撐著,光靠照相,連西北風都喝不到。劉老師悻悻地往回走,看來這個小城里唯一的照相館是指望不上了。走在街上,門上的那個號碼給劉老師打過來,說是晚上五點才能回來。
看來,這個表格上貼照片的地方只能開天窗了。但這樣的表格,交和不交,都是一個后果,學校是不會收的。
劉老師開始注意路邊的復印店,能不能用手機照一張,在復印機上打印出來。學校有復印機,但沒有相紙,另外,也沒有彩墨。實在不行,就用A4 紙打一張黑白的一寸照,也比開天窗強啊!劉老師開始佩服自己的想象力了,看來自己的身體老了,但腦子還很靈光。
他忽然想起過去街里有一家店鋪,頭幾年還給人印大頭貼什么的,不知道現在這個店是否還有,那個店鋪叫什么QQ,還是什么瓢蟲的,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叫這個名字。管他呢?死馬當活馬醫吧。他開始按照自己記憶中的方向走。
隨著記憶中目標的臨近,劉老師的希望也在激增。他還是希望這個店在,哪怕它換了名,只要經營的項目還有印大頭貼之類的,就不會讓人失望。失望對于一個要跌進河里的人來說,是經受不起的。
老師記不住學生,但學生會記住教自己的老師。
當劉老師走進這個店鋪的時候,坐在電腦后面的一個中年男人緩緩地站了起來,隨著他腰身的挺直,劉老師聽到這個中年男人說,你好!
劉老師也習慣性地附和道,你好!
請問……這個中年男人邊說邊打量著劉老師。沒過幾秒鐘,這個中年男人微微地笑了,您是劉老師?教過我地理的劉老師?
劉老師也上上下下地仔細看眼前這個中年男人。發質很硬,胡須挺重,眼睛里放出沉穩的目光,但面對著劉老師的對視,沉穩中也不時滲透些卑微。劉老師仔細打撈三十幾年的記憶,還是叫不出眼前這個認識自己的中年男人。三十幾年,他教過的學生太多了,記不住也是無可厚非的。
見劉老師還是想不起自己,這個中年男人就說出他們班學習好和調皮搗蛋的幾個學生的名字,以期喚起劉老師三十多年前的記憶。這是劉老師參加工作后教的第二屆學生,陳彥是他最中意的學生,所以,這個中年男人一說到他的名字,劉老師馬上想起了這是八年二班的學生。但三十幾年,物是人非,當年的少年已經長成滿臉滄桑的中年漢子,劉老師還是不能一一對號,即使是印象最深的陳彥,也是上高中之后就一直未見,就是現在站在他的眼前,恐怕也得仔細找尋當年的眉眼輪廓了。
我是陳彥的同桌。您還打過我。
見劉老師還是想不起自己,這個中年男人進一步提示說。
劉老師感到今天真是倒霉透頂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個還認識自己的學生,態度友好,卻還有不愉快的過去。劉老師眼睛里的刺猬伸了伸腰,但刺卻沒抖出來。憑感覺,他知道自己的血壓一定是涌上了150 的刻度。
他的臉,不自覺地紅了。教學三十幾年,打過的學生有,但不是很多,那個時候老師懲戒學生,家長是認可的,社會也是認可的。被懲戒的學生不但不會去告,家長也不會像現在這樣,還會和老師檢討自己教子不嚴。
我想起來了,你是王強。
對了。這個叫王強的中年男人沒想到劉老師經過這么多年,教了那么多學生,還能想起一個默默無聞的家伙。他簡直是太高興了,握著劉老師的手,眼淚都在眼圈里打轉了。
我那個時候學習不好,坐在陳彥的旁邊不敢發言。
不敢發言?那你怎么敢在我提問你海南有哪些特產的時候,你回答說苞米。
王強的眼神中卑微的成分又多了一層。他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課堂。
劉老師,那個問題,我真的不會,是陳彥小聲提示我的。
然后,全班的同學都笑了?
對。您知道他們為啥都笑了?
因為你的回答驢唇不對馬嘴。
王強搖頭,是因為他們背地里都叫您瞎苞米。
苞米?還是瞎的?劉老師也疑惑地笑笑,我怎么不知道?
他們說您的牙,就像籽粒長得癟瞎瞎的苞米,簡稱瞎苞米。
劉老師走到鏡子前面,張開嘴,仔細看看自己的牙齒,幸好還沒掉,但稀稀拉拉,并不飽滿,看來學生們對自己研究得很透。
劉老師轉過身,審視著王強。我怎么不知道?
只有您不知道,我們全班都知道。隔壁的兩個班,也都知道。
我是因為這個打你?
不是。王強說。您訓了我一頓,讓我坐下,我更聽不下去了,就拿出一張紙畫畫。我記得當時畫了一只王八,趁著您站在陳彥旁邊看作業的時候,粘在您的衣服后面。您還不知道,還在講臺上下走來走去。最后,大伙兒忍不住了,都笑了起來。您氣急敗壞,大聲問,是誰畫的?我不敢承認,最后,陳彥說是我畫的,您過來,拎起我就是一拳。
劉老師過來,拍一下王強的肩膀,說,現在還疼嗎?
王強尷尬地一笑,劉老師幽默了。您知道您這外號是誰起的?
誰起的?
陳彥。
劉老師一愣,不會吧?
您知道我畫的那個王八是誰讓畫的?
是誰?
陳彥。
劉老師又是一愣,怎么會?
怎么不會?我那時腦子笨,陳彥說,我把老師叫過來假裝問一個題,你把那個王八粘在他的后背上。
劉老師徹底崩潰了,怎么會這樣?我對他一直很欣賞。覺得他聰明、機靈。
但他有才無德。指使我的是他,告發我的還是他。王強說。
5
真是心亂如麻。
但是現在,劉老師還沒有閑工夫思考這件事,他的腦海里出現的還是張陽的最后通牒,三點鐘之前,必須拿到一寸照片。他匆忙打斷王強,說出原委。
王強忙說,自己這里除了制作廣告牌匾,還真沒有照相、印大頭貼的業務了。
劉老師眼里那兩只刺猬又變得急躁起來。看到劉老師無助的樣子,王強站起身,拿起桌子上的車鑰匙說,劉老師,您跟學校領導打個招呼,我拉您去市里,用不上兩個小時就能趕回來,保準趕趟兒。
劉老師猶豫了一下,現在也的確沒有其他好辦法了。兩個人鎖好店門,上了車,王強將方向盤麻利地一擰,車子轉頭就上了通往市區的柏油路。
劉老師掏出手機給張陽打電話,告訴她去市里拍照片,三點前一定趕回來。
望著身邊聚精會神開車的王強,劉老師的心底突然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愧疚,他動情地說,王強,老師真對不起你。如果你還是感到委屈,也可以給我一拳。
王強扭頭瞥了他一眼說,老師,您說的是什么話?不用說,是我當年不懂事,就是您打得再重一點,我也不冤枉,哪有老師給學生道歉的道理?我是看您實在想不起我,才提起的,尋思您應該能記得打我的事。
劉老師,王強說,我真得感謝您。您還記得不?您打我之前,從班長手里接過我畫的王八,仔細看了看說,不錯,畫得挺像。我還以為您是表揚我,一下子站直了身子,誰會想到,您過來拎起我就是一拳。您咬牙切齒地說,你有這個天賦,為什么不好好發揮,將來也許能吃上一碗飯,成天在學校里鬼混,將來要飯都找不到地方。
我是這么說的嗎?劉老師問。
我沒有記錯。您的話,我怕忘了,總是復制粘貼。
我的話,這么好使?
真的好使。您的一拳打醒了我。王強說,您還記不記得,我改食堂的飯票,連食堂管理員都看不出來。劉老師笑了。這是你的美術天賦。
對。王強說,我在職高學的園林設計。走到社會上,我的天賦,真的有了用武之地。
劉老師問,你做什么工作?
室內外的假山假水。
劉老師撲哧一聲笑了,一顆活動的牙差點噴出來。你小子,真是個歪才,把造假做到了極致。
說實話,劉老師,這都是您那一拳給我打出來的,沒有您那一拳,我可能真的找不到要飯的地方了。
這么說,你不記恨我,還感激我?
是的,王強動情地說,我真的不記恨您,反而,真的感激您。
這么說,咱們倆和解了?
沒有什么和解不和解的,提起這件事,不是我的本意,無意中的相逢,感激您,才是我的本意。
好!劉老師說,和解就好,讓學生將來有吃飯的本事,是我們老師的義務,也不存在感激。那你工作做得怎么樣?
遍及天南地北。
不錯!劉老師贊許中留有疑惑。那現在?
現在……王強沉默了。現在回來了,外面的水,太深。我掙了不少錢,但也吃了不少虧。從監獄里出來就回家了,繼承父母的小店,心里踏實。
進了監獄?劉老師不信。
真的進了監獄。王強把身子往前面伸了伸,離劉老師遠了一些距離,好像劉老師還會像當年那樣,拎起他來,就是一拳。
但劉老師沒有。在劉老師的職業生涯里,打學生真的屈指可數。
現在,劉老師的眼睛里沒有刺猬,有的是溫情和疑惑。
為什么?
還是因為陳彥。
劉老師眼里那兩只刺猬真的動了,且抖動皮毛,銀針根根直立。
你是狗嗎?記吃不記打?
王強從駕駛座挺直了身子,像一個犯錯誤的學生。
我……王強支支吾吾。當年,陳彥給了我十塊糖,我們就和解了。
劉老師嘆了口氣。片刻,劉老師緊緊咬著的牙縫里鉆出幾個字,王強,你就值十塊糖?
是的,王強囁嚅地說,當年。
那現在呢?是不是陳彥給你十捆錢,你又會上他的當?
王強差點哭出聲。老師,您不愧是我的老師,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什么了?我只不過是打個比方?
我承認。盡管我也走南闖北,見過世面,有了城府,但我不是陳彥的對手。他說他當上局長,城建的活兒任我挑。他答應給我十萬,他把和他競爭的一個副局長請到東方溫泉,讓我買通在這里打工的一個熟人,把那個副局長的手機給扔了,第二天就是競聘的日子,讓那個家伙無法和外界溝通。
敗類!劉老師咬牙切齒。你們成功了?
失敗了。
結果是,他們兩個都被取消了資格,紀檢一查,陳彥公職沒了,做假賬貪污的錢也罰沒了,他判了十五年,我判了三年。
這事和你關系很大?
不光是扔手機。我還幫陳彥做過假賬。
劉老師一拍大腿,刺猬的銀毫刺穿了王強的皮囊。你真是個造假的天才,竟然為虎作倀。
我是活該。但我承認,陳彥是個鬼才。他考上礦業大學,在畢業前夕煽動兩個班學生打架,被開除學籍。他又復讀,第二年,考上財經大學,畢業后在省廳工作,幾年后就負責城建。那時,我也在省城搞園林承包,他給我不少活兒,掙了不少錢。
王強說,在監獄里,我有時間去想我的半生。我和陳彥,真是孽緣。初中的時候,他煽動我給您起哄,我吃過他的虧,但十塊糖,我們就和解了。長大了,我還是吃了他的虧,十萬塊錢,我沒拿到。
但,我也成了他的老師。
6
劉老師像遇到了霹靂。
還算直挺的腰,瞬間化成骨片,癱在座椅上。他感覺碎片在分離,一點點下落,周圍是越來越多的海水,顏色由白變綠,水藻,游魚,不時滑過。綠色漸深,他的下面有山一樣的礁石,還有沉船的桅桿。他不能自已,和那些他看不清的東西起起伏伏。
老師——老師——
不知什么時候,他聽到了聲音,而且這種呼喚越來越真切。劉老師睜開眼睛,才發現,這個聲音就在自己的頭上。憑音質和音色,該是王強。他想挺直腰身,卻感覺上下分離,頓了頓,才血脈相通。他摸了一下前額,就好像剛從水里被人拎上來,濕漉漉一片。不光是臉,渾身都是。
可嚇死我了。王強做謝天謝地狀。
緩了一會兒,劉老師虛弱地問王強,我是不是很失敗?
老師,您是咱們那兒的名師,桃李滿天下,怎么說是失敗?
劉老師苦苦地咧嘴。說,你不提陳彥,我都無地自容了。再說了他的所作所為,我更是死的心都有了。我這不是失敗,而是一無所用。
王強見劉老師還在自責,就說,古人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老師在學校里能管,但管不了學生一輩子。
劉老師說,話是這樣說,但我總是感覺沒有盡到責任。在我的眼里,根本就沒有好學生和壞學生之分,你們都是一樣的。不管學習成績如何,做人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每天苦口婆心,就是希望你們能走正路。
劉老師越說越激動。但你們有人信嗎?你看看陳彥,再看看你王強。
老師,我信。
信個六,你要是信我一句話,還能進去?
王強也有點激動,眼睛微微水潤。您知道陳彥是怎么敗露的嗎?
劉老師說,你們都把我氣糊涂了,你不提,我也正要問。
王強說,是我給110 打的電話。
你明明是他的幫兇,這不是玩火自焚嗎?
我是玩火,但這是涅槃。
你也會受到懲罰的。
進監獄,是預料之中的事。我坐牢,是自罰,也是自贖。
看來你也是深思熟慮。你為啥要這么做?
我買通的那個熟人把手機扔進垃圾桶的那一刻,我猛地想起了您說過的一句話:私欲拱破天,害處大無邊。陳彥如果當上局長,會做更多的壞事。所以我把垃圾桶里的手機偷偷地放到了陳彥的后備箱里。但還是覺得不妥,想了半宿,還是拿起了電話。
我說過這樣的話?
說過。王強斬釘截鐵地回答。
劉老師的血脈開始奔涌。這么說,我還不是一無所用?
作用老大了。您說了那么多,學生小的時候當陳芝麻爛谷子,但工作了,成家立業了,關鍵的時候,哪怕想起一句您的話,就沒白說。
看來是你記起了我的話,但陳彥當成了耳旁風。
陳彥,過去不知道。現在,我知道,他也信了。
劉老師再次驚愕。
王強說,您興許還不知道。陳彥在法庭上罵我信老師的鬼話,但前幾天,他讓人給我帶信,說他是我的學生,是我給他上了深刻的一課。我回信說,我沒有你聰明,但我有糊涂中的清醒。劉老師的一句話,使我成了你的老師,但,我們都是劉老師的學生。
陳彥說,劉老師的話,讓我小時候厭煩,社會上那些人的話,又讓我迷失了自我,你給我上的一課,讓我記住了劉老師的話。我爭取早日出來,到時候,咱們倆,一起去看劉老師。
這么說,我說的不是陳芝麻爛谷子?
不是。
那我還要繼續說?
當然要繼續說。唾沫星子變成星辰大海,哪怕有一處閃亮,也不枉費您的這些水滴。
劉老師從車里出來,腰身活動自如,感覺比任何時候都有力量。他舒展一下筋骨,仿佛里面又有了剛性。
看著身邊的王強,平時不善飲酒的他,這個時候非常想喝一口。
7
車,快到小城的時候,張陽打來電話,說填表的事是一個烏龍。
劉老師牙齒打戰,眼睛里的刺猬鋒芒畢露,他真想罵娘。但他看看前面的王強,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張陽說,校長和書記在市里開會,也是在群里看到辦公室主任發的通知才知道的,就給會計打電話,說他那兒有校長書記的照片。會計在財政局辦事,一聽,也蒙圈了,仔細想想,說,這不是閑扯嗎?我都報上去快半個月了,也不用個人填表啊。原來是合并來的第一副校長業務不熟,看錯了日期和要求。
王強在前邊聽得仔細。
張陽還說,校長、書記責令第一副校長做出檢討,任何人不得馬虎做事。
呵呵!劉老師神情古怪地笑了。
王強說,白忙了?
是啊!劉老師此時就像一個沖鋒陷陣的戰士,歷經千辛萬苦,沖上敵人的陣地,才被告知他沖錯了目標。
這算什么事啊?王強說。
劉老師擺擺手,示意王強不要沖動。
正常。劉老師的手放下來,他的心也漸漸平復,眼睛里刺猬的銀毫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順勢滑落下來。仔細想想,剛合并的學校,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這一切,都會隨著磨合越來越少。
劉老師說,不用去學校了,直接開去你家,找家飯店,我請你吃一頓好的。
王強說,我家隔壁正好有家飯店。
坐在臨窗的座位上,他手指墻上的菜譜,說,王強,點菜,想吃啥就點啥。
那我點了。小笨雞燉蘑菇,清蒸鱸魚,鐵板羊肉,佛跳墻。
劉老師說,哪個價格高,就點哪個。看著自己學生幸福的樣子,劉老師覺得這一天真的沒白過。剩下的六天,要怎么做,他心里有數了。盡管自己微不足道,但身正為范的筋骨,他會挺得更直。
菜,點完了。劉老師聽著女服務員看著點菜器,報著菜名,說,快點上菜。
女服務員麻利地回答,好嘞!
看著女服務員往后廚疾走,劉老師收回眼光。
他抬眼看看遠處樓頂的天空,天,是靜靜的海面藍,沒有一絲雜質。風,輕輕的,似有似無,像絲綢一樣滑過樹梢,拂在自己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