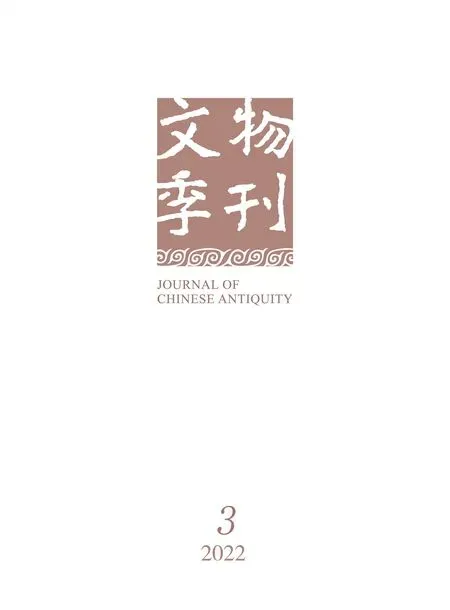經天緯地 照臨四方
——中國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談紀要
山西省文物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22年7月20~22日,“經天緯地 照臨四方——中國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談在山西太原召開,本次會議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承辦。
來自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中國國家博物館、南京大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單位十名專家,圍繞會議主題從考古、文獻、天文、建筑等方面進行了闡釋,凝練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論證的哲學邏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先秦史學會會長宮長為先生從歷史長河角度對陶寺進行了高度總結,他認為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即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應以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和發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時間上來講,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時代,乃至三皇時代,下延至春秋戰國時期,乃至秦漢王朝;從地域上來說,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向外擴展到不同的區域和范圍。這一階段歷史,與我們常說的中國早期國家階段相當。雖然期間產生了像紅山、良渚、石家河、石峁等許多文明,而從中國歷史看,中國主脈在陶寺,陶寺模式是中華主脈,這種模式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
首先,陶寺遺址是中國文明起源的寶典遺址,它就是一部書、一部寶典,就是一個最好的版本。現在不同時代的考古發現很多,但陶寺遺址是重要寶典版本。1926年2月,時任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國學研究院人類學教師的李濟先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先生,到山西晉南考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堯都平陽的記載,根據這個線索,還到臨汾查看了堯廟。其次,陶寺文化就是這一版本里的核心內涵,即經典文化。從1978年開啟陶寺遺址發掘,至1985年陶寺遺址分期已豐富到早中晚三期,奠定了陶寺文化的基礎;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預研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包括社科院創新工程的推進,陶寺文化內涵又得到不斷豐富發展,成為中國史前時期最為醒目和研究最為深入的考古學文化。其三,陶寺模式則是其作為經典文化的精神價值,以農耕文明為基礎,以部族關系為紐帶,以協和萬邦為理念,構成中國早期國家治理體系。農耕文明是地,協和萬邦是天,以部族關系為紐帶聯系天地人三者,體現出早期君主政體。這種君主政體形成“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結構體系,具有二元結構特征,《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天生民而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總之,從陶寺遺址到陶寺文化再到陶寺模式,不僅反映了對陶寺乃至中國文明認識的深入,體現了陶寺“經天緯地 照臨四方”的歷史功績,也是追尋中國文明起源,探討中國文明要義的必然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先生做了本次會議的主旨發言,對陶寺文明模式及與堯舜關系進行了深刻闡釋。40多年來,陶寺發掘與研究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證據鏈,證明陶寺是堯舜之都,而經天緯地正是陶寺文明的重要內容,并有重要的物證發現和實證研究,比如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圭尺第11刻度與陶寺都城性質、陶寺國家結合在一起,可以體現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中國最早”的概念,它實際上是宇宙觀的政治化。那么國家是文明的總括,陶寺是最初的中國,陶寺的邦國就是中華文明核心形成的起點,中華文明是多樣一體化,一體開始,實際上是形成于中國文明核心的開始,形成我們夏商周到現在的中國文明主干,這個主干的形成起點是陶寺。所以,歸結到一個核心,就是堯立中國,其治理國家一個最主要的精髓就是經天緯地,經天就是王權壟斷太陽地平歷、圭表測影太陽歷、陰陽合歷來控制年時,朔望月輪太陽歷控制月時,用盤古沙漏控制晝夜時間,從而把握社會各種生活的時間命脈,成為王權科學軟實力。緯地,王權制定長度基元,建中立極,辨證方位,陰陽八卦八方空間概念,天文大地測量,最終構建起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觀——表里山河,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間命脈,成為王權中道的核心精髓。這就是陶寺的時空政治文明,其核心是對于時間和空間精準管理,為王權與社會政治服務,成為陶寺邦國政治與制度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開創了中國文明當中政治與制度文明在時空管理上的先河。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曉陸先生以陶寺為例,分析了從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到國家起源階段的天文學主要成就。他指出在農業文明背景之下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應當是比較早的,其產生主要與照明、辨方向、定農時有關,尤其是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由于農業生產的需要,會獲得長足的發展。
陶寺遺址以及它的天文臺應當是一個國家級的大型天文機構,從文獻上來看,應對當時農時管理到國家政治管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了完整的制歷;出現了以觀測站、圭表等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測量儀器體系,不僅僅是測日的,對于重要的恒星也有所觀測;形成家族性的天文官員;在天學理論上與《周髀算經》中極具特色的“蓋天說”產生了淵源聯系,因其固有建筑促使以建筑構成出發給予天文度量成為可能;這一遺址體現了早期“赤黃合一”觀測體制,就全球來看,其建造水準不下于距今3000年的英國巨石陣。
周先生特別指出,新石器時代中國天文學逐漸發展,到陶寺階段,已經形成為王朝統治意識形態服務的成熟的科學體系,所以陶寺的功績,無論從農業、從建筑學、從天文學上說,都是非常好的標本,是中華民族階級國家一個重要的早期節點天文學標志。
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宋建忠圍繞第一性原理,對陶寺考古和文明起源問題進行了方法論上的思考。他指出,陶寺遺址經過40年的發掘與研究已經基本回答了陶寺文明是什么等五個“W”問題,但總體上在第六個“why”問題,也即文明演進的內在機制方面還缺乏系統的、有深度的、有說服力的解釋。宋建忠回顧了國內關于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重點分析了陶寺40年來的研究成果,強調不論是中華文明還是陶寺文明,均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和復雜的認知體系,若要揭示其文明演進的第一動力、內在機制、法則及路徑等問題,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中的第一性原理或其思維模式無疑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它不僅是一個概念和原理,更是一種思維模式。“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譯自亞里士多德《物理學》英文版,實際上在原版希臘文里也是“本原”的意思。亞里士多德認為,當我們分析一件事物的時候,我們需要知道該事物的首要條件,或者第一性原理,并且要分析到該事物最簡單的元素,只有在認識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最簡單的元素時,我們才認為是了解了這一事物。也就是說,“為什么”的所有含義,就是要指出這個結果必然是那個原因引起的。我們在文明溯源時,是什么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一定要有相對應的確切說法,不能提出很多原因,但最后多落在無根基的推測上,無法建立一個完全的對應和連接。我們應當有“只有最主要的原因,即第一性原理才引發這個結果;只有這個結果,才會是那個原因引起的”這樣一個思維模式。
任何一個系統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大到中華文明,小到陶寺文明,甚至再小到陶寺文明系統內某個更小的體系。比如關于陶寺觀象臺的演繹論證,首先是何駑構建了一個論證“陶寺觀象臺”的邏輯起點——天體運行規律,即4000年前的陶寺人已認識到日出日落有一個不可撼動的基本法則。接下來就是從邏輯上驗證陶寺遺址發現的“觀測縫”要與太陽運行(實際上是地球運轉)的關鍵節點有一一對應關系。經過對“觀測縫”的天文科學觀測,發現兩分兩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時的日出果然落在了相應的“觀測縫”內,再結合文獻有關記載,由此證明了陶寺觀象臺的觀象授時性質。這個演繹論證過程實際上采用了第一性原理思維模式,即古人眼中所謂的“太陽運行”有著固定不變的法則,它是導致世間萬物發展的第一性原理,也即本因。包括后來發現的圭尺、沙漏等,其實都屬于陶寺文明的觀象授時體系。盡管我們今天無法驗證這些考古發現究竟當時是不是這樣使用的,但從邏輯演繹推理看,這是一個從不證自明的、符合邏輯發展的第一基石、元起點、元動力出發的。這是一種科學的論證,是一種唯一對應的因果關系。這種具有哲學與科學意義的方法和思維,無疑應該更多地運用到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各個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先生強調,文明不是一個優秀傳統的持續單線進化,而是一個多元活動,各地區裂變、碰撞、融合發展的過程。良渚和陶寺均是如此。良渚的形成并不是本地傳統的發展,而是在“最初的中國”或者說是“中國相互作用圈”基礎上,良渚的領導者有意識地融合以前重要發展成果,形成了被稱作中華文明五千年特別重要的實證,為后來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榜樣。
陶寺是在黃土高原傳統文化和東部平原良渚文化的碰撞下,激發出的新的文明和新的政治實踐。同時,陶寺有了自己新的構建,包括天文觀測、城市布局等。與良渚王者宣揚宗教信仰并以此壟斷溝通天地權力不同,陶寺王權以更多表達自己在四方中特殊地位為目的,推動四方一體化的政治構想。因此,不能低估像陶寺這類可以建造30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郭和結構復雜的天文觀測設施、可以匯納四方物品和知識的先賢的胸襟和智慧,他們或許可以通過實施精彩政策,通過觀天象掌握天體運轉的規律,達到獨占溝通天極之神權力,在人間實現王者微服天下的效力,這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尚書·堯典》中提到的“協和萬邦”。堯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許不能僅以“傳說”視之,而可能是“天文版”的促進各地區一體化、構筑“理想的中國”的宣傳方案甚至實際努力。
陶寺和良渚這樣前赴后繼大范圍融合式發展,而不是單純從自己本地傳統延續而來,也是中華文明特別重要的特色,在這樣一個宏大的發展歷程中,能產生更遠大的政治思想,形成蘇秉琦先生理論的中國,至西周的分封制度落地,發展為現實的中國。
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戴向明先生提出中華文明從起源、形成到早期發展有三個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以良渚為代表,是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屬于長江稻作文明早期發展的巔峰;第二個里程碑以陶寺為代表,包括跟它大體同時的陜北石峁,屬于龍山時代黃河粟作農業文明發展的高峰,也是當時中國文明的又一個代表;第三個里程碑是夏王朝的都邑二里頭,創建了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的根基。
陶寺所在的晉南地區是黃土高原向華北平原、黃淮平原、江漢平原過渡地帶,屬于東西交匯前沿區域,先后有東西風潮的影響,這在文化和社會演變軌跡上都有體現。
廟底溝二期時期在東風西漸浪潮下,伴隨本地農業發展、社會的分化、聚落的成長,碰撞出了陶寺早期社會集團,出現了百萬平方米的大遺址,有核心宮殿區、大建筑,還有高等級貴族墓葬,形成中原乃至黃河中游文化最發達、社會復雜化程度最高的社會。
到了陶寺文化中期,歷史背景由東風西漸轉化為西風東漸,在整個黃土地區形成了一個大的鬲文化圈,晉南處于該文化圈的東南區域。這一時期的陶寺則孕育出了中原及黃河中游最早的國家組織,這樣一群人是中原華夏族群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說中的堯舜集團密切相關。
總之,在中國史前多元區域文明此起彼伏的演進過程中,陶寺是龍山時代中原文明的杰出代表,可以說也代表了當時中國文明的一個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高江濤先生總結了陶寺文明的“兩大特征”與“三種精神”,以此闡釋了“經天緯地 照臨四方”的陶寺模式。
他認為王權國家與禮制社會是以華夏文明為主體的中華文明的最大特征,陶寺文化與社會完全具有這兩大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陶寺文明是華夏文明的主脈。這一時期陶寺遺址的聚落等級分化嚴重且存在多個層級,復雜化程度較高,出現了為權力階層服務的宮殿區、倉儲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等,規模宏大、地位凸顯的宮殿夯土建筑與簡陋的半地穴式或窯洞式小房子形成鮮明對比,出現了金字塔式等級結構的墓地和王級大墓,以王權為核心的早期國家已經形成。同時,形成了嚴格秩序規定的成組陶禮器、玉禮器、禮樂器,出現具有禮儀性質的城門建筑——宮城南東門址。
在陶寺文化發展歷程中深刻烙印著海納百川、務實創新、傳承發展的精神品質,這也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獨樹一幟的深層原因。陶寺文明較為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可謂“經天緯地 照臨四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物保護科技技術研究院副院長王璐副教授,以陶寺宮城為例,從空間規劃與形制方面討論了營建思想和政治理念,指出陶寺城址的選址、方位、宇宙觀、天下觀、時空觀以及與此相關的格局,反映了都城的早期形態,展現了陶寺城址系統的宮室營建、禮儀制度、文化傳統和信仰觀念。許多營建和規劃思想都為后世所繼承發展,具有開創性意義,如陶寺宮城南東門,開闕門形制之先河,大型1號宮殿極有可能是早期宗廟性質建筑,從“擇中建都”到“擇中建宮”,表明了“邦國時代”都城布局正在從以血緣政治為主走向與地緣政治結合的道路,為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奠定了觀念上和行動上的基礎,體現了“經天緯地 照臨四方”的宏大政治抱負。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副研究員犁耕先生論述了陶寺在天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指出,天文觀測的出現跟我們農業的產生差不多是同時的,陶寺時候已經有了專門機構,這個機構延續到后來,就是我們所謂的欽天監。之后還產生了觀測日出方位和圭表測影等技術。在《周禮》里也有很多,像“惟王建國,辯正方位”,實際上明確地講到了這些傳統,古代要當一個王,就要建立一個都城,第一步必須要確立它的東西和南北,這就需要通過圭表測影這樣的方法。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華夏文明研究所所長張光輝,從黃土高原建筑傳統的轉變等問題,闡釋了距今5000年前后該區域文明化進程中的一些運動軌跡。他強調結合黃土高原建筑形式發生的兩次大變化,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始終都是這一廣大區域的主根,她奠定了黃土高原先民生存空間,經過兩千年的蓄勢,在公元前四千紀末期的仰韶晚期孕育出了龍山時代遍及整個高原的的窯洞建筑,成為南北共同的文化基因,延續至今。
進入距今5000年后,由于各自地理背景及文化傳統因素的原因,以石城為集合體的石構建筑在黃土高原北部興起,迅速成為整個龍山時代北方地區的標志性建筑形式,南部進一步發揮黃土特性,將土構建筑進行到底,最終在距今4000年前后發展出各自區域的高光時刻,即以石峁和陶寺為代表兩大區域文明,其一方面堅持著仰韶文化的深層基因,在建筑上繼續發揚仰韶以來的窯洞傳統;同時,還在黃土高原發展出用鬲傳統,形成新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又標榜著相互之間的不同,各自充分開發著當地地理資源:土與石,形成夯土墻和砌石墻建筑的差異;同時,又相互吸納對方一些先進和特色因素,融入到自身建筑傳統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見你的建筑風貌,基于黃土高原這類深厚文化聯系及歷史傳統,所以,像東方尚玉之風、西方冶金術借勢迅速遍及黃土高原也就水到渠成了,這也是黃土高原一個特性——東西匯流,南北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