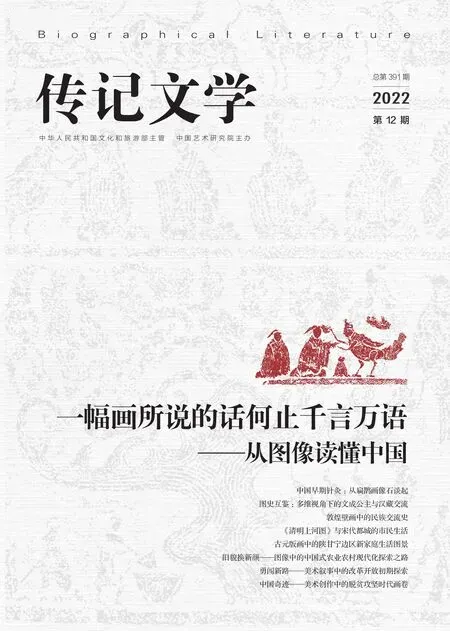2021 年中美傳記電影比較研究
儲雙月
傳記電影往往帶有歷史的印記,散發著時代的氣息,蘊含著人文精神、價值取向,能夠滿足觀眾求真的訴求,而且其中貫穿著的精神力量對觀眾具有重要的激勵或警示作用。
2021 年是中美傳記電影大放異彩的一年,許多在此年上映的傳記影片得到了重要電影獎項的垂青。中國傳記電影《守島人》獲得第3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革命者》獲得第34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美術獎、第11 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第28 屆大學生電影節最受大學生歡迎年度影片;《柳青》獲得第24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頻道傳媒關注單元最受傳媒關注編劇獎;中國香港傳記電影《梅艷芳》獲得第40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最佳服裝造型設計、最佳音響效果、最佳視覺效果獎。而美國傳記電影《國王理查德》獲得第94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第79 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電影類劇情類最佳男主角獎、第75 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獎;《塔米·菲的眼睛》獲得第94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和最佳化妝與發型設計獎;《里卡多一家》獲得第79 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電影類劇情類最佳女主角獎;《倒數時刻》獲得第79 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電影類音樂/喜劇類最佳男主角獎。
2021 年的中國傳記電影有劇情傳記電影《守島人》《柳青》《我的父親焦裕祿》《梅艷芳》,以及歷史傳記電影《革命者》,雖然在數量上較少,但與往年相比,已是傳記電影生產的豐收年。而美國傳記電影,亞類型更為豐富,除了《塔米·菲的眼睛》《里卡多一家》屬于劇情傳記電影之外,還有體育傳記電影《國王理查德》《新王加冕》《美國草根:庫爾特·華納的故事》,音樂傳記電影《倒數時刻》《尊重》,歷史傳記電影《美國叛徒:軸心莎莉的審判》《哈里·哈弗特》,犯罪傳記電影《蘭斯基》《無主之人》等。由于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對以真人真事為根基來真實記錄和深刻反思特定人物生平歷史的傳記電影進行比較研究,實屬必要。
樹立英雄模范的紀念碑與描繪普通人的肖像畫
2021 年的中國傳記電影以紀念性傳記電影為主,傳主的道德品行或個人成就都明顯高于普通人,歸入品德高尚者、事業有成者之列,值得后人紀念和瞻仰。除《梅艷芳》外,《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中的傳主都是正統的英雄模范。四部影片主要關注于刻畫傳主高大、光輝的人物形象,凸顯人物的高尚品德與事跡行為,強調善行是內在的、永恒不變的。創作者聚焦于傳主所崇尚的理想主義信念,從道德倫理角度審視人本身,是這四部中國傳記電影的共同創作趨向。
《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相比較以往的中國傳記電影,除了突出其中的道德含義與教化作用之外,更突出了傳主的堅定、忠誠、執著和樸實等鮮明品格,拉近了傳主與普通觀眾的距離。《我的父親焦裕祿》以女兒的視角深情回憶了一名共產黨員干部短暫而輝煌的一生,塑造了焦裕祿為官至臻、為夫至誠、為子至孝、為父至親的光輝形象。影片回顧并贊頌了焦裕祿“洛礦建初功”“蘭考戰三害”“博山生死別”三個時期的高尚事跡,“偉其事”、“詳其跡”,“試圖為死者樹立一座高聳入云的紀念碑,借死者的偉大來鼓起生者的勇氣”[1]。影片不僅注重傳主的個人成就或公眾生活,還較為注重家庭生活中傳主與親人相處的點滴瑣事,突出了傳主具有的高于常人的自律和對家人嚴格要求的道德品質。與《我的父親焦裕祿》一樣,《革命者》《守島人》《柳青》也借助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為觀眾提供可供效仿的范例,以實現對觀眾的鼓舞、指導和啟發作用,規范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言行。盡管四部影片有意塑造英雄模范的紀念碑,但是英雄模范并未因此失去生活色彩,也沒有變成神壇上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偶像。因為創作者盡力嫁接英雄情懷與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力圖還原其為有呼吸、有溫度的人,竭力讓真實親切的“平凡英雄”走入觀眾心靈。例如,《革命者》透過三一八慘案的再現,讓我們聆聽和目睹了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先驅內心的恐懼、掙扎與怒吼。作為塑造理想人格為宗旨的紀念性傳記電影,雖然仍免不了受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傳統觀念的影響,卻已經在有意識地探討歷史存在的豐富性。創作者為了表達得體的致敬,在記錄傳主驚天動地的豐功偉績與氣吞山河的豪言壯語的同時,又努力還原傳主為“我們”中的一員,達到“見事又見人”的效果,體現了傳記材料的博實與人物個性的彰顯。
中國香港電影《梅艷芳》則展現了梅艷芳成長為歌后與影后的心路歷程和作為“香港的女兒”的傳奇一生。《梅艷芳》以述人為主,以刻畫、描摹和凸顯傳主的性格為重,向觀眾展示了創作者所熟悉的傳主生平中的軼事,使傳主的人物性格惟妙惟肖、真實可信。傳主童年時期和姐姐一起登臺演出、養家糊口的場景讓人過目難忘。影片通過傳主與姐姐約好一起看婚紗卻沒有按時赴約而且拒絕道歉等情節描述,沒有避諱表達傳主性格中存在的某些瑕疵;影片還勾勒出了傳主心靈的傷疤:從小到大都沒見過父親,在心底里把形象設計師劉培基、華星唱片總經理蘇孝良、電影制作人何冠昌當作父親,等等。創作者擅長心理分析,并以此為工具闡釋傳主,試圖探索和呈現傳主的內心世界。
而2021 年的美國傳記電影重在描繪人物的歷史,致力于生動刻畫傳主豐滿而真實的形象,突出傳記電影是描繪普通人的肖像畫,即有明有暗的立體肖像畫,而不是歷史“大事記”、索引或目錄,也不是輪廓圖。它們不再以敘述歷史事件和人物成就為主,而對人自身產生了濃厚且意味盎然的興趣,因此將重點放在塑造可以決定其命運的人物性格上,對人物性格的重視高于歷史事件。這一時期的美國傳記電影更加注重通過軼事和細節刻畫人物性格,人物形象聚焦于雄心勃勃的運動員、青年音樂劇作曲家、有著明顯性格缺陷的娛樂圈知名人士、被美國政府以八項叛國罪名提起訴訟的播音員,乃至臭名昭著的罪犯和黑幫人物等。
正如英國18 世紀傳記理論和實踐先行者羅杰·諾斯所說:“傳記應該是一幅畫,如果它的特有質素被省略,那斷然算不上好作品。瑕疵、傷疤和污點應該和它的美一樣被描寫出來,否則它只能算一幅填滿了百合和玫瑰的輪廓圖。”[2]美國傳記電影大多專揀傳主私生活中細致入微的“瑕疵、傷疤和污點”開刀,通過日常瑣事和個性化的細節描寫刻畫人物性格,從而實現傳記電影的娛樂功用。例如,體育傳記電影《國王理查德》中的傳主不是世界網壇巨星威廉姆斯姐妹,而是美國黑人貧民窟出身卻將兩個女兒成功培養進入體育賽道金字塔頂的傳奇父親理查德·威廉姆斯。該片是美國黑人明星威爾·史密斯繼《拳王阿里》(2001 年)、《當幸福來敲門》(2006年)、《震蕩效應》(2015 年)之后主演的第四部傳記電影。在這部影片里,威爾·史密斯很好地塑造了網球明星姐妹背后挑戰既定規則、強勢犀利、縱橫隨心的不完美的父親形象:一位“充滿爭議、蠻橫霸道、愛自吹自擂的滋事分子”(影片語),充分展現了這位任性父親的矛盾和多面性,延伸出多層面、有深度、有意義的社會話題。理查德就像集權統治制度中的國王,用“自我中心主義”“狂妄偏執”“獨斷專行”等來形容沒有任何網球背景、完全靠自學的理查德的為人處世都不為過。影片從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細節著手,惟妙惟肖地刻畫出這位帶有普遍性的黑人貧民作為傳主的獨特性和客觀性。而音樂傳記電影《尊重》則將主視點放在自強自立的黑人女性身上,提出“種族歧視+貧富差距+社會性別”問題,以期改變主流社會對少數族裔、底層黑人女性的成見和歧視。對傳主青年時期的自身墮落,如過度飲酒以及與家人的摩擦、爭執等也一并展現,沒有隱瞞或避諱。影片并未因對“靈魂歌后”艾瑞莎·弗蘭克林心懷崇敬之情而在人物塑造上失去想象力,而是通過扎根于人物真實的情感經歷來再現她眾多成名歌曲的形成過程,音樂歌曲很好地成為激勵她人生奮進、拼搏的無形力量。影片強調了傳主瑣碎、私密的一面,通過情感歷程突出人物個性,且賦予深度和多層次的刻畫。這些更能真實地勾勒傳主的人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顯得更加光鮮亮麗、飽滿生動。
深化崇敬型認同與尋求體驗型認同
2021 年的中國傳記電影,主要著力于敘述傳主為國家與集體事業奮斗、奉獻和付出的事跡,用以強化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體系和凝聚力。《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強調了傳主對事業專注、投入的偉大精神和無私品德,有益于觀眾理解傳主道德完善的內在邏輯。影片通過文化身份的建構,把個人身份滲透到民族身份當中,使傳主逐步地變成民族寓言里的父型人物。在德智雙全的父型人物的形成過程中,民族身份的建構是至為關鍵的,占主導性的情感是崇敬型認同。四部影片均為觀眾樹立了崇高可敬的英雄模范形象,用以升起一股對英雄模范的崇拜。這些英雄模范的典型事件讓傳主形成了壁立千仞的權威人格,在情感和認知上具有排他性。需要指出的是,這四部影片除了采取自下而上的仰視視角之外,還引入了平視視角,即除了強調傳主的偉大之外,還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傳主的平凡,寫出了平凡里所具有的難以磨滅的價值,以接地氣。正是由于兩種視角的組合,使得影片突破了崇敬型認同的最大局限,即創作者對權威人格的依附所造成的視域遮蔽。雖然崇敬型認同這種自下而上的探視方式和認知方式讓觀眾看到了巨峰嘆為觀止的一面,卻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視域受阻”,但平視視角擺脫了一般崇敬型認同的窠臼,有效彌補了與傳主的人格契合。
在觀看《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的過程中,觀眾的靈魂能夠得到洗禮,精神能夠得到提揚,從而能夠引發反躬自省、激發愛國行動。就觀眾與創作者的關系而言,《我的父親焦裕祿》因雙重敘事視角的使用顯得較為親切。影片中,傳主的女兒在敘事中需要同時充當敘事者和傳記電影中的人物。“這就強調了敘述者具備敘述的權威性:與傳主關系親切,是傳主生平的見證人,是歷史事件的目擊者。”[3]敘事者在敘述與傳主之間的親切關系時,采用了傳主女兒的敘事視角和理解能力,這時觀眾通過傳主女兒的眼睛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是有限的,理解能力也是相對較低的;而在敘述傳主其他生平事件時則采用全知全能的視角,這樣敘事者不僅能夠知曉一切,而且能夠對過去的所有事件清晰、正確地洞察。這樣就能夠產生兩大好處:一是作為影片人物的傳主女兒成為傳記電影中所敘述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她刻畫的傳主就是經過自己的觀察加工之后的人物形象。這就使影片不僅能夠為加工手法找出依據,而且使傳主形象更為可信;二是極大地增強了傳記電影的生動性。這種手法將觀眾拉入敘事世界,并使觀眾透過傳主女兒的眼睛身臨其境地體驗經過戲劇化渲染的事件,這便使觀眾的觀看過程如同觀看紀錄片一般,大大提高了作品的逼真感。而《革命者》《柳青》《守島人》中的創作者則不是置身其內,而是置身于傳主的精神世界之外進行觀察。影片表面上以傳主的視點展示傳主與他人的關系、傳主與時代的關系,事實上是通過他人的眼光反觀傳主自身。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互動,特別是對傳主一生有決定性影響的人物之關系,把人當作一個整體,而沒有使傳主成為一座“孤島”。在由別人來證實的事實的“誘導暗示”下,創作者把握傳主的性格和精神氣質,從而產生一種崇敬型認同。
而2021 年的美國傳記電影都在講述傳主個人的生存和發展,以傳主的人生經歷、拼搏精神,給當下人的立身處世提供某種借鑒。大多數影片占主導性的情感是體驗型認同,創作者似乎在親自感受著傳主的生活,探索著不同的人生。在體驗型認同中,創作者不會過分關注自身的主觀傾訴,而是試圖進入傳主的心靈空間。創作者與傳主達到身體、思想、感情上的相融,從而達到一種精神、個性的契合,仿佛進入了無“隔”的化境。“融而不隔”,趨向一種整體性,即創作者與傳主之間“隱含著一種交流的相互性、合作的平等感”[4]。創作者的視野甚至進入了傳主個人的隱私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坦誠展現傳主私下里親密的一面,努力展現傳主作為“人”的各個方面。
就觀眾與創作者的關系而言,這一時期美國傳記電影的創作者大多力求在影片文本中與觀眾之間建立平等、親密的關系,讓觀眾自行判斷影片中所述事件,并接近傳主赤裸裸不加修飾的靈魂。例如,《美國草根:庫爾特·華納的故事》圍繞華納對愛情的真誠和執著、對夢想的追逐和堅韌,展示了他在遭遇挫折、低谷、阻力和打擊過程中的篤定和堅持不懈,即使坐了四年冷板凳仍然沒有放棄夢想并且堅定必勝的信念,讓人感受到他作為平凡人在不屈不撓中所練出的強大心臟和壯闊胸懷。華納對待順境和逆境的態度以及其所持有的愛情觀和人生觀是個人奮斗成功的普遍案例,易于與觀眾個體的生存體驗融為一體。而《倒數時刻》并沒有過多闡述拉森在首演前死亡的戲劇性命運,把他當神一樣來崇拜,而是把他當成普通人中的一員,描摹了他三十而立之時卻一事無成,帶著恐慌、急躁與困惑佇立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孤獨身影。影片背后折射著當代年輕人身陷現實與理想夾縫中面臨的種種問題和困境,使觀眾對于生存感悟具有強烈的代入感。如果說《美國草根:庫爾特·華納的故事》和《倒數時刻》通過傳主的勵志故事展現了傳主樂觀、積極、進取的個人品質,那么《美國叛徒:軸心莎莉的審判》則把軸心莎莉不可告人的一面予以曝光,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使人看清真偽。創作者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傾向性平衡,既重視個體生命的復雜性,又防止類化造成的“扁平性格”。也就是說,創作者沒有把軸心莎莉當作“類”來處理,而是當作活生生的“人”來刻畫。觀眾看到的是軸心莎莉變幻如虹的個性展示,是一種生存極限不斷受到挑戰之下反抗品質愈演愈烈的程度遞進。軸心莎莉在納粹德國官方廣播電臺“柏林之音”為納粹宣傳,瓦解美國軍隊士氣,是因為受到納粹德國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脅迫,身陷戰爭無法選擇對錯,迫于生存需要才淪為被操控的傀儡。創作者清晰的創作意圖了然可見:試圖通過冷靜的歷史分析,勾勒出軸心莎莉作為一個普通正常人的一面——對生命和愛情的強烈渴望,而不是用臉譜化方式去塑造一個遺臭萬年的人民公敵和一個助紂為虐、惡貫滿盈的女性形象。影片沒有把軸心莎莉描繪成一副沒有血肉的骨架,而是具有傳記電影應有的剖析深度,達到了藝術的完整性。電影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同類,觀眾在看傳主的生平故事就是某種程度的自我釋放、自我排解。在另一個人的蹤跡中,觀眾的內心產生一種共鳴,會反觀思考自我。在同樣的時代中,在同樣的處境里,觀眾會聯想到自己是否也可能出現同樣的困惑,犯下同樣的錯誤,走向同樣的道路。這就是體驗型認同帶來的必然結果。
秉持求善的標準與堅持述奇的原則
2021 年中國傳記電影《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的創作者強調通過描寫傳主生平中具體的事跡而不是通過抽象的講道來弘揚善德。創作者的目光主要聚焦于人物行為,抓住經脈,圍繞個人的歷史事件與成就展開敘述。同時,《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里的傳主都是以國家、集體的利益為重行事,他們本人的利益和國家、集體的利益是一致的,即是以善的標準來行事。四部影片強化和突出了傳主舍己為民的犧牲品格,藝術地揭示美德之美,秉持求善的標準來深化影片的主旨。
《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注意表現的是傳主心靈中不變的特征、永恒的品質。提煉心像是這四部影片的立傳點。“在人的整個一生中,行為變化莫測,境遇時好時壞。心像就要在這些不定的因素中提煉出本質的東西、不變的東西、極富特征的東西。”[5]雖然《守島人》敘說了王繼才起初并不愿意守島,但此后其人生的絕大部分時間是自愿和主動守島的,因此忠誠守島仍然屬于王繼才心靈里的不變本質。在《革命者》中,李大釗從1912 年回國到1927 年犧牲都是堅定地投身于馬克思主義事業的革命先驅,為國家命運、民族前途、人民幸福發出時代強音。影片基本上遵從通過圍繞人物心像敘述其成就和公眾生活的歷史敘述傳統。在《我的父親焦裕祿》中,公共事務和家庭生活的作用最為關鍵。影片詳盡地羅列出傳主的公共事務,以強調傳主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高貴品格。因為是傳主女兒的敘述視角,影片還把一部分心思放在家庭生活上,去展現日常生活中傳主是如何身體力行地教誨兒女的,竭力表現傳主世俗的偉大。影片《柳青》在塑造傳主心像上,既縱向貫穿了歷史發展的線索,同時也進行了橫向的交流互動,傳主的性格從一而終,始終是深沉地熱愛人民和土地的作家。總之,無論是李大釗、焦裕祿、柳青還是王繼才,創作者都注重表現他們與人為善的本質和善行。傳主本人的特質為傳記電影平添了生命的光輝。四部影片均寫出了傳主心靈中“本質的東西”,寫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東西,亦即圍繞心像寫出那些富有精神意味的行為、言辭和事跡,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敘述的真實性與準確性。
而2021 年的美國傳記電影的目光不局限于杰出個人,也不局限于人物光輝的一面。它們展現了美國的眾生百態,只要人物具有與眾不同的個性就可以成為傳主。既可以敘述善行也可以敘述惡行,創作者盡量保持客觀中立的敘述。它們普遍注重述奇且實錄,如實展現傳主的原貌、全貌,以栩栩如生的描述見長。真實性、準確性、傳奇性是美國傳記電影創作追求的目標,其中傳奇性獨具一格。
例如,《里卡多一家》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明星伉儷露西爾·鮑爾和戴斯·阿納茲在排演經典情景喜劇《我愛露西》第二季的五天軼事為主線,講述了鮑爾遭遇突然懷孕、政治身份質疑、丈夫出軌等人生階段中最嚴重的危機。發生在鮑爾身上接二連三的惡意誹謗是美國麥卡錫主義的縮影,影片以真實而辛辣的筆觸展示了在麥卡錫主義沖擊下演員的生存狀態,嘲諷了麥卡錫主義的荒誕可笑。同樣是講述電視明星伉儷故事的《塔米·菲的眼睛》,不再像《里卡多一家》一樣采取特寫式聚焦和橫截面敘事,而是講述了塔米·菲和吉姆·貝克這對夫婦作為電視福音布道家大喜大悲的人生。影片再現了夫妻二人艱苦創業的經歷,又披露了他們一步步跌落神壇的過程,兩人虔誠激情的福音布道和奢靡縱欲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強烈反差。兩部影片都抵近真實,帶領觀眾看到兩對明星夫妻婚姻破裂乃至事業隕落的真相,不避私生活,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觀眾追求傳奇性的情感需求。而《蘭斯基》以邁入古稀之年且隱居在邁阿密海灘的美國籍波蘭裔猶太人梅耶·蘭斯基找作家述說自傳為主線,回顧了他在20 世紀上半葉的血腥發家史。蘭斯基殺人如麻,在美國是愛國者也是逃犯。影片沒有美化他的罪惡、洗白他的污點,而是誠實以待,展示了這位黑幫大佬的經商邏輯和生存哲學,并穿插了罪與罰的因果報應。蘭斯基是一個正直與邪惡并舉、瑕疵與能力皆不尋常的人。整部傳記電影條理清晰,邏輯分明,人物展現極具穿透力和新奇感,把一位個性復雜、野心勃勃而又有情有義的蘭斯基描繪得光彩奪目、立體生動。影片把傳主的生平和許多瑣事也處理得極富戲劇性,這種富于歷史整合能力的敘事技巧使得影片的敘事緊湊生動、跌宕起伏,既把蘭斯基的性格描繪得活靈活現,并且準確地把握和反映了時代的特征,對于想了解20 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和黑手黨首領生活的觀眾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蘭斯基人性的真實和復雜,包括灰色地帶,在影片中都被詮釋得淋漓盡致。這種真實毫無遮掩,即使是最隱秘之處也呈現出來。創作者竭盡全力實現真實性和全面性,而且力圖展開微小的細節描寫以突出傳主不同于他人的個體差異性。
2021 年美國傳記電影大多以奇制勝,以奇聞軼事娛樂觀眾,娛樂性強、可觀賞性強是其突出特點。一方面,為了踐行傳記電影的娛樂目的,創作者善于抓住傳主與眾不同的個性和最典型的特征,包括邪惡的特征,充分體現對人物個性的重視;另一方面,在傳記電影中為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物立傳,實現了人物高度的全面性,忠實地呈現傳主的缺點、弱點和錯誤,善于從私密生活中挖掘豐富的細節,將人生的瑣碎細節和人物的千奇百怪刻畫得淋漓盡致,從小處發掘人物的過人之處或揭示人物的離經叛道,令人耳目一新。
結語
2021 年的中國傳記電影和美國傳記電影,都不再只是突出傳主的行為及外在的個性表征,而是努力探索傳主生活和思想深處之路徑,更加趨向于對傳主個人意識的探究,坦露的形式也轉向傳主的自我與內心。影片不僅是對傳主一生重大事務的記錄,同時也是對其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具有特性的細節的描述。中國傳記電影則更加注重于個人與時代發展的融合,弘揚社會道德的正向能量。此外,傳記電影創作不僅需要注重傳主的個性和多樣性,而且還要寓教于樂,運用各種手法將傳記的娛樂性與道德教化目的融為一體,在娛樂大眾的同時清晰、有力地表達觀點,以娛樂性為契機實現極好的道德教化效果。
注釋:
[1][4][5]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2 頁,第130 頁,第214 頁。
[2][3]唐岫敏等:《英國傳記發展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6 頁,第5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