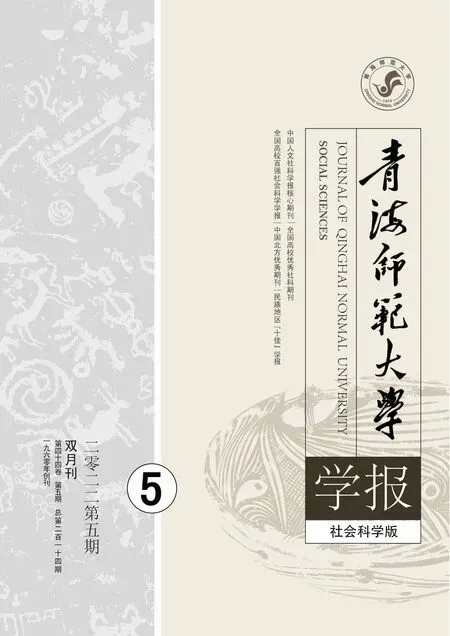寧夏古代文學文獻學建構的典范
——評田富軍《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
趙耀鋒
(寧夏師范學院 文學院, 寧夏 固原 756000)
《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是田富軍教授在《青銅自考》《辦苗紀略》之后的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寧夏古代文學文獻學研究成果,該著運用漢學考證學和宋學義理學相結合的方法對寧夏明清文學文獻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與研究,在文獻考證方面體現了近年寧夏古代文獻研究方面的新進展。《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為寧夏古代文學史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寧夏古代文學文獻的系統整理
首先,《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文獻是抵達以往歷史世界的通道,西方批評家薩義德認為 :“東方學,總的來說,是著作本身和引用著作的體系。”[1]薩義德對“東方學”的闡釋中包含了重視古代文獻的重要思想。在學術史上,寧夏古代文學文獻的價值未被充分重視,《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在寧夏古代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方面是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著作,黨懷興先生認為該著“全面整理總結寧夏明清時期的文獻,挖掘其價值,服務于當代的文化建設,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2]。利用寧夏古代文學文獻建構寧夏古代文學史,前人未曾進行過專題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是非常具有學術前瞻性的。
其次,《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是國內較早對寧夏古代文學文獻進行系統整理與研究的著作。黨懷興先生評價該著說:“他通過查找寧夏舊地方志,查閱各種工具書及相關文獻資料,以搜集著述為主線,進而引出著者,理清著者的生平、家世及著述的基本內容、文獻著錄、存佚情況等;他運用文獻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對傳世著述的館藏、版本、主要內容、寫作特色、價值評判及其對后世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力爭通過對明清寧夏人著述的梳理,找到它們之間的發展脈絡,概括出發展特點,總結其中規律性的東西。”[3]王茂福先生評價該著說:“對著述的相關資料,如作者的家世、生平,對作品的存佚、版本、館藏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全面、系統、細致的調查、搜集、整理和考索,其翔實程度是頗為值得稱贊的。”[4]從上述學者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出,《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對寧夏古代文學文獻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因而其在寧夏文學文獻學學科建構方面的價值值得重視。
再次,《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對區域文學文獻學的建構具有“范式”意義。《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在總體布局上“根據寧夏著述家族化明顯的特點,安排成以家族為基本單元,從核心人物切入,串聯起對整個家族的論述”。因而“形成了一個綱目分明、主次兼顧的結構布局”[5]。在具體的研究中,“對于作者,舉凡姓名、字號、生卒、籍貫、家世、生平、著作、創作分期以及后裔等基本問題,對于作品,舉凡內容、分類、特征、影響、地位、版本、收藏等主要方面,都努力依據史料深入查考”[6]。該著在結構上形成了比較嚴謹的體例,對區域古代文學文獻學的建構具有“范式”意義。
總之,《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對明清寧夏文學文獻的收集已臻完備,這為寧夏古代文學史的寫作打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二、寧夏古代文學史的經典闡釋
在寧夏古代文學史的闡釋中,《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比較重視學術史的梳理。關于胡侍的字,著者列舉了歷代文獻中關于胡侍的“字”的四種記載:第一種是康海《對山集》中記載的“承之”,第二種是《四庫全書總目》中記載的“奉之”,第三種是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記載的“侍字奉之,又字承之”,第四種是明凌迪知《萬姓統譜》記載的“永之”。[7]通過學術史梳理得出的觀點往往比較接近歷史真實。同時,因為學術史梳理涉及明清一流學者的著述,所以通過學術史梳理能夠實現寧夏地方文獻同整個明清中國學術界主流文獻的“預流”,從而將區域文學史的研究同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有機融合起來,這樣既可以提升寧夏古代文學研究的地位,同時又可以豐富學術界對明清文學的認識。
在寧夏古代文學史的闡釋中,《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比較重視以古代著名學者的經典觀點作為建立新的闡釋的文獻依據,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寧夏古代文學的研究始終不偏離學術史的譜系,從而很好地避免了“自我言說”弊端,較好地提升了著作本身的學術價值。該著在寧夏古代文學史的闡釋中往往能夠征引明清著名學者的評價作為批評的依據。對胡汝礪的評價,著者引用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呂柟《兵部尚書胡公行狀》、焦竑《兵部尚書胡汝礪傳》等著述中的史料作為評價胡汝礪的依據。[8]在研究管律生平事跡時,著者引用明呂柟《襄陵尹胡君墓志銘》、楊一清《關中奏議》等著述中的史料作為考證的依據。[9]通過歷代文獻的征引,《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包含了較為豐富的學術史知識,使得該著的學術品味得到了提升。
《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也特別重視寧夏古代文學文本的闡釋。首先,該著對寧夏古代經典作家作品的內容題材進行了詳細的分類研究。如著者把朱的詩詞根據其內容分為寫景、寫思鄉愁緒、寫現實中較大事件和反映百姓疾苦幾類。[10]在俞益謨文學創作的研究中,著者把俞益謨的文學作品分為詩詞和散文兩大類,在詩歌研究中,又把俞益謨的詩歌按題材分為寫景詩、詠物詩、行軍詩、贈答酬唱壽悼詩幾類,對每一類詩歌的思想性、情感性及藝術特征進行了詳盡的分析。[11]其次,著者還對寧夏古代文學作品的思想性進行了深入挖掘。在分析朱秩炅《靈州社學記》一文的思想性時,著者說:“文章從一個婦女守節義而上升到節義關乎到國家存亡道理,可謂言近而旨遠。”[12]這種對作品思想性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其次,著者還對寧夏古代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進行了深入提煉。如在分析趙良棟《奏疏存稿》的藝術性時,作者認為該著的藝術性體現為“感情真摯”“分析透辟,邏輯性強”“語言簡練”三個方面。[13]這種對作家藝術特色的分析提煉是比較深入細致的。同時,著者還經常將寧夏古代作家同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進行比較研究,這體現了著者力圖將寧夏古代文學納入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敘述之中的努力。如對于胡侍文學成就的評價,著者引用明代著名學者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中“雖于風雅未縣合,往往時材骨格殊”作為定評。[14]著者還重視寧夏古代文學作品的文獻價值之研究,如著者從版本價值、史料價值、藝術價值三個方面分析了《青銅君傳》的文獻價值。[15]上述文學作品闡釋方式較為契合現代科學的文學批評模式,因而《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完全符合當代文學史撰寫的學術規范。
《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也特別重視寧夏古代文學生成的文學環境的研究。法國浪漫主義的先驅人物史達爾夫人認為地理、氣候影響民族性格、社會制度以至文化藝術。[16]該著也非常重視文學生成環境的研究,著者在分析明代寧夏文學思想時說:“寧夏地處邊鄙,地理位置特殊,朝廷控制極嚴……思想觀念自然比內地更為傳統保守。”[17]“環境研究”增強了寧夏古代文學闡釋的深度。
同時,《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也提出了寧夏古代文學史建構的一些重大理論命題。因為寧夏古代著名文士較少,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作家之間的相互交流也少,作品的傳播范圍有限,文學創作長期較為沉寂,在這樣的背景下撰寫寧夏古代文學史面臨許多困難,著者對這些問題都進行過深入思考。對于寧夏古代文學的價值,著者反對“地域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余波”[18]的觀點,認為地域文學的差別“只是表達效果的問題,并不是我們所謂意義的本質特征”[19]。這肯定了寧夏古代文學史研究的價值與意義。著者也從三個方面提出了評價地域文學價值的標準:其一,“鮮明而準確地體現這種(地域)特色的文藝作品方能稱之為這一地域有代表性的作品,揭示出這種特色的文學史方能稱之為好的地域文學史”。其二,“地域文學或著述對該地現實社會生活有很好地反映和記述”,“能抓住這樣的文學和著述來進行史的評價的地域文學史也才是好的文學史”。其三,“地域文學能從整體上成為精神世界的承載者、心靈深處的寄托者、價值評判的外化者,就是很好的地域文學”。[20]這些深入的理論思考體現了著者在寧夏古代文學史的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理性思辨色彩。
三、廣博的文獻視野
首先,在文獻收集階段,《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對寧夏明清兩代存有著述的作者已搜羅無遺,而對作品的搜集也已臻完備的程度,即使有遺漏,怕也只會是斷簡殘篇了”[21]。而且,該著重視原始文獻的考索,注重從各種文獻版本源流關系的考證中得出結論。著者在全面而系統的文獻考證基礎上,制作了一系列統計表,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明清時期寧夏文人《詩文集簡表》和明清時期寧夏文人《其他著述簡表》,這些統計表從宏觀的角度初步勾勒了寧夏明清文學的發展脈絡。另外,在具體文士及其作品的研究中著者也制作了一系列統計表。家族內作家考證方面如《趙良棟后人基本情況表》[22],這個統計表清楚地呈現了趙良棟后人的世次、子女情況、官職履歷。作家文集版本考證方面的統計表如《〈青銅自考〉中科院刻本、北大抄本、臺灣抄本卷冊對照表》[23],該表詳細列舉了《青銅自考》各種版本在卷數、冊數、序跋、作品篇目、作品內容,以及同一作品在不同版本中的位置等方面的文獻差異,這些統計結果是建立在著者翔實的文獻考證的基礎之上的。這些統計表格為寧夏古代文學史的建構提供了較為扎實的文獻依據。
其次,在文獻的考證方面,《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較好的實現了寧夏古代文學文獻與中國傳統學術的“預流”。一方面,著者以寧夏方志的考證為切入點,通過對明清兩代寧夏方志中著錄詩文的整理建立了明清時期寧夏文學文獻的大體框架。以此為基礎,通過寧夏方志對明清士人生平記載的考證,深入挖掘明清士人散篇著作。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努力,著者初步建立了寧夏古代文學文獻的基礎。另一方面,著者通過明清時期相關書目文獻對寧夏士人及其創作著錄情況的考證,將寧夏古代文獻的研究納入整個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文獻的研究之中,這種研究理路提升了寧夏古代文獻研究的學術價值。如在胡汝礪研究中,著者對明代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焦竑《國朝獻徵錄》、雷禮《國朝列卿紀》、呂柟《涇野先生文集》等文獻中的史料進行了考證[24],通過胡汝礪生平的考證實現了寧夏明代文學同整個明代文學研究的有效銜接。在考證張嘉謨生平時,著者引用清李希賢《乾隆忻州府志》和清倪濤《歷朝書譜》等文獻中的史料作為考證的依據。[25]該著通過“互文”結構,將地方文獻與整個明清文獻相銜接,從而建立了豐富的、立體的寧夏古代文學文獻學體系。
再次,著者通過明清時期重要文獻書目對寧夏士人及其著作的考證確立了寧夏士人及其著述研究的學術價值。如著者通過《千頃堂書目》考證胡汝礪的籍貫[26],通過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考證張嘉謨的生平[27],通過明朱睦《萬卷堂書目》、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考證楊經《嘉靖固原州志》[28]。通過明清時期重要文獻書目的考證將寧夏文士的創作納入整個明清文獻體系之中,這種考證方式彰顯了寧夏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
四、科學的研究方法
郭沫若評價王國維說:“那遺書的外觀雖然穿的是一件舊式的花衣補褂,然而所包含的卻多是近代的科學內容。”[29]評價現代學術研究有兩個維度:一是系統性,二是科學性。系統性和科學性也是《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的學術價值之所在。
系統性主要體現在著者對各種文獻材料的組織方面,著者把所有文人著述的相關文獻材料按照“著者生平、文獻流傳、版本鑒定、內容分析、藝術探討、后世影響”[30]這樣的結構組織起來,雖然是“將五百多年的省級地域文獻研究在一部著作中囊括”[31],涉及時段長、作家多,但是作者以家族為結構單位,在每一家族中依據作家創作成就的高低把相關作家依次排列,這樣的組織結構使得本書層次分明,結構清晰,系統性強。
在文獻考證方法方面,《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建立了文學文獻研究的典范。該著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對史料文獻的具體考證,這種方法也是最為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如著者對胡侍生平中“尋命復職”一事的考證,通過《明實錄》、《明史》、胡侍文集的相關考證,得出胡侍昭獄之后一直在家閑居而“并未復職”的史實。[32]在具體文獻考證的過程中,重視歷代實錄、正史等基礎文獻的學術價值;同時,注重各種文獻記載之間相互關系的解讀。上述這兩個方面的考證功底往往影響研究的結果,史料考證顯示出了著者扎實的文獻學功底。
在文獻研究中重視“二重證據法”的運用。王國維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古史的研究中取得極高成就,就是因為他較早在研究中運用了“二重證據法”。 當代的學者往往重視傳世文獻的考證而忽略考古發現之史料。《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書較為重視考古發現之史料的價值,如在朱名字的考證中,著者利用了寧夏博物館收藏的《慶王壙志》碑文的相關記載,并以此作為考證朱名字的最為重要之證據。[33]在考證管律的散文作品時,著者利用《寧夏歷代碑刻集》的文獻進行考證。[34]在考證俞益謨事跡時,著者引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和寧夏博物館藏《俞益謨妻秦慈君墓志》碑作為考證的依據。[35]注重考古發現的史料也是該著的一大特色。
總之,《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運用科學的文獻考證方法對寧夏古代文學文獻進行了系統研究,該著是寧夏古代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典范,為寧夏古代文學史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