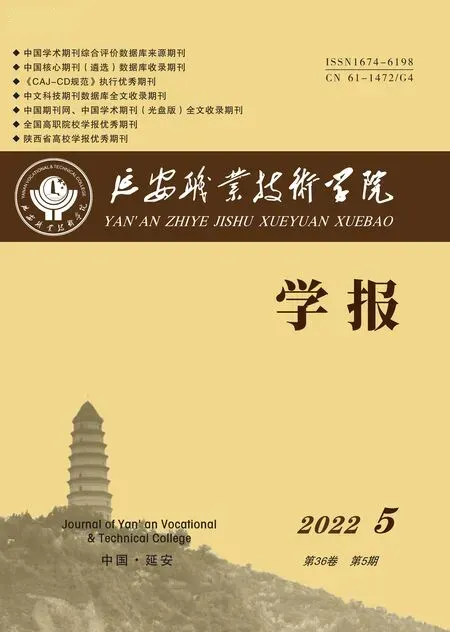晚明塵寰與文士的復雜心態分析
——以宋懋澄尺牘為例
洪月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宋懋澄(1569—1620)字幼清,號稚源,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人,明后期文言小說家。他喜詩文,尤喜小說家言,其文言小說《負情儂傳》《珍珠衫》后被馮夢龍重寫為《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影響著此后小說創作。的確,宋懋澄的小說創作是其文學生涯的犖犖大者。但是,其小說的抒情意味淡薄,心態的呈現遠不及尺牘顯明。此前學界多側重對宋懋澄文言小說的研究,對其尺牘關注不多。鑒于此,本文著重分析宋懋澄的尺牘文本,探究其尺牘中的隱微心態,管窺晚明塵寰中文士的復雜心態,一定程度上也可探微其小說文本的創作心態。
一、八股制藝下晚明文士的心態流變
八股制藝專為科舉而設,對文士思想極具控制性,毀譽各半。八股文歸屬于一種應試文體,原不屬于文學范疇,特定文化生態下卻成為了左右士人命運的文體。讀書人若欲入仕,便要掌握八股文的寫作技巧,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八股文成為了明清文士出仕的敲門磚。可是,明清兩代讀書人對八股取士的認知視閾并非一成不變,具有流動性,心境亦隨之流變。因此,晚明文士時常處于難以調和的矛盾之中。宋懋澄曾言:“弟少年,隆冬往來幽薊,耳面風削,略不忘生此傖,雖少加韻,猶是正月東風。”[1]652少年之時,盡管路途顛簸,寒風侵肌,他對未來仕途卻仍心向往之,殊不知科舉終將成為遮蔽其一生的烏云。
宋懋澄十歲始習制藝,然而他少年意氣,任由心性,專讀《資治通鑒》《左傳》《韓非子》《史記》之類古書,亦喜讀唐詩,于其尺牘皆有直接或間接的體現。他認為“嗜古則能文”[1]660,亦堅守“以讀書消歲月則樂,以之干功利則束情”[1]660與“讀書不必過人,正令得其趣”[1]657的觀念,宋懋澄認為讀書應以興趣作為導向,心懷好古之心,倘若僅以出仕為目的,則往往會被功利之心制約心性,可見其文化素養對讀書目的及范圍選擇的影響[2]147。如是,種種不合時宜的主觀傾向成為其科舉接連碰壁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懋澄的心態流變存在歷時性的轉變與關鍵性的節點,二者皆與其科舉經歷密切相關,且不同備考階段呈現不同狀態,因而尺牘書寫也顯現出微妙的心態變化與情緒的反復。談及科舉經歷與心態,宋懋澄言:“我二十年前,好名貪得,庚寅巳后,備嘗艱辛,始信奢儉苦樂,總是一妄。然猶以進取自勵,至甲午病胃犯噎,乃慨然束經,病中追思往念,悉已成空,遂并一切諸好,亦復澹然。”[1]653此言直接點明其在庚寅巳后與萬歷甲午兩個時間點前后心態的流變,即由“好名貪得”到“備嘗艱辛”,再到“亦復澹然”的轉變。他一生參加科舉考試十一次,除壬子年南京秋試中第,其他均落第。除萬歷甲午因胃病犯噎未參加秋試,他參加了有生之年所有的科考,整整十一次。因此,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宋懋澄內心其實是認同科舉制度的。可以想象,一個少年在一次次的鎩羽而歸,不得已強行調試心態,接著再作馮婦,重新鉆研八股制藝,在一次次的惡性循環中消耗了大量資產,也耗盡了所有的意氣,而晚明又有多少此類蹭蹬的少年,無法定量。歷經數次失意后,宋懋澄的心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對以八股文為功令文字的科舉考試有了更為深刻而復雜的認識。他言:“此君白雪微有寒,懇請雕商刻羽衣助暖律。”[1]653此處的“微有寒”有隱喻之意,既指冬日氣候的寒冷,也有對仕途不易的心境之寒,具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寓意。可見,科舉使其物質生活變得窮困窘迫,唯有向友人求援,更使其心態壓抑,意志動搖,心境寒苦,精神受到束縛。因而,他感嘆:“少苦羈紲,得志,但愿畜馬萬頭,都缺銜轡。”[1]662銜轡羈紲了千里馬,猶如八股文羈紲了蹭蹬士子,唯有雄鷹高飛,才能不受塵寰羈絆。此種象征性的抒情,是諷刺也是無奈。宋懋澄亦言:“吾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亦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自今甘君子之疾永遯世之貞。”[1]654看似甘心實則不甘,看似輕蔑實則無奈,看似遯世實則戀世。在以八股文為功令文字的科舉文化生態下,這種心態上的矛盾與流變普遍存在于晚明文士中。
二、晚明文士生存焦慮下的兩難之境
尺牘作為文人抒發心緒的載體,書寫著晚明文士的無奈與焦慮。生存焦慮源于生活,反作用于生活,兼具有形與無形的統一。宋懋澄尺牘中所透露出的復雜心態,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生存焦慮。于他而言,家族血緣與地域文化、以八股制藝為功令文字的科舉考試、“學而優則仕”的社會定見、個人的物質經濟狀況等是有形的;而由有形衍生的一系列諸如個人內在氣質、社會責任感、同輩壓力等無形之感,也早已內化為一個人的性情。有形與無形相抵牾時,人的心態便容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這種困境在宋懋澄的尺牘中可具化為情與理和情與禮的矛盾,也意味著他必將陷入在塵寰浮沉里欲罷還休的惡性循環。
宋懋澄出身于松江的文化世家,深受儒家傳統思想濡染。明代的松江府不僅是繁榮富庶的江南巨郡,而且是文教興盛的科舉重地,人才濟濟,這預示著他必將受到家族血緣、地域文化等人情因素的影響。從小浸潤于江南濃厚的文化氛圍與家族的文學傳統中,昭示著家族使命終將成為其一生的桎梏,甚而不得不將其內化為生存意義。談及家族使命,宋懋澄坦言:“弟之羈紲,夫何故哉?先人有未瞑之言,思籍一第以報命。”[1]655足以見得家族使命對宋懋澄的思想影響巨大,影響著他對人生路徑的選擇,甚而內化為一種無形的生存動力,乃至成為其一生的追求,以致轉為終生的桎梏。此外,宋氏家族既是文化世家,亦是巨賈之家,為其提供了充盈的文化資源與物質資源。因此,當其好友錢希言遇家難,不得已放棄科考從事小說創作時,宋懋澄卻因家境殷實,仍可潛心科舉。禍福相依,相對充盈的物質資源卻使其無任何理由放棄科考。他對稗官小說心向往之,卻不能潛心于此,在對功名利祿趨之若鶩的時代大生態下,他別無選擇,唯有在八股取士的道路上舉步維艱。
“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傳統陶染著諸多讀書人,宋懋澄也不例外。他熟諳經史古文,自小受儒家傳統思想熏染,“學而優則仕”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其潛意識里的理所應當,某種意義上也是晚明文士對政權依傍的體現,更是文士缺乏生存獨立性的表現。對此,他曾直接宣稱:“人生累我,豈惟父母妻子,皆為古人所累。”[1]658父母妻子的期待是有形的人情因素,但古人所遺留的出仕傳統卻是無形且根深蒂固的思想因素,此言顯然是對儒家出仕傳統的不滿與無奈。不過,他持質疑態度同時,卻也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他直言:“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1]661此處“經權”是宋明理學用語,是封建倫理綱常的具化,徑直體現了宋懋澄對傳統讀書目的的認同。顯然,一時的質疑只是其生存焦慮影響下的無奈之舉,其遵循的讀書宗旨完全符合儒家傳統,他的不自洽行為勾勒出晚明文士的微妙心態,蘊含著入世與出仕的矛盾。
可以說,宋懋澄與阮籍、嵇康等人皆非實反禮教。談及禮,宋懋澄直言:“仁義禮智信,終非止足處。”[1]659貌似對禮并不贊許,卻表征了他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現狀。龔鵬程言:“禮有兩種,一種是能使人達到生命和諧狀態的真正的禮,另一種是一般世儒所膠執堅守的那種純然外在的名義器數之禮。”[3]21其實,此處禮的兩種形式并無明確的界限,且常常共存,而多半晚明士人的郁結在于想要二者兼得,宋懋澄亦然。
宋懋澄自詡道:“世人見尋警尋,見尺警尺。他日見我,良應銷魂。”[1]658出語直率,除卻了傳統君子的溫柔敦厚與謙恭卑讓。他慨嘆:“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1]654顯然,宋懋澄認為識見與人品之間存在著沖突,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情與理的矛盾,亦是其生存焦慮的具化。談及情,宋懋澄寫道:“人生情耳,能無思乎?”[1]660他強調情是與生俱來的本能,講求性靈,與多數晚明文士一致。另外,他在尺牘中流露出對英雄、美女和山水的向往和熱衷。他直言:“士恨不生于戰國,當斬張儀而咤魯連。”[1]658可見其對建功立業的渴望與人生價值的多維審視,更是其現實心緒的折射。談及美女,他坦率說道:“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1]655其實,對美人的傾慕也只是其內心情緒抒發的窗口之一,是隱微情感的顯性化。可以說,這既是一個人的情懷,也是一個時代社會風氣與觀念的體現,即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區,女子可以游歷佛寺、參與廟會,觀念相對較為開放,生活和思想皆較為豐富多元。親近山水景物是晚明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友人間的尺牘往來顯露出晚明文士的共同關懷。宋懋澄曰:“宜水宜山一道人。”[1]661他對江南山水心向往之,但或許他更欣賞的是山水之外的至情人生。他亦寫下:“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煙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肅肅,與千秋俱下。”[1]653如是,自然景物也披上了心緒的外衣,顯得蕭條與清冷,皆是其幽微心路的顯性化表現。再者,山水亦難以親近,即其所謂:“彈夜光于碧漢,不可以為星沉;昭華于清流,不可以為月。”[1]652兩個“不”字,表面是對自然現象的客觀書寫,本質上卻顯露著他生于塵寰,累于萬物的幽微心態。如是,他直言:“讀書、飲酒、種樹、筆削皆養生之道,然萬物為其所累。”[1]658他認為閑適的讀書生活,本應是性情的釋放,但卻累于塵寰萬物,受限于禮。終究,情與禮還是互相抵牾,無法融合。
丁元薦《西山日記》寫道:“愿為真士大夫,不愿為假道學;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下此心,便是人欲。”[4]丁元薦直接談及“天理”與“人欲”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指明了當時常態化的社會現象。可見,情與理的矛盾心態普遍存在于晚明士大夫中。
三、晚明文士宗教觀念的淡化
晚明禪悅之風盛行,宗教是一個熱門的話題。然而,中國人的宗教觀念,遠遠沒有西方人那般虔誠與純粹,顯得更為理性與功利,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儒家傳統思想早已先入為主。較之宗教,中國傳統文士似乎更熱衷詩歌,“詩言志,詞言情”似乎已足夠吐露他們的失意與得意。于是乎,宗教的存在似乎更像是一個備胎,只是特定時期的產物,如魏晉亂世人們心靈長期無法得到撫慰之際,宗教便興起。戰國、魏晉、晚明等時期的宗教發展各有其特征,因而文士心態皆有或顯或隱的變動,如羅宗強言:“戰國、魏晉和明代后期,士風與士人群體之心態,都有著較大之變動。”[5]1此言明確點出士人心態深受易代影響,與政治環境有著密切關系。
晚明歷來受到學界重視,較之魏晉,晚明文士心態復雜得多。至晚明,八股取士制度固化、思想多元分化、土地兼并、流民增加等社會現象凸顯,時刻影響著文士的生存。如是,太多失意科舉、命途多舛、追尋人生意義無果的晚明文士選擇恬退,并以宗教安撫心靈。因此,他們參禪學佛,并非隨順時風,好奇呈異,也不是要以此對抗什么“封建禮教”與“程朱官學”,他們對宗教的關注基于對生命的關懷,或許只為妥善解決自身當下的生存焦慮。晚明士人的宗教觀可以具化為生死觀,生死觀是許多士人思想中的一個普遍存在,失意者更甚。晚明士人久困科場,對生死存亡有了更為深刻而復雜的思量。宋懋澄認為:“但愿一生受不死之疾,至四十許,杳然長逝可也。”[1]657也感嘆道:“自盤古以至今日,人未嘗死也。”[1]658前者將生死作為一種客觀的生命現象,后者將生死上升為一種精神力量,二者的書寫時間與語境存在差異,因而指歸不同,但卻殊途同歸,皆可管窺宋懋澄不同人生階段與境遇下的生死觀。可見,宋懋澄的生死觀是與時而變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理解,有時甚而上升為帶有宗教意味的哲思。此外,他亦言:“死如月過天上,影落江河溝廁,悉無一染。”[1]661死后才能無染,恰恰表明塵世有染,有所牽絆。“染”為佛家語,其對佛家彼岸世界的憧憬一定程度上是對現實塵寰失落的體現。
不可否認的是,宋懋澄的尺牘中確實蘊含了宗教情愫與佛道教義,也隱含著宋懋澄對塵寰萬物的關切與人生意義的思索,某種意義上是他回歸自我的調適,但也時刻流露著其迷惘的心態。宋懋澄言:“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成,恍然凈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1]653他認為宗教仙境為凈土,高潔神圣,自己功德不足,但卻心懷虔誠,心向往之,其復雜心態在“凈土”的陪襯下變得顯明。宋懋澄時常論及佛道之理,如“和尚不須梳鏡,未免壞卻剃刀。”[1]657詼諧的佛教理趣中也滲透著生活的哲思。另外,宋懋澄與佛道中人頗有交情,其好友當中亦有若干參禪悟道之人,如陳繼儒、錢希言等,皆科舉失意,一定程度上也是其社交語境的體現。再者,宋懋澄與友人的尺牘中頻頻直接或間接地滲透佛思,論及生存困境,抒發人生感慨,皆是其微妙心態的具化。他指出:“涉世不深,不知境苦;妄念不繁,不知業苦。”[1]654徑直闡明其深入塵寰與妄念生成后心態的流變,點明處世不易與出仕艱辛,以及漸漸對人生有了更為深刻而復雜的認知。他言: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于樹外見天,以為天盡于樹。”[1]661點明佛法的深邃,俗人對佛法的認知有其局限性,可謂徑直向友人傳播佛教教義,同時也暗含著宋懋澄對其時科舉制度弊端的認知,更表達了他對生于塵寰的感喟。他又言:“病者小人所苦,而君子之幸。人若未死,唯病可以寡欲。某不患無得,惟恐病之不常來。”[1]657與“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1]654君子以病態求得無欲無念,不為外物所動,不蠅營狗茍,順其自然,以求內心之平和與恬靜,字里行間皆滲透著人生之思[6]171-176。此外,宋懋澄尺牘亦徑直談及友人好佛,如:“吾友子晉,嘗言北行顧景生涕,子晉好佛,諸相未忘,雖鬢骨緇流,猶當質諸燕月。”[1]659此處“諸相”乃為佛教用語,指一切事物外現的形態,而“緇流”則指僧徒,可見晚明文士對諸多佛教用語極為熟稔,引用頗多,但“猶當質燕月”一句卻仍摻雜著現實的情愫,淡化了其中的宗教色彩。然而,所有的宗教情感與生存之思終究歸于一句“十年來奉教西方,而猶然以功利為戚,豈善男子邪?”[1]653宋懋澄坦率表露自己奉教西方卻仍被功利之心羈絆,俗心難泯的困境。要之,宋懋澄在塵寰的功利心性與濃厚的俗世愿望面前,宗教觀念亦不自覺隨之淡化,顯得不夠純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晚明宗教世俗化的體現。
的確,佛教中深邃的哲學思考吸引了宋懋澄,使其可暫時擺脫塵寰的困擾。但是,長期浸潤于儒家思想的他,無形之中早已對功名利祿產生了執念,看似云淡風輕的佛教觀念背后,是愈發執著的功名意念。要之,即儒家觀念并未在晚明文士的宗教觀念中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