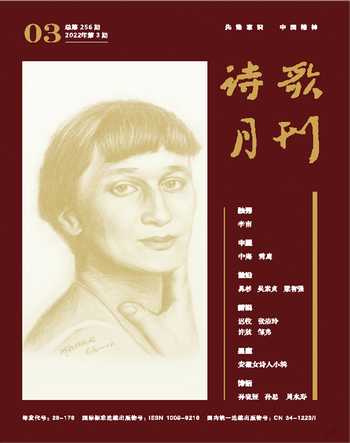詩人是稀缺的物種(隨筆)
李南
我大約是一個不喜歡湊熱鬧的人。常常,在生活中,我沒有什么人交談,寂寞、孤獨滲透了每一個毛孔。寫詩就是我和你,和他,和另一個我說話。我漫不經心,什么也做不好,經常丟三落四,我總懷疑自己不配過正常人的生活。
寂寞是詩人的唯一可靠的朋友,它一直在清理詩人的精神結構,把那些非詩的碎片剔除,詩人與寂寞相伴,寂寞讓詩人心靈干凈,也是對詩人最好的回饋。
年輕時,曾經狂熱地愛著詩歌,把詩歌看成一種精神的宗教。隨著歲月更迭,對詩歌的熱愛也產生了位移。在我看來,這個世界上,比寫詩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還有很多。
詩歌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白描、還原,更不是提升,而是交織在現實與臆想之間的最高杜撰。“詩在語言上的成功取決于組詞的方法,詩歌表現必須產生驚訝的效果”,1990年,我第一次聽埃利蒂斯這樣說。出色的詩藝表現在一種新的、陌生的、不確定的語言成份,同時也表現在一種思維的“出乎意料”和“情理之中”。我試圖通過自己樸素的語言來踐行這些。
我反復地問自己,是不是已經進入到詩歌的內部?回答是,我不知道。在寫詩上,我有許多盲區,不敢輕易僭越。進入新世紀以來,我的詩風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先追求詩歌語言的絕對純凈,而現在漸漸消失,夾雜進許多看似混濁的詩句;且從詩意捕捉上,也在不斷地拓寬表達的邊界;原先形式單一整飭的吟詠,現在變得矛盾重重,出現了復調。越寫,越發現我弄不明白的元素太多,有詩歌技能方面的挑戰,也有表現客體上的篩選。
我身邊的詩人朋友說起大師是一臉羨慕,對于這個問題,我經常感到困惑。我常常反思,這是一個波譎云詭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精神匱乏的時代,我們目前的寫作是否能配得上這個時代?我想起過去的詩人們,他們是怎樣面對他們的時代,用詩歌來表達他們所經歷的一切?每每想到此,感到作為一個詩人的路途漫長,我們離大師的距離幾乎讓人絕望。不過沒關系,對我來說,寫詩只是一個完成自我的過程。
自白話詩寫作以來,歷次詩歌的前行,無不伴隨著精神的解放、語言的革新、創造力的爆發。在當今,快節奏的生活、快餐式文化的消費、互聯網的介入無疑都在一點一滴地消蝕著詩歌的抒情本質。解構當然是對詩歌的一種貢獻,我更加崇敬那些為建構詩歌做出貢獻的詩人。
能成為一個優秀詩人,也是許多詩人不懈的追求。我覺得一個優秀詩人的標配:經典化的寫作,跨文體的駕馭能力,以及可持續的創作力。
有一陣子,我對詩歌產生了懷疑。既然它不能改變詩人的三觀,不能給詩人帶來豐厚的物質生活,為什么總是有詩人前赴后繼,源源不斷地加入到詩人的行列?我在一首詩中寫道:詩人是一個物種/瀕臨滅絕。但看到一波又一波比我們這一茬詩人學問好,見識多,更有創造力的年輕詩人一直在為詩歌的存在正名,我感到很欣慰。因為在當下,這個問題遭受到很多人的質疑,詩歌的小眾化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考驗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他的定力,他的執念,他對文字無條件的熱愛,他決絕、義無反顧地擔負起這份責任,他們正是這個時代稀缺的物種。
這兩年,我一直在學習在詩中如何釋放自己。我正在試圖改變戴著面罩寫作,或站在道德高地寫作,還原一個日常真實的自我。恰巧,我讀到米沃什的《烏爾羅地》,第一章中他就寫到了這個問題,他說“釋放自己意味著同讀者對話,同時期待著他們的理解和信任的眼神”,但是如何釋放自己?他沒有談到。
以我淺薄的理解,釋放自己就是從個人記憶中挖掘,從個人經驗中尋找,從日常生活中感悟,從反復的詞語練習中淬煉,但是作為一個內心羞怯的人,是不是能夠向讀者敞開心扉?這不僅僅是個語言表達問題,也是詩歌倫理學的問題。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說過一段話,讓我記憶深刻:“作者不含著淚寫,讀者就不會含著淚讀。寫的人既然沒有驚喜,讀的人也絕不會覺得有趣。”
這是在講詩人的“真”,“真”是詩人詩歌寫作的前提條件。我無法想象一個渾身上下都摻假的詩人,怎么可能寫出激越人心的好作品?當然,也并不是只要有“真”,就一定能寫出好詩,詩歌說到底是一種藝術,藝術的言說方式自有它的特點,詩歌語言是一個詩人終生溫習的功課。真誠面對讀者,真實書寫內心,真切關懷世界,心靈的真實與藝術的幻覺產生了奇妙的平衡,才有可能寫出優秀的詩作。我力求自己避免空對空的抒情。一堆華麗詞句的堆砌,在詩中看不到詩人的面目,感受不到詩人的心跳,哪怕一丁點也沒有,這樣的詩無疑是偽詩。
如何甄別一首好詩?初學寫詩時你是無法判斷的,常常是人云亦云,一首詩好在哪里,妙在何處,你還沒有能力精確地指出來。這不要緊,我們都是通過漫長的詩歌練習期,大量的閱讀,走心的體悟,或與詩人朋友交談,你都會有新的長進,分辨一首詩的好壞,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
這兩年以來,全球疫情改變了世界,可以說每個人都有了一次深度反思的機會,關于活著和死亡、人性的幽微……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現實。我已經沉默了許久,無法用詩的語言來描述。
我仍然在寫。常常仰望著詩歌那高高的金字塔尖,其中甘苦,心中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