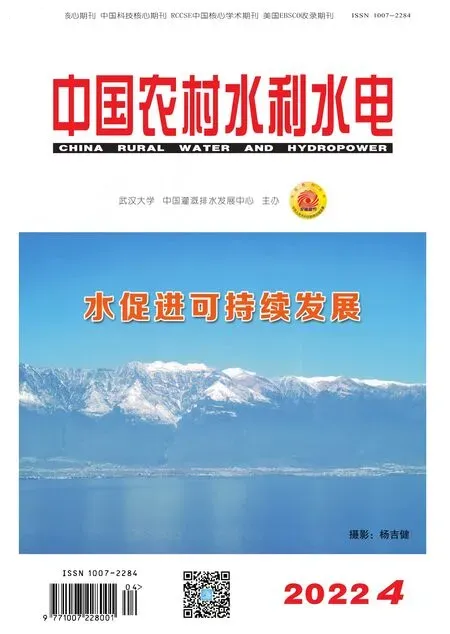農戶參與度對河長制政策獲得感的影響
劉 芳,朱玉春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楊凌712100)
0 引言
村域河流資源作為基礎自然資源與經濟資源,是鄉村振興建設中生態宜居、產業興旺的重要保障。隨著河流治理成效逐步凸顯,河長制對公共資源治理的借鑒意義越來越受到政界和學界的重視,而公眾參與河湖治理被視為突破政府科層權威、釋放農戶話語權、賦予農民治理主體地位從而實現河流治理目標并創造公共價值的重要途徑。農戶參與村域水環境治理對公共資源治理提供了新的經驗。已有研究證明公眾參與能補齊基層河長“單核治理”能力短板[1],彌補河長制“運動式治理”弊端[2]。現有少量研究實證分析公眾環境監督行為對城市工業污染的治理效率[3],但其研究結論未必適用于農村地區。相較于近年高位運行的輿情熱度,一方面,農戶參與鄉村環境治理成效的實證研究相對稀少,主要集中于理論介紹、模式探討等方面;另一方面,關注農戶自身需求滿足感與政策獲得感的研究尚缺,更多以政府投入-產出效率為研究視角探討公眾參與對政府管理的工具價值。
人民對環境治理政策的獲得感,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論的重要體現,是檢驗政策實施效果重要標準之一,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內在要求。獲得感是人們付出勞動使得自身需求得到滿足后的愉悅感,與自身需求緊密相關[4]。借鑒貧困人口扶貧政策獲得感定義[5],本文將農戶“河長制”政策獲得感定義為其在參與“河長制”政策實施中的客觀性滿足與主觀認知評價。基于王力長江經濟帶河長制政策推行的準自然實驗結果,實證檢驗了河長制的環境與經濟雙重紅利效應[6],再結合實地調研情況,農戶關注河流治理的生態績效,更關注村集體治理社會綜合效益溢出,故將政策獲得感分為生態獲得感和社會獲得感。本文研究聚焦農村區域,以農戶政策獲得感來衡量居民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普惠性,基于江蘇、湖北兩省農村調查數據,考察農戶參與度、政府信任與政策獲得感的影響機理,用層次回歸線性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嘗試為激活農民參與效能,提升“河長制”政策獲得感,優化河長制制度提供針對性方案。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農戶參與度是否提升政策獲得感
“獲得感”概念源于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是基于客觀獲得而形成主觀感受與評價[7]。盡管獲得感是現實獲得的主觀感受呈現出個性化樣態,但其背后承載著以“勞動-獲得”邏輯為支撐的客觀規定性[8]。少有研究論證公眾參與度與政策獲得感的關系,但公眾滿意度影響公眾參與關系被證實。以湘潭社區數據的實證證實公眾參與社區服務與公眾滿意度存在顯著正相關[9];在江蘇省蘇州市數據實證中發現公眾參與對公共服務滿意度有積極作用[10],側面論證公眾參與影響獲得感。農戶參與村域河流環境治理是爭取自身談判權表達利益訴求,并降低整體交易成本提高治理績效的舉措。
首先,農戶參與表達自身人居環境需求偏好,幫助政府調整治理績效目標,契合農戶治理需求。Ho證實公眾參與利于政府識別績效目標,扭轉以資源投入和組織產出為績效標準的傾向[11],縮小公共物品供給與民眾需求偏好間的差距[12]。農民作為村域水資源直接受益者參與治理,根據自身需求與政策情景經驗獻策,可彌補領導與專家認識理性有限性,實現行政決策科學性。農民作為制度直接實踐者,更了解渠道構建與機制設定缺陷,可幫助政府優化參與制度建設,實現政民間良性協作契合農戶環境需求,甚至效益溢出至社區綜合治理范疇。
其次,農戶參與可建立自下而上信息反饋機制強化外部問責,糾正基層政府政策執行偏差,滿足農戶治理期待。公眾參與減少信息傳遞扭曲概率,吸納多方政策資源,降低政府決策失誤[13]。農民出于自身生存需求與產業發展需求愿意對政府問責,運用信息資源優勢約束政企共謀行為并矯正執行偏差,確保政策落地實施。農戶參與環境治理監督-管護-決策,分擔部分環境治理職責,既降低政府對排污行為的監察壓力與基層環境治理漏洞的檢查壓力,約束政府尊重農戶意愿。高程度農戶參與改善治理效率,滿足農民人居環境治理期待,增強政策獲得感。
假說1-1:農戶參與度對生態獲得感有正向影響。
假說1-2:農戶參與度對社會獲得感有正向影響。
1.2 政府信任在農戶參與度與政策獲得感中的中介作用
政府信任,指公眾與政府互動中形成對政府組織自主承擔公共責任、實現公共利益的信任程度[14]。公眾參與治理可消除政府與公眾間隔閡進而改善信任水平[15]。首先,公眾參與政策制定更易形成公眾對政府支持[16]。農戶參與決策過程后更確信政府決策正確性與長期收益性,并隨著參與程度越高更易接納各方利益矛盾最終形成利益共識。其次,在縱向層級結構中,鄉鎮政府作為農村環境治理的直接實施者,是距離農民最近的體制末梢,其政府回應性與農民參與程度相輔相成[17]。農戶參與程度越深越能與政府形成加強網絡,增強開放性與回應性,進而改善農戶對政府的信任度。
假設2:農戶參與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作用。
政府信任是依賴于法律、政治等制度環境,建立在“非人際”關系社會現象上的信任[18]。隨著傳統鄉土社會消散,鄰里間日常往來頻率降低,人際信任日漸淡薄,政府信任成為環境治理重要工具。其一,高政府信任可提升行政決策認同感與實際支持率,實現政策目標改善治理績效[19]。政府信任代表著農戶與村級河長緊密合作關系,可提升農戶政策支持度,節約政策執行交易成本,調節農戶對政府的期待值與回應性,促使政府提供優質環境治理服務。其二,政治信任是一種倫理約束,要求治理政策制訂與實施要以民眾環境需求為導向,避免政策執行扭曲,提高治理效率與效果。其三,高水平政府信任幫助公眾形成穩定樂觀預期[20],農戶相信政策實施的短期低成益將通過持續措施得以轉變,提升政策的公眾支持率與公眾獲得感。
假設3-1:政府信任對生態獲得感有正向影響。
假設3-2:政府信任對社會獲得感有正向影響。
基于以下研究假設,本文為探討農戶參與度對政策獲得感的影響,提出研究假設模型(圖1),重點考察農戶參與度對政策獲得感的直接影響與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圖1 研究假設模型Fig.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2 模型、數據與變量
2.1 模型設定
本文選取Baron 和Kenny(1986)提出的因果逐步回歸方法直觀、形象地驗證中介模型[21],并輔以Preacher 和Hayes(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檢驗中介效應[22]。
(1)基準回歸模型。被解釋變量是政策獲得感,衡量維度分為生態獲得感和社會獲得感。衡量指標是主成分分析后的綜合得分值為連續變量,選擇普通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式中:Y為農戶i對政策獲得感;k取1 和2,分別代表生態獲得感、社會獲得感;Ic、Rc以及P為解釋變量,分別表征個體特征、河流特征與農戶參與度;?i表示誤差項。
(2)中介效應檢驗與分解。農戶參與度會通過政府信任度影響政策獲得感。

式中:GT為政府信任度,根據系數χ、?1與?2差值的系數符號與數值大小,初步判斷政府信任中介效應是否存在,再通過Bootstrap檢驗中介效果并分析作用程度。
2.2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9年8月在湖北省和江蘇省開展的實地調研。湖北省和江蘇省均位于長江中下流、水網密布、河湖眾多,屬于水資源豐富、河流資源問題復雜的代表性區域。在實地調研過程中,遵循分層抽樣與隨機抽樣相結合的原則,采取問卷調查與農戶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兩個省份80 個行政村共730戶農戶被抽取,剔除缺失數據和有異常值的問卷,最終獲取有效問卷694 份,有效回收率為95.06%。本文選取長期居住在流域附近的農民作為樣本,對村域河流治理情況、政府信任、制度規則都有較高認知,能充分反映不同性別、年齡、學歷人群對河流治理績效評價,樣本農戶與河流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樣本農戶特征及河流特征統計性描述Tab.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sample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river characteristics
從樣本基本特征來看,受訪農戶呈現如下特征:以男性為主,占79.39%;以46~55 歲和56~65 歲為主,分別占31.7%和24.93%;以初中文化為主,占比為41.50%,其次是高中或中專水平,占19.16%。樣本的基本情況符合農村老齡化,農民文化程度低的現實情況。從河流基本特征來看,58.21%的農戶認為河流資源在社區經濟發展中發揮較大或很大作用,只有6.63%的農戶認為河流資源對經濟發展作用較小或很小;67.29%的被調查者認為在過去三年本社區的生活、生產活動未受到了水污染的影響,這表明農戶基本認可河流在農村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并且有相當部分的農戶認為環境影響到日常生活,說明村域河長制政策實施有其必然性。
2.3 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生態獲得感是指農民因參與村域水環境治理而使得其人居環境中河流水質、河流水量、流域植被、水土保持、河岸整潔發生變化而產生的愉悅感。社會獲得感是指農戶因參與河湖治理而獲得對政府工作效率、公平公正作風及村集體創收的認可,進而導致總體生存環境改善后愉悅感。在傅春建立的河流健康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基礎上[23],結合被農戶的參與需求,構建生態獲得感與社會獲得感量表,題項設定見表2。經檢驗各維度指標間相關性較強,KMO 值分別為0.89 和0.67,Bartlett 球形檢驗值為0。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分別求得生態獲得感綜合得分(EG)與社會獲得感綜合得分(SG),作為最終的被解釋變量。

表2 生態獲得感與社會獲得感題項設定、賦值與描述性統計Tab.2 Item setting,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核心解釋變量:農戶參與度。公眾參與環境治理指環境利益相關個人或社會組織、直接或間接參與環境政策、計劃或項目決策過程[24]。本文基于2015年環保部制訂的《環境保護公眾參與辦法》結合調研農民參與情況,將農戶參與河流治理細分為前期的決策、后期的管護、全程的監督三個部分。借鑒林建平采取參與項目環節數表征公眾參與度[25],將農戶參與度定義為參與環境治理監督-管護-決策的環節數。具體賦值為:農民未參與賦值為0,參與1 項賦值為1,以此類推,參與3 項賦值為3,探討農戶參與度與河長制政策獲得感的關系。
中介變量:政府信任。借鑒鄒宇春等在研究自雇者與受雇者的社會資本差異過程中,將政府信任表征為農戶對村域河長的信任[26],通過詢問“您對村域河長的信任程度?”,按照“很不信任”、“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的回答從低到高賦值“1~5”。
控制變量:農戶政策獲得感受個人稟賦特征、村域河流特征影響,本文將控制變量分為個體特征和河流特征兩類,分別包含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治理知識四個變量,河流的經濟作用、河流對生活的影響兩個變量。
2.4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為比較農戶參與度對各指標的影響,本文將總樣本中參與程度低于1/4 分位數值列為低參與組,記為A 組;農戶參與度高于3/4 分位數列為高參與組,記為B 組,對A、B 兩組進行均值對比,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3。均值比較分析發現,高參與組的政策獲得感普遍高于低參與組,一定程度上證實了自我歸因理論,且高參與組普遍具有年齡偏低、教育好、治理知識多、政府信任高特點,初步證實農戶參與度、個人特征、河流特征、政府信任與政策獲得感存在相關性。

表3 描述性統計分析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3 結果分析
3.1 農戶參與度的直接效應
表4中模型1和模型3為個體特征、河流特征與農戶參與度對村域河長制政策生態獲得感與社會獲得感的線性回歸結果,結果顯示農戶參與度正向直接影響農戶政策獲得感,假說1a和假說1b 得到了證實。其中,治理知識、河流特征也是影響政策獲得感的主要因素。
從個體特征看,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對政策獲得感的影響并不顯著,而民眾對河湖治理知識的掌握程度顯著正向影響治理績效。可能的原因是,隨著信息化發展,農戶河湖生態環境治理常識與治理技能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個體特征。農戶在村政府多方位宣傳以及自主獲取治理信息過程中,提高參與治理能力為村級河長提供更具價值的政策建議并有效表達自身利益訴求。
從河流特征看,河長制政策獲得感與河湖資源的經濟價值正相關,與河流造成的生活影響呈負相關。該結果符合經濟人假設,因獲得感是對客觀獲得的主觀評價,當河湖與農戶日常生活及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時,農民高度關注村河湖資源,參與意愿與行為增強,村政府基于民眾的輿論壓力與經濟需求,尊重農民治理意愿與發展需求以期獲取農戶政策獲得感。
從農戶參與度來看,農戶參與度對生態獲得感與社會獲得感均有促進作用,假說1a 和假說1b 得到證實。可能的解釋是,農戶參與河湖治理范圍越廣,自下而上地信息傳輸鏈條愈完整,可彌補政府主導河流治理而出現標準失衡與監督缺位,實現治理與農戶需求相匹配。農民作為河湖資源直接利益者,自發性監督可降低政策執行成本,強化農戶參與的政策獲得感。公眾作為直接實踐者,擁有政策情景經驗可幫助政府修正政策目標,實現公眾環境治理偏好。
3.2 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與檢驗
為檢驗政府信任的中介效應,分別構建以生態獲得感、社會獲得感為因變量并納入政府信任為解釋變量的模型2和模型4,以政府信任為因變量的模型5,結果如表4。回歸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模型2農戶參與度對生態獲得感的直接影響程度小于模型1,同樣模型4 中農戶參與度對社會獲得感的直接效應要比模型3 小。另外,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政府信任正向影響生態獲得感和社會獲得感,假說2 得到證實且初步驗證政府信任對農戶參與度影響政策獲得感的中介作用。

表4 基準回歸結果Tab.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因偏差矯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可通過調節序列區間的百分位點糾正中介效應計算值[27],本文選擇processv3.4 中Bia-corrected 對中介效應進行驗證與分解,以探討政府信任影響河流治理績效的中介機制與邊界條件。如表5所示,政府信任作為中介變量,其總效應、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皆為正值,且95%偏置信區間皆不含0,再次驗證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這表明農戶參與河湖治理可影響政府信任度,政府信任關系迫使政府關注農戶人居環境偏好與利益訴求,實施以農民為主體的河流環境治理。村政府與農戶間良性互動可節約溝通成本與信息搜尋成本,推動政策實施。結果證明農戶參與度對“河長制”政策獲得感既有直接影響,也可通過政府信任對政策獲得感產生間接影響,驗證了假說3a和假說3b。

表5 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Tab.5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數據顯示,農戶參與度對生態獲得感的總效應是直接效應的1.43 倍,政府信任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9.89%;農戶參與度對社會獲得感的總效應是直接效應的1.23 倍,政府信任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18.97%,表明政府信任在農戶參與度與生態獲得感的中介效應要比對社會獲得感的作用效果強。可能的解釋是,農戶參與程度一定時,社會獲得感是依托于村域治理現實基礎與區域資源稟賦的綜合評價相較于更具化的生態獲得感而言,農戶參與效能激活可能受到更多政府信任以外的因素影響。
3.3 異質性分析與穩定性檢驗
進一步來看,政府信任促使政策獲得感的提升,得益于農戶參與者與村政府的履約與遵約能力建設。制度規則影響農戶參與治理所需資源[28]與農戶治理預期概率[29],并約束政府的行為決策,利于加強兩者的關系網絡,改善治理效果。制度規則既有由政府組織制訂具有強制性的規章制度,也有基于群體共識經年累月形成,用以約束成員的社會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思想工具[30]。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曾界定:“制度是約束人們相互行為而人為設定的規則,包括正式規則(規章、法律)、非正式制度(習俗、倫理規范)與規則的執行特征。”[31]。正式制度通過選擇性激勵解決農戶的搭便車行為強化農戶參與獲得感。在熟人社會與強鄉土歸屬感的農村,非正式制度對農民與村領導均有著強約束作用,可推動形成村集體共有價值觀,實現有序治理。政府官員迫于道德壓力與輿論譴責,更傾向做出符合集體利益的決定,將政府信任轉為化農戶政策獲得感。由此,村莊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完備情況可能會調節政府信任對政策獲得感的影響程度。為檢驗村莊制度規則的異質性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研究采用構建交叉項回歸進一步檢驗,以驗證制度規則的調節作用。
本文將正式規則表征為政府是否出臺治理河湖資源的規章制度,將非正式規則表征為社區集體治理河湖資源是否有自有風俗習慣,回答“是”賦值為1,否則為0。因調節變量為二分類顯變量,將其賦值為虛擬變量,為減輕共線性,故在原模型上將治理制度和政府信任度中心化處理后納入兩者的交叉項,構成了模型6 和模型8,考察正式制度對政府信任度與生態獲得感、社會獲得感的調節作用;在原模型上將風俗習慣和政府信任度中心化處理后納入兩者的交叉項,構成了模型7 和模型9,考察非正式制度對政府信任度與生態獲得感、社會獲得感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6。

表6 制度規則調節效應檢驗與穩定性檢驗Tab.6 Regulatory effect test and stability test of institutional rules
結果顯示,模型6 與模型2 相比,主效應的系數同向減小,治理規則與政府信任的交叉項系數為正,并通過統計性檢驗。模型8 估計結果顯示,交叉項系數為正,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解釋是,治理規則強化信任關系下的輿論壓力,迫使政府以農戶利益訴求為治理目標,修正政府河流治理舉措改善生態獲得感,但制度規則專用性特點導致正式制度未能約束政府社會治理作為,無法調節政府信任與社會獲得感的關系。模型7 與模型9 中,風俗習慣與政府信任地交叉項系數顯著,并通過統計檢驗。可能的解釋是,在熟人社會的鄉村以地緣為基礎的人際關系是農戶重要人力資源,且農戶與同村村民擁有同樣河湖水資源訴求。因此,代表著集體共同價值觀的非正式制度會比正式制度更具有普遍約束力,故非正式制度對生態獲得感與社會獲得感均有調節作用。
借鑒何凌霄替換調節變量指標檢驗調節作用穩定性檢驗[32],本文用“獎懲制度”代替“治理規則”表征正式制度,用“道德譴責”代替“治理風俗”來表征非正式制度,分別對生態獲得感、社會獲得感做回歸,驗證制度規則對治理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獎懲規則僅在政府信任影響生態獲得感中有調節作用,而道德譴責在政府信任影響生態獲得感、社會獲得感中均有調節作用,回歸結論與主回歸分析結論基本一致。
4 結論與建議
文中基于長江流域兩省694 份農戶調研數據,運用多層次回歸分析與bootstrap 方法分析農戶參與度對政策獲得感的影響,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農戶參與度對生態獲得感和社會獲得感均有顯著的提升效應,并且個體治理知識特征、河流對日常生活影響程度均對雙重政策獲得感有影響。
(2)政府信任的中介效應分別占農戶參與度影響生態獲得感、農戶參與度影響社會獲得感效應的29.89%、18.97%。
(3)正式制度對政府信任影響生態獲得感有正向調節作用,而非正式制度對政府信任影響生態獲得感、政府信任影響社會獲得感均有正向調節作用。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
(1)基層政府要注重農民對政府信任的培育,可搭建信息監督平臺做到政策執行有反饋、公眾意見有回應,實現政民間的良性互動,滿足農戶治理需求,增強農戶參與意愿。
(2)政府要制訂選擇性激勵措施并為農戶參與治理賦權賦能,激活農戶參與內生動力滿足農戶參與需求,增強農戶參與效能。
(3)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時,村組織要聯合鄉村精英力量形成規范、習俗、聲譽等非正式制度約束,促進農戶與村組織達成集體治理共識,強化農民與政府的關系網絡,促使雙方共同維護治理目標,提升農戶政策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