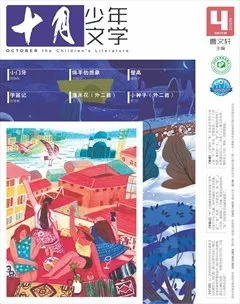周曉楓的童年敘述
《小門牙》的作者周曉楓在散文領域耕耘多年,業績突出。近年來開始涉足童話寫作,亦不乏關注。我也關注她的創作,但說實話,對她的童話創作我更多的是警覺和挑剔,當然也可以說是客觀評價。我關注的點不少,但最關注的是她的童話適不適合兒童閱讀,會不會太“深”,也即她的童話有沒有童年性。具體點兒說,就是她的作品是外在的、刻意的、游離的童年點綴,還是融入作品內里的童年敘述。
我們先看看《小門牙》這部作品講述的是一個什么故事。簡單說,這是一個精靈故事,一個小門牙和他的小伙伴們在精靈谷生活及其與人類交往的故事。小門牙們的主要工作是吃夢,有的夢很長很長,吃一個撐得不行,有的夢很短很短,不夠吃。夢要趁剛做好的時候吃,要不然咔嚓一口下去,只咬到一嘴空氣。在精靈谷,除了吃夢的小精靈,還有捕夢師和神通廣大的計夢師。
任何人都離不開夢,但大人的夢與小朋友的夢不可同日而語。夢在小朋友那里是非功利、有趣的,是親密的伙伴。換句話說,作品所講述的是一個兒童容易接受、喜歡、好懂的故事,是很“淺”的故事。“淺”,是故事很重要的前提。有了這樣的“淺”,如果接下來作品有可能“深”的話,自然也就不讓人擔心了。事實上,故事的發展也的確如此。精靈谷是小門牙們的天堂,也是小門牙們的家園。這里的一切是美麗的、如詩如畫的、如夢如幻的;這里的一切又是日常的、普普通通的、有悲有喜的。在這里,一切皆有可能,有夢想就有希望。每個小精靈都可以戰勝膽怯,戰勝膽怯就可以變得勇敢,變得勇敢就可以成為調夢師。其實,要說“深”,也并不“深”,誰都知道勇敢是一種優秀的品質,這都是“常理”, 但恰恰是“常理”的講述、推演和展示,才是讓人信服的“深”,不是嗎?
不過,雖說這個故事適宜兒童閱讀,但還不夠,我們還要看看作者如何來講述這個故事。這部作品有共計七章,七萬余字,整個故事讀下來,作者依然有恰到好處的表現。且舉三例。
例一,人物出場安排。在第一章人物出場時,作者一一介紹了小門牙、小羽毛、小音符、小翻和小滾,還介紹了捕夢師。“天啊,人物太多了吧?都快記不住了!別急,我保證:你絕對不會把各種角色弄亂了。”對于一時半會兒還不起作用的計夢師,作者僅提及名字,一筆帶過,留個伏筆。“但計夢師的事情,我們放在后面再說。否則,會破壞講故事的氛圍,會影響聽故事的情緒。”直到需要計夢師出現的第五章才給予介紹和描述。這樣的敘述安排,一方面體現了作者對整個故事架構的掌控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對兒童線性閱讀習慣的了解和把握。
例二,具象跟進。作者在講述故事或描述人物時,最后總會落到一個實體的具象上。比如作者介紹捕夢師獨特的捕捉能力:“他有一個特制的圈網,可以在短時間內把夢凍住,就像吹泡泡時的泡泡能短暫卡在圈環里一樣。”通常來說,講述到這里,應該也可以了,但作者沒有,她還繼續往下說:“拿什么裝那些夢境呢?只能用蝴蝶羽化以后剩下的空蛹,不能用其他的容器。捕夢師的動作敏捷,他飛快地把捕到的夢放到蛹衣里,然后飛快地縫合……”很顯然,這個具象就是“空蛹”。由于“空蛹”的出現,捕夢師捕捉夢境的能力變得更為形象生動了。
例三,童年語義。“當黑夜沉得晚風都吹不動,沒有誰愿意留在外面,鬼氣森森”這樣的語句,不乏周氏散文特點。但這樣的語句也僅僅是有特點而已,看不出明顯的讀者意識。我想說的是,只有當上面的語句與后面的語句連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時,敘述的童年性才能夠清晰呈現出來。這就是作者在“鬼氣森森”后面加了一個“的”,“鬼氣森森的”,一下子讓閱讀的“硬”轉“軟”了,更重要的是緊接著作者來了句“真讓人害怕啊”,這就完全進入了兒童讀者的閱讀節奏和方式。成人文學很少會出現這樣的敘述,但放在童話里就恰如其分了。
這就是周曉楓的童年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