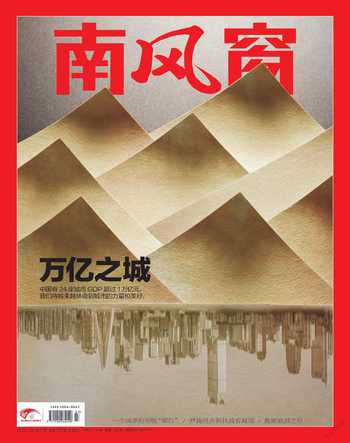韓國轉向與東北亞變局
雷墨

在3月9日的韓國總統選舉中,保守派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以0.73%的微弱優勢擊敗進步派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成功當選下一任韓國總統。這樣的微弱優勢,創下了韓國選舉史上的紀錄。而這場“險勝”,很可能會創下另一項歷史紀錄,即韓國的總統選舉結果,對東北亞局勢未來走向產生較為實質性的影響。翻遍大韓民國的歷史,還找不到這樣的先例。因為尹錫悅的外交政策傾向,將成為影響地區格局的重要變量。
當然,這倒不是說韓國的分量已經舉足輕重到能塑造格局,而是它的地緣政治角色如何變,能對微妙且不確定性增加的東北亞局勢產生顯性影響。在拜登政府的政策操弄下,日本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已做出了較為明顯的選邊。盡管不具備日本那樣幅度轉向的本錢,但從拜登政府戰略布局細節來看,韓國政策“微調”的空間是存在的。競選期間明顯表現出“親美”的尹錫悅,對美國的戰略競爭做出一定程度的“配合”將是大概率事件。
韓國在轉向
這次韓國總統選舉,除了候選人得票率差距“史上最小”以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即保守派與進步派之間權力交替的間隔,是自1987年首次直選總統以來最短的。韓國總統任期五年且不得連任。1987年盧泰愚贏得總統選舉后,青瓦臺主人的輪替,在保守與進步陣營間都以十年為時間軸。也就是說,每個陣營的內外政策,大體上都能超出一任總統的任期。
這樣的“規律”,終止于剛剛結束的總統選舉。
與文在寅同屬進步陣營的李在明敗給保守陣營的尹錫悅,雖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反映出韓國處在歷史抉擇十字路口這樣的現實。因為只有在國家發展方向上的舉棋不定,才會導致權力更替的高頻率,這也是選舉政治的特點。特朗普沒能連任,拜登為民主黨保住白宮的前景不被看好,就與“美國應該向何處去”的爭議呈正相關性。尹錫悅勝選,很可能意味著韓國將出現“告別過去”式的變化。
最可能且更具實質意義的變,將發生在外交領域。雖然在選舉政治中,選民關注內政多于外交,但作為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韓國如何看待外部環境、如何經營對外關系,將直接影響內政的諸多領域。選民在投票時或許不會過多考慮這種聯系,但韓國政治人物都心知肚明。從競選期間的政策宣示來看,尹錫悅與李在明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外交上。具體來說,就是韓國外交在國際上的定位,以及如何應對中美戰略競爭。
2月8日,尹錫悅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闡述其外交理念的文章中寫道,與朝鮮打交道是歷屆韓國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但它不應該代表首爾外交的全部。“韓國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它有潛力成為國際社會中更加負責任和受人尊敬的國家。然而,現任韓國政府一直以來以狹隘和短視的國家利益觀念為指導,為了改善與朝鮮的關系而制定的外交政策,使首爾在全球中的角色縮小了。”
尹錫悅的觀點,絕非只是為了顯示與政治對手的政策差異,更是韓國外交理念上的轉向。美國著名韓國問題學者維克多·查在近期的文章中寫道,這次韓國大選,是他記憶中執政黨與反對黨外交政策分歧,首次超越對朝鮮態度的差異。金大中總統時期以來,韓國大選中的外交主題幾乎都圍繞對朝政策展開,即進步陣營主張對朝接觸政策,保守陣營主張對朝強硬。在維克多·查看來,韓國應該對中美戰略競爭作何抉擇,是這次大選中主要的外交政策分歧。
因為只有在國家發展方向上的舉棋不定,才會導致權力更替的高頻率,這也是選舉政治的特點。
爭議的焦點是,韓國應保持“戰略模糊”還是轉向“戰略清晰”,即維持對中美的“平衡”還是做出更傾向于美國的選擇。尹錫悅在上述文章中寫道,“美國與中國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給韓國和許多其他東亞國家帶來了戰略困境”。但他認為,“與華盛頓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盟,應該是首爾外交政策的核心。韓國受益于美國領導的全球和地區秩序,首爾應該尋求與華盛頓建立更全面的戰略同盟,美韓雙邊合作的性質應該適應于21世紀的需要”。
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依賴中國,是韓國保持“戰略模糊”的重要原因。但在某些韓國學者看來,外交應該適應局勢的變化。韓國學者Kuyoun Chung和Andrew Yeo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稱,在一個安全和經濟相互交織、價值觀被嵌入戰略優先和經濟現實的世界里,這樣的二分法非常不適用了。“韓國在大國戰略競爭中不選邊的‘戰略模糊,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時代,已經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了。”
布局與配合
當地時間3月10日上午10時許,尹錫悅與拜登通電話,這是他接到的第一個祝賀電話,距離他發表勝選感言僅5個小時。據韓媒報道,這次通話原本安排在3月11日,但應美方要求提前了。如果考慮到首爾與華盛頓的時差,通話時是美國時間3月9日晚9點。而“3月9日”是韓國大選的日子,也就是說,拜登以提前通話的安排,實現了“當天祝賀”。這樣的安排,開創了美韓關系的先例。拜登為何如此著急?因為尹錫悅的勝選有利于他的戰略布局。
拜登政府外交的突出特點是重視同盟,而重視的優先方向就是東北亞。2021年3月16日至18日,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一起訪問日本、韓國。那次訪問,是拜登入主白宮后的首次內閣級別高官外訪。美國新一屆政府成立后,首次訪問日韓即是國務卿與防長“組團”,冷戰結束以來還未曾有過。布林肯在訪問韓國時說:“我們把韓國和日本作為拜登政府首次內閣級別外訪對象,并非偶然。”
布林肯說這話,有著特殊的意義。在奧巴馬第二任期里,擔任副國務卿的布林肯,就是美日韓三邊合作的主要推動者。那次“組團”訪問后僅半個月的4月2日,美日韓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最高官員,就在華盛頓舉行了三邊會晤。同年4月底,三國軍方最高領導人又在夏威夷舉行了三邊會晤。激活并升級特朗普政府時期一度沉寂的美日韓三邊合作,是拜登政府東北亞布局的重要一環。
在這一點上,尹錫悅很可能對拜登政府做出一定的配合。因歷史問題引發的韓日雙邊關系不睦,一直是美日韓三邊合作的“阻點”。從政策表態來看,尹錫悅對日關系的基調是“向前看”。他在上述文章中強調了調整對日外交的重要性:“與日本的關系需要重新思考,首爾應該認識到與東京關系正常化的戰略重要性。”尹錫悅的“向前看”能在政策上走多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對日外交將讓美日韓三邊合作產生更大的空間。
配合還不止于此。至少在意圖上,當選領導人的通話對象,是能反映其外交傾向的。截至3月17日,尹錫悅的通話對象分別是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英國首相約翰遜、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和印度總理莫迪。眾所周知,拜登政府印太戰略中的“聯盟圈”,除了美日韓三邊合作,還有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和美英澳同盟。而尹錫悅優先通話的對象,剛好涵蓋了這些國家。很難相信這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性是顯示對美國戰略上的配合。
拜登政府東北亞戰略的另一關鍵布局,是把與日本和韓國傳統的聚焦安全的同盟,升級為包括安全、經濟、高科技和供應鏈等在內的綜合性同盟。這與尹錫悅對同盟的看法有著相當程度的契合度。他在上述文章表示,“僅僅平衡特定軍事威脅的同盟已成為過去,特別是通過經濟報復或技術攻擊對手已成為常見做法,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聯盟涉及在各種問題上的復雜合作網絡,包括個人隱私、供應鏈和公共衛生等領域”。
東北亞變局
這次韓國大選的結果,很可能意味著東北亞進入變局時代。首先,這不只是進步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權力更替,而是韓國對外戰略方向的變化。用悉尼大學韓裔學者Peter K Lee的話說,這次刮的不是陣風,而是季風。進步派的盧武鉉總統,曾說過要讓韓國成為“東北亞均衡者”,保守派的李明博也曾提出“全球外交”的理念。但那個時代與現在最大的不同,是沒有大國戰略競爭。所以,尹錫悅對韓國外交角色的定位,與其前任們有著本質的不同。
其次,在目前的東北亞格局中,韓國扮演著微妙但重要的角色。從戰略角度看,韓國與美國戰略布局的配合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導致東北亞失去戰略平衡。此前韓國一直被認為是美國東北亞同盟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關鍵的原因是韓國在對華和對美外交中維持微妙的平衡,即保持所謂的“戰略模糊”。但尹錫悅明確主張韓國應加入“四方安全對話”,并加強美日韓三邊合作。如果韓國在這些領域邁出更大步伐,勢必增加中美戰略競爭的烈度。
根據韓國產業聯合會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2017年至2021年,韓國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度上升了3.8%,日本僅上升0.1%,而美國則下降了4.2%。
從安全角度看,韓國與美國軍事“融合度”越高,越可能給東北亞安全造成不穩定。樸槿惠政府時期部署美國的薩德反導系統,曾導致中韓關系惡化。尹錫悅競選期間曾表態稱要增加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即便這只是競選語言,韓國今后也有可操作的空間。比如,部署“自主研發”的反導系統。但鑒于安全同盟與軍事技術之間的“孿生性”,這樣的操作不可能打消中國的疑慮。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不會放過在東北亞哪怕是“變相”打造反導網絡的機會。
從安全視角看待經濟、科技、供應鏈等問題,韓國這種與美國相匹配的轉向,對東北亞格局的影響將更大。根據韓國產業聯合會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2017年至2021年,韓國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度上升了3.8%,日本僅上升0.1%,而美國則下降了4.2%。該報告認為,必須采取行動降低這種“風險”。不難想象,主張“戰略清晰”的尹錫悅就任總統后,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的調整,只會是幅度而非方向問題。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尹錫悅的“戰略清晰”反映到具體政策上,不可避免會帶有“灰色空間”。如果說美國把戰略競爭作為目的,那么韓國更多的是將其作為外交的“背景板”,并以此為前提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以韓國的優勢領域半導體為例,韓美勾畫了合作藍圖,韓企也開始在美國投資建廠。但根據韓國貿易協會的數據,中國吸納了韓國半導體出口的40%。如果美韓“合作”導致韓企在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的份額萎縮,那么這種合作就很難持續。
今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建交50周年。這是歷史留給中日韓三國打造和平與合作的東北亞的機遇。但不得不說,美國對戰略競爭的癡迷,在侵蝕抓住機遇的可能性。盡管如此,韓國應該如何與中美相處,不是簡單地靠“戰略清晰”就能解決的問題。
韓國貿易部長呂漢辜曾說,“我們進入了這樣一段過程,即找到在超級大國間共存和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韓國的轉向不可能跳出這個框架。而東北亞的變局,也不太可能是美國戰略直接的“影像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