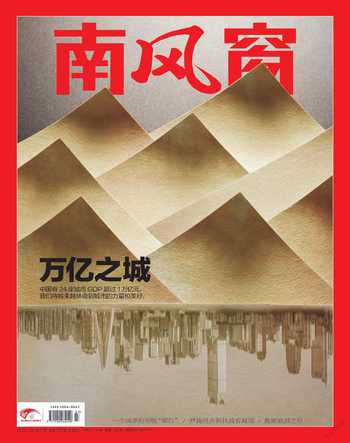王莽:哪有什么穿越者
何子維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作為古代中國最高掌權者中最特殊的一人,王莽是改革家、空想家,還是左派儒教士、早期社會主義者?自20世紀以來,因社會觀念的激蕩,他被不同評價撥弄為一只擺動的鐘擺,甚至還出現了“欲言又止、矛盾反復”的狀況。
新銳文史作家張向榮以其新書《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以下簡稱《祥瑞》),試圖把被傳統偏見釘到牢籠里的王莽釋放出來,讓其呼吸站立,舉起火把,照亮兩漢之交時代的劇變陰影。
透過光亮,辨認王莽的面孔是高尚抑或偽善,追夢抑或貪婪,深刻抑或急躁,開始變得可以被擱置。或者說,相比簡單地貼上某某標簽蓋棺定論,被選中的王莽如何應對時代挑戰,西漢與新莽政權之間如何碰撞、消解與嬗變,這個過程,更為驚心動魄。
符合邏輯的常人之思與堅實的歷史事實陳列本身并置在一起,讓《祥瑞》一躍成為2021年度歷史佳作。雖然張向榮未曾預計寫作的成功,但畢竟,重訪那個傳說中“王莽謙恭未篡時”的機會,誰也不應錯過。
儒家思想的“獵物”
南風窗:能否先談談你的學思歷程。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研究王莽和他的時代以及儒學的?
張向榮:2010年前后,我寫的博士論文是以兩漢為背景,談漢代《詩經》,論兩漢儒學與政治的關系。研究時便很容易注意到,王莽在兩漢儒學與政治的關系中扮演的樞紐角色,但歷史上,側重從儒學變遷書寫王莽的卻很少。
時間悠悠,近幾年非虛構寫作的浪潮令無數前輩的歷史非虛構作品在眼前展開,讓我想到那一小段學術歷程。時空的交錯與啟發下,《祥瑞》誕生了。
南風窗:寫了多長時間?
張向榮:得益于部分內容在讀博期間有研究基礎,純粹的寫作時間大概一年多。我是名上班族,工作日的白天要養家糊口,寫作只能放到晚上和周末。寫書期間我的女兒出生了,有時候還得等到她入睡后才開始寫作。
除了偶爾睡眠不足,寫作的過程還是很開心。我一直期待寫長故事的契機,期待將一個人以及那個人的時代掰碎了看透徹,這是個挑戰,也是抵抗虛無的方式。
南風窗:隨著研究的深入,王莽這個人物越來越立體地呈現在你面前,他會讓你驚訝嗎,最驚訝的是什么?
張向榮:印象里的王莽是篡位者、空想家、小丑式的人物,就連連環畫也將其畫成一個欺負小皇帝劉嬰、兇神惡煞的模樣。直到寫博士論文,讀了《漢書·王莽傳》,我非常驚訝王莽還做過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要說最驚訝的,莫過于他對家庭的摧殘。幾乎找不到像王莽這樣會把所有繼承者“弄死”的皇帝。殺死至親,在武則天、唐太宗身上發生過,但殘忍到把所有繼承人,包括侄子全部殺死或逼其自殺的,王莽是獨一無二。
王莽的二子王獲因殺死一個奴婢,被王莽逼迫自殺,是一例典型。在那個時期,奴婢是可以買賣的財產。王莽此舉在今天看來有點小題大做,但恰好證明了儒家思想對王莽的極度影響——逼子自殺,不是王莽的虛假大義滅親,而是一位父親以“仁者愛人”的儒家倫理迫使兒子羞愧自殺,是對親人的道德救贖,是對儒學的忠實實踐。
我們可以理解為,王莽自視為儒家圣王之軀,該軀體里住著的不僅是王莽自己,還包括他的家人。一旦家人做出有違儒家倫理之事,那么,王莽就會像改造軀體某個缺點一樣,不惜除掉某位家人。
凡此種種,王莽在腦海中活了過來。他不再是篡位者,而是一個以儒家圣王自詡并死心塌地篤信的“怪胎”,要用儒家教義來拯救危亡。好似儒家靈魂不斷在歷史中尋找肉體投胎,王莽是被選中了的完美獵物。
南風窗:在書里你用了一個現代心理學術語“神經癥人格”。用心理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人物內心的想法和動機,刺探王莽的多面性,這很時髦。
他不再是篡位者,而是一個以儒家圣王自詡并死心塌地篤信的“怪胎”,要用儒家教義來拯救危亡。好似儒家靈魂不斷在歷史中尋找肉體投胎,王莽是被選中了的完美獵物。
張向榮:寫的時候我正好在看有關神經癥人格的書。我發現對該癥狀的很多細膩描述,與王莽的行為相吻合,焦慮又偏執,傲慢又自卑。可惜沒有辦法與王莽見一面,只能隔空診斷。我寫了進去并做了注釋,或許這些解釋史料的新方法能讓讀者也更有代入感。
南風窗:除了你正在讀的書,還有生活狀態和心境,比如你剛提到了女兒的出生,對你寫這本書有影響嗎?
張向榮:這確實太巧了。自女兒到來后,我成為了一名父親,再看待王莽與他女兒之間的關系就更加有感觸。所以《祥瑞》出版之后,就有讀者告訴我,他比較喜歡讀王莽和他女兒那一段。
王莽跟他女兒的關系其實很差。女兒厭惡王莽,畢竟女兒少年守寡完全拜王莽所賜。王莽則有千般悔意,更有萬般疼愛,幾乎在惡劣的人際關系里面,女兒是他唯一愿意付出真情的出口。最后,《漢書》用“敬憚傷哀”四個字來描述這對父女之間的關系,這是何其的準確。
南風窗:“莽敬憚傷哀,欲嫁之。”
張向榮:對,這和王莽對他的兒子完全不一樣。在我成為父親后,一下子就理解了。父親能容忍女兒對自己做的任何事情,哪怕她突然沖過來,一巴掌把我的眼鏡打下,我也不會生氣。
我也有意在《祥瑞》中讓女性的出場率高于傳統史書對女性的描寫。比如王莽的王氏家族作為西漢的外戚,王政君等女性家族成員的事跡,其實都對時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卻往往著墨不夠。
背后的導演
南風窗:受到帝制時代主流思想的影響,在過去常見的敘述里,王莽對權力的欲望是非常夸張的,說他為奪取西漢政權,處心積慮、蟄伏多年。《祥瑞》似乎試圖打破這種印象,你是如何考慮的?
張向榮:依托史料,人物傳記常常流于“成功學”敘事,我希望跳出此思維,不圍繞王莽的成敗,不強調王莽的權術,不評述王莽的長處與弱點,而是將其放在儒學發展的脈絡中,關注這個人對時代的文化、觀念與權力的作用。
但這確實不好處理。有讀者說《祥瑞》看了三分之一還沒有談到王莽,而是用了很多篇幅來解釋儒學變化,只有看完才明白意圖——不講清楚儒學,就沒法理解王莽。

西漢在建立之初就不斷遭遇歷史遺留問題的挑戰:一是政權的合法性在哪里,所謂“建國”;二是政權如何組織,所謂“建政”。因此,無論主動或被動,西漢的所有統治者、官僚以及士大夫一定會去回應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被逐步回應的過程,就是王莽得以登臺的背景,也是儒家獨立作為統治思想的嬗變過程。
南風窗:就像你的觀點,如果王莽是這本書的主人公,那么儒學就是背后的導演。
張向榮:是的,同時這還是一個關于我們如何認識儒學的問題。
我身邊有不少朋友認為,儒學從孔子以來就是現在理解的這樣,從諸子百家后沒有發生過變化。實際上,儒學不停在演進。以近代來說,五四期間人們對儒學持否定態度,著名的經學研究家周予同先生就曾滿懷激憤地寫下《僵尸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呼吁:“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到了本世紀,學術界的認識和研究突飛猛進的發展,對儒學的態度逐漸正面化,而且還得到了強調。
儒學不斷塑造著普通人的觀念。應運而生的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說辭也納入了儒家思想,最終,這套時人皆信的說辭,讓上天通過祥瑞、符命來確認了王莽的天命和合法性,又通過災異來確認了漢朝的沒落。
我們應該始終以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待儒學,回到漢朝就更加直觀了。劉邦時期,儒學只是為了讓儀式有秩序、無足輕重的司儀,談不上在思想上對帝國有影響,劉邦還曾往儒生帽子里撒尿。到了文帝一朝,儒學的境遇有了顯著變化,漢文帝重視對儒家經典書籍的搜求、整理、研究和推廣。漢宣帝之后的幾位皇帝則已完全被儒學征服,不斷對標儒家實施祭祀、宗廟等制度改革。皇帝如此,大臣更不必多說,儒道逐漸占據了社會主流。儒學不斷塑造著普通人的觀念。應運而生的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說辭也納入了儒家思想,最終,這套時人皆信的說辭,讓上天通過祥瑞、符命來確認了王莽的天命和合法性,又通過災異來確認了漢朝的沒落。
南風窗:流行說王莽是穿越者,這個說法頗具戲劇性、荒誕感。但“穿越者”這個詞是不是也透露了一種潛意識——我們總希望有一個來自未來的“神”,帶領我們快速走出當下的困局?
張向榮:網友們指出王莽留下了很多穿越的“證據”,比如短裙、游標卡尺,其實這些看似新奇之物未必是王莽造的,而是我們作為現代人把古人看得太古了。
穿越作為文化現象,拋開純粹講兒女情長的穿越小說,還有很多嚴肅類穿越文本。這種穿越帶著某種政治色彩,會考慮去了過去要如何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看待王莽時,確有這方面意圖。
另一方面,大家從王莽的改革里看到了很多現代制度性的東西。比如,胡適認為王莽制定的諸多政策具有近似于社會主義的思想。胡適所言的是當時歐洲盛行的社會主義思潮,和現在說的社會主義自然不是一回事。但可以說,王莽的行為看上去和社會主義的某種價值追求相符合,如追求公平正義、消除貧富分化。只是要注意,王莽的動機來自儒家。
懸置的烏托邦
南風窗:如果現在有機會,你可以穿越到王莽時代,穿越至王莽改革之前、去實現他的儒家宏愿之前,你會對王莽說什么?
張向榮:如果穿越見到王莽,我會勸他的改革別操之過急,但估計他很快就會把我殺掉(笑)。
作為后來人,我們都知道王莽的改革失敗了。然而,哪怕把東漢劉秀的治理方式整理出來告訴王莽,“劉秀跟你其實差不多,只是慢點、中庸些”,也于事無補。歷史不允許假設,王莽和劉秀面對的社會問題背景大相徑庭。劉秀建立了東漢,做事的邏輯和方式其實都借鑒了王莽,但又從王莽覆滅中吸取了很多教訓。比王莽幸運的是,東漢初經過幾場戰爭后,人口變少,土地變荒,原來難做的改革,比如土地重新分配,劉秀及其繼承人與擁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會容易些。
南風窗:從圣人王莽到全民公敵,關于王莽的失敗,眾說紛紜。但多數都是肯定了王莽天真的改革動機,卻沒有統一回答失敗的原因。你認為,王莽改制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張向榮:今天制約我們對王莽做出公正評價的最主要因素是,史料太單一。比如王莽的土地改革,《漢書》里只有兩三句話概括,其中的法令細則怎么寫的只能靠猜。這就造成了評價難統一,大家各說各話。
中國的歷代帝王在王莽之后都一定要回應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一定要標榜禮教,無論以什么形式,無論是否真心。總之,王莽的遺產就像懸置的烏托邦,成為后來帝制時期各位帝王的壓力,也不斷向所有人叩問:儒家的靈魂似乎還在,但身體在哪里?
普遍認為王莽改制的失敗在于,短短幾年改革全面鋪開。這個判斷本身沒有問題,只不過還是過于寬泛。看得仔細一點,會看到在王莽的改革里情況不一。比如,土地制度改革下了一道政令,但根本沒有推行;貨幣制度改革則是先改,改不好再改回去。所以,無論王莽的改革是停留在空想,還是實質推行下去又半途而廢,我們說,王莽改革的失敗與王莽新朝的覆滅,兩者看似緊密結合其實是分開的問題。
王莽的那些改革除了折騰新朝,最根本弊端是沒有解決西漢后期的社會問題,比如土地兼并、人民流離失所、私人奴婢過多過濫,而再造了一個秦皇漢武時期的內外危局。
當初,王莽能登臺就是因為他有儒家圣王的承諾,人人都期待他會讓國家變得更強大。壓倒性的政治支持,意味著一旦理想社會的承諾沒能兌現,圣王的形象便瓦解,王莽必然會被時代拋棄。
南風窗:你在書里總結道,“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現實,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馴服君主,是古代中國政治天平上的砝碼”。盡管王莽失敗、新朝短暫,但我們不得認真討論王莽的政治遺產。
張向榮:我認為王莽的政治遺產主要有三點。一是以和平而非流血的方式實現了政權轉移,猶如儒家版本的“光榮革命”,是西漢政治儒學結出的最大也是最直觀的成果。
二是對儒學發展的影響,終結了西漢的政治儒學,那種旨在馴服君主,用天人感應、災異祥瑞來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臺的做法,漸漸失去了感召力。
三是新朝留給東漢甚至是整個帝制中國的遺產。日本學者東晉次在《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中有一個總結,大意說中國之所以成為儒教中國、禮教中國,王莽是轉折點。進一步講,呂思勉先生曾在《秦漢史》指出,兩漢之交是比周秦之交更大的變局,因為王莽的出現賦予了帝制中國一個基因:必須符合仁政、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說,中國的歷代帝王在王莽之后都一定要回應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一定要標榜禮教,無論以什么形式,無論是否真心。總之,王莽的遺產就像懸置的烏托邦,成為后來帝制時期各位帝王的壓力,也不斷向所有人叩問:儒家的靈魂似乎還在,但身體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