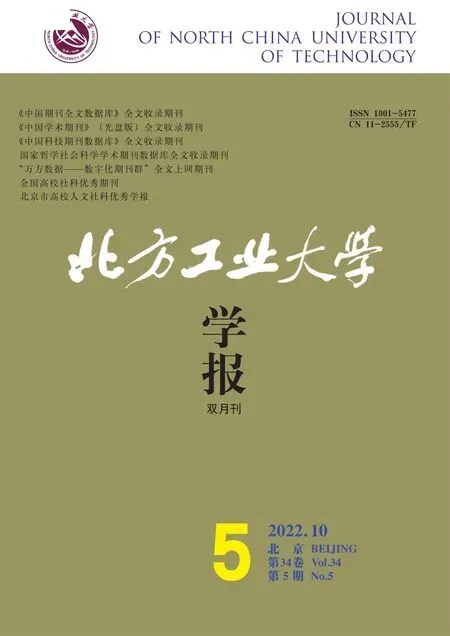論《云使》的蒙古文翻譯與影響*
薩其仁貴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010021,呼和浩特)
《云使》(Meghadūta)是古印度大詩人迦梨陀娑(Kālidāsa,4—5 世紀)所著抒情長詩,全詩共400 多行,由同一種詩律完成,是古典梵語抒情詩巔峰之作。 《云使》長期以來深受東西方文人的喜愛,14 世紀中葉,該詩首次被翻譯成藏文邁出了印度國門。 18 世紀中葉《云使》由藏文被轉譯成蒙古文。 20 世紀初,《云使》傳入西方,先后被譯成英、法、德等多種語言,很快得到廣泛傳播。20 世紀中葉,《云使》再度從藏、漢、英文被轉譯成蒙古文,一時涌現出3 種不同的《云使》蒙古文譯本。 到了21 世紀,《云使》又有了兩種不同的蒙古文譯本,一個是蒙古國的從藏文翻譯的轉譯本;另一個是我國蒙古族譯者(本文作者)直接從梵文翻譯的直譯本,這也是《云使》第一次從原文翻譯而成的蒙古文譯本。 至此,近300 年的《云使》蒙古文翻譯歷程中產生了多種譯本,各譯本翻譯水平不齊、翻譯途徑不同、翻譯背景、起因、所涉及到的中間語言等各因素都各不相同,足見《云使》蒙古文翻譯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本文將系統梳理《云使》在蒙古的翻譯歷程,探討各譯本的翻譯背景、翻譯特征、翻譯得失及其原因和翻譯影響等問題,這對印度文學在東亞的傳播以及多語種文化交流交融研究均有重要意義。
1 《云使》各蒙古文譯本翻譯歷程及背景
在蒙古文學史上,18 世紀中葉至今先后共有過7 次《云使》翻譯實踐。 其中有1 個是只譯了6個詩節的翻譯淺嘗試,其余6 個都是完整的全譯本。 在6 個全譯本中前5 個譯本是轉譯本(包括3 個藏轉譯本、1 個漢轉譯本和1 個英轉譯本),最后1 個是從梵文翻譯的直譯本。 下面按照時間順序依次介紹這些譯本產生的因由、背景和特征。
1.1 1749 年《丹珠爾》之譯本
《云使》最早的蒙古文譯本是通過藏文翻譯而來的。 公元13—14 世紀,隨著吐蕃分裂時期的結束,藏族譯師們開始打破舊時佛經翻譯中的嚴格規定和限制,提出“世俗學科”概念,提倡修辭優美的古印度名篇佳作的引進。 藏族著名譯師、佛學家、語言學家強秋澤摩(1315—1379)積極響應改革趨勢,選擇翻譯屬于“外道”的婆羅門教信徒迦梨陀娑所著愛情題材抒情詩《云使》,為藏族“世俗學科”建設做出了突破性貢獻,也成為了《云使》東亞傳播第一人。 據藏族學者扎布教授考證,強秋澤摩“大約在公元1354 年”完成了《云使》的藏文翻譯。[1]該藏譯本后來被收錄到藏文大藏經《丹珠爾》的“聲明部”。 此時,當時的元朝朝廷已歸依佛教,奉佛教為國教,大力支持藏文佛經的整理與翻譯,為今后的藏文《甘珠爾》和《丹珠爾》的蒙古文翻譯奠定了基礎。 從此,元明清一脈相承的蒙古文佛經翻譯活動一直沒有中斷,且得到了官方大力支持。
18 世紀中葉,在清朝乾隆年間官方組織開展了藏文《丹珠爾》的蒙古文翻譯活動,歷經7 年多的時間(1742—1749),把225 卷的北京木刻版藏文《丹珠爾》全部翻譯成了蒙古文,稱之為北京木刻版蒙古文《丹珠爾》。 隨之藏文《丹珠爾》中的《云使》也被翻譯成了蒙古文,產生了《云使》最初的蒙古文譯本,即蒙古文《丹珠爾》之《云使》譯本。 譯者是喀爾喀蒙古(今蒙古國)政教領袖哲布尊丹巴一世札納巴咱爾(1635—1723)的徒弟格勒堅贊和洛桑堅贊二人。 可見,古典梵語文學經典《云使》的第一部蒙古文譯本,是通過官方組織的集體佛經翻譯活動產生的,可它已經偏離了真正文學作品翻譯的軌道,在譯本中明顯存在因文學翻譯和佛經翻譯之間、集體翻譯和個人翻譯之間的差異而導致的系列問題。
1.2 20 世紀《云使》蒙古文譯本
在蒙古文《丹珠爾》之《云使》譯本(1749)之后,到了1950—1960 年代,蒙古文學界又出現了一小波《云使》翻譯熱。 它們的產生都與當時的國際文化交流背景有關。
1.2.1 拉祜·維拉訪問蒙古國及賓·仁欽院士的《云使》譯本
印度著名學者、語言學家拉祜·維拉(Raghu Vira,1902—1963),于1955 年先后訪問中國和蒙古國,獲得了大量的珍貴佛教文獻資料,包括108 函北京木刻版《甘珠爾》,105 函庫倫版《甘珠爾》,225 函北京木刻版蒙古文《丹珠爾》的縮微膠卷和從列寧格勒獲得的各種布里亞特蒙古文刻版書籍。 回國后拉祜·維拉先生創刊《百藏叢書:印度-亞洲文學》('Sata-Pitaka Series:Indo-Asian Literatures,簡稱《百藏叢書》)系列叢書,開始刊登從中蒙兩國收集到的文獻資料。 他還邀請蒙古國學者和高僧到印度參與《百藏叢書·蒙古卷》的編輯工作。 其中貢獻最大的屬蒙古國著名學者、語言學家、作家和翻譯家賓·仁欽(1905—1977)院士。 賓·仁欽于1960 年前后赴印度協助出刊《百藏叢書·蒙古卷》,正是在此期間他完成了印度偉大詩人迦梨陀娑的抒情長詩《云使》的蒙古文翻譯。 他采用的底本是加爾各答學者、語言學家Kumudrajan Rai 的梵孟英三文合璧版本。 他依據其中的英文釋義文把《云使》翻譯成了基里爾蒙古文①四行詩。 該譯本行文流暢、修辭優美,還對近40 條名詞術語做了解釋,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十分貼近原文。 賓·仁欽院士在1962 年譯完《云使》,次年與《云使》其它蒙譯本合并成一冊在烏蘭巴托出版,1981 年該譯本被轉寫成回鶻蒙古文②,在北京出版。
1.2.2 迦梨陀娑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及呈·達木丁蘇倫的六詩節譯文
1956 年,迦梨陀娑被世界和平理事會評為年度“世界文化名人”,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迦梨陀娑紀念活動熱潮。 當年,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先生分別翻譯出版了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戲劇)和《云使》,季羨林先生又撰文《印度古代偉大詩人迦梨陀娑的〈云使〉》來紀念迦梨陀娑。 在蒙古國,“蒙古國人民也與世界人民一同紀念迦梨陀娑,并為增強蒙印兩國政治、文化關系努力采取了種種措施”。[2]蒙古國學者呈·達木丁蘇倫先生,根據藏文《丹珠爾》之譯本,用基里爾蒙古文轉譯了《云使》前六個詩節,發表在蒙古國《文學》報紙上(1956 年)。 不久該譯文被轉寫成回鶻蒙古文在《內蒙古日報》上刊登。 1982 年,由仁欽戛瓦、斯琴朝格圖摘錄整理的《智慧之鑒》一書中也收錄了該六個詩節的譯文,不過他們誤以為這是來自《丹珠爾》的譯文。 該六詩節的譯文內容嚴重偏離原文,對《云使》的閱讀和傳播,意義不大。 詳情參見拙文《跨語言傳播中的〈云使〉》。[3]
1.2.3 首屆“國際蒙古學家大會”及《云使》藏轉譯本和漢轉譯本
1959 年,首屆“國際蒙古學家大會”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舉行。 在本次會議召開之際,蒙古國甘丹寺住持大喇嘛額爾敦培勒為了“引起國際蒙古學界對《云使》舊譯本(引者注:指蒙古文《丹珠爾》之譯本)的關注和研究”,依據藏文《丹珠爾》之譯本,再次把《云使》轉譯成了蒙古文。同時他還讓他的朋友薩嘎拉札布從漢文轉譯《云使》。 薩嘎拉札布依據我國金克木譯本把《云使》轉譯成了蒙古文。 這兩個譯本是由回鶻蒙古文完成的,曾附在賓·仁欽譯本之后于1963 年在烏蘭巴托出版。 而與賓·仁欽譯本不同,這兩個譯本始終沒有在中國出版過,鮮為人知,這與該兩個譯本的翻譯水平有關。
1.3 21 世紀《云使》蒙古文譯本
21 世紀,蒙古人對《云使》的熱忱與執著有增無減。 2002 年,蒙古國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阿拉騰其木格把《云使》的3 個回鶻蒙古文譯本全部轉譯成基里爾蒙古文,與賓·仁欽的基里爾蒙譯本一起在烏蘭巴托出版。 該書的主編蒙古國國立大學文學研究者畢力貢達來談到:“遵循和繼承賓·仁欽先生的遺愿,讓更多的文學愛好者閱讀《云使》,從而激發他們的文學創造潛能,促進后生以更優美的語言和詩律寫出更好的蒙古語《云使》”。 在蒙古國,從事語言文學專業的老師和學生對《云使》內容都很熟悉,能順口背誦其中的詩句。 在中國,蒙古族文人學者同樣喜愛《云使》,賓·仁欽譯本在校園、詩人中知名度很高。 隨著國內梵語學習條件的成熟,年輕的蒙古族學者學習梵語,為直接從梵語翻譯《云使》打下了基礎。 在此環境下,蒙古國和中國分別出現了新的《云使》蒙古文譯本。
1.3.1 蒙古國的藏轉蒙《云使》新譯本
2017 年,蒙古國著名藏學家、歷法學家勒·忒熱畢希先生,依據藏文《丹珠爾》之《云使》譯本再次把它轉譯成了基里爾蒙古文,在烏蘭巴托出版。 這是繼蒙古文《丹珠爾》之譯本和額爾敦培勒譯本之后的第三次從藏文轉譯而成的《云使》蒙譯本。 該譯本還把《云使》的梵文以及藏、漢、英和俄文譯本全附錄在后,對讀者提供了多語文本對照閱讀的便利,不過要注意附錄內容缺乏嚴謹性、存在傳抄中的謬誤。 就譯本本身而言,它代表了到目前為止從藏文轉譯而成的譯本中的最高水平。
1.3.2 中國境內的《云使》蒙古文譯本
2019 年,是蒙古文《丹珠爾》誕生270 周年,也是《云使》第一部蒙古文譯本問世270 周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云使》蒙譯本的譯者,都是今蒙古國境內之人,而不是我國境內的譯者。 當1981 年國內引進(轉寫出版)賓·仁欽譯本之時,蒙古文學界對《云使》的關注度和熟悉度是比較低的。 轉寫后的“內容簡介”是根據我國金克木先生漢譯《云使》的“前言”而編寫的,其中有一句話寫道:“其中的(指《云使》的——引者)訓諭詞至今仍被印度人所傳誦,可見詩中的詞句到了何等優美程度。”這句話在金克木先生“前言”中的原句是:“其中(《云使》)的一些名句和《沙恭達羅》第四幕中的送別詩句同為印度人所傳誦,被認為迦梨陀娑的最杰出的詩行。”那么,在蒙古文“內容簡介”中之所以把它改寫成那樣是因為:第一,編者對《云使》及迦梨陀娑的作品不熟;第二,編者被蒙古文學史上訓諭詩的地位和影響所誤導。 在蒙藏文學關系中“訓諭詩”的比重很大,是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分。 受印、藏文學的影響,蒙古高僧們寫的訓諭詩數量眾多,語句優美,比喻形象生動,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可是《云使》不是“訓諭詩”,也不是因“訓諭詞”打動了讀者。 編者的話,顯然是被固有的關于訓諭詩認知所誤導的。 賓·仁欽譯本傳入中國后,得到了一些文學愛好者的喜愛,但其傳播的范圍還是非常有限的。 在印藏蒙文學關系中,學者們的關注重點在佛教文學和民間故事,而《云使》及其翻譯研究相當滯后。 鑒于此,本文作者在學習梵語基礎上以《云使》蒙古文譯本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并依據《云使》梵文原文把它翻譯成了蒙古文。 譯本入選內蒙古少兒出版社“從母語到母語”系列叢書,于2019 年10 月出版。
2 《云使》各蒙古文譯本翻譯特征及得失
如上所述,自1740 年代起《云使》確實經歷了好幾次的蒙古文翻譯。 但其水平參差不齊,可讀性、藝術性、流傳性等也有天壤之別。 這都取決于翻譯本身的成與敗,下面來談談各譯本的翻譯成敗得失。
2.1 18 世紀譯本(蒙古文《丹珠爾》之譯本)
該譯本是集體佛經翻譯的產物,這導致它文學性降低、可讀性差,以“半成品”的形式問世。其原因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 其一,《丹珠爾》的翻譯是以佛經翻譯為主,因此《丹珠爾》集體佛經翻譯的總綱領和譯程是針對佛教經典的翻譯而設定的,這未必適合于屬于純文學的《云使》的翻譯。 比如,作為《丹珠爾》翻譯指導綱領而編寫的藏蒙正字法工具書《正字智者之源》中,并沒有收錄《云使》詞匯,但是《云使》翻譯仍要依據此工具書,從而會導致翻譯的偏差與僵硬。 其二,集體佛經翻譯都是按照一定的翻譯流程進行的,《丹珠爾》翻譯也不例外,在翻譯過程中有明確分工和順序。 大體而言,首先是字對字地逐字譯,然后調整語序,再后潤色語義。 然而該譯本只停留在“逐字譯”環節上,并未從蒙古語的角度進行語序調整和語義潤色,所以譯本晦澀難懂、語句不通,若不與其藏文底本進行對照,則難以理解。因此,可以把它看作尚未完成的“過渡性”文本或“半成品”。 其三,該譯本的譯者是被安排的,而不是自發性翻譯。 從《云使》譯本的跋文中我們不難看出,譯者是虔誠的佛教徒,想通過此舉造福眾生,發揚佛法,得到佛果。 “歷來認為,抄寫、供養經典可以得到無限的功德,……虔心收集、翻譯、整理、傳寫、供養、修造佛典與大藏經的人前仆后繼。”[4]佛教信徒們虔誠的宗教心理,在佛經翻譯過程中往往會導致“逐字譯”的翻譯現象。因為“逐字譯”可以減少或避免因意譯而產生的誤差。 在蒙古文佛經翻譯實踐中“逐字譯曾為主要翻譯原則,只有個別杰出的翻譯家才能克服它”。[5]蒙古文《丹珠爾》之《云使》譯本,正是在這樣的佛經翻譯心理下完成的。 譯者沒有把《云使》當作文學作品來翻譯,從而失去了文學意義。
蒙古文《丹珠爾》之《云使》雖然在翻譯上存在一些問題,但在詞匯層面卻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早在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之前,梵語佛教詞匯通過中亞傳到了蒙古高原。 因此,從藏文轉譯的蒙古文文獻中一直貫穿著“名從其主”原則,即名詞術語要采用通過回鶻文傳進來的梵文音譯詞,使得梵文音譯詞逐漸融入到了蒙古語詞匯中。 另一方面,該譯本在“藻飾詞”翻譯上,全采用了“照譯”方式。 所謂“藻飾詞”是指“通過借代、比喻、用典等手法來表達某人、神、物概念的”具有形象化特征的文學語言。 比如“夜的主人”是指“月亮”的藻飾詞。 在印藏文學中藻飾詞的使用頻率很高,一個名詞可以擁有多個藻飾詞。 所謂“照譯”是指照著藻飾詞字面意思翻譯,比如把“夜的主人”翻譯成“夜的主人”,而不是把它翻譯成“月亮”。 《云使》中的大量藻飾詞,以照譯的方式被保留下來,增加了蒙古文學詞匯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2.2 20 世紀譯本(轉自藏、英、漢的三種譯本)
20 世紀藏轉譯本,實際上是18 世紀藏轉譯本的微調版。 該譯本是在18 世紀蒙古文《丹珠爾》之譯本的框架上,連改帶抄完成的。 字詞層面雖然有些改動和糾正,但并未對舊譯本笨拙的語句做根本性調整。 總體而言,該譯本不僅沒有達到新的高度,反而破壞了18 世紀譯本中有些字詞的傳統表達方式。 正如其譯者額爾敦培勒喇嘛所說,該譯本的主要目在于“為了引起國際蒙古家對舊譯本(18 世紀譯本)的關注和研究”。此次翻譯的重點并不在于翻譯,而是為了引起學界對《云使》舊譯本的重視和研究。 同時他還邀請薩嘎拉扎布先生從漢文翻譯《云使》,進一步加強被關注度。
薩嘎拉札布把金克木先生的115 詩節漢文韻文體譯本翻譯成了散文體譯本。 從內容來看,該譯本比較正確和忠實地轉述了金克木譯本的意思。 但其最大的問題在于名詞術語翻譯得混亂與寫法的不統一。 大量的梵文名詞術語,早在13—14 世紀已融入到蒙古語詞匯中,因此即使到了17—18 世紀蒙古人從藏文轉譯梵文典籍時,在名詞術語上一般都會采取已有的梵語音譯名稱。 但是,薩嘎拉札布譯本在名詞術語的翻譯上卻采取了從漢語音譯方式,比如他根據漢文“摩訶迦羅”的讀音把它譯成了“Mukajiluu”,而在蒙古語詞匯中“Mahākala”已經是人們很熟悉的名字,若把它翻譯成“Mukajiluu”是很奇怪的。 類似的譯法與傳統發生割裂,使讀者產生疑惑,從而影響對文本的閱讀和理解。
較之以上譯本,賓·仁欽譯本,是20 世紀唯屬真正詩歌翻譯的譯本。 在形式上,它嚴格按照梵文《云使》四個音步(pāda)為一個詩節的格式,并兼顧了蒙古文詩歌押頭韻原則。 在準確把握、優美再現原文意思和意境的同時,該譯本也沒有忽略從傳統翻譯中吸取營養。 如上文所述蒙古文《丹珠爾》之譯本的主要成就體現在字詞翻譯上,尤其是藻飾詞的翻譯給蒙古語詞匯注入了新的血液。 賓·仁欽譯本很巧妙地從《丹珠爾》譯本字詞中提取所需成分把它融入到現代譯本中,使得印藏蒙一脈相承的詞匯表達形式得到傳承和發揚,很好地對接了傳統與現代;把充滿異域風情的古印度詩歌展現在了廣大的蒙古語讀者和詩歌愛好者面前。 該譯本雖然并不是直接從梵文翻譯的,但譯者能熟練駕馭古印度的文化意境并能把它順利轉換成優美的書面蒙古語的詩歌,這與他跟拉祜·維拉等印度學者們的學術合作也離不開。
2.3 21 世紀譯本(藏轉蒙譯本和梵譯蒙譯本)
首先看2017 藏轉基里爾蒙古文譯本。 從文學翻譯角度而言,前兩個藏轉蒙譯本是失敗的。那么21 世紀的,第三次藏轉蒙譯本,回歸了文學翻譯軌道上,成為了三個藏轉譯本中最好的譯本。 具體特征和成就有以下幾點:
1)譯者把德格版、那塘版和北京版的三種藏文版《丹珠爾》之譯本之間進行比較,再以德格版的《丹珠爾》譯本為主要依據版本,以其他兩個為參考進行翻譯,從而避開了因版本問題而引起的錯誤,更準確地把握了底本的內容。
2)《云使》的翻譯離不開對它的研究和對字詞的注解,該譯本中共有180 多處注釋,材料性和研究性都比較強,有助于讀者理解和譯本傳播。
3) 對“藻飾詞”的翻譯比較重視,盡量以照譯的方式保留藻飾詞的形式。
4) 譯本中蒙古語詞匯比較豐富,偏向用古詞和書面語。
5) 形式上以壓頭韻的四行詩組成,每一詩行都比較長,平均每一行15 個字,30 ~40 個音節,有時不免有些冗長繞口。
該譯本是蒙古國藏學者自發性地研究、欣賞和翻譯《云使》的結果,跳出了佛經翻譯和集體翻譯的窠臼,回歸到文學翻譯并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再看2019 年梵譯蒙譯本。 本次翻譯最大的意愿是更大范圍地普及《云使》,讓更多的蒙古語讀者能夠閱讀和欣賞這部古印度經典作品。 雖然前面已經有了很好的譯本(賓·仁欽譯本),但是該譯本,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學素養和印度文化基礎,也是很難讀懂和深入理解的。 所以,很需要一部通俗易懂又不失文雅的翻譯來滿足更廣泛的需求。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本次翻譯在形式上放棄了每個詩節行數等同的整齊格式來更完整明確地表達原文意思,所以譯本的每個詩節的行數從8—16 行不等。 古印度文學著作都有做注釋的傳統。 當帶有濃厚地域文化特色的《云使》被翻譯成其他語言時,更需要有注釋來解釋詩文深層的內涵,尤其是《云使》的“前云”,即前半部分。 因此,在此譯本中按照古印度注釋文的傳統,在“前云”每個詩節后面都做了一段注釋,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原著。
3 《云使》對蒙古文學的影響
如前文分析,《云使》雖18 世紀中期已由藏文轉譯成了蒙古文,但因譯本的可讀性差而未能有效傳播,也無從談起影響。 而隨著16 世紀下半葉藏傳佛教二度傳入蒙古地區,藏語在蒙古佛教界的地位越來越高,以致多數蒙古喇嘛高僧直接用藏文著書立說。 此時,精通藏語的蒙古喇嘛直接用藏文閱讀《云使》并從那里吸收營養運用到藏文創作中。 所以,在古代蒙古文學中,《云使》的影響體現在蒙古族喇嘛用藏文創作的作品中,這些作品主要有贊美詩、書信文學和游記文學。
在蒙、藏佛教文學中,贊美詩是一種常見的體裁,以佛教贊美詩為主。 然而自17 世紀以后的蒙古喇嘛文人的藏文撰寫的作品中開始出現了對世俗女性的感官描寫和贊美。 比如,喀爾喀班智達·益西桑布在他的《切斷欲望之根的利刀》中對美人的頭發、眼睛、臉蛋、笑容、牙齒、乳房、腳步從上到下進行了細膩地描寫。[6]本文認為這種印度式描寫是來自《云使》對女性感官的細膩描述。 關于書信文學,作為“信使詩”的開創,《云使》深深影響了蒙古喇嘛的書信文學。 早期蒙古喇嘛從小出家、背井離鄉,刻苦求學,與傳道受業的恩師感情深厚。 《云使》真摯的情感往往在他們心中產生共鳴,在他們寫給恩師良友的信件中《云使》的影子屢見不鮮,甚至有人直接稱自己的信件為《新云使》,把恩師比作為“拯救者云”、“甘甜的雨水”,形容閱讀信件的聲音如同“雷鳴”般洪亮,信中還會出現“雷聲”與“孔雀”的意象,寫道“聽到雷聲孔雀翩翩起舞一樣,聽聞您的善行我心非常高興”,[7]這些都是《云使》中常見的意象。 可見,蒙古喇嘛高僧們在創作中“從迦梨陀的《云使》中吸取養分”[8]是無疑的。關于游記文學,《云使》從南到北如數家珍般領略了一番印度北半國的自然風景和人文圣地,所以它具有游記文學的特征。 在蒙古喇嘛文人的游記文學作品中,有些描繪和意境與《云使》是如出一轍的。 比如,在19 世紀末一位布里亞特蒙古喇嘛到俄羅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游后撰寫的一部長篇抒情詩《空中飛翔》[9]中,對城市的描寫和鳥瞰大地的視角不得不讓人想起《云使》的構思和想象。 可知,以“半成品”形式問世的《云使》蒙古文譯本雖在傳播和影響方面有局限性,但精通藏文的蒙古喇嘛文人通過藏文的閱讀和書寫傳播和傳承了《云使》的精華。
那么,真正把《云使》引進到蒙古語文學的是賓·仁欽譯本。 通過他的譯本人們捕捉到印度詩歌的魅力,《云使》的藝術感染力也在蒙古語詩歌中綻放開來。
1)民歌。 賓·仁欽譯本出版不久,在當時的蒙古國便出現了一首民歌,歌中寫道:
灑下細雨的云啊,是來自遠方喲,向我心愛的她喲,帶到我的祝福吧。
山頂上的云啊嚯,向前游走了喲,給我心愛的她喲,送去我的問候吧。③
學者們指出這是受《云使》影響而作的。 從此,在蒙古國詩人中也常出現“托云傳情”題材的詩歌,天上的白云促使人們的浪漫想象,成為了寄托思念的使者。
2)蒙古現代詩中的意象和意境。 在《云使》原文中出現了古老印度文化的“植物孕癖”現象。這個神秘又美妙的藝術想象,讓蒙古詩人著迷,有人以起名為《蒙古詩》的詩歌來把它“占為己有”。 蒙古國著名詩人B. 亞布呼蘭(1929—1982)的詩作《蒙古詩》中寫道:
美麗女子的腳
碰觸無憂樹之時
每個枝節將會
盛開花朵結果實
古代蒙古詩歌
如此驚妙的意境
在我人生之中
對我訴說著什么
燃起了我朦朧的靈感之光
點亮了我熱愛女人之初心。④
“無憂樹”不是蒙古高原上的植物,在迦梨陀娑《 云 使》 中 出 現 的“ 紅 色 的 無 憂 樹”(raktā'soka),通過藏譯本的“mya ngan med shing dmar”傳入到蒙古文《丹珠爾》 之譯本中,稱“γasalang ügei ulaγan modun”,接著在賓·仁欽譯本中得以傳承,并解釋到該樹“據說當美女的腳碰觸之時會開花”。[10]由此,該意象被現代蒙古詩歌所吸收。 “無憂樹”成了蒙印文學關系中的一棵常青樹。
3)愛情詩中的“思念”。 20 世紀蒙古國著名抒情詩人喬諾木(1936—1979)有一首情詩《向兒子的媽媽俯身傾訴》里寫道:
在他鄉的姑娘纏綿的情意中
在花鹿般歌女嘹亮的歌聲中
在北方仙女依戀的淚光中
在傾國美人的盈盈秋波中
都沒有找到我那個小可愛
都沒有聽到她那輕柔私語。⑤
這不得不讓人想起《云使》中的詩句:
我在藤蔓中看出你的腰身,在驚鹿的眼中
看出你的秋波,在明月中我見到你的面容,
孔雀翎中見你頭發,河水漣漪中你秀眉挑動,
唉,好嬌嗔的人啊! 還是找不出一處和你相同。[11]
這兩首詩的內在相同性是非常明顯的。 本文認為,熱·卻諾木的靈感來自迦梨陀娑的《云使》,其中的橋梁無疑是賓·仁欽的譯本。 在蒙古詩歌界,詩人們對古印度的迦梨陀娑充滿了敬意,也不斷在傳唱和傳播他的詩歌。
綜上所述,漫長曲折的翻譯路,不屈不撓的探索精神,在過去270 余年當中蒙古人多次反復翻譯古印度經典詩歌《云使》,一直在尋找和再現《云使》最美的姿勢。 有的譯本在歷史的洪流中已被淘汰,有的譯本雖存在著不可彌補的遺憾,但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 有的譯本已得到讀者的認可,有的譯本新鮮出爐,繼續迎接時間的考驗。
注釋:
①基里爾蒙古文:用基里爾(西里爾)字母記錄蒙古語的文字體系。 蒙古國自1946 年起使用該文字。
②回鶻蒙古文:也叫傳統蒙古文,起初仿照回鶻文而成,由此得名,從上而下書寫,自13 世紀初被創造之時起一直沿用至今,使用范圍最廣、使用時間最長的蒙古文字。
③蒙古國民歌,筆者譯。
④參見:阿迪雅.巴特爾,整理.B.亞布呼蘭詩集(蒙古文)[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614,筆者譯。
⑤參見:畢·達木丁蘇榮.喬諾木文集·抒情詩(蒙古文)[M].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4,筆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