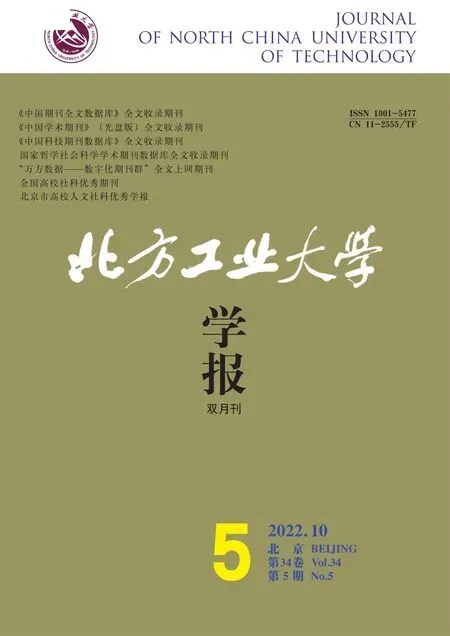論清代經學大師劉文淇的學派歸屬*
郭院林
(揚州大學文學院,225002,揚州)
清末以來,學者討論乾嘉漢學特色與區別時,往往按地域將學者納入到不同派別,通常分為吳派與皖派,甚至還有揚州學派、常州學派與浙東、浙西、湖湘學派等,不一而足。 1902 年梁啟超以地域劃分清代漢學為二:“其儼然組織箸學統者。 實始乾隆朝,一曰吳派,一曰皖派。 吳派開山祖曰惠定宇……皖派開山祖曰戴東原。”[1]稍后,章太炎繼承此說,[2]而劉師培則結合時代將學術地域更加推廣擴大為浙學、關中、贛省、湖湘以及常州、皖北、浙中、淮南、燕京等。[3]以地域劃分學派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其原因正如章太炎在《訄書》中所指出的那樣:“視天之郁蒼蒼,立學術者無所因。 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舒,而名一家。”[4]“地齊、政俗、材性”是形成古代學術派別的三大主因,其中“地齊”即指地域,地域性特征對學派的形成具有最直接的影響。 劉師培撰寫《南北學派不同論》,對諸子學、經學、理學、考證學、文學不同時期南北差異俱有論述,他認為學術之所以有地域差異,其原因在于:“中國古代,舟車之利甫興,而交通未廣,故人民輕去其鄉村。狉狉榛榛, 或老死不相往來。 《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齊,故民群之習尚,悉隨其風土為轉移。”[5]
在交通不便的時代與地區,以地域劃分學派是可以的;但在清代,江南水系交錯,水運發達,尤其是揚州,作為當時的水運樞紐,既有長江溝通東西,又有大運河連接南北,學人無論趕考還是謀生,都會途經此地,他們或長期寄寓,或短暫客居;同時此地學人受到不同地域的影響,也會走向各地,因此形成多樣的治學特色。 比如作為吳派代表惠棟和皖派代表戴震就相識于揚州轉運使盧文弨署內,揚州學人江藩是惠棟的學生,而王引之又是戴震的高足,焦循、阮元治學體現出兼采的特色。 勉強以地域劃分學術流派,不僅會將人靜態地看待,而且會將復雜的學術傳承簡單化,遇到多元影響與豐富特色時,這種論述就會顯得無所適從。 以清代揚州經學大師劉文淇為例,當初章太炎的學生支偉成將劉文淇歸于皖派與地理學,并在《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記錄詢問如何看劉文淇學術與吳派與皖派的關系:
問:……儀征劉氏孟瞻父子祖孫及凌曉樓、陳碩甫諸先生雖出皖系,其篤守漢儒,實吳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吳否?
答:儀征劉孟瞻本凌曉樓弟子,學在吳皖之間,入皖可也。 ……蓋吳派專守漢學,不論毛鄭,亦不排斥三家;碩甫專守毛傳,意以鄭箋頗雜,三家不如毛之純也,仍應入皖。[6]
從問答中可以看出,以地域來看學者特色,顯得有些尷尬,很難單純地將劉文淇歸為哪一派。 下文筆者將惠棟、沈欽韓與劉文淇學術觀點與治學特色相比較,結合時代與社會發展來分析劉氏治學的特色與歸屬問題。
1 劉文淇承繼惠棟治學方向
提及儀征劉氏,學界多以其能世代相傳,共治一經而贊嘆不絕,常與吳門惠氏三傳相比。 如汪士鐸就認為:
國家以文德化成海內,百年來尤重經術。江、淮間,推儀征劉氏。 自孟瞻先生以經學純德,師表儒術,余同年伯山繼之,其良子恭甫又繼之,三世通經精博,學者企若吳門惠氏。[7]
汪氏似乎僅從三代傳經賡續形式上將劉氏比附惠氏,實際上單從劉文淇看,他對惠氏治經理念與具體意見接受頗多。 劉文淇(1789—1854),字孟贍,經明行修,與劉寶楠并稱“揚州二劉”;治學尤肆力《左傳》,成書《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一書長編已具,而未能卒業。 雖然劉文淇早年受學于皖籍學者,梅花書院山長洪梧指導生徒各自專治一經,包世臣給予研治《詩經》的建議,早年為阮元家庭教師,親從問故,校書多受其指導,交游中除揚州劉寶楠、薛傳均、梅植之、羅茗香、楊亮、王西御與王句生外,多為皖籍,如包世榮、包孟開等;[8]但仔細分析劉文淇學術著作內容與特色,卻可以發現,他的《左傳》學深受吳地學者影響,他的治學方式方法與惠棟一致。
惠棟(1697—1758),字定宇,號松崖,他是最先明確打出漢學旗號,并確立漢學治經模式的經學大師。 章太炎論清代漢學興起的過程時說:“士奇《禮說》已近漢學,至棟則純為漢學,凡屬漢人語盡采之,非漢人語則盡不采,故漢學實起于蘇州惠氏。”[9]惠棟學宗漢儒,推尊漢說,尚家法而信古訓。 他說: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 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并行。 《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 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10]
“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11]他的《左傳補注》六卷,無論其治學的宗旨,還是具體的考釋方法,與他以漢學治經的脈絡體系完全合轍。 《左傳補注》為《九經古義》系列之一,由于最先完成而刊版別行。 該書援引舊訓以補杜預《集解》之遺,書名由《左傳古義》更改為《左傳補注》。 他在《左傳補注序》中說:
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為古學,故所載古文為多。 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 及孔穎達奉敕為《春秋正義》,又專為杜氏一家之學。 值五代之亂,服氏遂亡。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 自杜元凱為《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 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 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剌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為《補注》六卷,用以博異說,祛俗議。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掩;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 其中于古今文同異者尤悉焉。[12]
劉文淇從事《左傳》研究,其出發點與認識與惠棟相同,都是對杜預《注》不滿意,想恢復舊注(惠棟稱為漢注):
嘗謂《左氏》之義,為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系襲取舊說。 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 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 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 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 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 泛若此者,皆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13]
洪榜概括惠棟訓詁堅持漢儒的古義時說:“東吳惠定宇先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于漢經師以來賈、馬、服、鄭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于今者,旁搜廣摭,裒集成書,謂之‘古義'”[14]首先從恢復古字古音開始,以期還原《左傳》本來面目。 惠棟大量指陳傳文中的古文古字,或考證傳文某字與某古字相通,主要依據《說文》所引《春秋傳》,他認為:“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15]因為許慎師從古文經學大家賈逵,《說文解字》中引用《春秋傳》都為《左傳》內容。 依據的其他經典還有《禮記》《儀禮》《周禮》《詩經》《史記》《漢書》等經史之漢注,以及《經典釋文》所存之異文,有時并考校于石經、碑文及宋本。 惠棟認為:“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焉”;[16]“古訓之亡自杜始”。[17]惠氏著力輯存漢儒舊說,尤以賈、服為多。 他綴次古義、輯存古學目的,就是以古義糾杜之違,以漢學匡杜之失。后來,發明賈、服之學,匡正杜《注》之訛,成為漢學家研治《左傳》的主流。
漢學的價值在于“去古未遠”,在于漢儒有師承家法。 所謂“去古未遠”,就是“去圣未遠”。[18]惠棟追求漢注,劉文淇恢復舊注,二人在推尊漢說的方向上一致。 劉文淇認為:經學要先專后博,要守家法師法;先通一經,然后通群經,而不是相反。 “劉自孟瞻先生《青溪舊屋集》出,精蘊內斂,若弓之受檠,田之有畔,謹守師法者宗之。”[19]劉文淇在《題黃春谷先生承吉一經授子圖》詩中說:“古讀一經通群經,思無越畔農功好。今習群經經反荒,甫田不治田生草。”[20]詩歌用耕田的方式作比,強調各經要有“田畔”,亦即范圍與約束。 同詩還談到審音識字的觀點“我聞讀書先識字,字義不明經難曉。 我聞識字先審音,聲音不明義難了。”[21]劉文淇在《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詁序》中談到從黃春谷那兒學習到“古人文字重聲而不重形,故得其聲,凡與聲相近之字,皆可通假。 近為《文說》,發明以聲為綱之義”。[22]“先生謂六經莫外于小學,小學者即載道之文字,而文字之訓詁莫非本于聲音,故凡字義,以所從之聲綱為主,而偏旁乃逐物形跡之目。 又謂字義必視乎隨文所用,而字之本義,則一核其本字之聲。 斯義無不明,而其字義遷流之故,亦即于字中可見。”[23]
以“旝動而鼓”為例,可以看出劉文淇對惠氏的治學方式與學術觀點的接受情況。 惠棟云:
賈逵曰:“旝,發石,一曰飛石。 《范蠡兵法》曰:‘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二百步。’”《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從聲。 《詩》云其旝如林。”《三國志》:“太祖為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 杜以旝為旃,蓋本馬融。 (追,古文磓)。[24]
劉文淇所采賈逵注與惠棟完全一致,同時《疏證》內容也多相同:
《說文》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用賈說。 追,古文磓,《釋文》:“磓,古外反。 又古活反,本亦作檜” ,而亦引建木發機之事。 如《釋文》說,是又有作檜之本矣。 《御覽》三百三十七引《春秋》舊說:“旝,發石車也。”與賈同,當亦左氏家說。 《三國志》:“太祖為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惠棟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 杜以旝為旜,蓋本馬融。”按:《說文》旝字下又引《詩》曰:“其旝如林。”當系三家傳詩。 馬融《廣成頌》云:“旜旝摻其如林。”惠氏謂杜本馬融以此,而《御覽》三百三十七引杜《注》:“旝,旟也。”與今本“旝,旜也”又異。 《疏》但云“旜之為旃”,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為然,而引賈注駁之云:“按《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旜也。 發石非旌旗之比。 《說文》載之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且三軍之眾,人多路遠,遠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為擊鼓候也。 《注》以旃說為長,故從之。”[25]
劉氏《疏證》一方面梳理各家見解的來龍去脈,認為《說文》對“旝”的解釋來源于賈逵,另外增加《經典釋文》與《太平御覽》佐證賈說,同時對惠氏的見解指出依據。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引述惠棟觀點254 條,比如文字方面有“鄭人來渝平”條引惠棟云:“渝讀為輸,二《傳》作輸。 《廣雅》曰:‘輸,更也。 與懌、悛、改同釋。'《秦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 渝,更也。 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為‘變',必俗儒傳寫之訛。”[26]地名考證方面有“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條肯定惠棟的意見:“惠棟《左傳補注》云:‘蔑,本姑蔑。 《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27]禮制方面有“則公不射,古之制也”條引惠棟云:“此指祭祀射牲。 《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左史倚相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候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是也。 朱子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魚,如漢武親射蛟龍江中之類',恐未然。”[28]然后劉氏加案語指出朱子“弓矢射魚“之說,系誤仞矢魚之矢為弓矢之矢,肯定惠氏駁之。
惠棟明確指出杜預“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29]乃援引舊訓,尤以漢儒舊注為主而作《左傳補注》,開啟乾嘉學者綴次古義、集矢杜《注》的風氣。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則是在全面輯佚賈、服等舊說的基礎上,建立起《左傳》新注新疏之代表。
2 劉文淇接受沈欽韓治學觀念
劉文淇受吳派學者最直接影響的人物當屬沈欽韓。 沈欽韓(1775—1831),字文起,號小宛,江蘇吳縣人,主要著作有《春秋左氏傳補注》《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春秋朔閏異同》。 據包世臣所撰凌曙《墓表》,凌曙曾師從沈欽韓問疑,由此“益貫串精審”,[30]則劉氏作為凌氏的外甥,也得以問學。 沈氏《與劉孟瞻書》和劉文淇討論《資治通鑒》作者用心以及新舊《唐書》長短,指出劉氏認為《新唐書》“史筆謹嚴”之誤,是“未免震秦之余威也”,而認為“一代信史,先務明白詳贍,而后求其文章議論。”[31]
作為吳派經學名家,沈欽韓承襲同郡惠棟“漢學”宗旨,竭力張大“漢學”思潮。 在《左傳》研究上,受惠棟《左傳補注》的影響,表現為尊漢崇古,重視訓詁與考據,維護古文經學《左傳》。與惠棟及其后來的漢學家相比,沈氏更加強調古文學派的師承家法,追蹤賈、服舊注,極詆力排《公》《穀》二傳,而獨尊《左傳》;于杜《注》孔《疏》,批判尤為強烈,全盤否定杜預《集解》,以其詳盡的禮制典章考辨,為《左氏》古學正本清源。
杜預之前,《左傳》研習者遺文十數家,但杜預對《左傳》舊注多有不滿,特舉四家之違失:“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 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32]孔穎達解釋說:“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33]杜預襲用前賢成果而不標明,有違學術規范,成為清儒集矢的緣由之一,至有謂攘善剽竊者。 沈欽韓就說:“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為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為《左氏》之巨蠹。”[34]他在《與周保緒書》云:“為《左氏》之疻痏而得罪于圣經者,無如杜預也。 賈、服之注,今已不傳,其精者偏為杜預攘取,孔《疏》惟摘其細碎以為嗤笑。 然他經如《周禮》《儀禮》疏中所引服氏,猶可想見向來經師之講習、《左氏》之面目,未至顛倒變易。 杜預乃盡翻家法,移《左氏》之義以就其邪僻曲戾之說,創《長歷》以為牽附移掇之計,造《釋例》以成其網羅文致之私。 疏家及后之為《左氏》者,動輒惑于其例。 于是《左氏》之學亡,而杜預儼然專門名家矣。”[35]而對于孔穎達《正義》,則云:“孔穎達等素無學術,因人成事,《五經正義》稍有倫理者,皆南北諸儒之舊觀。 其固陋之習,最信《偽孔傳》、杜預。 于鄭氏,敢斥曰不通、不近人情;于服氏曰尚不能離經辨句,何須著述大典;尊崇杜預,謂《禮經》為不足信;狂惑叫號,而鄭之他經,服之《左傳》,由此廢亡。 名曰表章經學,實乃剝喪斯文,可勝恨哉!”[36]
劉文淇學習沈欽韓所著《左傳補注》,“竊嘆《左氏》之義為杜征南剝蝕已久,先生披云撥霧,令從學之士復睹白日,其功盛矣”。 受此啟示,劉氏覆勘杜注,發現其中錯誤橫生,而稍可觀者都是賈逵、服虔之說,“文淇檢閱韋昭《國語注》,其為杜氏所襲取者,正復不少。 夫韋氏之注,除自出己意者,余皆賈、服、鄭、唐舊說。 杜氏掩取,贓證頗多”。 他的疏證的作法是:
取《左氏》原文,依次排比,先取賈、服、鄭君之注,疏通證明。 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 其襲用韋氏者,亦一一疏記。 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家之學。 又如《周禮》《禮記疏》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 凡若此者,皆以為注而為之申明。 疏中所載,尊著十取其六,其顧、惠《補注》及王懷祖、王伯申、焦里堂諸君子說有可采,咸與登列,皆顯其姓氏,以矯元凱、沖遠襲取之失。 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37]
劉氏對杜預《注》的觀念與沈氏一致,沈氏觀點多被采納《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同時,劉氏治經的的家法與沈氏一致,尊信《左傳》:“至若左氏之例,異于《公》《榖》。 賈、服間以《公》《榖》之例釋《左傳》,是自開其罅隙,與人以可攻。 至《春秋釋例》為杜氏臆說,更無論矣。 文淇所為《疏證》,專釋詁訓、名物、典章,而不言例。 其左氏凡例,另為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釋左氏。 其不知者,概從闕如。 杜氏以經訓飾其奸邪,惠定宇微發其端。焦里堂《六經補疏》以杜氏為成濟一流,不為無見,然以杜氏之妄。 并誣及左氏,則大謬矣。”[38]
鄭玄《六藝論》論三傳的特點:“《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39]唐初孔穎達等學者,已經承認或論定《春秋》可以當禮書看。 沈欽韓《左傳補注》注重發明《左傳》禮學之旨,以禮解經的特色更為鮮明。 他在《自序》中開宗明義地表述道:
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 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 時則下陵上,裔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 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為修整于既往。 ……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祥焉。 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于一書。 ……以全《春秋》付托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 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為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為《左氏》之巨蠹。 ……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 注疏之謬,逐條糾駁,各見于卷。 則左氏之沉冤稍白,杜預之丑狀悉彰。[40]
沈氏撰《惠氏〈左傳補注〉后序》,亦曾論及《春秋》《左傳》與禮的關系。 他說:“道有污隆,則禮為之變。 夫子作《春秋》,使紀事不失其實,以補禮之窮,維世之具,如是而已。 左氏作《傳》,略舉凡例,而詳于言禮。 至于升降揖讓、尊俎籩豆之間,曰是儀也,非禮巸已。 若左氏者,其深知文、武、周公致太平之道矣。 例不可以概論禮,則是非兩端萬變不窮,后之學者舍禮而言《春秋》,于是以《春秋》為刑書,以書法為司空城旦之科,紛紜轇轕,跬步荊棘,大率尾牽皮傅以自完其例,而圣人經世之法,為其汨沒。”[41]其《幼學堂文稿》卷一有《出母嫁母服議》《妻為夫之兄弟服議》《父為長子三年辨》《出后之子為本生祖父母議》《諸侯之臣為天子辨》;卷七有《答許鳧舟問庶母庶祖母服書》。 這六篇文章,主要依據三禮考論喪服之禮;卷二則有《吊生不及哀解》《先配而后祖解》《大夫宗覿解》《用致夫人辨》《駁杜預與會位定論》《妾母不得為夫人論》《既獻召悼子及旅召公鉏考》《叔孫豹違命論》《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辨》等九篇,是關于《左傳》禮制典章的專論。這些禮制典章研究之文,寫作于《補注》撰著之前。 沈氏的禮學學養及前期成果,是他《補注》以禮解經特色形成的基礎。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的“注例”,專門有“釋《春秋》必以禮明之”一條:
《周禮》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禮明,而后亂臣賊子乃始知懼。 若不用周禮,而專用從殷,(原注:《公羊》家言《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殊誤。)則亂臣賊子皆具曰予圣,而借口于《春秋》之改制矣。 (原注:《鄭志》曰:“《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 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所謂禮,即指周禮。)[42]
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原稿眉批曰:“哀十四年疏稱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為孔子修《春秋》,約以周禮。”這一句也就表明了古文經學的立場,因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43]東漢《左傳》學興起與劉歆密不可分,在他的努力下完全實現了《左傳》的傳化,確立了《左傳》學的歷史理論和邏輯理論,所以劉歆當之無愧是《左傳》學的創始人。[44]但是劉歆等研究成果留存極少,而賈逵、服虔注釋卻在《左傳正義》和其它典籍保存不少。 劉文淇回到了劉歆的立場,也就回到了漢代《左傳》學的起點,對內找到了賈、服等漢儒舊注的源頭,為期疏證舊注奠定了基礎;對外則與漢代的《公羊》學乃至《谷梁》學劃清了界限。[45]漢朝制禮用《左傳》。 孔子作是因為禮崩樂壞而作以示褒貶,那么《左傳》要傳經,必歸于禮。 《左傳》有一個明顯而一貫的歷史觀,這是“禮”。 作者把當時一切的興亡成敗的原因都歸結到人與人,國與國間相互交往時有禮或無禮……即是在中國文化中人與人的關系,國與國的關系,以禮為共同遵守的準繩,并以有禮與無禮為文明(華)或野蠻(夷)的分別。 所以劉氏強調《左傳》的禮學意義,正得其要穴。 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二有《既殯后復殯服說》《親喪既殯后見君無稅衰說》二文為論事說禮,同時有《朱芷汀夏小正正義序》,校《禮記訓纂》(朱彬撰)。 他的治禮事業為后人繼承,兒子劉毓崧著《禮記舊疏考正》一卷,孫劉壽曾著《昏禮重別論對駁義》二卷,曾孫劉師培更著有《禮經舊說考略》《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逸禮考》等多部專著。
沈欽韓《左傳》學精于地理,詳考制度。 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也多取于沈氏,共計711條。 禮制方面如“發幣于公卿”條引沈欽韓云:“《聘禮》:歸饔餼之明日,賓朝服向卿。 卿受于祖廟。 庭賓設四皮。 賓奉束帛入,致命降出。 又請面如覿君之幣,畢乃餼賓。 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主人朝服迎外門外,再拜,賓升一等。 大夫從升,再拜受幣。 此敬賓之禮。 而凡伯不然。 故戎嫌之。”[46]劉文淇以案語肯定沈氏之說“發幣”。 再如“針子曰:‘是不為夫婦。 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條引沈欽韓《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 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 反而不告至,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 是為墮成命而誣其祖。 又先配后祖解云:蓋禮有制幣之奉。 春秋有告至之文,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 況昏禮之大者乎? 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于嫡,而惜跬步之勞于祖,已即安伉儷焉?是為誣其祖也。”又云:“針子曰:‘不為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劉氏以為:“沈氏不用賈、服、二鄭君義而言廟見,言未成婦,仍賈、服義所有也。”因為“其說禮意甚精,謹附著之。”[47]地理方面如:“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條引述沈欽韓云:“《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 或謂盟于瓦屋即此。'《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 杜預謂周地,非也。”[48]“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條引述沈欽韓云:“《方輿紀要》:‘汶水出泰安州萊蕪縣北七十二里原山之南。 《水經》所謂北汶也。'《運河記》:‘汶水自泰安州經寧陽汶上縣界,又西至東平州,注濟水,比故道也。'應劭云:‘水北為陽,南為陰。'蓋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北。 漢置汶陽縣,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非此汶陽也。”[49]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搜羅前人注釋最富,隱公傳“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條,舊注列“服云:僨,仆也。”劉文淇疏證不僅對僨意進一步證實,而且補充濟水在何處,涉及字意理解與地理方位。 所引有《釋言》、舍人注、《水經注》、沈欽韓注、《元和志》,指出杜《注》與《正義》理解錯誤,杜錯在全憑臆說。 全文如下:
《釋言》:“僨,僵也。”舍人注:“僨,背踣意也。”《水經注》:“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至鞏縣北入于河。”沈欽韓云:“《方輿紀要》:大清河在長清縣二十里,自平陰縣流入境。 又東北入齊河縣界,即濟水也。 鄭伯之車僨于濟,蓋在縣界。 《元和志》:劉公橋架濟水,在鄆州盧縣東二十七里。 又北去濟州長清縣十里。”杜《注》:“既盟而遇大風。 傳記異也。”《正義》曰:“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墜濟水,非常之事。”文淇案:傳文無風吹事,杜注意為之說。[50]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集《左傳》研究之大成,取著廣博,資料豐富。 “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左證。期于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復明。”[51]近人著述,多采入其中,或作佐證,或作駁論。
3 劉氏治《左》的時代局限
劉壽曾將揚州學人的學術淵源追溯到江永,他認為:
國初東南經學,昆山顧氏開之,吳門惠氏、武進臧氏繼之。 迨乾隆之初,老師略盡,儒術少衰,婺源江氏崛起窮鄉,修述大業,其學傳于休寧戴氏。 戴氏弟子,以揚州為盛,高郵王氏傳其形聲訓故之學,興化任氏傳其典章制度之學,儀征阮文達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師說。 風聲所樹,專門并興,揚州以經學鳴者,凡七八家,是為江氏之再傳。 先大父(劉文淇) 早受經于江都凌氏(曙),又從文達問故,與寶應劉先生寶楠,切劘至深,淮東有‘二劉’之目,并世治經者,又五六家,是為江氏之三傳。 先征君(劉毓崧)承先大父之學,師于劉先生。 博綜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視文達為近。 其游先大父之門,而與先征君為執友者,又多綴學方聞之彥,是為江氏之四傳。 蓋乾嘉道咸之期,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常外,東南郡邑,無能與比焉。 ……江氏生于孤特,不假師承,猶且開揚州之風氣,以大昌其學術,今距四傳之時,淵源濡染,近不越十余年,歲會月要,鍥而不舍,其為江氏之五傳,蓋無難也。[52]
江永系統研究《左傳》的代表性著作《春秋地理考實》,成于晚年。 全書著重探討并考證《春秋》以及《左傳》文本中地名所涉及的地理位置與區域沿革等多方面的問題。 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引述江永觀點139 條,如“戎伐凡伯于楚丘”引江永曰:“《匯纂》:‘今兗州府曹縣東楚邱亭是也。'今按曹縣今屬曹州府。 二年戎城,亦在曹縣。 則此楚邱為戎邑,非衛邑也。”[53]再如“哀侯侵陘庭之田”條引江永云:“翼,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庭城。 《志》云即陘庭也。 又《水經注》:‘紫谷水出白馬山,西逕榮城南,西入澮,亦在翼城南。'則陘庭即熒庭,亦即榮庭也。”[54]
但江永治學無門戶之見,漢宋兼采。 他在具體考釋《左傳》地理時,面對古今眾說,毫無成見,既兼收博采,又考疑辨誤,惟是之求,表現出兼收并蓄的學術胸襟和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 《春秋地理考實》多處采錄了《公羊傳》《穀梁傳》的說法。 如桓公四年《經》:“公狩于郎。”江永據《公羊傳》云:“譏遠也”,考此年之“郎”,當為《左傳》隱公元年費伯帥師所城之郎,在清兗州府魚臺縣東北。[55]夏鑾與胡培翚討論當時學術,謂“兼漢學宋學者,惟江慎修。 江氏書無不讀。 人知其邃于《三禮》,而不知其《近思錄集注》,實擷宋學之精。”[56]劉氏《左傳》學強調家法,追求舊注,與江氏之學還是有很多區別的。
戴震是公認的考據大家、當時學界中心人物之一,弟子及再傳弟子甚多,段玉裁、任大椿、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諸人。 受戴氏影響者亦不少見,尤其是揚州學者,如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 王昶在《戴東原先生墓志銘》一文中這樣評價戴震:“東原之學,苞羅旁搜于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于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于理道。 本朝之治經者眾矣,……端以東原為首。”[57]戴氏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 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會通古說,不尚墨守。”[58]而且戴氏于義理、考核、文章能得其源,由博返約。 在考證方法上,戴震辨彰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歸納;而且戴學最可貴之處在于“于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窮理。”“格物者格物類也,窮理者窮實理也,與宋、明虛言格物窮物者不同。”[59]如果從考據學這方面看,劉氏《疏證》旁征博引,或近于戴學。 但劉《疏證》僅引戴說3 條,似與其關系不大。 相比較而言,劉氏就缺少義理這方面的思考,學術上多繼承,思想更多趨于保守傳統。 劉壽曾從揚州學者多從戴震受教立論,但以此來斷定劉氏與皖學的聯系,似乎流于形式,從劉氏具體情況看,所言并不準確。
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引述多家,僅《春秋》《左傳》類初步統計就有29 部,經部88部,比如段玉裁的《春秋左氏古經》、李富孫的《春秋三傳異文釋》、王引之的《經義述聞》、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等。 惠棟確立漢學宗旨,其《左傳補注》為漢學發皇,羽翼聲張者甚眾。 在他們的《左傳》著述中,表現了由惠棟開啟的相輔而行的兩種學術趨向,一是綴次古義,還原古學;一是批判杜《注》孔《疏》。 《左傳》多古字古音,由文字、音韻、訓詁以尋求義理,是漢學家考據《左傳》的主張,所謂“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60]清人追蹤《左傳》漢學古義,專門輯存賈、服舊注,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 劉師培在《經學教科書》中總結清代《左傳》學時說:“治《左氏》者,自顧炎武作《杜解補正》,朱鶴齡《讀左日鈔》本之,而惠棟《左傳補注》、沈彤《春秋左傳小疏》、洪亮吉《左傳詁》、馬宗璉《左傳補注》、梁履繩《左傳補釋》咸糾正杜《注》,引伸賈、服之緒言,以李貽德《賈服古注輯述》為最備。 至先曾祖孟瞻公作《左傳舊注正義》,始集眾說之大成。”[61]該書特色也在于“掇拾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末下己意, 以定從違”[62]因為體大思精,要歸屬于哪一派也是不容易的。
章太炎認為吳派“好博而尊聞”,“篤于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而皖派“綜形名,任裁斷”,“分析條理,皆縝密嚴傈,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63]這樣的分析要讓吳派心服恐怕未必。倒是劉師培清代漢學分期論更為合理,他依據學術發展時代展示的不同特色劃分為:懷疑派(順、康之交)——征實派(康、雍之間)——叢綴派(雍、乾之際)——虛誣派(嘉、道之際),征實派“長于比勘,博征其材, 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為憑。 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征不信者矣”。 此派雖以江永、戴震為顯著,但不排除吳派學者,如“嘉定三錢,于地輿、天算,各擅專長;博極群書,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即惠氏之治《易》,江氏之治《尚書》,雖信古過深,曲為之原,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然融會全經,各申義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 律以江、戴之書,則彼此二派,均以征實為指歸”,這是一個時代的特色而非地域的特征。劉氏家學興起于嘉慶、道光之際,介于“征實派”與“叢綴派”之間,而后劉氏子弟處“叢綴”學風下篤守“征實”之代表。 劉師培對此階段考據特色論述道:
自征實之學既昌,疏證群經,闡發無余。 繼其后者,雖取精用弘,然精華既竭,好學之士,欲樹漢學之幟,不得不出于叢綴之一途,尋究古說,摭拾舊聞。 此風既開,轉相仿效,而拾骨、襞積之學興。 一曰據守。 篤信古訓, 跼蹐狹隘,不求于心,拘墟舊說;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 二曰校讎。 鳩集眾本,互相糾核。 或不求其端,任情刪易,以失本真。 三曰摭拾。 書有佚編,旁搜博采;碎璧斷圭,補苴成卷。 然功力至繁,取資甚便。 或不知鑒別,以贗為真。 四曰涉獵。 擇其新奇, 隨時擇錄。 或博覽廣稽,以俟心獲。 甚至考訂一字,辨證一言,不顧全文,信此屈彼。 ……然所得至微![64]
以乾嘉學風治經,劉文淇是《左傳》學之總結。 劉文淇應該知道歷代學人對《左傳》的認識和評述不乏史學的定位。 東漢桓譚肯定《左傳》記事的價值,說:“《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65]唐代劉知幾也是從史學的角度肯定《左傳》,他說:“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 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后來學者兀成聾瞽矣。”[66]但《左傳》畢竟疏于義理,所以朱熹說:“《左氏》是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是經學,理精而事誤。”又說:“《左氏》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呂大圭也說:“《左氏》熟于事,《公》《穀》深于理。”[67]劉文淇出于古文經學家的家法考慮,崇漢尊《左》,治經對象個體與方向地選擇更多在于發掘《左傳》中的“古”的東西,包括文字字形、訓詁以及名物制度等。 《左傳》客觀記錄了當時的禮制,但僅是客觀反映,并沒有統一的禮學觀念與禮制思想。 劉文淇舍棄義理的研究,從禮制作疏解,墮入叢綴派。 雖然材料比前代學者更為豐富,但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架床疊屋,耗費四代人的精力,最終也沒有完成,成為遺憾。
正如本田成之所說:“清朝的學問很嚴謹,不過只是小學訓詁的學問。 把經書視為神圣,對于漢儒也太過重視,當然是由宋儒大膽批評的反動,其弊不免怯懦。”[68]梁啟超一方面肯定漢學的勤奮,另一方面也指出他們對于社會的無用:在《清代學術概論》評論道:“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 其最有功于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他認為這些新疏大都“博通精粹,前無古人”,“皆擷取一代經說之菁華,加以別擇結撰,殆可謂集大成”。[69]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中認為:“惠戴之學,固無益于人國,然為群經忠仆,使后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誣也。”但是“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70]
我們研究《左傳》,復原其中的禮制當然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從學術思想史角度來看,更要看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研究的方向與重點有何不同,為何產生? 如果不從歷史語境考察,唯古是求,一方面很難理清孰是孰非,另一方面也是將經典博物館化,而要讓經典活化起來,則不能不研究其時代性,亦即不同時代學者研究經典時對時代的回應,他們內在精神以及對當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