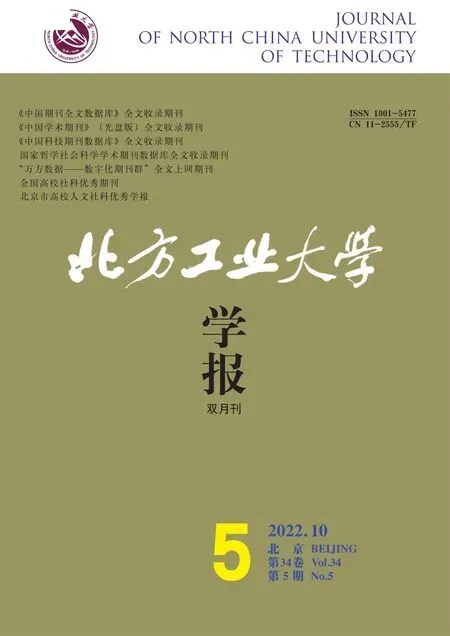春秋盟禮之“信”探析*
羅軍鳳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710049,西安)
盟禮本屬周代禮樂制度。 《周禮》設玉府,掌管盟會之物;戎右掌辟盟之役,司盟掌盟載之法。玉府、戎右、司盟這些職官都是天子所設官職,掌管王室與公室、公卿、諸侯之間的盟禮。 《禮記·曲禮下》鄭玄注:“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1]周王室盟禮,與遇禮、會禮、誓禮一樣,均已失傳。 《左傳》《國語》等文獻記載的盟禮不是周王室與諸侯或卿大夫的盟禮。 王室東遷之后,周淪落為普通諸侯國,周與諸侯之間的盟禮已失王室盟禮的本義。 周初設盟禮,是為解決王室與諸侯之間的猜疑、嫌隙,周天子仍保有神權、王權,但春秋時期,周天子的神權、王權均已失落,盟禮上增設“交質”這一儀節,尤其是王室卑微的象征,不能再用周王室禮樂制度來解釋。 學者分別討論盟禮和交質,卻未將二者聯系在一起。[2]本論文以“周鄭交質”一事,論述春秋盟禮的新變化,并分析《左傳》君子曰對盟禮之“信”的闡發,以補前人之未備。
1 盟禮的特點
先秦典籍中的“盟”,均為盟禮。 漢唐注疏對“盟”的解釋多種多樣,側重各不相同,歸結起來有如下幾種:第一,指向盟禮“殺牲歃血”這一重要儀節,以此與“誓”相區別。 《禮記·曲禮下》:“約信曰誓,蒞牲曰盟。”[3]《周禮·秋官》“司盟”鄭玄注:“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4]《說文解字》《文心雕龍》還具體指出盟禮所用犧牲和器物:“諸侯……十二歲一盟。 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5]“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6]
第二,指向盟禮的禮義“信”,以盟禮取信于雙方,以防“將來”之不信任,此與“詛”相區別。《國語·魯語》:“夫盟,信之要也。”[7]《穀梁傳》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8]《淮南子》“周人盟”高誘注:“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盟者,殺生歃血以為信也。”[9]《說文解字》:“《周禮》曰:‘國有疑則盟。 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 盟,古文從明。”[10]《周禮·春官》“詛祝”賈公彥疏:“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11]盟字從“明”字得其義,盟禮之后雙方不再安藏禍心,一切擺在明面,以防將來之患。
第三,指向人神之間的約束機制,假借鬼神以約束不守信用的一方。 《周禮·司盟》鄭玄注:“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兇。”[12]《春秋左傳正義》引杜預《春秋釋例》:“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13]孫詒讓《周禮正義》認為周初即有“盟詛之禮”,即“盟禮”。[14]《釋名》:“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15]盟禮是鄭重其事在鬼神面前立盟,若有違背,則由鬼神降兇于人。 盟禮由鬼神施加懲罰于人,這一點,盟禮與會禮相區別。
根據“盟”的前兩種解釋,一是點明盟禮的儀節“殺牲歃血”,一是解釋盟禮的禮義“信”,不免讓人迷惑:何以殺牲歃血這樣的行為能取信于雙方,而且能防患于將來? 所以要解釋盟禮,必須深入到古人的社會心理,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盟于鬼神,就可以致信,就可以達成兩國之不疑?“盟”的第三種解釋就是回答了這個問題,即假借鬼神的威力,對人形成約束。 考察春秋時期的盟辭,我們更能深入理解人神之間的約束機制。
僖公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諸侯,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若諸侯不擁戴王室,那么鬼神就會殺其身,亡其師,滅其國,且禍及子孫。 成公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盟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晉楚兩國世代相好,如有違背,就會亡師滅國。 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鄭與諸侯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盟書上列四項不該做的事、四件該做的事,若有違誓,所有的天神、山川之神、諸侯的祖先,都可以誅殺違盟之人。 鬼神的權力很大,不僅可以誅殺訂盟之人,并可以禍及軍隊、國家、家族、百姓。 鬼神的約束是盟禮得以奏效的重要保證,故云“使不信者必兇”。 “盟禮”背后潛藏著根深蒂固的社會心理:鬼神有超人的能力,對人世間的人事有懲罰能力。 如果不相信鬼神能懲罰人,則盟禮失去約束力。
終春秋之世,盟禮“殺生歃血”的儀節未變,把“信”作為禮義這一點未變,但人神之間的約束機制卻發生了極大變化。 盟禮在人神約束之外,加入了“交質”這一環節,這是春秋時期的大變革,《左傳》以“君子曰”之口闡述了盟禮不可用質、盟禮重歸于人神之信的主張。
2 盟禮“交質”的出現
至于盟禮的儀節,除了“殺牲歃血”之外,先秦文獻及三禮未有更多儀節的記錄,唐代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第一次詳細討論,[16]今人多引用、補正,踵事增華。 學者陳夢家結合考古資料,考證春秋盟禮的儀節有十步:為載書、鑿地為坎、用牲、盟主執牛耳、歃血、昭神、讀書、加書牲上、埋書、藏盟書之副于盟府。[17]山西侯馬盟書遺址是春秋盟禮的歷史見證,坑內有璧、璋等玉器,和牛、馬、羊等家家畜骨骼,尤以羊為多見。 無論是考古,還是傳世文獻,盟禮皆無“交質”一事。
然而,參加盟禮的雙方“交質”是盟禮在春秋初期的大變革,也是盟禮的大破壞。 《左傳》記載隱公三年周鄭交質,這一事件最易忽視的環節是盟禮。 為方便論述,茲將《左傳》隱公三年“周鄭交質”與“君子曰”之文錄于下: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王貳于虢。 鄭伯怨王。 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秋,又取成周之禾。 周、鄭交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茍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釡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18]
周、鄭兩國交質,必有盟禮在先。 《左傳》君子曰反對盟禮交質:“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杜注:“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19]明確指出周鄭二國盟,清《詩義折中》:“春秋之世,人君有與其臣下盟者。 觀周鄭之交質,則王之盟其臣可類推也。”[20]亦謂周鄭交質時有盟禮。
《左傳》有盟禮之外附加“交質”的記載,雖然沒有成功,但可以證明“交質”附加在盟禮之上。 哀公八年,魯國欲與吳國盟,唯恐吳國不聽從魯國,魯國以景伯為質,請求用吳太子為質。杜注:“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于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21]魯人“不以盟為了”,于是提出“交質”,吳人不愿意出質王子姑曹,最后交質不成,只舉行了盟禮。
春秋時期,盟禮出質的現象時有發生。 馬非百《秦集史》謂周鄭交質之后,“諸侯交質,遂成為國際交涉之慣例。”馬氏統計交質事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六見焉”。[22]馬氏統計有誤,“交質”說亦不成立。 所謂“交質”,其所列舉六事,只有五次出質,如晉太子圉為質于秦(僖公十七年),鄭子良為質于楚(宣公十二年)、齊公子強(宣公十八年)及太子光(襄公元年)為質于晉,蔡昭侯使其子為質于吳(定公三年),都是單方面出質,而無“交質”;而哀公元年越王勾踐行成于吳,并未出質。 諸侯之間每每盟禮后出質,或因質而求盟。 如宣公十二年“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宣公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強為質于晉。”成公二年,楚師侵衛,“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這些都說明了“質”與盟禮關系密切。 可以說盟禮出質,成為國際交涉之慣例。
本文所論交質,更能說明盟禮的變革。 除隱公元年周鄭交質之外,還有文公十七年晉鄭交質、昭公十三年宋元公與華亥交質。 晉國合諸侯而與鄭國有隙,晉“行成于鄭”,當有盟禮,最后晉鄭二國交質。 宋元公與華亥是在盟后交質。 可見,春秋交質都與盟禮相伴而行。
2.1 《左傳》君子曰強調人神之“信”
不僅“周鄭交質”背后的盟禮被忽略了,在明清評點中,《左傳》君子曰以“信”為主旨,亦多被誤解。 《左傳》君子曰論及多個范疇,如“質”“禮”“忠”“信”“恕”,糾纏繚繞,在明清《左傳》評點著作中,眾多評點家認為君子曰以“質無益也”為主題句。[23]清末學者林紓《左傳精華》論君子曰所論不在周鄭交質的“質”,而是在“質”之外,欲“發明一義”:
后人讀此篇,以《左氏》不主君臣之義立論,而以“質之無益”為言,似為失辭。 不知古人作文,皆以發明一義為言,……君子曰下一段,夷猶淡施,風致絕佳。[24]
林紓否定君子曰的主旨是“質無益也”。 至于君子曰所發明之義,林紓并未點明。 本文認為,隱公三年君子曰所欲發明之義在開篇第一字——“信”。 “信”是一個概念、范疇,《左傳》有意將其措置于周鄭交質之事后,是因為“周鄭交質”是春秋時期第一次在盟禮中加入了“質”,違背了盟禮的本旨“信”。 君子曰以“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句開始,以“昭忠信也”句結束,實際上以“信”為始,亦以“信”為收束,其議論始終不離“信”。 隱公三年君子曰第一句便拈出“信”作為論述范疇:“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信”不能不發自于內心,而“質”無益于“信”。 第二句指出依“信”而行“禮”,不需要“質”。 第三句,論述如果內心有“信”,祭祀鬼神可以是微薄之物。 第四句反問,依“信”行禮,何須用質? 第五句,指出“信”之義隱含在《詩》之義當中。 總之,“信”存于“禮”之中,而非“禮”之外。 此禮,即二國之盟禮,而“質”,不是盟禮應有之義。 乾隆時期學者李紹崧已發覺君子曰的主旨是“信”。 “篇中屢用‘信'字駁‘質'字。”“究只論‘信' 之得失。”“‘信'字是謀篇主腦,為‘質'字勁敵。”[25]君子曰排斥“質”,重申人神之“信”,冀復歸于盟禮的本來面目。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指出盟禮要出自真心。 盟禮殺牲歃血以祭神,這些儀節均用以表內心的誠信,求信于鬼神。 在鬼神面前,如果沒有誠信,鬼神是不會幫助他維系盟禮的約束作用的。 《左傳》襄公九年記載鄭國大夫說:“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 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26]《春秋左傳正義》引服虔云:“質,誠也。”鄭國大夫子駟、子展指出若要鬼神照臨,那么人必須有兩個品質:一為誠(“質”),二為“信”(人言之信,信守自己的承諾)。 這兩個品質實際是一個,即相信鬼神。 惟有真誠地相信鬼神,才能使鬼神照臨。 惟人相信鬼神的約束力,盟辭方才有效,鬼神的懲罰才會降臨在當事人中的另一方。 鄭國大夫所說“要盟無質”,是指當年晉鄭盟,晉卿士莊子強迫鄭國接受自己所擬的盟辭:“唯晉命是聽”,這樣的盟辭并非出自鄭國真心。 所謂“要盟”,即出于脅迫、而非出于內心意愿的盟禮。 鄭國大夫相信,“明神不蠲要盟”。[27]杜注:“蠲,潔也。”明代學者劉績解釋道:“神不以要盟為潔而臨之。”[28]晉人要挾鄭國訂盟,鬼神不會讓他如愿。 盟禮要起作用,主要在于在人通過誠信,與神建立可靠的“信”,盟禮是人在鬼神面前達成契約。
春秋時期,諸侯屢盟,《詩經·小雅·巧言》譏之:“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認為盟禮失信是天下大亂的根源。 桓公十二年一年之間,魯公與宋公多次會盟,宋沒有與魯和解,卻與鄭伯盟,魯遂帥師伐宋。 《左傳》君子曰評論魯宋之間會盟無信,并引《詩經》為證:“茍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襄公二十九年,鄭國諸大夫盟于伯有氏,鄭大夫裨諶引用《詩經》“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謂鄭國大夫之盟是“長亂之道”。 襄公三十年,鄭伯又與其大夫盟,《左傳》君子曰認為鄭國的盟禮如此頻繁,將使“鄭難不已”。 春秋時期無信之盟比比皆是,盟禮中鬼神對人的約束力轉弱,故出現“交質”的極端例子。
當鬼神的約束力減弱的時候,主盟之人便用數量(尋盟)加以強化。 昭公十一年,晉與諸侯會于厥慭;昭公十三年,晉又合諸侯于平丘,欲尋盟。 周天子之卿劉獻公認為沒必要:“盟以厎信。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此所謂“信”,即信守盟禮當中自己的盟辭。 《左傳》哀公七年,魯與吳盟,哀公十二年,吳欲與魯尋盟,魯國拒絕了。魯子貢認為“盟,所以周信也。 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寡君以為茍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盟,所以周信”杜注:“周,固。”“明神以要之”杜注:“要以禍福。”[29]盟禮通過鬼神禍福加身的方式強迫人固守誠信,歸根到底,人在鬼神面前立盟,就意味著要信守自己立下的盟辭。 所以盟一而已,不必尋盟、改盟。 有人神之信,便可守住人言之信,不必用強權對盟禮加以干涉、強化。
綜上,盟禮的“信”,有兩層意思:首先,人言為信。 訂盟雙方皆需信守盟辭;人言若不信,則鬼神懲罰于人;其次,人神之信。 鬼神為誠信的人施加懲罰于不守信的人;若不誠信,則鬼神不臨。 盟禮的最終歸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 盟禮的神圣之處在于用一系列的儀式,動用鬼神,來約束人與人之間的“信”。 神高于人,但神為我所用。 神高于人,說明盟禮是信奉鬼神的時代特有的現象,是殷商巫鬼文化的遺留;神為我所用,則是春秋時期所遵奉的“理性精神”,此“理性精神”是禮樂文明超越巫鬼文化的根本特點。[30]
春秋時期,屢盟、要盟、尋盟、改盟屢見不鮮,皆因人不再信守盟辭;而人不信守盟辭,是因為不再相信鬼神的約束力,盟禮的社會心理機制崩塌了。 隱公三年君子曰針對盟禮“人神之信”的缺失,重申盟禮之“信”,而欲以“信”取代“質”。君子曰:“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2.2 君臣“交質”破壞了君王的神權
“周鄭交質”的核心事件是“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子狐、公子忽的身份不可忽視。 兩人分別是周王和鄭莊公的嫡子,在眾多子嗣中,身份最為尊貴。 將嫡子送往對方的國都,以致造成“交互”“互通”的雙邊關系,若有戰爭或糾紛,都將對雙方極為不利。 “周鄭交質”使周鄭兩國在盟禮的鬼神約束之外形成新的互為約束的關系,而破壞了盟禮本有的人與神之間的“信”。
《說文解字》:“質,以物相贅。”“贅,以物質錢。”[31]段玉裁注:“質、贅雙聲,以物相贅,如春秋交質子是也。”[32]質的本義為以物作抵押,以換取錢,而以人為質,則為換取二國之間暫時的安寧。 周鄭交質,《荀子》《穀梁傳》等文獻稱之為“交質子”,即互相抵押嫡子。 《左傳》宋堯叟注:“交質子以為信。”[33]清代學者譏周天子“以質為信,不亦懦乎?”[34]“周鄭交質”指明這樣的事實:周天子藉盟禮約束自己未將權力轉移,以示好鄭莊公,仍嫌不夠,還要將王子狐作抵押,換取與鄭國的相安無事,后來二國之間的安寧終究被葛之戰撕得粉碎,最終以周天子身中一箭收場。 周天子曾經集神權、王權于一身,至春秋初年不僅喪失了神權,亦喪失了王權,甚至到了要用嫡子作抵押以換取鄭國的信任的地步。
與“周鄭交質”相似的事件是昭公二十年宋元公與華亥交質: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 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 公子問之,則執之。 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35]
宋卿華亥因害怕華氏被宋元公排擠、誅殺,先發制人,誘殺宋公子六人之后,劫持宋元公,與宋元公盟,并交質子。 宋元公、華亥交質與周鄭交質的相似之處在于:第一,盟禮在君臣之間進行。 第二,盟禮與交質先后舉行。 第三,雙方抵押的是身份最為尊貴的子輩,包括“嫡子”,且抵押的人數一致。 華亥與宋元公交質,因為華亥一方有三個主謀,故質子三人;相應的,宋元公亦質子三人,包括太子及其母弟。 第四,盟禮順應臣的利益,而限制君的權力。 以臣抗君,臣勝,君敗。 君臣博弈之后,君臣關系導向盟禮并交質子,這是臣子的勝利。
君臣盟禮意味著君權的失落。 君臣原本尊卑不對等,盟禮降低君的地位與臣實行“亢禮”“敵禮”,這與西周王室設立的盟禮并不合拍。 漢代古文經學家認為周禮本有盟禮的設置。 許慎《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于禮得盟。 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36]孫詒讓認為:“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37]許慎、鄭玄等人支持《左傳》古義,認為“太平之時即有盟禮”,大抵指西周君臣秩序井然之時,“凡國有疑”則盟。 《玉篇·子部》:“疑,嫌也。”[38]《一切經音義》:“疑,貳也。”[39]盟禮藉助神權,解決周王室與諸侯之間的“猜疑”“嫌隙”。 彼時,周天子具有宗族、宗教等意義上的絕對威權,周天子的世俗王權能亦能確保盟辭的應驗,盟禮能使君臣回歸原有秩序。 漢代今文經學認為上古無盟禮而春秋有盟禮,霸主在則無交質子,亦指出交質子伴隨權力衰微而出現。 《春秋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40]《春秋穀梁傳》隱公八年:“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41]“五帝”“三王”指傳說中的上古時期,人言為信,不行盟禮;“二伯”指齊桓、晉文所處的春秋時期,人們行誥誓、盟詛,藉鬼神鞏固人言之信;天下無霸,則至于交質子。 王充《論衡·自然》征引今文經說:“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改《穀梁傳》“二伯”為“五伯”,其意仍是擁有霸權的諸侯。 孫盛注:“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于周微。”[42]也認為君王無強權,亦無強權(霸主)替代的時候,就會出現盟禮交質子的現象。
君臣交質亦意味著君王神權的失落。 春秋伊始,周天子用盟禮加質子的方式向鄭國表明自己沒有沒有貳心;宋元公在被劫持的狀況下,與華氏盟,故君臣盟禮,人君或多或少有被脅迫的意思,即所謂“要盟”。 臣子強迫君盟,卻不大相信鬼神,因為臣本身并不具備神權,所以就不依賴神權,轉而要求“交質”,以人為抵押,所謂“質之為言信也。 要盟無信,于是以人為質。”[43]盟禮而交質,君王依賴鬼神對人實施的約束減弱了,君王的神權也就被打破了。
春秋時期,交質不盡是交換嫡子。 文公十七年晉鄭交質,晉國一方,趙穿、晉侯女婿公婿池為質,鄭國則太子夷、大夫石楚為質。 與鄭太子夷對等的是晉卿趙穿。 大國質卿而小國質太子,交質子變而為一方質卿大夫,體現出權力的不對等,亦是盟禮交質擴大化的表征。 而盟禮單方面出質,往往系卑弱者所為,也是權力不對等的反映。
侯外廬認為:“春秋霸主的盟約還有其相對的神圣性,而戰國諸侯的‘人質'便成了危機的標幟了。”[44]春秋時期的盟禮有鬼神參與,固然有其神圣性,但春秋時期盟禮之外已交質,信用危機即已開啟。 《左傳》君子曰推崇并維護盟禮中的神權,要求重建人神之信與人言之信,重回盟禮的本真。 君子曰強調盟禮之“信”,是在信用危機的時代里,重建“信”的信仰。
3 君子曰引《詩》重“信”之義
隱公三年君子曰引詩之義,歷來富有爭議。清代左傳學評點著作,如金圣嘆《左傳釋》、馮李驊《左繡》,都發現了隱公三年《左傳》君子曰引詩的怪異,其結構與全書體例頗為不合。 馮李驊《左繡》:“《左氏》引詩,大都先點而后注,此獨先注而后點;又直寫本文居多,此獨撮舉大意,蓋點化之妙,此為第一矣。”[45]通觀《左傳》全篇,君子曰的格式大多先點明主題,再引《詩》來論證,此即“先點后注”;而此處的君子曰卻是先引《詩》,而后點明主旨,此即“先注后點”。 加之《左傳》引《詩》一般直接稱引詩句,而此處卻概括大義。這是此篇君子曰引詩的特異之處。 遺憾的是,馮李驊沒有繼續探究君子曰“撮舉之義”來自何處,故不能由《詩》入手,分析君子曰的主題,不了解“忠信”的涵義。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謂《左傳》引《詩》“不必盡依本旨”,[46]也是說引《詩》之旨與“忠信”無關。 引《詩》而無關主旨,那又為何引《詩》? 這種觀點必然存在認識上的歧誤。 本文認為,《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標舉《詩經》四篇篇目,詩義統攝在“忠信”二字之內。君子曰用《詩》之義,與《毛詩》之義相通。
君子曰征引的《采蘩》《采蘋》《行葦》《泂酌》四詩,都與“忠信”相關。 此“忠信”之義,與《毛傳》、《詩》小序之義相通,取自春秋時期的共同知識庫。 《采蘩》毛傳:“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之草,猶可以薦。”意謂祭祀之人有“信”之德,故祭祀以薄物而神饗之。 君子曰以“薄物”為紐帶,將《采蘩》《采蘋》的“沼沚溪澗之草”和《泂酌》中的“橫汙行潦之水”引申至“信”之義,而與《毛傳》相通。 君子曰又從《行葦》文本出發,由宴樂兄弟,得“忠”之義,與《詩》小序相通:“《行葦》,忠厚也。”簡言之,君子曰征引《采蘩》《采蘋》《泂酌》等三首詩,用其“信”之義;征引《行葦》,用其“忠”之義。 對此,筆者有專門論述,[47]在此不再贅述。
君子曰征引的四首詩皆關乎祭祀。 盟禮與祭祀有相似之處,二者皆為人與鬼神的對話,對話的實質就是人和神之間的禮物交換。 祭祀物品越豐富,鬼神的回贈愈豐厚,物品與回贈是正比的關系。 只不過祭祀希冀鬼神的回贈,盟禮借重鬼神的懲罰。 回贈和懲罰,均為鬼神之職責。君子曰征引四詩,皆與祭祀鬼神相關,引詩人相信,即便提供的祭祀飲食微薄,鬼神亦能慷慨饋贈。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祭祀提供了與鬼神“慷慨饋贈”相對等的“信”。 同理,希望鬼神施加懲罰,也要送上禮物;如果人內心有人神之“信”,則無需貴重的禮物,鬼神也能助人得償得愿。 祈求鬼神施罰,與祈求鬼神回贈一樣,提供的祭祀飲食可以微薄,只不過特別需要以“信”作為祭品。盟禮交質,卻反其道而行之。 當事人缺少人神之“信”,卻以“人”為質,當作祭祀鬼神的附帶條件,加重祭祀鬼神的籌碼。 君子曰借祭祀以論盟禮,因為盟禮和祭祀一樣,都講求人神之“信”。
如前所說,君子曰欲發明之義為“信”,此“信”字在開篇第一字上,而在君子曰的末尾,卻變成了“忠信”,似乎有跑題之嫌。 其實未必。“忠信”不是一個詞語,而是“忠”和“信”的組合,“忠”特意針對周鄭交質的“質”。 “忠”之義來自《行葦》之詩,為春秋亂世提供了兄弟燕飲、比射的歡樂場景,這算是從正面闡述了兄弟之間的正確相處之道:以燕禮宴樂之,而非“交質”以換取安樂。 可以說,二國之間有“忠”,便不會有“交質”的事情發生。 與現實中盟禮“交質”不一樣的是,君子曰提出盟禮加“忠”的模式。 二國之間用人神之信約束,又用宴樂交好,可以確保兩國關系不脫離正軌。
隱公三年君子曰終篇論述的“信”,否定、壓制了“質”;而結句言“忠信”,則用燕禮代替了“質”,在二國盟禮之外,拓展出兄弟交接的燕禮來。 君子曰由周鄭交質事件引申出來的,便是重建盟禮,輔以燕禮,這也就是君子曰所發明之義。二國交接,除了盟禮的人神之“信”之外,還當有兄弟交接之“忠”。 周、鄭兩國是兄弟之國,既有盟禮,也當有燕禮,方為全面。 “忠”是“信”的拓展,而非“信”的反面。
周鄭交質這一事件表明,周天子的神權、王權盡失,受制于諸侯。 周鄭交質未能阻止周鄭交惡,盟禮交質不能挽救“信”的危機。 《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認為唯有回歸人神之信,方能有人言之信;唯有重建盟禮中的鬼神信仰,方能挽救“信”的危機。 《左傳》君子曰的嘉言懿語,將道義禮信置于富強攻取之上,其風流文雅,為后世所向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