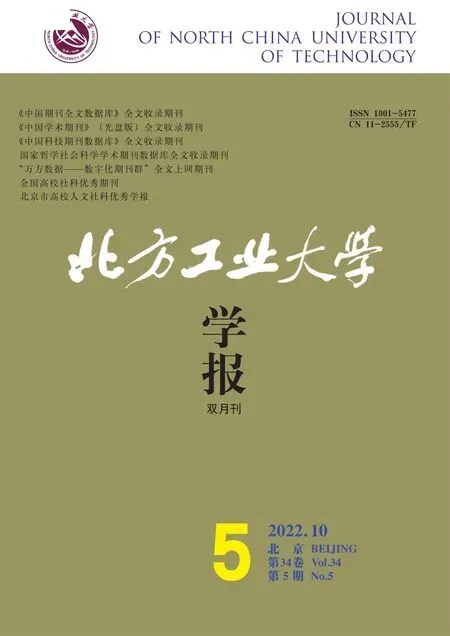戲影晏然*
——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審美探微
李小剛
(運城學院中文系,044000,運城)
元代劇作家關漢卿創作的元雜劇《竇娥冤》首次面世于1582 年,被譽為元曲第一。 該劇是一部泣血而歌、為民而書的大悲劇,同時也是一部典型的公案劇。 該劇被王國維盛贊為最有悲劇性者之首,“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1]全劇以孤寡婆媳的悲慘命運為起點,通過敘述竇娥之含冤負屈直至屈死的過程,揭露了封建社會官場的腐朽黑暗。 《竇娥冤》作為“曲圣”關漢卿的代表作、中國悲劇文學的集大成者,具有極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曾被諸多地方劇種移植改編,諸如京劇、評劇、豫劇、越劇、滇劇、徽劇、漢劇、黃梅戲、昆劇、秦腔、同州梆子、粵劇、湘劇、滬劇、莆仙戲、川劇、湖南花鼓戲、河北梆子、臺灣歌仔戲、上黨梆子、蒲劇等,亦成為歌劇、話劇和影視爭相改編的對象,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改編態勢。[2]其中又以蒲劇版《竇娥冤》于1959 年率先被改編為電影,蒲劇版《竇娥冤》是中國首部蒲劇電影,一經上映轟動全國。 因為成功的改編而得到市場的廣泛歡迎,故于1997 年、2020 年兩度再次被改編。
1959 年由張辛實執導,王秀蘭、閻逢春、楊虎山、莜月來等著名蒲劇演員主演、長春電影制片廠出品的彩色蒲劇電影《竇娥冤》的面世,是元雜劇《竇娥冤》首度被改編成為蒲劇電影,1959 年版蒲劇電影《竇娥冤》一經上映便受到了廣泛關注,成為了時年山西戲曲電影的一張名片,故在1997 年再度被改編成蒲劇版電影,而2020 年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則是在1997 版的基礎上改編而成,該片亮相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戲曲電影展映單元。
2020 年版《竇娥冤》沿用同名戲曲蒲劇班底,由著名蒲劇表演藝術家景雪變、郭澤民、閻雅珍聯袂領銜主演,在文學底本、唱腔和音樂設計上都基本遵循蒲劇版原著,尤其是敘事模式以及在結構故事情節、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主題思想和處理戲劇結局等方面與蒲劇《竇娥冤》基本一致,充分尊重了戲曲舞臺呈現的敘事框架,較好地呈現了舞臺藝術的完整性。 同時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將電影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與蒲劇特有的舞臺藝術魅力完美整合,實現了新時代電影技術與中華優秀傳統蒲劇文化的完美對接、深度碰撞融合,有效地完成了以傳統審美為范則的視覺奇觀。
1 虛擬與真實:場景、唱腔與鑼鼓點的改編
1.1 場景的“虛”“實”處理
戲曲是運用舞臺布景、音樂伴奏及歌舞化、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完成表演藝術、塑造人物形象的一門綜合性藝術,以其豐富的“虛實相生”的表演程式來表現宇宙萬物。[3]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戲曲藝術承載著中國人的思維方法、人生經驗以及哲理思考,同時也反映著中國人的文化、生活、思想和情趣,它天然地攜帶著中國傳統美學的精神追求,而虛實相生正是中國哲學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美學特質。 戲曲舞臺的場景設置就踐行了這一美學特點,延續了寫意的布景設置方式,多采用“一桌二椅”形式。 舞臺之上的“一桌二椅”在表現赴宴、坐帳的戲劇場面中,它們呈現出的就是桌椅的實存狀態;但在戲曲舞臺上桌椅也常以變形的虛擬手法來指代臥榻、洞口、山坡之類的寫實場景。一切皆是以“虛”造“實”,“因心造境”,將中國戲曲虛擬表演和舞臺時空創造相融合,亦為“有生于無”的宇宙認識論到“虛實相生”的藝術創造的美學原則體現。 “虛實相生”是戲曲藝術的重要表現手段,戲曲場景的設置不能不考慮“虛實相生”的美學規律。[4]因此,“一桌二椅”不僅僅是舞臺上的具體實物,它更是一種精神,一種理念,是一種符號化的呈現方式。 故中國傳統戲曲最為顯著的藝術特征是虛擬性、程式化和綜合性。而對于虛擬來說,既是戲曲反映生活和創造舞臺形象的基本舞臺表現手法,也是一種“夸張甚至是變形手法”,“戲曲的變形和生活的原型”距離較大,主要借助于虛擬手法來“拉近”彼此的距離。[5]囿于中國傳統美學觀的影響,戲曲在“處理藝術與生活的關系時,不是一味追求形似,而是極力追求神似”。[6]由于戲曲的動作是虛擬寫意的,戲曲虛擬手法更重視神似,其要義是變形美觀,以身體作材料來“寫”世界,以“虛”為真,眼見“想”真,因此就遠離了寫實派的路子,不把舞臺藝術單純作為模仿生活的手段,而是強調演戲是對生活的虛擬,是作為剖析生活本質的一種武器。[7]事實上,戲曲藝術對于虛擬手法的創造性應用,突出地體現在場景的“虛”“實”處理方面,尤其體現在虛擬手法所追求的“對舞臺時間和空間處理的靈活性”上。[8]再比如在同一戲劇情境中,相較于真實生活,戲曲表演藝術通過對虛擬這一獨特藝術表現手法“活”的應用,亦即通過虛擬表演或唱念來實現時間或空間的變化——時間的壓縮、延伸和空間的重疊、轉換。 諸如打個盹即可表示“時間跨越幾十年”,跑一個圓場就代表著“人行千里路”,來一個趟馬就象征著“馬過萬重山”,這是戲曲舞臺“虛擬時空”的美學特征與觀眾審美聯想的契合。 再有以開門關門、上樓下樓、行船走馬、翻山越嶺、兩軍對陣對峙等一系列的虛擬舞蹈動作來激發調動觀者的聯想想象,從而創造出特定戲劇情境中的特定舞臺形象,且這種被廣泛使用的虛擬表現手法經過高度提煉升華最終以戲曲身段、動作程式固定下來,讓觀者獲得藝術享受、審美感受,產生審美評價。[9]誠如費穆對戲曲中“虛”“實”辯證關系切中肯綮地論述:“演員的藝術與觀眾的心理必須互相融會、共鳴,才能了解,倘使演員全無藝術上的修養,觀眾又缺乏理解力,那就是一群傻子看瘋子演傀儡戲,也就等于一幅幼稚的中國畫,水墨淋漓,一塌糊涂,既不寫實,又不寫意,完全要不得了。”[10]所以,戲曲演出形式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虛擬性、寫意性,亦即在特定的戲劇情境中,借助演員虛擬性、程式化的舞臺表演來創造戲劇性,激發調動觀眾的聯想、想象,從而完成舞臺形象的創造。但是如果在舞臺上進行實景演出,演員的表演空間勢必會受到擠壓,一定程度上必然會降低戲曲所著力表現的程式美和營造的意境美。 而戲曲電影所要表現的對象,是具有舞臺假定性的藝術樣態,要實現舞臺同銀幕的完美融合,就是要“以影就戲”,以實寫“虛”,實現戲曲敘事原則下的電影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用虛擬性、程式化的表演來展開敘事、層層推動演出節奏向高潮發展,將戲劇性從布景推及到演員以實現人物形象的塑造,將戲劇表演舞臺的“向心性”與銀幕空間的“離心性”完美結合、有效契合,才能達致這兩種藝術形式在表達方式上的融合式統一。[11]
綜上所述,虛實相生、虛實結合是戲曲電影生成的法則和哲學基礎,也是戲曲電影的重要表現手段,戲曲與電影聯姻的可能性,也就是戲曲電影虛實相生的哲學可能性。 而虛實相生相互滲透、轉化的路徑也就是戲與影的辯證法。 戲曲是虛,戲曲的動作是虛,念白是虛,鑼鼓點節奏是虛,戲曲的虛擬性表演是虛, 表演的技藝性是虛,“虛”是舞臺對生活的“虛”,是對生活的高度提煉與嚴格規范。 因之,高度提煉和嚴格規范的“虛”是藝術意義上的“虛”,是舞臺化的“虛”。一定程度上,此處的“虛”是一種代指,而非“有無”的“虛”,時空意義上的“虛”。 與此同時,戲曲電影必須建立在戲曲程式之上,“戲曲電影是戲曲與電影這兩種不同藝術形式的內部融合,這種結合并不是誰代替誰的問題”,但卻“主要應該是電影服從戲曲”。 “電影要服從戲曲,不能離開戲曲這個基礎,既要保持舞臺風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要打破舞臺框框。 要利用電影藝術的表現手段,諸如電影實的影像、對白、故事性節奏、生活態表演以及表演的生活性,更加發揮戲曲藝術的特點,力求將“虛”與“實”在影像中銜接起來,做到有虛有實,虛實結合、情景交融、優美動人。”
有鑒于此,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中大量采用了半實半虛的場景設置,“景”在演員身上,所謂:“柳枝西出葉向東,此非畫柳實畫風。 風無本質不上筆,巧借柳枝相形容。”[12]以戲曲程式來表現情感,將演員的虛擬程式動作與人物情感的發展渾然一體,最大限度地彰顯中國戲曲舞臺表演的美學原則和表現人物的心情。 如“竇娥行刑前劊子手推推搡搡帶她游街示眾”的場面,以人物一系列的舞臺程式動作來模擬再現竇娥被他們推得前合后偃、東倒西歪的現實慘況,尤其是翻跟斗之后的跪立一式,折射出的是劊子手的冷酷無情、兇殘暴戾。 同時還有“對竇娥用刑逼供”一段,同樣是以戲曲舞臺程式動作來展現嚴刑逼供直至屈招的場景,通過一系列看似唯美的舞臺程式化身段動作,將竇娥被毒刑拷打下的筋骨皆斷、痛不欲生以及縣衙官吏的心狠手辣、慘無人性甚至古代刑罰的野蠻森冷、殘忍至極表現得淋漓盡致,加上觀眾的聯想想象來完成藝術的創造,以一種半實半虛的畫面設計來展示一種藝術的真實,并將這種虛實結合提升到了至高至純的境界。 一方面通過景別的變換來表現主人公竇娥所處地理位置及活動場景的全貌、戲劇場面的大小、人物之間的關系,進而透視主人公多重復雜的心理空間,傳達人物在動作程式下隱藏的情緒。 客觀上通過電影紀實功能,直觀地呈現人物的心理狀態;另一方面又給角色留足了展現戲曲程式之美的表演空間以彰顯戲曲舞臺的場面感,在時空處理上體現著極大的自由性與假定性,將傳統戲曲程式化的審美特征、寫意性的審美追求和電影藝術寫實性的整體審美取向達致完美融合融通,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實現有限之中的無限、戲曲與電影的“共贏”,實現在形式的完整性上、藝術的共通性上合二為一,[13]以突破有限的形象來揭示事物的本質,造就氣韻生動的神妙藝境。
另外,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除保留了蒲劇本身的藝術魅力之外,還充分利用電影長于表現空間形象的特征,在“買藥”和“探獄”等場景的敘述中,將原劇中各個情節點進行寫實化的情景再現,如藥店、柜臺、牢房、牢房通道、獄門等,有別于原劇,竇娥在不同空間場景的唱詞在真實可感的環境中,其悲愴的戲劇效果更強。 情景交融的形式使得從未接觸過原著的觀眾更易于理解,細膩而真實的場景設計,提供了更多的敘事信息,進而打破觀影區隔,使得不同年齡的受眾均可理解故事內容。 綜上所述,改編后的電影中豐富的道具與實景的陳設,既豐富影片空間想象的同時又做到了有機銜接,使得戲曲的寫意性和電影的寫實性得到了最佳的融合,讓觀眾既看到了傳統藝術的美,又獲得了迥異于舞臺版的藝術體驗。
1.2 唱腔與鑼鼓點的“虛”“實”處理
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基本原封不動地保持蒲劇的唱腔、方言、韻白、鑼鼓點以及景派的表演藝術風格,最大限度地存留傳統蒲劇唱腔曲調的“舞臺味”和“蒲韻精華”,以達到昭顯蒲劇唱腔、絕技和景派藝術的目的。 如竇娥在毀滅前情感大爆發,臨刑前指斥天地發下三樁狠誓的場景中,在生命行將終結的法場上,在“浮云為我陰,悲風為我旋”的精神不死的自由歌唱中,竇娥唱得是蕩氣回腸、氣勢磅礴,慷慨激昂的精華唱段,字字珠璣的憤激之辭,高亢激昂鏗鏘有力形神兼備的梆子唱腔,于無形之中透露出的是演員扎實而又深厚的蒲劇演唱功底;折射出的是竇娥斥責貪官枉法的氣魄,敢于反抗邪惡勢力的韌性抗暴精神,舍己為婆蹈湯赴火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和人性光芒,她至死不屈的決心和拼死抗暴的意志行動是對世道蒼生一種下意識的擔當;體現出的是其時吏治的殘酷黑暗和如竇娥般冤屈的被壓迫勞動人民的慘痛遭遇和悲劇命運,以及感天動地的悲劇藝術效果。
2 靜止與運動:電影的鏡頭呈現
古老而傳統的戲曲藝術憑藉精彩絕倫的舞臺呈現來彰顯一種宏觀的藝術魅力和獨特張力,在戲曲藝術的觀演關系當中,如果把觀者的眼睛比作鏡頭,那么舞臺全貌盡收眼底。 在賞析戲曲經典的過程中,觀眾可根據個人喜好及舞臺呈現的吸睛之處,隨時切換自己的聚焦點,但鏡框式舞臺呈現永遠是自我的聚焦視點。[14]而戲曲電影(戲曲片)是中國民族戲曲與電影藝術結合的一個片種,亦即戲曲與電影的合體,將戲曲藝術表現手段與電影藝術表現手段結合起來,使之兼備二者之長。[15]主要依據戲曲本質及導演創作目的,將一幕幕精彩紛呈的場景呈現于銀幕之前,從觀眾的觀影角度來說,無需進行主觀選擇卻可以更直觀形象地享受戲曲與電影的視聽盛宴。
戲曲之妙妙在唱腔,美在身段。 要將戲曲美妙而又韻味十足的唱腔、絕美優雅的身段與人物紛繁交織的情感分毫不差地呈現在銀幕之上,這就需要將戲曲唯美的沉浸式舞臺全景與電影技術加以糅合,實現靜止鏡頭與運動鏡頭的有機組接。 誠如高小健先生在《戲曲電影藝術論》中曾經指出,把戲曲從舞臺形態轉化為銀幕形態的作用機制是鏡頭,“戲曲電影的以鏡頭為基本敘事審美單位的概念中,應該也包含著戲曲舞臺敘事審美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和精神,這樣的戲曲藝術片的審美才是一種綜合性的審美,同時也是一種不同于單純的戲曲審美和電影審美的新審美”。[16]
在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中,導演和攝影師根據戲劇場面所要表現的內容,合理安排機位和搭配鏡頭的遠近虛實,在靜止中“精雕細刻”力求逼真展現人物個性,在行動中呈現人物的性格和情感。 如在對竇娥進行“嚴刑逼供”、竇娥“質天問地”及臨刑前“蔡婆前來一祭婆媳對唱”到最后“發下三樁誓愿”等的場景中,就采用鏡頭推進的方式,呈現較多的面部大特寫高清鏡頭以突出人物豐富復雜而又深沉細膩的表情神態,呈現悲壯激越的情感波瀾。 影片中演員五味雜陳的情緒表演,既要表演感情,還要保持“形式美”,更要符合戲曲的“詩化”審美節奏,以表現昏官的屈判枉斷毫無人性大施酷刑,重刑之下竇娥十指連心、肝腸痛斷;竇娥斥天問地時,通過面部表情特寫的豐富變化展現對天地的聲聲質問,向靜默遼闊的大自然哭訴枉陷冤獄的內斂無聲、不威而自怒的憤,表達蒙冤抱屈的無奈以及對昏官咬牙切齒的控訴和批判、自我的心有不甘但又無可奈何的窘境。 在刑場喋血含冤就死前,竇娥發下三樁毒誓的場景中,運用特寫及近景鏡頭的同時,通過長鏡頭的調度方式,既將演員豐富的表演細節得以具現,傳遞出明確的情緒表達,又保證了影像的連貫性,使得觀眾充分體驗影片的魅力和演員既保持“形式美”又觀照戲曲“詩化”審美節奏的情緒表演,具有極強的臨場感。 該段竇娥的唱段慷慨激昂,唱詞字字珠璣膾炙人口,唱腔鏗鏘有力,唱得蕩氣回腸、氣勢磅礴,將一腔怨氣如火般噴出,啼鵑泣血沖天喊出自己的奇恥大冤,借助鏡頭的景別變幻,增強視覺沖擊力、聽覺震撼力和情感感染力,使得受眾感受到高亢激越的唱腔唱段之美、體味唱腔的悲劇化呈現。
除了敘事性鏡頭的設計,在影片中還有部分鏡頭極具主觀性。 如在“赤地痛裂旱三年”的場景中,通過搖鏡頭具象地呈現旱地景觀,其中包括:地面肌理、灌木荒野、枯枝碎木等。 并以疊畫的形式,將不同旱地景觀進行并置,不斷地疊畫使用營造出連續不斷的視覺觀感。 這一系列鏡頭的使用,為“赤地痛裂旱三年”的臺詞描述進行了具象畫面的補充,客觀地呈現了水土之干涸、環境之惡劣,更加清晰地呈現了竇娥冤情之深,使受眾對竇娥的不公命運產生憐憫。 除此之外,這一組鏡頭的設計,也可視為作為亡魂的竇娥對自己所發出的誓愿的一種巡禮,以全知視角為開端到平角為結束,也是竇娥從游魂回到人間的歷程,故影片接下來就是竇娥幻境中向父親陳述自己的冤情,而這一組鏡頭亦可視為竇娥的主觀視角畫面。
再有,影片還充分利用電影鏡頭視點位移技巧,通過反復打破畫面水平的方式不斷地制造傾斜運動,利用快速的循環傾斜運動模擬人物異常的身體狀態,形成具有真實可感的主觀視覺體驗。 如張驢父親陰差陽錯喝了羊肚兒湯“嗚呼身死”前暈頭轉向的眩暈場景;竇娥在衙門對簿公堂之際遭受“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的嚴刑拷打,被折磨得眼發黑頭發昏天旋地轉的時候,出現的“公堂見官”眩暈場面。 改編后電影《竇娥冤》通過靈活的鏡頭與自由組接方式,打破戲曲舞臺的空間限制,最大限度地實現場景的變動不居。
3 夢幻與現實:蒙太奇手法的運用
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巧妙融合電影語言,利用電影平行、交叉、類比等諸多敘事蒙太奇手法,通過交叉剪接將電影語言與戲曲舞臺表演完美融合,使得戲曲舞臺表演的藝術性、表現力大幅提升,最終完成現實空間與夢幻空間兩個迥然相異的敘事表意空間的自然轉換。 影片將兼具表現效果和敘事功能的戲曲舞臺表演和觀眾熟知的現實片段完美穿插,將現實內容與夢幻內容充分融合,實現夢幻與現實的交互對接、有機互動,最終達致渾然天成,加強敘事節奏和情感張力的同時,讓觀眾知悉體悟劇情發展動態、享受一場視聽與光影的盛宴。 具體體現在蔡婆跟著賽盧醫去討債的場景中,就是使用電影蒙太奇的內在邏輯來加速畫面的切換,將唱腔內容通過鏡頭畫面的變化實現視覺化、形象化,“活”的畫面,符合觀眾對戲曲電影視覺形象的審美需求。 再如竇娥被枉殺后,竇天章父女“夢中陰陽相會”訴冤的場景中,尤其是身為鬼魂的竇娥在如幻似夢的幻境中現身山陽縣衙與父親相會之際,竇娥突破“陰陽相隔”的壁壘,由陰間回到陽間,一邊向老父說明事實真相、提供線索,一邊以強烈的水袖舞動作抒發內心情緒。 誠如顧春芳所言“戲曲表演是生命情致的在場呈現,它所呈現的是心靈世界的摹本”。[17]竇娥以一襲約七尺長的白練式的水袖左右飄舞、上下翻騰,以水袖花、雙沖袖和雙上沖水袖花等一系列水袖舞這一“離形得似”的手段和戲曲絕活的程式化表演,將她涌泉般的思父之情和怒不可遏的悲憤之情以強烈的水袖舞程式化表演氣韻生動地外化出來,她的表演唱做俱佳、技驚四座,將蒲劇的高亢激越、人物的剛烈鏗鏘表現得痛快淋漓,取得迥異于舞臺版的藝術體驗與效果。 影片運用各種電影化手法與鏡頭語言(長焦、近景、特寫、長鏡頭等),將水袖舞的精彩表演凸顯出來,做到“實中有虛”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存戲曲傳統精華,并將水袖舞表演這一傳統戲曲絕活,完完整整地用光的影像保留和“光大”。 另外,竇娥向老父細述“赴泉臺”之因時以大段優美唱腔訴衷腸,極大地增強了影片對觀眾的吸引力,同時慷慨激昂而又感人肺腑的唱段,將她的激越情緒、滿腔悲憤、感天動地的冤屈酣暢淋漓地宣泄出來,將她滿腹整腔屈冤與上揚袖、水袖花和下沖袖等水袖表演及身段唱腔糅合起來,將水袖技巧化入情感之中,將情感現于水袖之功,形神兼備動靜結合,賦予水袖極強的“語言性”,蒲劇唱念做打的程式身段之美、手法唱腔之美和巨細靡遺的舞臺呈現給人以悲美的視聽享受,極大地增強了竇娥人物形象的感染力,增強了電影的藝術表現力,完成蒲劇舞臺風格和電影影像風格的深度融合,完美達致電影蒙太奇手法化用于充滿戲劇性和張力的戲曲舞臺精彩演繹之中,實現夢幻與現實之間的聯動和穿越,達到氣韻生動傳神寫照的境界,創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充分彰顯了演員的“手法身段”“唱腔程式”之美。
4 戲影聯動:表演形式的改編
傳統戲曲的程式化表演是以“虛”作“真”,電影的鏡頭運用則是以“實”作“真”,前者是以身體作材料來“寫”世界,后者卻是以鏡頭為基本敘事單位的藝術形式,以鏡頭來“藝術”地記錄世界。 從理論上來說,戲曲強調演戲是對生活的虛擬——舞臺造型,電影追求的則是生活本身的再現——影像再現。 而戲曲電影作為中國特有的電影類型,是東方美學的天然代表。 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戲曲電影作為東方奇觀再度崛起,這一全新藝術樣式的“第二春”再次到來。 在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中,戲曲與電影這兩種有著殊異美學追求和審美原則的藝術形式,不是“戲曲+電影”的簡單疊加,而是戲曲特性與電影表達藝術相互聯動激發碰撞,實現戲曲寫意風格和戲曲美學與電影藝術的寫實風格和電影美學的共融,兩者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最大限度地達成傳統與現代雙重藝術形態之間的互動,著力探索調和中國美學范式的全新配方。
在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中運用全景、近景、特寫鏡頭以及蒙太奇等電影手段,采用分鏡頭的選擇、把控、運用和組接等方式,以及電影化的鏡頭調度和動作剪輯拼接,將蒲劇演員的舞臺表現分為若干個鏡頭,通過光影切換和鏡頭語言的巧妙運用從多角度將竇娥婆媳的面部表情、身段等“完整”地展現在銀幕上,同時通過鏡頭內外部運動、后期剪輯、特技合成等手段將電影鏡頭和戲曲內涵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創造出有別于“日常生活”的視覺體驗,實現電影藝術的魅力與戲曲藝術的魅力珠聯璧合,讓戲曲與電影這兩種藝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給人以視覺和聽覺的雙重審美體驗和愉悅。[18]
除了追求演員本身的高質量表演之外,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的導演還巧妙地將電影的敘事框架、敘事結構、故事情節和場面與蒲劇的劇本安排做了巧妙融合,將情節的發現突轉集中到撼人心魄的特殊時間段,給觀眾以更猛烈的視聽覺沖擊。 而一場由蒲劇演員的表演,唱腔、對白、身段,以及演員的功法撐起的戲曲表演藝術,借助電影導演的美化加工而成為戲曲電影,賦予其戲影晏然的精神氣質,而其藝術價值與美學價值亦自不言而喻。
總之,戲曲電影畢竟是人類藝術史上的一個“創新”——一種最傳統而又古老的表演藝術與一個最現代的大眾化的電子藝術的結合,兩種藝術的融合是人類對藝術的一次創造性大膽探索,是探索突破藝術的分類原則后的一種藝術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是開創了人類藝術史的新篇章。它還原和再現的并非客觀現實時空,而是一種具有超現實特性的審美空間。[19]
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寫意風格和電影的純寫實特征集于一身,在最大限度地保留蒲劇藝術獨特唯美的表意特征的基礎上,實現電影銀幕展示的最大化,亦即將戲曲的“空靈與寫意”和電影的“技術與寫實”進行了深度融合,使整部影片都浸透在傳統文化的審美之中。 它的成功,有賴于蒲劇舞臺藝術和電影藝術表現形式的合理調和,有賴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蒲劇自身藝術門類的邊界,把構成蒲劇的基本要素從戲曲框架中剝離出來,與電影藝術的元素混搭、疊加直至完成深度跨界融合,將蒲劇融入現代文化,讓蒲劇蘊含的美完整地呈現在銀幕之上,將傳統性與現代性相結合,有效克服“戲曲”與“電影”的融合度問題的同時用電影的視聽語言升華蒲劇藝術的舞臺效果,體現出恢弘雋永的影片氣質,終而達到解剖人性與社會、關注現實又深入社會的本質目的。 同時,新版蒲劇電影《竇娥冤》的全新推出是電影與戲曲有機結合的產物,使得銀幕成為戲曲美學的新載體,對電影和蒲劇這兩種藝術樣式來說是一個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的過程,使得兩種藝術的美被融合、被發現、被延展,兩者相得益彰幾無違和之感,影傳戲唱、戲助影播,從而獲得更加深遠的文化意義。中國戲曲電影由于傳統戲曲的介入而形成自我獨特的電影類型,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又一藝術觀賞樣式,鑄就非凡的光影之夢的同時有可能掀起中國戲曲電影的新浪潮;而極具“詩化美”的傳統蒲劇藝術借助電影這一綜合的現代科技與藝術得以記錄并廣泛傳播,憑借現代技術傳承傳播傳統蒲劇文化的平臺與途徑,擴展蒲劇受眾群的同時有效助推了蒲劇在全球范圍內的流播,對保護傳承弘揚傳統蒲劇文化,促進蒲劇事業繁榮發展,對催發蒲劇藝術活動煥發新時代光華,對蒲韻越悠長、常飄香、永流芳都是大有裨益的。一如梅蘭芳所言:“一個演員就是消磨了終身的歲月,也不能夠周游中國境內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來表演他的藝術,這回卻可以利用西方新式的機械,拍成有聲的影片,把中國世代積累下來的藝術,傳遍遐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