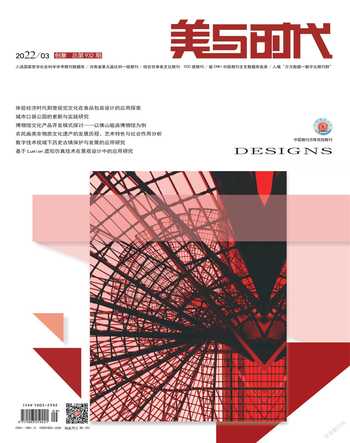重慶地區蜀繡視覺表現的創新探索
摘? 要:重慶地區的蜀繡作為蜀繡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分支,不僅有傳統蜀繡所具有的針腳整齊、片線光亮、緊密柔和的特點;而且還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綻放出獨特的山城文化藝術魅力。通過文獻法和訪談法,考察重慶地區蜀繡視覺表現的現狀,并且分析其主要存在的構圖單一、書畫內容晦澀難懂的問題,嘗試通過多種形式構圖、形色結合以及將時空與意念相結合的的方式來進行創新表達。
關鍵詞:重慶地區;蜀繡;視覺表現;創新探索
重慶地區蜀繡在“戰時陪都”、挑花刺繡廠和正則藝專的影響下,成為蜀繡傳承與發展一個重要的分支。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也逐漸發展出濃郁的地域特色。
一、重慶地區蜀繡簡介
蜀繡在清代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發展達到極盛。重慶作為四川地區的第二大經濟體(在1997年成為直轄市之前),自然而然也造就了蜀繡在重慶地區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商品繡的崛起,以及蜀繡行業的出現,無不激發著工匠不斷創新。
重慶因其優越的地勢地貌條件,在1937年11月到1946年5月這八年半的時間里一直作為中國的“戰時首都”,這在某種程度上極大地促進了重慶地區蜀繡的發展。此外,藝術教育家呂鳳子先生創辦的正則藝專于1937年西遷至重慶璧山,其繪繡科的招生教學對重慶地區蜀繡的發展也頗有影響。
解放后,1990年10月4日,重慶挑花刺繡廠成立,召集了一大批優秀的蜀繡工藝家到廠指導教學,開展刺繡工作。它的成立不僅成為當時重慶蜀繡的主要集中地,也極大地推動了重慶地區蜀繡的發展。
重慶地區的蜀繡作為蜀繡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分支,不僅有傳統蜀繡所具有的針腳整齊、片線光亮、緊密柔和的特點,而且還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綻放出獨特的山城文化藝術魅力,其代表性人物有康寧、黃敏、閆永霞等人。通過他們的研習傳承和發展,重慶地區的蜀繡在技法上新增了具有特色的雙扣針針法,并且還融入了蘇繡亂針繡的針法;在材料上加入了傳統的夏布材料和現代新式材料如皮革、PVC等;生產制作方式也兼具傳統的人工刺繡和機械刺繡。重慶地區的蜀繡在針法、題材、載體、工藝等方面,表達了重慶人對于生活的熱愛和不畏艱險勇于拼搏的文化精神,傳承的同時加以創新,也豐富了它原有的定義,使其更具有地區性、時代性和實用性。
二、重慶地區蜀繡視覺表現的現狀及問題
(一)視覺表現
“表現”從狹義的角度來說是指透過某人外貌和行為中的某些特征,對其內在情感、思想和動機進行把握的活動。正如阿恩海姆在他的書中寫到的“每一件藝術品,都必須表現某種東西”,這種東西既可以具體而微,也可以浩瀚無垠。即是說視覺表現具有相對性。它的狹窄性表現為:沒有將不表現內在精神活動的表現和行為包含在內;而它的廣泛性表現為:它把理性從藝術形式中間接推斷出來的東西包括在內。任何事物都具有表現性,所以表現性自然而然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外部表現性甚至在我們的知覺活動中占據著優先地位。
“視覺表現”往往是人們通過知覺對象本身的性質,由這些性質在觀看者的神經系統中所喚起的力量傳遞。視覺表現可以將外在的東西和內在的東西相聯系起來。貝克萊在他的《新視覺論》一書中講道:“我們之所以能夠從變化中看到情感,是因為它們在我們的經驗中總是伴隨著情感一起出現,如果預先沒有這樣一些經驗,我們就分不清臉紅究竟是羞愧還是興奮的表現。”可見,視覺表現不僅是我們對于事物外在內容的準確反映,更能夠反映出我們對于該事物內在的把握。
(二)重慶地區蜀繡視覺表現的現狀
對重慶地區蜀繡的視覺表現的現狀,主要從題材、構圖、用色、技法、載體和展示設計這五個方面來進行闡述。
市場上常見的題材類型為極富寓意的求福、求子和驅災辟邪以及一些地域性題材。繡娘在刺繡的過程中常常采用不同的題材來描繪人們稱頌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以表達他們最真摯的祈盼。頻繁使用的求子求福的題材有:比擬愛情的美好用鴛鴦、鳳凰等;用葡萄、石榴、麒麟等象征子嗣的綿延;用仙桃、壽星等寓意長壽;用佛手、蝙蝠等寓意多福;用蓮花、鷺鷥等寓意一路高升;用萬字紋寓意萬事吉祥如意;用魚、鹿等寓意高貴富足。祛除災禍求得神仙庇佑一類的題材反映了人們內心對于渴望安康的精神寄托,帶有濃郁的宗教色彩,常見的有暗八仙、關公等。也有不少的佛教題材,如唐卡、觀音和佛祖等。地域性的題材主要是一些有名的景點、經典的建筑以及重慶市花——山茶花等。
構圖因受繪畫的影響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如對角式、環形式、對稱式等,但常見的還是中心式構圖法。
顏色上得益于現代染色技術的不斷發展,更加的絢麗多彩刺繡作品在顏色上過渡得更加自然,畫面飽和度更高,更加的生動形象。
在技法上,重慶地區的蜀繡在繼承傳統蜀繡技法的同時,新發展出便于繡制雙面異形異色繡的雙扣針法和將亂針繡針法融入蜀繡技法來表現富于層次變化的畫面。
在載體上,除了常見的綢、緞、錦、帛等料地之外,還有皮革、夏布及較為柔軟的PVC等新型材料,突破了傳承材料所呈現的視覺效果,更加富有時代感。
在展示設計上,隨著文化創意產品的興起,蜀繡的展示更加多元化。常見的有蜀繡音響、蜀繡掛鐘、蜀繡針插、蜀繡肖像、蜀繡字畫、蜀繡油畫、蜀繡工筆畫、蜀繡座屏、蜀繡臺燈等新穎的展示設計。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展示蜀繡技藝,各大門店還有現場刺繡,動靜結合,促進銷售的同時也讓人們領略重慶地區蜀繡別樣的風味。
(三)重慶地區蜀繡視覺表現所呈現的問題
隨著時代的更迭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們對于蜀繡的視覺表現有了更具時代性和藝術性的需求。反觀重慶地區蜀繡的視覺表現,雖然較傳統蜀繡而言,有很大的發展和進步,題材種類更加豐富、色彩更具視覺沖擊力、技法更為精湛、載體更加新穎、展示設計更加多樣,但是這種程度還遠遠不能夠滿足多元的快消費時代人們因生活方式改變、外來文化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而對蜀繡作品視覺表現產生的新需求,仍然存在不足,這種不足集中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重慶地區蜀繡的構圖表現形式主要以中心式為主,這種構圖雖然具有主體物突出、一目了然的特點,但是這種傳統的構圖模式在市場上千篇一律,顯得過于單板,缺乏創新性,不能夠激起人們持續性的興趣和關注,也不能很好地促進此類作品的銷售。
其次,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家普遍對重慶地區的蜀繡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比如說各大極富美好寓意的題材老幼皆識,人們對于一些傳統的蜀繡技法能夠輕松的辨識,并且對蜀繡作品中色與色的結合,色與形的構成組合所體現的審美寓意要求更高,或直抒胸臆,或溢于言表。但這種視覺表現的普識性從重慶現有的蜀繡作品來看,除開一些辨識度高的地域性題材,如吊腳樓、山茶花、人物肖像等,一些書畫作品,如美術家王明勤的《桃花源》、工筆畫家蓮子的《家書》和畫家郎世寧的《乾隆皇帝閱駿圖屏》等,非專業人士根本無法進行鑒賞,就連繡娘可能也不明白畫中胸臆,而欣賞者們就只能走馬觀花,全然不能領略這些無字史書所蘊含的真情實感,更不能激起欣賞者內心的滌蕩。
三、解決辦法
新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新的視覺表現需求是人們精神價值的擴張,即是說精神和形式上都強調變化、創新和突破,這對重慶地區蜀繡的傳承與發展無疑既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挑戰。
由于刺繡的特殊性,它不能夠簡單依據繪畫的形制來進行創作,而是要根據具體的繡制內容選擇適當的技法來進行恰如其分的構圖。針對重慶地區蜀繡作品中心式構圖居多的現狀,可大膽采取一些繪畫中常見的構圖方法對其進行豐富,比如使畫面顯得既莊重又不過分拘謹且主體形象格外醒目的井字構圖;給人以堅強鎮靜且具有良好烘托效果的正三角形構圖;給人以明快、充滿活潑動態之感的倒三角構圖;使畫面主次分明的斜三角形構圖;使主體物巍峨高大而富有氣勢的垂直式構圖;用以表現物體運動變化的斜線式構圖;使景物顯得安靜而又穩重的水平式構圖;使畫面線條優美、感染力強的曲線式構圖;利用逐漸過渡的手法來表現更強的視覺效果的漸進式構圖;符合黃金分割定律的九宮格構圖等。多種多樣的構圖方法不僅能夠使我們的刺繡畫面更加的生動,而且在展示時還能夠更具吸引力,并能夠滿足更多的審美需求。
除此之外,構圖和施色也可以充分的結合起來,在視覺反映中,色彩和形象相比,更有先聲奪人的功能。它能夠集中地表現繡娘的智慧和生活情懷,同題材一樣具有一定的寓意象征和隱喻語言的意義,把本來無關聯的因素結合起來,將色彩符號演變而產生意想不到的戲劇性效果,實用、裝飾、夸張和想象的特點更能夠有效滿足人們多樣的需求。
對于書畫作品意蘊難懂的問題,可能最為直接的解決方式就是設專人進行講解或者在作品旁加上特定的標注,但是這種方式使得欣賞者顯得被動,不能主動去感悟作品深層次的內涵,這種情況下可以在時空轉換中來尋找新的視覺表現方式,使人們的感官系統能夠敏銳地去感覺繡品,把繡品置于時空和意念的錯位中,以此來創造出“懂”的立足點。作品的意蘊往往是通過表現來傳達的,而表現又是存在于結構之中的,按照詹姆斯在其《心理學原理》中的見解,雖然身與心是兩種不同的媒質——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非物質的——但它們之間在結構性質上還是可以等同的。那我們還可以嘗試從心理學的這一點出發,重新探索蜀繡中書畫繡品意蘊的表現性。阿恩海姆在解釋結構的表現性時說道:“不管知覺的對象是運動的(如舞蹈演員或戲劇演員的表演),還是靜止不動的(如繪畫和雕塑),只有當他們的視覺式樣向我們傳遞出‘具有傾向性的緊張力或‘運動時,才能知覺到它們的表現性。”這里提到的“具有傾向性的緊張力”或“運動”完全可以采納分離、重構、錯位等多種辦法,先破而立,讓這種動態的、多義的、方式上變化發展的創意傳達不僅能夠使人們用眼睛體會過程,還能夠涉及人們的心理、經驗、感情、文化、價值觀等各種因素。眾所周知,在通常情況下,一件藝術品往往是通過它的題材、構圖、運色以及技法來向我們進行其自我的展示,我們可以靈活地運用各部進行有機的組合,既不是簡單的復刻書畫作品,還能使作品淺顯易懂又不失獨特韻味。
四、結語
雖然針對重慶地區蜀繡視覺表現的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提出了采用多種形式構圖、形色結合以及將時空與意念相結合的破而立的解決方式,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還會面臨更多具有現實性和挑戰性的問題,科學的進步還會不斷地改變人們的時空觀念,人們的文化心態和藝術趣味也會進一步提高。因此重慶地區的蜀繡需要緊扣消費者不斷變化的新需求進行創新,使得重慶地區的蜀繡得到新的突破,得到更好的傳承與發展。
參考文獻:
[1]孫佩蘭.中國刺繡史[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145-161.
[2]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朱疆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05-611.
[3]楊憶.蜀繡設計基因的提取與應用研究[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18.
[4]左漢中.中國民間美術造型[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2:165-171,259-261.
[5]劉曉蕾.巴渝蜀繡文化生態變遷研究[J].美與時代(上),2016(8):44-46.
[6]馮鋼.藝術符號學[M].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3:90-91.
作者簡介:任霞,重慶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設計史與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