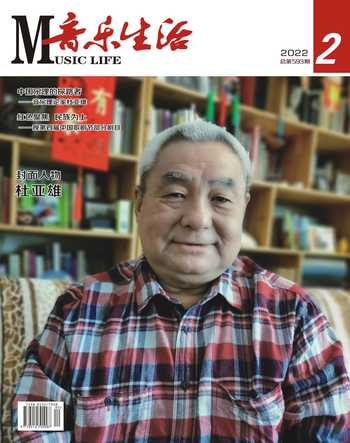談冼星海《生產(chǎn)大合唱》創(chuàng)作心路
李沫
《生產(chǎn)大合唱》是我國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大合唱作品。這部合唱亦是作曲家到達(dá)延安后歷見根據(jù)地軍民響應(yīng)黨的號召,蓬勃開展“自己動手,風(fēng)衣足食”的大生產(chǎn)運(yùn)動的偉大見證。在抗日戰(zhàn)爭相持階段的艱難歲月里,該作品給予當(dāng)時的人們團(tuán)結(jié)一心、抗戰(zhàn)到底的信心與力量。筆者從發(fā)表于1940年的樂譜初稿入手,結(jié)合多方史料,對該部合唱作品進(jìn)行深度的梳理與分析,從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心路中窺探其音樂創(chuàng)作思想之蛻變與升華。
(一)《生產(chǎn)大合唱》創(chuàng)作始末
1935年,冼星海在法國學(xué)習(xí)結(jié)束后回到祖國。從上海到武漢,從武漢到延安。他幾經(jīng)輾轉(zhuǎn),懷著對民族危亡積極關(guān)切的拳拳之心,帶著對抗日救亡音樂創(chuàng)作的熱情與憧憬來到延安。1938年冬,毛澤東同志發(fā)表了《青年運(yùn)動的方向》的講話。這一紀(jì)念“一二 · 九”運(yùn)動的著名演說,成為了當(dāng)時革命根據(jù)地軍民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chǎn)運(yùn)動的號角。1939年3月初,在與劇作家、詩人塞克暢談討論之后,冼星海第一次嘗試以“民族形式,進(jìn)步技巧的作風(fēng)”[1],創(chuàng)作了二幕活報型歌劇——《 生產(chǎn)運(yùn)動大合唱》。當(dāng)時該作品分為三個部分,即:第一幕《生產(chǎn)與抗戰(zhàn)》,第二幕《農(nóng)村小景》(續(xù)),第二幕《農(nóng)村小景》(續(xù)完)[2]。這部作品經(jīng)演出后,最終定名為《生產(chǎn)大合唱》。其表演形式,也從原來帶有一定服裝、道具及故事情節(jié)表演的“大型歌舞活報劇”改為純合唱的表演形式。而根據(jù)1954年出版的《冼星海歌曲集》,我們可以看到最終版本將《生產(chǎn)大合唱》的內(nèi)容確定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開荒與春耕》,第二部分為《播種與抗戰(zhàn)》,在冼星海去蘇聯(lián)后,又把1940年完成的獨(dú)立合唱曲《秋收突襲》編入生產(chǎn)大合唱中,作為第三部分并改名為《秋收》[3]。而原作第三部分改為《豐年》,列入附錄與前三場共同保留。《生產(chǎn)大合唱》是冼星海初到延安時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合唱作品,其創(chuàng)作思想上終貫穿著“堅持抗戰(zhàn)到底,就必定要努力生產(chǎn)”的指導(dǎo)思想,其創(chuàng)作思路體現(xiàn)了冼星海一直堅持做“大眾化、民族化、藝術(shù)化”[4]的中國“新音樂”[5]重要藝術(shù)追求。正是這部合唱作品,為冼星海后來的《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的創(chuàng)作奠定了堅實(shí)的實(shí)踐基礎(chǔ)。
(二)《二月里來》與《酸棗刺》
冼星海的《生產(chǎn)運(yùn)動大合唱》的創(chuàng)作僅用了六天的時間便順利完成。其中第二幕中的(原作第一幕)《二月里來》與《酸棗刺》兩個段落至今被廣泛傳唱,并常作為獨(dú)唱、童聲合唱曲目活躍在今天舞臺之上。特別是《二月里來》,充滿了“田野氣息與江南風(fēng)格”[6],實(shí)為一首優(yōu)美浪漫的抒情歌曲。在這首歌曲中,作曲家展現(xiàn)了大生產(chǎn)運(yùn)動中人民群眾積極、樂觀、樸實(shí)、向上的精神風(fēng)貌。作品開始演出時本來是以活報形式并加上化妝來演出的,但在后來的生產(chǎn)運(yùn)動大合唱座談會上幾經(jīng)探討,認(rèn)為化妝演出不如純粹合唱的形式好,將活報型二幕歌劇改為純大合唱的表演形式。于是,《生產(chǎn)大合唱》最終應(yīng)運(yùn)而生。而《二月里來》這首小調(diào)則在還沒有正式排演之前就已在延安傳唱開來,成為當(dāng)時“新音樂”的經(jīng)典之作。
《酸棗刺》是一首童聲合唱歌曲,其曲調(diào)非常簡單,只用了兩個不斷重復(fù)的上下樂句貫穿始終。這首歌曲較之《二月里來》有很大不同,音樂激昂奮進(jìn),表達(dá)了軍民邊生產(chǎn)邊抗戰(zhàn)的信心與決心。曲目排演時,冼星海還專門從魯藝學(xué)員里找了幾位年紀(jì)最小的孩子來扮演大生產(chǎn)運(yùn)動中的小動物。可以說,從作曲到排演,冼星海都親力親為,對這首兒童歌舞劇形式的歌曲可謂用盡心思,務(wù)求標(biāo)新立異。演出時,冼星海還加入舞蹈,秧歌等表演形式,同時使用大量的民間打擊樂器,使歌曲獨(dú)具特色,樂觀又活潑。
《二月里來》與《酸棗刺》這兩首歌曲奠定了整個合唱的基調(diào),時至今日,仍被傳唱。與《黃河大合唱》相比,《生產(chǎn)大合唱》目前被保留演出的歌曲即是《二月里來》與《酸棗刺》,由此可見,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與價值。
(一)來自座談會上的批評之聲
《生產(chǎn)大合唱》首演后引發(fā)了當(dāng)時延安文藝界的爭論與批評。1939年5月9日,延安文藝和音協(xié)組織為了總結(jié)該作品,專門舉辦了《生產(chǎn)大合唱》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延安文藝界的工作者們對這部《生產(chǎn)大合唱》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評價與總結(jié)。詞作者塞克這樣總結(jié)了當(dāng)時的演出結(jié)果:“至于談到演出的成效,可以說完全不是預(yù)期的樣子,在裝置化妝服飾道具上,個別同志演出的不認(rèn)真,弄得是一塌糊涂……”[7],而冼星海自己也進(jìn)行了自我評價與批評:“我常常在演出過后,去向觀眾求取許多意見,許多意見都是很對的,對我都有很大幫助。……許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間音樂做基礎(chǔ)參考西洋的音樂進(jìn)步成果,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中國音樂形式。我很不斷努力在做,收獲總未能滿意……”[8]。隨后,艾思奇、向隅、呂驥等同志相繼發(fā)言,提出意見。由此可以看出,當(dāng)時《生產(chǎn)大合唱》一亮相并沒有獲得滿滿掌聲,反而使冼星海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與困境。經(jīng)查閱文獻(xiàn),筆者將對《生產(chǎn)大合唱》的批評意見集中總結(jié)為以下幾點(diǎn)內(nèi)容:
第一,創(chuàng)作背景方面:整個合唱歌曲的歌調(diào)未能夠充分反映出人民大生產(chǎn)活動的現(xiàn)實(shí)。如第一場開荒用人力拉犁,并不符合延安的事實(shí)。拉犁歌是碼頭工人的歌聲,且音調(diào)過于壓抑沉悶,并不符合當(dāng)時生產(chǎn)自建的精神風(fēng)貌。而《二月里來》雖然旋律優(yōu)美,但江南風(fēng)味很重,很難引起陜北老百姓的共鳴。
第二,作曲創(chuàng)作方面:整個作品風(fēng)格上不夠統(tǒng)一,《拉犁歌》選自電影《壯志凌云》的插曲,曲調(diào)沉悶壓抑,不能表現(xiàn)為祖國解放而開荒播種的愉快情緒。而《二月里來》又過于浪漫柔美,《酸棗刺》節(jié)奏鮮明活潑,與之前《拉犁歌》沉悶的音樂風(fēng)格構(gòu)成相沖突。而《公雞高聲叫》是模仿印度碼頭工人的歌曲。《建立新中國》又是一首中外音樂有機(jī)結(jié)合的曲子,和聲太過西洋化。因此,這兩首歌曲與之前的《拉犁歌》《二月里來》《酸棗刺》,又形成中西音樂風(fēng)格的沖突。從而,造成整個作品風(fēng)格的不統(tǒng)一,甚至混亂。
第三,演出效果方面:由于當(dāng)時演員(主要是魯藝的學(xué)員們),表演技術(shù)不熟練,人力資源有限,加之舞臺窄小,無法舒展,導(dǎo)致表演第三幕時人與動物的模仿混聲秩序混亂,破壞了歌曲情節(jié)的發(fā)展,使整個演出未能達(dá)到預(yù)期效果。用冼星海自己的話說:“要修改的地方還很多”[9]。
盡管向隅、呂驥等同志都肯定了《生產(chǎn)大合唱》的價值與成功,但是,從刊載在當(dāng)時《新音樂》第一卷四期上的《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座談評論的具體內(nèi)容來看,在回答《生產(chǎn)大合唱》是不是一個偉大作品時,呂驥同志這樣說道:“剛才還有一位同志談及生產(chǎn)大合唱,是不是一個偉大作品。我敢大膽說,今天中國新音樂這樣幼稚,如果產(chǎn)生像貝多芬那樣偉大的作品,是不可能的,還沒有這樣的條件……”。這次會議一直進(jìn)行到夜里十二點(diǎn)方才結(jié)束。可見,當(dāng)時延安文藝工作者們對于該作品存在爭議之大。有鑒于此,《生產(chǎn)大合唱》在首演后就遭到了當(dāng)時各界的批評與爭論,而這部作品,雖然不乏經(jīng)典唱段佳作,但在當(dāng)時或可推測是一次存在爭議,甚至是“失敗”的創(chuàng)作嘗試。顯然,由作曲家提出的“大眾化、民族化、藝術(shù)化”的新音樂之路,在實(shí)踐過程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也正是這樣的爭議與質(zhì)疑為后來的恢弘巨著《黃河大合唱》的創(chuàng)作埋下了伏筆。
(二) 冼星海創(chuàng)作心路的蛻變
那么,造成這種“不成熟”原因是什么呢?是作曲家技術(shù)不夠好?還是對民間音樂研究不夠呢?筆者認(rèn)為,除上述原因之外,也許還存在著創(chuàng)作思想“不夠成熟”的原因,而這個原因或許是影響作曲家整體創(chuàng)作水平的最終因素。
根據(jù)當(dāng)時樂稿,可以看到原作(二幕型活報歌劇)本來的創(chuàng)作順序?yàn)椋旱谝荒弧渡a(chǎn)與抗戰(zhàn)》(《二月里來》,《酸棗刺》);第二幕(續(xù))《農(nóng)村小景》(引子《拉犁歌》曲調(diào),《雄雞高聲叫》),以及第二幕(續(xù)完)《農(nóng)村小景》(《建立新中國》)。由此排序可知冼星海初到延安的心境。1938年冬,冼星海懷揣追求自由音樂氛圍的夢想和抗日救亡的理想,來到延安。此時,正趕上轟轟烈烈的大生產(chǎn)運(yùn)動。他站在溝壑上,眺望遠(yuǎn)景,新奇地欣賞著延安人民與人民軍隊(duì)熱火朝天生產(chǎn)勞動的美好景象。與此前在上海、武漢的心境截然不同,他的心里早已譜成了優(yōu)美曼妙的旋律……這是一位來自國統(tǒng)區(qū)音樂家在延安的真情實(shí)感,也是《二月里來》充滿了濃重的江南歌調(diào)風(fēng)格的原由。因?yàn)椋谶@里仿佛看到了秀美的江南春光,看到了革命春天的到來。作曲家在這里自由地呼吸著鄉(xiāng)土氣息,從教學(xué)生到住窯洞……生活變得單純而美好。這種美好,使作曲家在《酸棗刺》中所表達(dá)的對抗戰(zhàn)號召情緒也變得愉快而歡樂起來。原作第一幕即是《二月里來》與《酸棗刺》,而這兩首歌曲是整個大合唱中最優(yōu)美精彩的部分,這也恰恰符合一個心懷理想初到革命根據(jù)地的音樂家的心境。
在第二幕《農(nóng)村小景》的創(chuàng)作上,冼星海使用了1936年電影《壯志凌云》中《拉犁歌》的相對沉重的曲調(diào)。這一點(diǎn),與之前歡樂愉快的氣氛截然不同。筆者以為,這恰恰是作曲家參加勞動生產(chǎn)后的真實(shí)心境寫照。對于一名輾轉(zhuǎn)于大城市之間的文藝工作者來說,參加勞動確實(shí)是辛苦不堪的。因此,將勞動生產(chǎn)寫成像《酸棗刺》那樣活潑愉快,也許是當(dāng)時冼星海所不能達(dá)到的思想境界,此曲被批評不符合延安現(xiàn)實(shí)也是緣由與此。冼星海基于中西音樂的探求心理,將這首模仿印度碼頭工人的歌,填詞而作,努力探索歌曲的新風(fēng)格,因此,忽略了該曲的音調(diào)與情緒比較之前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沖突問題。
第二幕的兩首歌曲,都不同程度受到批評。這是作曲家向“民族化、大眾化、藝術(shù)化”創(chuàng)作之路前行的必經(jīng)階段。雖然這種批評在現(xiàn)在仍然存在爭議,但在當(dāng)時確實(shí)代表了延安地區(qū)音樂工作者的主流意見。而這種批評,并不簡單的一個音樂創(chuàng)作探索的問題,更有可能是作曲家還沒有做好從一名具有救亡意識的民族音樂家向一名具有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的革命音樂家蛻變的問題。從冼星海自述的《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一文中,可以看到關(guān)于他在延安接受思想洗禮與蛻變的文字:“還有一種批評,給我的感觸較大,那就是負(fù)責(zé)當(dāng)局地關(guān)于方向的指出。譬如他們所主張的‘文化抗戰(zhàn)’,對我關(guān)于音樂上民族、民主、大眾化、科學(xué)化的方向,給予我對于新音樂建議的研究和實(shí)行問題很好的啟示……為了學(xué)習(xí)浪潮的推動,我也學(xué)習(xí)理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我竟發(fā)現(xiàn)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不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xué)理論上竟得到解答。且不說大的方向,如音樂與抗戰(zhàn),音樂與人類解放等問題……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過去我以為是因?yàn)樗麄儯üまr(nóng)階級)受苦,所以在吸收工人地呼聲及情緒入作品時,總表現(xiàn)的‘形式化’。現(xiàn)在我知道了……勞動者所想的實(shí)在是最高尚的,正確的……感情是健康的……因之他們的聲音,感情就能充滿著熱愛和親切,真誠和真摯”[10]。這是冼星海關(guān)于在延安時期(新環(huán)境)的一段論述:也許上述提到關(guān)于創(chuàng)作、表演的原因都客觀存在,但究其根本,應(yīng)是作曲家的思想意識還沒有達(dá)到一名革命音樂家所具有的境界與高度問題。正是這部《生產(chǎn)大合唱》,使冼星海看到了自己創(chuàng)作技法上的“不足”與思想高度上的“不夠”。也正是關(guān)于這部作品的爭議與質(zhì)疑,使冼星海最終確立了自己精神信仰的方向,激發(fā)了他空前的創(chuàng)作熱情。在僅僅半月之后,冼星海同樣用了六天時間,一氣呵成創(chuàng)作了經(jīng)典巨著《黃河大合唱》。而這一次,他終于獲得了實(shí)至名歸的掌聲與贊頌。
天才不是一蹴而就的。當(dāng)人們感嘆《黃河大合唱》的氣度與宏大時,很少有人能夠看到作曲家在創(chuàng)作《生產(chǎn)大合唱》后所承受的批評與徘徊。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延安那么多音樂家,唯獨(dú)冼星海擔(dān)當(dāng)了“人民的音樂家”的稱號呢?筆者以為,這個稱呼實(shí)至名歸。
首先,冼星海是一位具有民族憂患意識,關(guān)心同情勞苦大眾,勵志研究民族救亡音樂的音樂家。他心系民族大義,拒絕創(chuàng)作“新毛毛雨”之類靡靡之音,專注寫救亡歌曲,盡管生活窮困,顛沛流離,但他仍然堅守自己的音樂操守,不為斗米折腰。這一點(diǎn)在冼星海《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一文中可知一二,原文這樣寫道:“……我在1935年回國后,眼見民族的危機(jī),民族的壓迫,人民的困難,流離失業(yè),饑荒,工業(yè)的艱苦,被壓榨,被剝削……使我漸漸自覺了自己的任務(wù),毅然地加入了救亡運(yùn)動,專心寫救亡歌曲……”[11]。由此可見,冼星海憂國憂民的高潔品格和志存遠(yuǎn)大的藝術(shù)理想。正是這些獨(dú)特品質(zhì)與氣魄,為冼星海后來的思想轉(zhuǎn)變與升華,打下堅實(shí)的基礎(chǔ)。
其次,冼星海畢生都致力于民族音樂研究,立志創(chuàng)作“大眾化、民族化、藝術(shù)化”的中國“新音樂”。他以民間音樂為基礎(chǔ),結(jié)合西洋音樂的技術(shù)成果,開創(chuàng)了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之路。他不斷嘗試與創(chuàng)新,堅持筆耕不輟,始終堅定著自己的藝術(shù)理想與追求。在后來的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的座談會上,冼星海這樣總結(jié)道:“現(xiàn)在作曲家表現(xiàn)了三種不同態(tài)度:第一種,死硬地模仿西洋音樂,第二種則頑強(qiáng)地固執(zhí)著中國音樂作法,第三種是盡力想使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作適當(dāng)?shù)慕Y(jié)合。我非常贊成最后那一種,不過今天中國作曲家走上這道路還很少。在此我順便提出三個口號:音樂應(yīng)該是大眾化,民族化,藝術(shù)化。只有能夠朝著這方向干下去,才能成功為中國寫出很好的音樂”[12]。正是這份執(zhí)著與勤奮,使冼星海堅持“為人民而創(chuàng)作”的音樂理想,為喚醒民族意識,弘揚(yáng)民族音樂做出了卓越的貢獻(xiàn)。
再次,冼星海秉承著謙虛嚴(yán)謹(jǐn)、求真務(wù)實(shí)的工作作風(fēng)。從教學(xué)研究到創(chuàng)作耕耘,時刻戒驕戒躁,腳踏實(shí)地。在延安魯藝執(zhí)教時期,他與學(xué)員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深受魯藝學(xué)員們的尊敬與愛戴。在音樂創(chuàng)作方面,他一貫謙虛謹(jǐn)慎,對他人虛心求教,對自己嚴(yán)格要求。他在《生產(chǎn)大合唱》的座談會上這樣總結(jié)道:“這首曲子是很短時間內(nèi)趕出來的,后來收獲到了一些朋友的愛好,我很慚愧。我想講大合唱能收到一些效果,應(yīng)該是塞克同志創(chuàng)作歌詞的功勞。……整個歌曲來說,要修改的地方還很多……”[13],冼星海熱情地贊揚(yáng)了塞克同志的作詞,卻在分析問題中,客觀地進(jìn)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從這一點(diǎn)我們可以看到,冼星海謙虛務(wù)實(shí)的人品與性格。冼星海曾這樣寫道:“延安人民喜歡新的東西,也喜歡批評。他們常常對我的作品發(fā)表意見,而且有一套道理。我因之常常以他們地批評作參考,改正某些地方。但是也有些人批評時常以過去或現(xiàn)在某作品為標(biāo)準(zhǔn),這種稍微帶點(diǎn)保守性的批評,是在別的地方也不能免的。這種批評對我也有幫助,使我看見我地作品個性、進(jìn)步還是退步”[14]。以上種種,使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這樣謙虛嚴(yán)謹(jǐn)、不驕不躁、務(wù)實(shí)求真的做事風(fēng)格,使冼星海深受大家尊重與愛戴。他有傲骨卻不自傲,在音樂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一直務(wù)求嚴(yán)謹(jǐn),虛心受教。無論是文藝工作者還是人民群眾的意見,他都會認(rèn)真聽取,積極改進(jìn)。除此之外,他還如饑似渴地學(xué)習(xí)無產(chǎn)階級革命綱領(lǐng)和理論。努力從思想意識上融入當(dāng)時革命生活,使自己成為一名堅定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戰(zhàn)士。正是這樣的人格與品質(zhì)造就了冼星海,使他在延安期間迅速地完成了由救亡派進(jìn)步音樂家向堅定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音樂家的思想蛻變。最終獲得人民的認(rèn)可與喜愛,成為了實(shí)至名歸的“人民的音樂家”。
總之,《生產(chǎn)大合唱》也許是“不成熟”的,但它又恰似一塊“試金石”,它激發(fā)了冼星海空前的創(chuàng)作熱情,使其在為人民、為民族而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筆耕不輟、自強(qiáng)不息。可以這樣說,沒有《生產(chǎn)大合唱》就沒有后來的《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這部作品的意義已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其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正如呂驥所言:《生產(chǎn)大合唱》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一改中國音樂過去的萎靡與傷感,是非常健康而充滿革命熱力的。它有光有力,輕快活潑,非常值得我們贊揚(yáng)。也許,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在當(dāng)時存在一定爭議,但這絲毫不影響其獨(dú)特的歷史價值與藝術(shù)魅力。它記錄了延安軍民大生產(chǎn)運(yùn)動的滿腔激情與火熱場景[15];它唱出了延安人民昂揚(yáng)向上、樂觀堅韌的精神與風(fēng)貌;它表現(xiàn)了延安軍民一致抗戰(zhàn)、堅持到底的宏大氣魄與決心,它是時代的縮影,歷史的豐碑,是冼星海革命精神洗禮與歷煉的最好見證。
參考文獻(xiàn):
[1]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
[2]賽克、冼星海:《生產(chǎn)大合唱》,《新音樂》第一卷五期,1940年。
[3]賽克、冼星海:《生產(chǎn)大合唱》,《新音樂》第一卷六期,1940年。
[4]冼星海:《冼星海歌曲集》,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1954年。
[5]冼星海:《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華北新華書店,1951年。
[6]孟紅:《〈生產(chǎn)大合唱〉:大生產(chǎn)運(yùn)動的全景式寫照》,《黨史縱覽》,2015年。
注釋:
[1]冼星海:《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華北新華書店,1951年,第23頁。
[2]賽克、冼星海:《生產(chǎn)大合唱》,《新音樂》月刊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0頁。
[3]冼星海:《冼星海歌曲集》,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1954年,第37-72頁。
[4]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3頁。
[5]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3頁。
[6]冼星海:《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華北新華書店,1951,第24-25頁。
[7]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4頁。
[8]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4頁。
[9]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5頁。
[10]冼星海:《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華北新華書店,1951年,第25頁。
[11]冼星海:《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華北新華書店,1951年,第26頁。
[12]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6頁。
[13]佚名:《關(guān)于生產(chǎn)大合唱文藝座談》,《新音樂》第一卷四期,1940年,第26頁。
[14]冼星海:《創(chuàng)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jīng)過》,《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華北新華書店,1951年,第27頁。
[15]孟紅:《〈生產(chǎn)大合唱〉:大生產(chǎn)運(yùn)動的全景式寫照》,《黨史縱覽》2015年,第28頁。
李 沫 沈陽大學(xué)音樂與傳媒學(xué)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