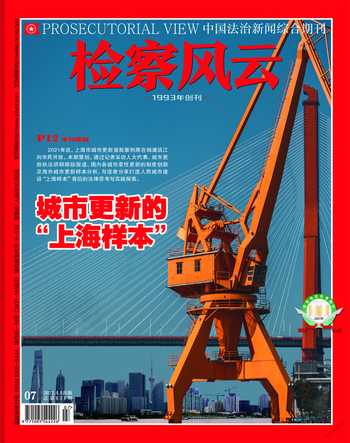商標惡意注冊中“使用目的”的法律思考
許辰諾 楊慧 溫潘紅
商標的本質,是根據現實中生產經營的需要,利用特定符號在商品與消費者之間建立的一種聯系。
近十年來,我國商標注冊申請量持續高速增長。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 中國商標網”官網公布的全國省市縣商標主要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全國范圍內的商標注冊申請數量達到了701.3萬件,同比增長4.77%。隨著商標品牌戰略的有效推進,商標注冊申請數量依舊保持穩步增長,其中有效注冊累計數量為523.1萬件,有效注冊率91.9%,數據表明我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商標方面的快速發展。
但與此同時,近十年來我國的商標申請數量和增長率均遠超國內生產總值及增長率,馳名商標的數量也沒有明顯增長,這與我國由商標大國向商標強國的轉變目標不符。我國商標注冊仍未適應由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的經濟發展趨勢,商標注冊行為現狀、商標真正投入使用情況堪憂。其間,不乏“火神山”“雷神山”等社會熱點被搶注商標、“茶顏觀色”起訴“茶顏悅色”等一系列商標惡意注冊引起的侵權事件。2019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簡稱《商標法》)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值得思考。
首先,商標申請審查階段規制作用未能體現。
從商標惡意注冊行政糾紛案由的角度進行統計,我國商標注冊在商標異議階段以及商標無效宣告階段的爭議最為明顯,分別高達41.7%和45%。從商標注冊的流程來看,對于惡意商標注冊的規制環節相對靠后,基本是通過處理異議商標及宣告商標無效的事后手段進行補救,而前期規制階段的商標申請駁回糾紛僅占9.6%。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商標申請階段的審查環節可能存在疏漏。
2019年修訂的《商標法》中僅規定了對“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予以駁回”,但并未列明無使用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行為具體種類,也并未細致規定商標注冊申請審查人員對于使用目的的正當性的判斷標準,導致新增的“使用目的”的審查規則在實踐中難以發揮其真正的作用。
商標的注冊應以具有真實使用的意圖為前提,究其本質,“使用目的”是一種主觀心理狀態,而商標申請者“使用目的”無法查明,商標管理部門主要依靠注冊申請人提供的紙質申請文件來推斷商標注冊申請是否具有使用的目的。一方面,審查沒有統一的判斷標準,具有極大自由裁量性;另一方面,書面材料具有固定化、格式化的要求,難以體現申請者的使用意圖,使得商標惡意注冊行為難以在審查階段被發現。2019年《商標法》第四條規定的“使用目的”條款在我國現實執法環境中面臨缺乏可操作性的情況,我國商標注冊申請的審查亟須能夠證明商標申請具有真實使用目的的證據規定,來填補這一空白。
其次,“使用目的”規則與其他條款存在沖突。
從商標惡意注冊行政糾紛適用法律依據的角度進行統計,僅根據統計出的有效數據顯示,程序問題適用的相關法律條款在商標惡意注冊行政糾紛中出現頻率高達73.8%。商標注冊糾紛需要對商標的真實使用意圖進行判斷,然而我國商標審查部門與司法實踐的認定標準存在較大分歧:相似的糾紛事實存在適用不同法條的問題。究其根本,《商標法》中缺失對于商標具體適用規則的解釋,有違執法司法一致性的精神。

2019年修訂的《商標法》中,新增“使用目的”條款與其他規定之間存在交叉重合,導致審查理由存在競合,以至于一個行為同時可以適用兩個規則進行規制,也是導致商標的惡意注冊行為并未得到有效規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具體來說,“正當使用目的”可以視為誠實信用原則在商標審查領域的子原則,法院的說理部分也存在將兩者混同使用的情況,筆者認為欠妥。商標的“正當使用目的”確立之前,司法實踐中常會以“不正當手段”作為兜底性的規制理由對商標進行無效宣告,但由于“不正當手段”的適用具有局限性,商標注冊過程中把“使用目的”與“不正當手段”相提并論進行規制的,屬于法律思維慣性,應當加以糾正。
商標的“使用目的”要件應盡可能在商標注冊全過程有所體現,尤其是應在商標申請階段著重規范。我國司法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商標申請程序中審查事由具有相對性導致認定標準存在分歧,而在商標異議階段和無效宣告階段進行事后規制。鑒于現實情況所反映出的問題,更應明確相關規定,從而在商標注冊的各個環節均對惡意注冊行為產生有效遏制作用。
立法方面:明確我國對于商標“使用目的”作為審查理由的適用順序。
為解決“使用目的”規則與其他法律規定事由的適用沖突,可將“缺乏正當使用目的”單獨作為一條列明,與“其他不正當手段”地位相同,作為我國商標局不予商標注冊的依據。參考德國司法實踐的經驗,建議可以將商標的惡意注冊行為分類,大致分為侵害合法的在先權利、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非法利益、搶占社會公共資源等類型。據此,建議按照《商標法》之規定進行如下劃分排序:第一,對于侵害在先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在先權利的惡意注冊行為,適用第十條、第十一條等法定的相對理由予以駁回;第二,對于看似合法的不正當、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惡意注冊行為,應按照“欺騙手段”的絕對事由不予認可;第三,對于搶占社會公共資源的商標搶注、囤積等惡意注冊行為,可以按照“缺乏正當的使用目的”進行認定,唯有窮盡所有具體規則以及不具備“正當使用目的”的情況下,再考慮以“不正當手段”此類兜底性條款予以規制。依照此種法律適用順位對商標惡意注冊行為予以規制,既可以將現行《商標法》中新增“使用目的”的立法精神在司法層面得以落實,同時也能夠解決我國《商標法》先前規則與新增規則之間適用沖突問題。
執法方面:完善我國商標申請階段對于商標“使用目的”的審查規定。
對于商標“使用目的”審查不能僅停留在法律條文表面,還需要在行政與司法實踐落實具體措施,通過總結,將經驗上升到法律層面,以實踐促進理論的更新與發展。雖然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已經列舉了審查部門應考量的因素,但由于“商標的近似程度”“申請人的注意程度”等參考標準缺乏可操作性,實踐中依靠行政機關的主觀判斷,易受不可控因素影響,進而引起行政相對人與審查機關的爭議糾紛。
參照美國《蘭哈姆法》中的商標審查制度相關規定,建議我國行政機關要求商標申請人在提交有關商標申請時附帶提供相關證據,通過實體有形的客觀證據,來作證其商標的“使用目的”確為善意真誠。為減少商標惡意注冊行為的發生,行政機關應要求有惡意注冊之嫌的申請人提供書面聲明,在審查時特別注意申請人對商標主觀方面及客觀方面的陳述,包括但不限于申請人先前申請商標的經歷、申請人的誠信記錄、對于商標構成的解釋、申請的商標計劃投入使用的領域等大致情況,以便審查機關合理排除商標惡意注冊行為。另外,針對我國目前常見的商標惡意注冊行為,即“搭便車”的近似商標注冊行為和商標搶注囤積行為,此類商標的申請明顯存在惡意,行政機關對其申請不予核準后,還可以對惡意申請人進行處罰,條件成熟后可將相關信息公開。在商標的申請階段就將惡意注冊行為進行嚴厲精準打擊,處以特定時期內禁止再次申請注冊商標的處罰,以絕后患。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等學校大學生實踐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大數據環境下利用分析模型對商標惡意注冊的預測及規制”,項目編號:FX202110329004)
編輯:夏春暉 3867532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