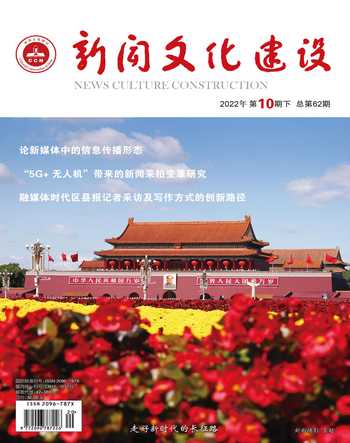后現代語境下紀實影像的虛構與真實
鄭丹琳
摘要:本文立足于后現代語境下的大眾傳媒特點,重點分析了傳統與后現代語境下大眾傳媒特點的變化。從紀實影像的虛構與真實的角度,分析了后現代語境下虛構手法的變化,概括了“搬演”“情景再現”與“數字模擬”三個主要的虛構手法,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掘了后現代語境下紀實影像虛構手法的創新意義,從記錄真實到挖掘真實事物的本質規律。
關鍵詞:后現代語境;紀實;虛構
21世紀,隨著后現代主義的發展,虛構與真實之間的界限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在傳統的紀實影像中,創作者往往通過不間斷的記錄來反映事物的全貌。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對真實的定義突破了“眼見為實”的思維。如今,“真實”不僅停留于視覺層面,更能通過數字模擬與數字推理的方式呈現到我們面前。本文通過深入的分析,詳細闡述了后現代語境下紀實影像虛構與真實的發展與意義。
一、后現代語境下大眾文化的發展趨勢
后現代主義源自現代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對現代主義包含的文化矛盾,特別是社會與人的異化的反抗。與現代主義相比,后現代主義顛覆了傳統的價值觀念,拉近了藝術與生活的距離,模糊了理性與非理性的界限。后現代主義對藝術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將割裂化、扁平化視為主流的審美特征。人們在快消時代所追求的完美感、另類感恰好與后現代的審美特征相吻合,割裂化與扁平化的美學取向極易激發人們的非理性需求,這種需求通過大眾傳媒手段的加持,能夠開拓出更大范圍的文化市場。
從文化的角度看,現代主義文化是文化創造者充分體驗并審視自然、社會與人生后,帶有形而上價值觀創造的屬于少數人的高雅文化;也是高度個性化與風格化,不斷探索事物更深層次意義的純文化。與現代主義文化不同,后現代主義文化則是一種深受資本邏輯支配的消費文化。后現代主義文化與大眾傳媒手段相聯系,具有模式化與類型化的特點,可以被批量復制,人人可享。快節奏時代“商品邏輯至上”的觀念使后現代主義文化拋棄了深度體驗與歷史感,成為僅僅反映瞬時體驗的一次性文化,往往與如今碎片化的時間和人們游戲的態度相適應。后現代主義文化一方面突破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壁壘,促進二者相融;另一方面為了逐利放棄了對文化內涵的堅守,空有廣度而沒有深度,具有兩面性。因此,后現代語境下的藝術創作也頗有研究價值。
二、紀實影像的虛構與真實
根據影像種類的不同,紀實影像可以分為紀實攝影和紀錄片兩種形式。紀實攝影是通過照片講故事,而紀錄片則是運用攝影機觀察人們的生活,通過視頻影像展現事物的全貌,從而喚醒或加深人們的認知。有關紀錄片的真實性的探討,歷來是紀錄片研究的熱點,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英國紀錄電影學派的創始人約翰·格里爾遜首次提出“紀錄電影”是“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吉加·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論”強調真實、非虛構,主張對現實進行客觀的展示。那么,究竟什么是虛構,什么是真實呢?紀實影像的虛構與真實并不是一組對立的詞匯,二者之間并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系。在紀實影像的創作中,“虛構”與“紀實”是一組相輔相成的創作手法,也是紀實影像的表現方式。[1]與“紀實”不同,“真實”是紀實影像的本質屬性,也是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區別所在。紀實影像的真實性要求創作者從現實生活中尋找素材,并以非虛構的方式進行創作,著名紀錄片導演周兵曾說:“做紀錄片的底線就是非虛構。”這里的“非虛構”并不是與“虛構”對立的創作手法,而是等同于“真實”,是紀實影像創作的原則。
但在紀實影像的發展歷程中,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做到絕對的真實。“真實電影”的代表人物,紀錄片大師弗雷德里克·懷斯曼曾過:“我無法表現總體真實。”因此,紀實影像所追求的“真實”并不是“絕對真實”,而是依附于一系列條件下的“相對真實”,其大致應劃分為三個層次,即客觀真實、心理真實與意義真實,難度遞增。客觀真實與心理真實指向物質狀態與心理狀態,意義真實則需要創作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揭示真實背后的意義,從而使紀實影像的題材“超越題材本身”。
三、后現代語境下虛構手法的變化
在后現代思潮出現前,虛構的手法已經被廣泛地應用于紀錄片的創作。20世紀初,紀錄片之父羅伯特·弗雷哈迪提出了“非虛構搬演”的手法,即通過表演對真實的生活場景進行再現,成為后現代前主流的虛構手法。在《北方的納努克》中,弗雷哈迪拍攝的并不是納努克當時的生活,而是根據歷史,并通過對愛斯基摩人的觀察,以“搬演”的方式記錄他們的傳統生活。 [2]20世紀初,受到地理環境與設備等種種限制,創作者往往通過運用“搬演”的虛構手法來實現紀錄片的“意義真實”。
縱觀電影與電視的發展史,紀錄片的演化經歷了“虛構—非虛構—再虛構”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受到后現代文化的影響,設備的升級與科技的發展為紀錄片帶來了更多可能性。后現代文化推動了紀錄片“再虛構”的發展,紀錄片的創作也進入了紀實與虛構相融合的階段,通過虛構尋求深層的真實成為主流的創作手法。紀錄片大師弗雷德里克·懷斯曼認為:“捕捉事物的現象不等于揭示事物的本質,創作者應采取一切手段與策略以達到真實。”
在后現代語境下, 影像資料的不足是紀實影像創作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因此,“情景再現”成為應用最廣泛、最成熟的虛構手法。[3]它通過運用場景搬演、人物扮演的方式,表現客觀發生過的事與人真實的心理活動,彌合了因“不在場”而造成的“時空斷點”。“情景再現”的虛構手法通過對客觀事實的“復現”推動了敘事的發展,并沒有改變影片敘事的故事空間與心理空間。此外,在一些文化思辨類的紀錄片中,創作者為了以當今的視角,重新解構歷史事件并提出自己的見解與反思,采用“主觀設問”的虛構手法。這種手法在批判現實、實證調查的紀錄片中多被應用,如埃羅爾·莫里斯的《細細的藍線》,這部影片沒有一句旁白,僅通過采訪對象的講述推進故事的發展。“主觀設問”的虛構手法是對思辨的重構,它彌合了“思辨的斷點”,推動了“紀錄”本身的發展。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數字模擬”成為紀實影像的“新虛構手法”。互聯網時代潛移默化地完成了對人們審美的重塑,如今,“極簡主義”與“科技感”成為主流的取向。“數字模擬”手法通過3D建模,將抽象的數據具象化,這種展現方式也更符合人們的審美偏好。“數字模擬”在一些科普類的紀錄片中已被實驗性應用,杰夫·奧洛威斯基在《社交困境》中就運用了這種手法解釋社交媒體背后的算法與流程,將復雜的大數據算法擬人化,這也是“數字模擬”手法應用的雛形。未來,科技手段將在紀實影像領域進一步普及,“數字模擬”這一利用互聯網技術代替高成本人工勞動的創作手法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
四、后現代語境下虛構與真實的意義
傳統的紀實影像注重對真實時空、真實場景盡可能客觀的敘述,傳統的創作者也以客觀事實為前提,來指導觀眾對自然、社會等問題的思考。在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新紀錄電影應運而生,后現代文化與新紀錄電影的融合則對紀實影像的真實性有了不同的闡釋。新紀錄電影提倡通過虛構的敘事手法表現真實,不再拘泥于眼前的真實,而是著力于超越眼前的真實。由此可見,后現代文化充分尊重了紀實影像真實的特質,也為紀實影像的真實性賦予了更廣泛、更深遠的意義。
1960年,讓·魯什與埃德加·莫林執導的“真實電影”《夏日紀事》通過運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模式展現了巴黎的眾生相。后現代紀實影像的真實性源于“真實電影”,又高于“真實電影”。在后現代語境下,先進的科技與多元化的敘事手法讓我們能從多視角反映真實,不再提供“唯一解”。
在后現代語境下,科技的發展為我們帶來了更多探索真實的渠道,“真實”也打破了文字與影像的局限,可以通過更加多樣化的方式呈現。如今,僅僅通過衛星的觀測數據,我們就能分析出宇宙的真實形狀。在紀實影像的創作中,虛構的手法使我們能最大限度還原真實,將文字、數據等符號轉化為視聽語言,用人們更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講故事。虛構的創作手法不僅能將“真實”具象化、可視化,增強紀實影像的觀感,也能反映出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下事物的真實。
五、結語
在后現代語境下,紀實影像的虛構與真實被賦予了更深層的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紀實影像的虛構手法也結合后現代主義的特性進行了升級。創作者不僅可以通過“搬演”“情景再現”與“數字模擬”還原真實,也可以借助高科技的手段,更大限度挖掘“超越眼前的真實”,將抽象的“真實”具象化,用人們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現宏觀背景下的真實。
參考文獻:
[1] 劉潔,梁振紅,韓柳潔.紀錄片的虛構:與紀實一起抵達“深度真實”[J].中國電視(紀錄),2010(9):13-16.
[2] 顧小慈.淺析紀錄片的紀實與虛構[J].新聞研究導刊, 2016,7(12):198+216.
[3] 朱賢亮.紀錄片的虛構和非虛構[J].吉林藝術學院學報,2018(3):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