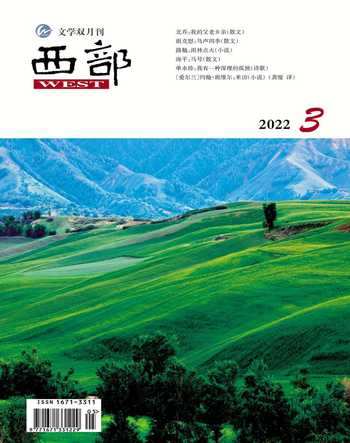圓圈
周齊林
一
薄暮時分,整個村莊被夕陽的余暉籠罩著。我與丙偉各自手里拿著一根粉筆,在墻壁上畫下蹩腳的圓圈。我們在比賽,看誰在墻壁上畫的圈圈圓,誰輸了就給對方一顆糖。一直到夜幕完全降臨,我們依舊沒分出勝負。次日醒來,晨曦中,我看見凹凸不平的墻壁上畫滿了不同形狀的圓圈。
童年時這一看似簡單的場景卻蘊含著生命的寓言,它隨著時光的流逝慢慢裸露出來,浮現在我們的腦海里。每個人都在各自的生命里畫著屬于自己的圓圈,我們用腳步丈量出生命的直徑。
歲月流轉,這是二〇一五年初秋時某天的黃昏時分,從異鄉回來養病的我每天和丙偉待在一起。薄暮下的村莊泛著柔和的光澤,我們緩緩穿過村落中央那塊空地時,隱約聽見在空地上納涼的幾個老人正竊竊私語著什么。“村子里三個得腎衰竭的年輕人,去世了一個,還剩兩個。” 見丙偉來了,老人們突然噤聲。這話他聽了無數遍,此刻傳到耳里,還是感到有些刺痛。在枯寂單調的鄉村,他沒想到自己成了鄉里人茶余飯后的談資。
兩天前大米的去世仿佛一聲巨響,驚醒了沉睡的故鄉。沒有任何娛樂新聞的村莊,因為一個人的死變得熱鬧起來。大米是我初中同學梅的二哥。大米比丙偉大五歲,他的死無形中提醒著丙偉。二〇〇六年大米在深圳南山一個建筑工地打工時,不慎從高處墜落,造成下肢癱瘓,整日臥床。彼時我讀大二,暑假從學校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正是晌午時分,一輛急救車呼嘯著從我身邊疾馳而過。隨后急救車戛然停止,我看見從車上抬下來的人正是從深圳大醫院送回來的大米。命運沒有出現向上的轉機,而是不停地往下沉。二〇一三年,癱瘓引發腎衰竭,大米的生命岌岌可危。
此刻,初秋時分,落葉飄零的季節,大米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這十年里,他終日睡在他家老屋的暗房里,屋里的那扇小窗自始至終開著,陽光慢慢斜射進來,落在他的臉上、鼻子上,落進他的眼里。有一年春節,我和丙偉去梅家拜年,在那間陰暗潮濕的小房間里,看到了癱瘓在床的大米,他微笑著朝我們點頭。環顧四周,我看見一株茂密的爬山虎攀緣到窗沿,在陣陣微風的吹拂下左右搖曳著,窗口的這抹綠映射出生命的荒涼。從窄小的房間出來,梅忽然對我和丙偉說,我哥哥經常望著窗口的那抹綠默默發呆。梅簡短的話仿佛一塊石頭在我心海里掀起陣陣漣漪。一整天,窗口的那抹綠和癱瘓在床的大米的渴望而渙散的眼神不時顯現在我的腦海里。爬山虎倚靠日復一日地攀緣不斷拓展著自己生命的直徑,不斷延伸的直徑讓生命的圓圈得以不斷放大。大米卻癱瘓在床,畫地為牢,他生命的直徑不斷變小,直至化成一個細小的點。
二
屋外激烈的鞭炮聲震醒了寂靜的村莊。鞭炮聲響了許久,滅了,村莊變得愈加寂靜起來。鑼一聲接著一聲地響著,遲緩、沉悶,嗩吶聲傳遍了山野,送葬的隊伍零零落落地沿著山間的小路走去。他看見大米睡在了牛角屏山腳下那個小小的土堆里,與他家只有一里路的距離。他妹妹紅花站在門檻前,就能看到他的墓地。丙偉從大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宿命。
穿著白衣的送葬隊伍稀稀拉拉地沿著山上的小路下來。那條小路他走了許多年,他想著自己終究也要化為牛角屏山上的一抹塵埃。前去送葬的人都得到了一把天堂傘。他母親帶著一把天堂傘回來,把傘塞進了抽屜里。他打開抽屜,久久端詳著這把傘,仿佛它就是離世的大米哥,正靜靜地躺在里面。
他靜靜地倚靠在窗前。窗外有兩條路,一條小路延伸著通向遠方,另外一條路通向他的學校,他每天在這條路上來回走著,路上的一草一木早已爛熟于心,閉上眼,他也能順利抵達學校。他曾經渴望沿著這條鄉村小路,走向遠方。老天仿佛畫了一個無形的圈,把他的一生圈在了里面。通往學校的那條小路平坦順暢,他的人生之路卻一直磕磕碰碰,滿是陷阱和深淵。
村里三個患腎衰竭的年輕人,除了已經去世的大米,另外兩個就是丙偉和他的舅舅。中秋前夕,他跟著母親去探望舅舅。八年前那個落雨的清晨,舅舅起床后忽然暈倒在地,送往縣醫院后被查出了尿毒癥。晴天一個霹靂,天仿佛坍塌了。他想起年幼時住的老屋,深夜的一場狂風暴雨吹垮了老屋,矗立在屋子中間的橫梁發出咔嚓的響聲,轉瞬便坍塌在地。雨夜,父親帶著他們借住在鄰居家。疾病的蛛絲馬跡早已顯露出來,這一兩年每天早上起來小便,舅舅忽略了馬桶里漂浮著的泡沫。他忽略了身體發出的細微求救聲,身體只有發出更大的警報和求救聲來引起他的注意。午后,在醫院寂靜的走廊上,舅媽摸著漸漸隆起的肚子,陷入悲傷的沼澤。她懷孕近四個月,此刻懷孕的喜悅慢慢變成無法逆轉的悲傷,她不知道是繼續走下去還是終止妊娠。“小華得了這個病,這個小孩怕是不健康呢。”在家里人的勸阻下,她還是把小孩引產了。雙重的打擊讓她跌入絕望的深淵里。休養好身體后,她強忍著悲傷,操持著家里的一切。那天到舅舅家已近中午,舅媽在廚房里忙碌著,十幾只雞在門外的空地上啄食。她把一箱牛奶和一箱蘋果放在桌子上,跟隨著母親進了舅舅的臥室。舅舅剛從縣城人民醫院透析回來,正躺在床上休息。見他們進來,舅舅蒼白的臉上露出一絲血色。舅舅是喜歡熱鬧的人,未生病前,每年春節都會做一桌豐盛的飯菜,然后帶著他們去附近小鎮的KTV唱歌。現在,喧囂散去,空留滿身的孤寂。命運變成了一出悲涼的獨角戲。舅舅每周要往返縣城透析三次,這個繁重的任務落在了年逾七旬的外公身上。站在學校教學樓的三樓,課間休息時,他經常會看見外公推著輪椅中的舅舅行走在那條通往遠方的小路上。他們往小鎮的汽車站走去,身影愈來愈模糊,直至變成兩個豆大的影子。舅舅沒多問他的身體情況,只跟他說了句“注意身體,別太累”。他們彼此心知肚明,知道這句話背后的深意。窗口擺著的一盆綠蘿正盛放著。回來的路上,他一直沒吭聲。他的母親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走上前,輕輕用手摸了下他的頭。他回頭看了母親一眼,五十出頭的她已經鬢邊發白。
三
在丙偉一次次的敘述里,我清晰地看到了他命運的紋路。那是一九八八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屋外寒風呼嘯,丙偉年逾七旬的奶奶抱著四歲的他在廚房的柴火旁烤火,不慎將他掉落在燃燒正旺的柴火堆里,火焰吞噬著他的臉。屋子里發出吶喊呼救聲,老人的臉上滿是驚恐。父母正在幾十里外的小鎮上趕集,匆匆趕回來時已是傍晚。面對兒子的責備,老人溝壑縱橫的臉上掛著淚痕。治療過程中,屋漏偏逢連夜雨,引起急性腎炎。臉上的燒傷治好后,急性腎炎最終轉化成慢性腎炎。
臉部的燒傷導致年幼的他下巴有一塊疤痕。他總是把自己關在屋子里靜靜地發呆。站在鏡子前,看著鏡中的自己,頓感陌生。去村里的小學上學時,同學們都奇怪地看著他。在學校受了委屈回來,他總是獨自躲在被子里哭泣。母親見他這么小就受了這么多磨難,心底頗為內疚,只有加倍疼他。
在隔壁鎮上讀高中時,因和同班同學在同一個飯盆里吃飯,他被傳染上了乙肝。那時的他沒食欲,渾身無力,噴香的米飯也難以咽下。肝腎都染上了慢性疾病,無異于雪上加霜。吃治療肝炎的中藥對腎臟不利。肝炎病情得到控制后,腎炎病情又加重了。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性腎炎越來越嚴重,高三他開始痛風。逢年過節,家家戶戶大魚大肉之時,他只能吃些素菜。吃葷就會引來疼痛。痛風成了一種自修課,一痛就會持續一周,疼起來雙腿不能動彈,他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仿佛癱瘓了一般。
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身體的疼,那種刺心般的疼痛。高考完,他去了福州大學大哥那里玩,大哥在福州大學讀研,土木工程專業。在那里他結識了一個年輕的醫學博士。在得知他痛風后,給他開了一個方子。服藥半年后,痛風得到了緩解,卻加重了肝病。原來方子里有一味藥叫雷公藤,有活血化瘀、消腫止痛的作用。雷公藤長著米白色的花朵,米白的花讓他想起爺爺下葬時插在墳墓上的白幡。它是治病的神藥,又是致命的魔鬼。這種藥毒性較大,雖然能治痛風,但對肝臟副作用很大。
七月,畢業的季節,烈日火爐般烘烤著大地。吃完班里組織的散伙飯,同學們各奔東西。宿舍里八個人,他一個個把他們送到火車站。回到宿舍已是深夜,廢棄的書本和生活用品散落一地。曾經喧鬧的宿舍寂靜無比。窗外馬路邊的霓虹燈散發出昏黃的光線,他站在窗前,望著窗外的世界默默發呆。宿舍八個人,七個人選擇了去廣東、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發展,只有他選擇回老家教書。一個月前,他已通過老家教育局的考試,分配到了離家十里路遠的一個小山村里當小學老師。疾病束縛著他遠行的腳步。他那個村小的老師大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報到的那天,一個年逾五旬的老教師問他,這么年輕怎么不出去發展,要回到這個窮鄉僻壤教書,他啞口無言。日子過得波瀾不驚,他每天騎著摩托車往返于學校和家,按時服用母親給他煲好的中藥。有時他會跟著幾個比他大十幾歲的同事去幾十里外的水庫釣魚,有時也會跟著他們上山打獵。鄉野的青山綠水讓他的心變得安靜了許多。這樣上山下水的機會不多,下課后同事們大都聚集在宿舍里打麻將,一根接著一根煙抽,屋子里云霧繚繞。“我們孩子都快有你這么大了,日子也就這么過了,你可不要學我們。”同事老余一邊打牌一邊抽煙,回頭看了一眼旁邊的他,意味深長地說道。老余在這個村小教了幾十年書了,是學校的教導處主任,他的兒子在浙江的一所大學讀大三。騎著摩托車回家的路上,遠處重巒疊嶂,樹木青翠,馬路旁的山野密集的墳墓矗立其間。想著適才老余對自己說的話,他感到憂傷,疾病會加速把他推進路邊的墳墓里。多年后在宿舍里打麻將的同事在家里抱孫子,頤養天年時,他想那時自己應該靜靜地躺在了墳墓里。
他所任教的石里小學離他的家里有近十二里的路程,他每天騎著摩托車往返,風里來雨里去,也甚辛苦。一個冬日,天空下著綿綿細雨,雨水打濕了路面,他騎著摩托車與迎面疾馳而來的大貨車會車,大貨車幾乎占據了整個路面。龐大的貨車映襯出他瘦弱的身軀,路坑里的水濺了他一身。貨車險些擦著他的摩托,他一扭方向盤,連車帶人掉進了一旁的水溝里,頓時渾身濕透。
一年后,通過熟人的幫忙,他順利調到了離家只有三百米的東里小學,上班的路便捷起來。他回想自己的來路,同齡人都在一年又一年的漂泊里與故鄉愈來愈遠,而他的人生軌跡則是不斷地靠近故鄉,靠近那盞熟悉的燈火。
命運并沒有給他喘息的機會,而是步步緊逼,一次次把他推到懸崖邊。二〇〇九年夏天,起初他只是感到渾身乏力,身體變得消瘦,直到有一天同事們見了他都擔心地問他臉色怎么變得這么蠟黃。他渾身仿佛涂抹了一層暗黃色,這是一種病態的色彩。他心底一驚,去醫院檢查,發現是肝硬化壓迫脾臟,血紅蛋白已經降到四十,必須盡快進行脾臟切除手術。拿著化驗單,他靜坐在醫院的走廊上,陷入虛無中。這個結果讓母親的心徹底涼了下來。母親抱著他,無助地流著眼淚。
半個月后,在南昌的省醫院,肝膽科的醫生面對他復雜的病情,告知手術風險太大,很容易命喪手術臺。醫生建議他轉院,或者回家保守治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醫生的話說得委婉。如果不做手術,回家就意味著死亡。他還想繼續活下去,哪怕多活一天,他也能多看幾眼這塵世溫暖的陽光。省城的人民醫院人滿為患,許多人為一個床位而焦灼地等待著。醫院不敢手術,催著他早日出院。他一直堅持著不出院,“出了什么風險,我不要你們負責。不做手術我只有死路一條,做手術我還有一線生機。我情愿死在手術臺上。”他的一再堅持讓肝膽科的主任深受觸動。權衡之下,主任做了立刻手術的決定。兩個實習醫生推著他進手術室時,看著他毫不緊張的神情,朝他豎起了大拇指。醫生安慰他不要緊張,他笑著說沒事。五個小時后,從手術室推出來,脾臟順利摘除。主治大夫朝他豎起了大拇指。從醫多年,他很少見過這么看淡生死的病人。一個月后,從鬼門關走了一趟的他回到了老家。汽車緩緩駛入鄉野,坐在車上的他聞著田野里熟悉的泥土氣息,仿若重生。
脾臟把人體精微的營養輸送到身體的各個角落。 脾臟切除后,免疫力驟然降低,他的身體變得異常虛弱。春天,他躺在床上,看著窗外油菜地里閃爍著的陽光,心底是歡喜的。不時有親戚和朋友來家里看他,送一些雞蛋、水果或者幾百塊錢。
疾病加重著一個人的貧窮。從讀大學開始,他一直在吃西藥,每個月要花費一千多。做完脾臟切除手術后的一年,每個月吃中藥和西藥的費用增加到了三千多。在鄉村小學做老師,轉眼十多年過去,他的工資剛好四千。一個月的工資剛剛夠他每個月的醫藥費。手術后第一年,每個月的醫藥費是他哥哥負擔。第二年,他沒再麻煩他大哥,哥哥在南昌工作,有兩個小孩,生活的重壓如影隨形。
為了省點錢,他去縣城圖書館買了幾本專業的藥用書籍,對照著上面與自己相同的病歷,然后照著書上的藥方去藥店抓藥。母親看他隔三岔五去藥店抓藥,問他哪里來的藥方。他搪塞過去,不敢告訴她真相。
他孤注一擲,決定拿自己的身體做實驗。有一次,當天黃昏把藥煎好,服下,到了晚上,忽然尿不出尿來。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仿佛熱鍋上的螞蟻,膀胱越來越脹,身體幾乎要炸裂開來。看著窗外濃濃的黑夜,他陷入巨大的恐慌。去醫院需要一個多小時。一直熬到半夜,正當他一臉絕望準備去醫院時,閘門開啟,一泡尿終于尿了出來。躺在床上回想起去藥店抓藥時,藥店老板指著藥方上的一味藥說,熟附片沒有,用生附片可以嗎? 他說可以。深夜迅速打開電腦,查生附片的藥效,原來一字之差,生附片服用后對身體泌尿系統有很大影響。時間已是下半夜,他離開電腦,望著窗外的沉沉黑夜,忽然悲從心來。他一抬頭,仿佛就看見了自己的宿命。在自己日漸不堪的軀體里,他看見死神正加快步履朝他趕來。他站在房門口,聽見隔壁傳來母親微弱的鼾聲。疾病長久的折磨,對于生死,他早已看透,只是想起日漸年邁的母親,心禁不住涌起陣陣心酸。年近四十,未曾孝敬過父母一回,一直讓父母擔憂。而母親,一直擔心著她哪一天老去,誰來照顧多病的兒子?
年底,村里在外打工的人都回來了。高中同學輝跟他說起剛在外買下一套房子的事,月供要三千五,一個月工資才五千八,上有六十多歲剛做完大手術的母親,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壓力巨大。他說你身體這么棒,怕什么,熬一熬就緩過勁來了。回家的路上,他想起自己這些年每個月的藥費三千多,也相當于供著一套房子,相當于房奴。身體的宮殿岌岌可危,只能靠每天煎服中藥來延緩肉體這座房子隨時坍塌下來的危險。
房子是棲息之地,是生命溫暖的港灣。父母縫縫補補,蝸牛般吞吐唾液,搭起沉重而結實的殼,讓年幼的他們免遭風雨的侵襲。老屋坍塌后,父母用多年的積蓄給他弟弟一家四口蓋了一棟新房。父母打算給他也建一棟房子。打地基時,被他強行制止了。那晚,昏黃燈光的映射下,他用央求的語氣說,爸,媽,你們把給我建房子的錢好好存著,將來老了好養老。母親看著他乞求的神情,不由眼角溢出一滴淚來。以防不測,他買了兩項大病保險和汽車意外險,哪天他離去,這些保險能給他父母的晚年提供一些保障,這樣長眠地下的他會安心許多。
我時常會寄一些文學類的書籍給他看。他最喜歡看史鐵生的散文集,看了好幾遍,對一些段落爛熟于心。“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他說這句話對他觸動很大。每次身體的劇烈疼痛讓他心灰意冷,自殺的念頭在心底涌起時,他就會想起這句話,想起史鐵生。他感覺自己有了強大的精神后盾。當身體的疼痛潮水般退去,希望的曙光瞬間透過窗戶映射在他眼底。
四
初中同學明從上饒師范學院畢業后,選擇了回到老家文竹中學教書。逢年過節回到老家,我一次又一次地問他為何不趁年輕去外面闖一闖,要年復一年地困死在這個山村中學教書時,明淡然一笑道,在哪里都是過一輩子,我在家里雖然過得平淡,但也安逸,還能照顧家里日漸年邁的父母。明的話讓我陷入深思,我長年漂泊在外,無法照顧疾病纏身的母親。當我在外為生計奔波而撞得頭破血流時,明正在距離學校二十里地的水庫里垂釣。他喜歡釣魚,說釣魚能讓他的心安靜下來。寒暑假時,他也會到市里做培訓,掙一些碎銀子,改善家里的生活。
明與丙偉是堂兄弟。明有健康的身體和淡然的性格,他平淡而安逸的鄉村教師生活映襯出丙偉鄉村生活的傷痕累累。明用健康的體魄給自己的人生畫下巴掌大的圓圈,圈圈的線條色澤清晰而明亮。
丙偉是因病困在家里,我身邊有不少在外漂泊的人,是身患重病后不得不離開打拼多年的城市,回到熟悉而陌生的故鄉。不時有熟悉的人抱病歸來,他們面色灰暗,神情焦灼。城市是沒有硝煙的戰場,是前線,而寂寥的鄉村是受傷的戰士養病的地方。故鄉成了他們的療養地,部分人在經過短暫的療養后,重新回到了城市里討生活,還有一部分人長久地留了下來,他們虛弱的身體無法再支撐他們回到城市。
他們以迅速奔跑的姿勢不斷拓展著自己生命圓圈的范圍,一步步遠離故鄉,直至與故鄉愈來愈遠;卻又因疾病而轉身,生命的圓圈慢慢萎縮,直至重新回到巴掌大的村莊里,步履維艱。
不時有人加入留守鄉村的隊伍里。城市高速旋轉的機器容不下一顆生銹的螺釘。高中同學群在剛剛組建的那段時間熱鬧了一陣子兒,興奮勁一過,變得寂靜,不再有人在群里說話。勇鋒患尿毒癥的消息無異于一顆炸彈,引爆了同學群。同學們在群里議論紛紛,為捐款出謀劃策。記憶中的勇鋒身體強壯,高中三年堅持洗冷水澡,無論春夏秋冬。冬季降臨,當我們在為一瓶熱水而爭得“頭破血流”時,他提著一桶涼水朝我們輕蔑地一笑,而后一邊哼唱著歌曲一邊洗起澡來。他的壯舉引起了我們的圍觀,不時有路過的女生朝這邊張望。不知道勇鋒大學畢業后這些年經歷了什么,只隱約得知他從事銷售行業,為了簽單經常陪客戶喝得爛醉如泥。現在他曾經通過喝酒而簽下的單掙下的錢,都成為他救命的藥費。過濾的血液通過管子重新流入他的體內。紅色的血液仿佛他當初在異鄉的酒店喝下的一瓶瓶鮮紅的葡萄酒。勇鋒加入了丙偉留守的隊伍,相同的病情讓他們彼此憐惜。
命運在不斷地下沉。有的人離鄉時還是活蹦亂跳的青年,回鄉時卻變成了灰燼。我在東莞多年的好大哥閆永群,在東莞漂泊多年后,終于在東莞大朗碧桂園買下一套漂亮的房子。他有兩個爭氣的孩子,一個讀小學,一個讀初中,成績很好。他邀請我去他家里玩,去的前一晚提前打電話詳細問我喜歡吃什么菜。次日到了他家,他做了一桌我喜歡吃的菜。寒冬來臨時,他快遞了一件毛衣給我,囑咐我在外多注意身體。我羨慕他有這樣一個溫馨的家庭。然而世事無常,命運露出猙獰殘酷的一面。二〇一四年年初,永群哥忽然暴瘦二十多斤,很快就被查出黏液腺癌。在病痛中苦苦掙扎一年多后,永群哥帶著不舍離開了人世。他兩個年幼的孩子伏在他漸漸冰涼的身上號啕大哭。身材健壯的他變成了一個窄小的骨灰盒,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河南老家。一年后在惠州參加一個活動時,遇見一個東莞大朗的文友,我才得知病痛中的永群哥寫下了“擊碎病床燈”的詩句。這簡短的五個字映射出他對塵世的諸多不舍。
從我的高中同學勇剛到永群大哥,他們以相同的方式離鄉,有的人衣錦還鄉,有的人抱病而歸,有的人歸來時已奄奄一息,還有的人已化為灰燼。更多的人一輩子都留守在巴掌大的村子里,畫地為牢。
丙偉與我提著水果驅車來到江畔村看望病重的勇鋒。勇鋒從縣城透析回來。他見我們來,臉上露出僵硬的笑。他正在為女朋友離去的事而憂傷。他早已做好了主動與女朋友分手的打算,但現實比他想象的要殘酷。自從被查出尿毒癥,女朋友就與他劃清界限,不再聯系他了。
五
從勇鋒的情感遭遇里,丙偉不由聯想到了心中的她。
身邊的90后紛紛結婚生子,一九八四年出生的他感到恐慌,村里三十五歲還沒結婚的就剩他一人了。他渴望愛,卻又不敢愛。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整日待在家里,足不出戶。每次走出房門,村里人總會用異樣的眼神看著他。他們問他怎么還不結婚。不時有媒婆上門來為他介紹女孩子,都被他憤怒地趕了出去。在鄉里人眼里,他成了一個怪人。與他家有矛盾的鄉里人,每次在路上與他擦肩而過,總是用意味深長的眼神看著他,嘴角露出一絲冷笑,眼底滿是不屑的嘲笑和可憐的復雜意味,他視而不見。然而當這種帶有明顯優越感的示威降臨到父母頭上,他就感到內心的傷仿佛被撕裂開來。他把自己關閉在屋內,自虐般緊握拳頭,使勁捶打墻壁,直至拳頭溢出血絲。他用這種自虐的方式來緩解內心的壓抑和無奈。
在他日漸蒼老的母親苦口婆心的勸說下,他跟吉安泰和縣一個離異的女人見了面。女人有一個六歲的兒子,他心中的忐忑頓時緩解了許多。見面的那一刻,當滿臉紅潤的女人出現在他面前,他還是感到了恐慌和內疚。女人紅潤健康的臉色映襯出他臉上的灰暗。一種無形的壓力籠罩在他的頭頂。女人叫娟,說你的身體情況,你媽媽都事先跟我說了,我不在乎,只要你對我好就行。女人顴骨突出,臉頰上有幾個小黑斑。她這突如其來的話一下子把他心頭的疑慮打消了。她的話讓他很感動。沖著這句話,他發誓一定要對這個女人好。娟的前夫嗜酒,經常喝得醉醺醺,借著酒意打她,下手又狠,把她打得鼻青臉腫,甚至肋骨斷裂,醒來卻又哭著跪在她面前懺悔。酒醉時,他是一只面目猙獰的獅子,酒醒后,卻是一只看似可憐的綿羊。殘酷的家暴令她漸漸絕望。反反復復兩年多,她終于下定了離婚的決心。
他開始頻繁往返于文竹村到泰和,周末在那里住兩晚,再返回家里。一切仿佛塵埃落定,他們甚至已經談好了準備結婚的種種細節。母親建議,結婚那天暫時不要把她的孩子帶過來。他覺得無所謂,不在乎外人的眼光。她那個好賭的哥哥經常以他妹妹結婚作為籌碼,向他借錢,帶著要挾的口吻。第一次他借了三千塊錢給他,隔了不到一個月,他又要借五千。丙偉果斷地拒絕了。他開始給丙偉穿小鞋,每次去看望娟,他都指桑罵槐,堅決不同意他們的婚事。
這天,他驅車從娟的家里返回文竹村的路上,右拐是一望無垠的田野,忽然一個人影從盛放的油菜地里竄了出來。他緊急剎車,險些撞到對方。他按了幾次喇叭,對方卻站在路中央不動。他正準備下車時,這個人忽然疾步走到車窗前,從背后亮出一把金光閃閃的刀。突如其來的刀讓他感到恐慌。他試著讓自己安靜下來,看了對方一眼,眼前這個男人臉上掛著一塊細長的疤痕。這刀疤讓他瞬間明白了對方是誰。“你要是敢跟她結婚,我就對你不客氣。”刀疤臉把明晃晃的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厲聲說道。那晚回到家,他依舊心有余悸,不知道當時自己說了些什么,又是如何逃脫的。
夜色幕布般慢慢覆蓋在大地上,遠處的燈火在夜風中搖曳著,縷縷炊煙讓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溫暖。他驅車返回學校,看到鎮中學體育老師的白色別克車停在學校的操場上。學校宿舍里,那盞他熟悉的燈亮著,房門緊閉。房間里的女孩與他同教四年級數學,曾表露過喜歡他的想法,被他委婉拒絕了。他鼓勵她趁年輕好好拼一把。她是積極的離鄉者,而他這些年,如一顆釘子深深嵌入故鄉的土地里,直至銹跡斑斑。幾分鐘后,他看見鎮中學的體育老師載著她駛出了校門,車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他緩緩往家的方向走去。走到距離家門口五十米的地方,他看見鄰居家的兩個小孩借著屋檐下昏黃的燈光,在他家新房的墻壁上用粉筆畫著圓圈。見他走來,兩個畫得起勁的小孩一哄而散。這一幕如此熟悉,恍若如昨。他用手輕輕撫摸著墻壁上那一個個蹩腳的圓圈,那些細碎的往事又浮現在他的腦海里。疾病這把無形的手早已給他畫下一個巴掌大的圓圈,這是無形的牢籠。這些年他像一頭猛獸般在牢籠里橫沖直撞著,直至筋疲力盡、鮮血直流。他開始像他的父母和祖輩那樣在巴掌大的村莊安心地活著,一輩子也不曾離開過村莊。
他繼續走著。家近在咫尺,就在眼前的這棟房子里。家又在看不到的遠方。走進房間,他躺下,繼續翻開那本熟悉的《我與地壇》。夜深了,我忽然收到他發來的微信。他說雖然因病被困在了村里,書籍卻時刻讓他的生命充盈著、行走著。
望著這條信息,我久久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