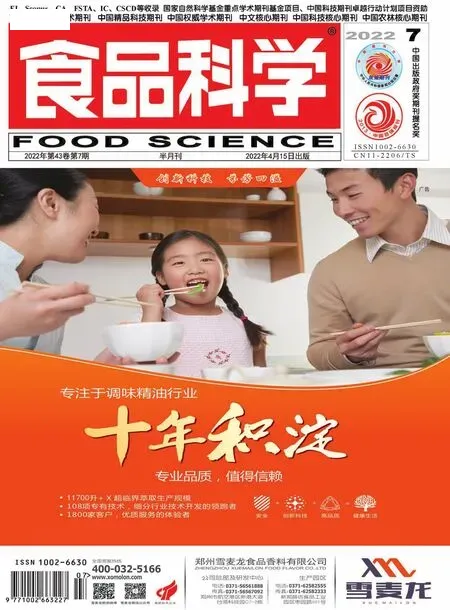花色苷遞送系統研究進展
馬小強,白衛濱,陳嘉莉,孫建霞,*
(1.廣東工業大學輕工化工學院,廣東省植物資源生物煉制重點實驗室,廣東 廣州 510006;2.暨南大學理工學院,食品安全與營養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632)
花色苷作為植物中常見的功能色素物質[1-4],具有廣泛的生理功能,如抗氧化[5]、抗癌[6]、抗肥胖[7]、預防心血管疾病[8]等。然而研究發現,花色苷穩定性較差,加工過程中容易受到溫度、光照、pH值等環境因素的影響,發生不同程度的降解[9-10]。此外,有研究表明花色苷進入人體后的生物利用度較低[11-14]。花色苷的生物利用度取決于食物基質、其他食物成分以及花色苷的結構。其中,花色苷結構是生物利用度的決定性因素,如以3-羥基花色苷為基礎的花色苷比B環上有更多取代基的花色苷更容易被吸收[15],而親水性基團較多的花色苷比羥基數量較少、親水性較低的花色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16];酰化作用能夠提高花色苷的穩定性,但同時會顯著降低其生物利用度[17]。花色苷被人體攝入時,通常會與不同的食物基質結合,從而影響人體對花色苷的吸收[18-19]。
花色苷消化吸收過程如圖1所示,從口腔開始,一部分花色苷在中性/弱堿性pH值條件下轉化為查耳酮形式,并且口腔內的微生物也可以將花色苷裂解為小分子化合物,目前原兒茶酚酸和間苯三酚醛已被證實是其主要的降解產物[20]。由于食物很快被送到胃中,口腔對花色苷的降解作用可以忽略不計。當食物到達胃時,花色苷在胃中的狀態是相對穩定的[21]。雖然花色苷會被部分降解,但是隨著食物的攝入,花色苷含量也在增加,降解作用會被抵消,且花色苷在胃中是可以被吸收的。研究表明,花色苷可以通過不同的胃細胞模型轉運,并且其吸收速率與孵育培養時間、pH值、花色苷結構以及相對分子質量有關[22]。在胃細胞模型中,隨著接觸時間的延長和花色苷濃度的提升,花色苷的吸收增加[23]。據報道,單體花色苷可能比其衍生物具有更高的吸收速率[22,24]。食物從胃部到達腸道后,未被胃吸收的花色苷進入小腸的堿性環境中,主要以甲醇假堿形式存在。花色苷可通過被動轉運和主動轉運的形式被腸上皮細胞吸收。小腸上皮細胞對花色苷的吸收受花色苷分子大小和結構影響,但糖苷部分對矢車菊素型花色苷的吸收沒有影響。此外,花色苷代謝迅速,除了進入血液循環以外,還會以完整或者代謝產物的形式進入到膽汁中[25]。進入膽汁的花色苷及降解產物其中一部分被小腸重吸收,由門靜脈重新回到肝臟,另一部分則進入大腸,隨糞便排出。

圖1 花色苷在人體內的消化過程示意圖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nthocyanins passing through the human digestive system
如何穩定花色苷結構、降低花色苷在胃腸道的降解速率、提高細胞的吸收率,成為花色苷進一步應用于食品、藥品等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迄今為止,許多研究表明利用遞送系統給藥是一種有效提高花色苷穩定性和生物利用度的方法[26-27]。
遞送系統是一類應用前景廣闊的定向、定位、控釋給藥載體系統。它是將功效物質吸附、包埋或直接連接于載體,利用載體的理化性質和選擇性分布特點,從而解決藥物在遞送過程中存在的溶解度低、穩定性差和吸收受限等問題,除此之外,遞送系統還能夠增加藥物的溶出速率和吸收速率,提高生物利用度。總的來說,遞送系統在藥物輸送方面具有許多優越性:1)控制藥物釋放、延長作用時間;2)靶向藥物遞送;3)在保證藥物作用的前提下,減少用藥劑量,減輕或避免不良反應;4)提高藥物的穩定性及生物利用度[28-29]。遞送系統為改善藥物的穩定性等問題提供了較理想的給藥手段。
近年來,研究發現利用蛋白質、多糖等天然生物大分子以及脂質等作為制備微囊、納米顆粒、乳液、脂質體等的遞送載體,具有優良的生物相容性、安全、無毒等優點[30],可用于食品功能因子的遞送,對于改善功能活性物質的穩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實用價值。
常見的花色苷遞送系統包括:1)蛋白質-花色苷遞送系統;2)多糖-花色苷遞送系統;3)脂質體-花色苷遞送系統;4)復乳體系遞送系統;5)復合遞送系統。花色苷的緩釋對于所負載生物活性物質的潛在生物活性和生物利用度至關重要,以下針對5種主要的花色苷遞送系統進行介紹,以期為花色苷在食品及其他行業中的進一步應用提供參考。
1 蛋白質-花色苷遞送系統
常見的蛋白質類載體材料包括動物來源的乳清蛋白、酪蛋白、明膠等,以及植物來源的大豆蛋白和玉米醇溶蛋白等。動物源性蛋白質具有良好的成膜性、較好的生物相容性等特點[31],可以迅速分散形成穩定的乳化液。植物源性蛋白因其來源豐富,所以加工成本低,并且具有較好的成膜性和一定的抗氧化性。
乳清蛋白和酪蛋白是天然乳蛋白中的主要成分,常作為壁材保護生物活性物質。乳清蛋白是一種具有較高親水性的致密球狀蛋白,酪蛋白含有較多的親水基團和疏水基團,常以球狀膠束的形式存在[32]。Liao Minjie等[33]利用酪蛋白和乳清蛋白,通過噴霧干燥技術制備了負載花色苷的微粒。花色苷和蛋白質主要多肽鏈中的C、N和O通過氫鍵結合,形成的酪蛋白和乳清蛋白微粒的包埋率分別為(49.73±0.68)%和(59.99±0.49)%。同時花色苷和蛋白質通過非共價結合改變了蛋白質的三級結構,使內源性疏水氨基酸更具親水性。通過體外胃腸消化模擬,負載花色苷的酪蛋白和乳清蛋白在胃液中表現出穩定的蛋白質結構,有利于維持微粒的結構和保留花色苷,胃消化結束時,兩種微粒的釋放量遠低于單體花色苷,花色苷在微粒進入腸液后得到釋放。在小腸環境中,兩種微粒的釋放時間從180 min延長到300 min,最終釋放率分別為52%和40%。Wu Yue等[34]研究了不同載體材料在體外模擬胃腸消化和結腸發酵過程中對花色苷釋放和降解以及腸道菌群調節的影響。其中,大豆分離蛋白可以通過疏水作用和靜態猝滅與花色苷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增強花色苷的穩定性,包埋率可以達到(91.89±1.71)%。并且在體外消化2.5 h后,經大豆分離蛋白包裹的花色苷微囊中花色苷的釋放率最低,為27.1%。其次為明膠包裹的微囊,包埋率為(89.45±1.47)%,在體外消化中花色苷的釋放率為28.7%;而未微囊化的花色苷釋放率為70.9%,大豆分離蛋白和明膠顯著降低了花色苷在體外模擬胃腸消化中的釋放率,對花色苷起到了較好的保護作用。且實驗結果表明微囊化增強了花色苷的結腸可及性,使花色苷更容易到達結腸,并利于腸道微生物的利用。
目前對花色苷遞送系統的研究主要基于體外胃腸模擬,而關于體內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的研究甚少。Mueller等[35]通過讓志愿者攝入負載花色苷的乳清蛋白微粒,研究其尿液、血漿和腸道流出物中的花色苷及其降解產物,并與攝入花色苷志愿者的數據進行比較。結果表明,與攝入花色苷相比,攝入乳清蛋白微粒會導致尿液中花色苷及其降解產物濃度升高,可能會增加花色苷在體內的濃度和短期的生物利用度。但是,其實驗結果并未表明乳清蛋白微粒可以在腸道環境中穩定花色苷,尿液中花色苷及其降解產物含量高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通過乳清蛋白延長花色苷在胃中的停留時間實現的。除了傳統的蛋白質類壁材,Liu Yuqian等[36]對廣泛分布于植物、動物、細菌和真菌中的鐵蛋白進行了綜述,發現鐵蛋白具有納米級的殼狀結構和可逆的自組裝特性,可以達到穩定、溶解和靶向遞送的目的。同時,可以利用鐵蛋白的電荷特性和可被修飾的外表面從而提高鐵蛋白的穩定性和花色苷的生物利用度。但其包埋率較低,并且由于鐵蛋白在胃腸道中不穩定,需要利用共價作用以及非共價作用對鐵蛋白外表面進行有效的修飾,從而抑制其在胃腸中的降解。Zhang Tuo等[37]利用鐵蛋白的可逆解離和重組對花色苷分子進行包埋,花色苷分子與鐵蛋白內表面的氨基酸殘基之間有著強相互作用,一個鐵蛋白殼層中負載了(37.5±4.5)個花色苷分子。這種包裹作用使花色苷分子的熱穩定性和光穩定性提高了約2 倍,并且與游離花色苷相比,包裹在載鐵蛋白納米籠中的花色苷分子被Caco-2細胞吸收的速率更高,具有更高的轉運效率。
2 多糖-花色苷遞送系統
多糖是單糖的聚合物,可獲得性廣、價格低廉,并且容易進行化學修飾,此外還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因此被廣泛應用于微載體藥物遞送系統[38]。瓊脂、海藻酸鹽、卡拉膠、殼聚糖、纖維素、瓜爾豆膠、果膠、淀粉和黃原膠等多糖的分子結構和功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的生物來源、提取方法和后續加工方式[39]。
殼聚糖是一種聚陽離子多糖,由天然甲殼素經堿性脫乙酰化而成,無毒并且具有較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40]。殼聚糖已被開發出各種納米結構,如納米顆粒、納米水凝膠、納米纖維和納米復合材料,這些納米結構已成功應用于各種生物活性化合物的遞送[41]。Sun Jianxia等[42]將殼聚糖、殼寡糖、羧甲基殼聚糖與離子交聯劑γ-聚谷氨酸或氯化鈣復合,制備了殼聚糖納米粒子。與其他幾種殼聚糖納米粒子相比,花色苷-羧甲基殼聚糖-氯化鈣納米粒子具有最高的包埋率(53.88%)和載藥率(5.11%),并且具有較好的粒徑(最小粒徑可以達到180 nm)、良好的穩定性和血液相容性。這是因為包埋率受材料的極性和花色苷作用影響。羧甲基殼聚糖是帶負電荷的多糖,相比帶有正電荷的殼聚糖,更容易與帶有正電荷的花色苷發生作用,花色苷的羥基也會與羧甲基殼聚糖的羧基和氨基發生作用。該研究還表明花色苷-羧甲基殼聚糖-氯化鈣納米粒子是溶酶體環境中最適合調節細胞凋亡的遞送系統,釋放率可以高達75%。
盡管殼聚糖可以提高花色苷的穩定性,但是其在酸性條件下易發生解離,導致在胃環境中藥物的快速釋放,這限制了殼聚糖在口服遞送系統中的應用[43]。因此,殼聚糖常和其他壁材一起用于提高整個遞送系統的穩定性。Tan Chen等[44]以接骨木提取物為花色苷來源,利用殼聚糖和硫酸軟骨素通過靜電作用絡合形成花色苷聚電解質復合物,其包埋率最高可達88%,粒徑約為350 nm。多糖基聚電解質復合物的結構受pH值和多糖濃度的影響,由于花色苷在強酸性條件下更穩定,所以多糖溶液均調節到pH值為3。在此pH值條件下,硫酸軟骨素中的磺酸基處于部分電離狀態,并與殼聚糖中完全電離的氨基發生強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穩定、均一的聚電解質復合物。研究還表明,與單獨的花色苷相比,花色苷聚電解質復合物能夠改善花色苷抗氧化活性和穩定性。Zhao Xue等[45]為了提高花色苷的穩定性,以帶正電荷的殼聚糖和帶負電荷的果膠為原料,采用靜電自組裝的方法構建花色苷納米載體(圖2)。結果表明,殼聚糖/果膠/花色苷的質量比為1∶1∶3時,納米載體為粒徑在100~300 nm之間分散良好的球形。花色苷的包埋率為66.68%。體外消化實驗表明,包埋后的花色苷在胃酸環境中較穩定,在腸環境中得到緩慢釋放。在體外細胞模型中,通過細胞存活率和細胞凋亡實驗證明了納米載體對丙烯酰胺誘導的細胞損傷有保護作用。運用秀麗隱桿線蟲模型進行研究進一步發現,花色苷納米載體可以延長線蟲的壽命,增強線蟲對氧化應激、熱休克、紫外線輻射和老化等不良反應的抵抗能力。這些結果表明殼聚糖-果膠納米顆粒可以作為載體來提高功能性因子花色苷的穩定性和生物利用度。

圖2 果膠-殼聚糖納米粒負載花色苷的示意圖[45]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pectin-chitosan nanoparticles loaded with anthocyanins[45]
海藻酸鹽也是一種常見的多糖類壁材,其來源豐富、無毒、可生物降解。Zou Chao等[46]的研究表明,帶正電荷的花色苷和帶負電荷海藻酸鈉的羧基之間存在靜電相互作用,同時花色苷上的羥基氫原子可以通過氫鍵與海藻酸鈉上的氧原子成鍵,使得花色苷和海藻酸鈉形成絡合物,在模擬腸道消化中的穩定性顯著提高。在模擬腸條件下30 min,花色苷的生物可及性只有大約64.2%,花色苷的生物可及性在90 min(生物可及性74.2%)和120 min(生物可及性69.5%)保持較高水平。通過小鼠模型進一步驗證了海藻酸鈉對花色苷的吸收促進作用。小鼠灌胃給藥1 h后,測定血清和糞便中的花色苷含量。結果表明,海藻酸鈉的結合作用使花色苷血藥濃度提高27.40%。相反,糞便中花色苷的含量顯著降低。通過其他天然聚合物與海藻酸鹽結合,可以獲得在酸性條件下更穩定、更好的遞送系統,從而特異地在腸道中釋放,并提高降解率和藥物包封率。Kanokpanont等[47]制備了海藻酸鈉-殼聚糖復合微粒以提高花色苷的穩定性和生物利用度。海藻酸鹽與殼聚糖通過靜電作用形成復合微粒,粒徑大約為500 μm。結果表明,海藻酸鹽微粒在質量分數0.05%殼聚糖溶液中反應而成的海藻酸鹽-殼聚糖微囊體系是適合包埋花色苷的體系,能夠包埋較多的花色苷,并且在模擬胃液條件下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在模擬腸液中能實現花色苷的緩釋。
卡拉膠是一種天然紅藻多糖衍生物,具有形成親水膠體、增稠、穩定分散等特點[48]。由于卡拉膠具有帶負電荷的磺酸基團,可以與具有相反電荷的花色苷通過靜電相互作用形成聚電解質復合物,有助于實現藥物的控制釋放,從而提高藥物的生物利用度[49]。疏水相互作用和分子間堆積在復合物的形成中也起著重要作用。Jeong等[50]用殼聚糖和卡拉膠作為壁材負載含有花色苷的濃縮果蔬汁,并研究了其在體外胃腸模擬體系中的穩定性以及氧自由基吸收能力。殼聚糖的氨基與卡拉膠的磺酸基之間在胃的酸性條件下表現出強烈的離子相互作用,然而在腸道條件下,氨基被中和,導致兩個官能團之間的離子相互作用減弱,從而使納米顆粒膨脹,粒徑增大,實現芯材的釋放。與未經包埋的游離果蔬汁在腸條件下的抗氧化穩定性迅速下降相比,納米微粒中的芯材在緩釋過程中受到壁材的保護,具有相對較強的抗氧化穩定性。
3 脂質體-花色苷遞送系統
脂質體遞送系統已被認為是一種用來改善藥物在體內遞送局限性的方法,具有良好的生物利用度和治療效果[51]。脂質體是由磷脂或合成的兩親化合物組成的雙層微球形囊泡,具有疏水和親水性區域[52]。它們是由疏水相互作用作為主要驅動力和其他分子間作用力共同作用形成[53],可以用于遞送各種親水性和疏水性物質。由于無毒、無免疫原性、生物相容性、可生物降解性和兩親性,脂質體在遞送藥物和食物等方面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Quan Zhao等[54]通過乙醇注射法利用磷脂酰膽堿和膽固醇制備花色苷脂質體,制備的微球粒徑和包埋率分別為(234.00±9.35)nm和(75.000±0.001)%。并且該學者以總抗氧化能力和丙二醛含量為指標評價花色苷脂質體的抗氧化活性,結果表明,花色苷脂質體能明顯提高總抗氧化能力,降低丙二醛含量,通過激活相關的抗氧化途徑保護人GES-1細胞免受H2O2誘導的胃黏膜損傷,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和調節細胞生物活性的作用。Zhao Lisha等[55]利用超臨界二氧化碳法制備了花色苷脂質體,其粒徑為(159.0±0.2)nm,包埋率為50.6%。花色苷和磷脂的磷酸基團之間存在靜電相互作用,同時花色苷和磷脂的羥基之間形成氫鍵,且隨著花色苷的濃度增加顆粒的均勻性降低。脂質體中的花色苷在模擬胃液中釋放緩慢,在模擬腸液中釋放較快,這主要是胰蛋白酶對囊泡的降解所致。有研究通過體外體內實驗發現,脂質體形式花色苷的抗糖基化活性優于游離花色苷形式,可用于糖尿病的治療[56]。
雖然傳統的脂質體在遞送中有著廣泛的應用,但是也存在局限性,如雙層膜與血液中的循環蛋白發生相互作用,并被網狀內皮系統的某些巨噬細胞攝取,從而導致血液循環時間短,并迅速從血液中排出[51]。研究人員開發出固體脂質納米粒來改善傳統脂質體的局限性。固體脂質納米粒是由固體脂質在乳化劑的作用下穩定在水分散體中,將藥物包裹于固體脂質中,減少了藥物與水分散相及外界環境的接觸,提高了藥物的穩定性(圖3)。固體脂質納米粒可以有效地遞送各種分子,包括親脂和親水分子。此外,固體脂質納米粒還具有較好的生物相容性、可擴展性等優點。Ravanfar等[57]將此技術運用于花色苷遞送,將花色苷負載到納米球形顆粒中,包埋率為(89.2±0.3)%,平均粒徑為(455±2)nm。此外,該學者還研究了花色苷納米顆粒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沖液中的體外釋放情況,以及不同溫度下,在pH 7.4磷酸鈉-檸檬酸鈉緩沖液中的短期穩定性。結果表明,固體脂質納米顆粒可以提高花色苷在pH值和溫度較高情況下的短期穩定性。關于固體脂質納米粒應用于花色苷遞送中還需要通過體外模擬體系和動物實驗進一步驗證。

圖3 傳統脂質體和固體脂質納米粒示意圖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ditional liposomes and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4 復乳體系遞送系統
復乳也稱為二級乳,是在單乳基礎上進一步乳化而形成的具有雙層或多層乳化結構的復合體系[29]。指將簡單乳液包裹于另外一種連續相中,簡單地可以分為將水包油型單層乳液分散于油相中(O/W/O)、將油包水型單層乳液分散于水相中(W/O/W)、將固體分散于油相中再分散于連續的水相中(S/O/W),其中W/O/W型乳液是比較常見的類型。復乳作為載體能夠保護內水相或油相物質不受外界影響,具有緩釋、靶向釋放、減少某些食品配料用量等優點[58]。雖然復乳體系具有巨大的應用潛力,但是因為其固有的熱力學和動力學性質不穩定性,使其在食品上的應用受到限制[59]。所以研究新型復乳體系提高其穩定性是非常必要的。Teixé-Roig等[60]利用羧甲基纖維素鈉提高含花色苷W/O/W型乳液的穩定性和生物可及性,并對其在模擬胃腸道條件下的行為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乳化劑中加入羧甲基纖維素鈉后,包埋率可達90%以上,粒徑小于10 μm。與花色苷提取物的水溶液相比,負載花色苷乳液的生物可及性顯著提高,加入羧甲基纖維素鈉穩定的W/O/W型乳液中生物可及性為(31.08±1.73)%,這可能是由于油滴在模擬胃腸液中更穩定,羧甲基纖維素鈉的加入減緩了游離脂肪酸的釋放,延長了對花色苷的保護時間。也有研究將酪蛋白鈉溶液作為外水相制備W/O/W型乳液用來保護花色苷,結果表明在模擬胃液中花色苷得到了有效的保護,經過胃腸液消化后,抗氧化活性明顯提高[61]。
近年來為了提高復乳體系穩定性,皮克林粒子常被用作穩定劑。它使用固體粒子代替表面活性劑,能夠抑制液滴凝聚,利用顆粒在油滴表面的吸附來實現體系穩定的乳狀液,具有較高的穩定性[58]。乳狀液的穩定主要通過增加空間位阻和改變連續相的界面性質或流變性來實現,內相包裹敏感活性物質以提高穩定性和控制在胃腸中釋放。與傳統的W/O型乳液相比,皮克林乳液的脂肪和鹽含量更低,符合現代人類飲食的趨勢。Lin Xiaoying等[62]利用含辛烯基琥珀酸藜麥淀粉的去離子水作為外水相,含聚甘油蓖麻醇酸酯的大豆油作為油相制備了負載花色苷的雙重皮克林乳液(圖4)。皮克林粒子替換了部分的表面活性劑以穩定乳液界面,界面上的固體顆粒在毛細管力或范德華力的作用下抵抗聚結和奧斯特瓦爾德熟化。負載花色苷的雙重皮克林乳液包埋率最高可以達到95.8%,平均粒徑可以達到30 μm,并且在模擬胃液中消化時能保持花色苷結構的完整性和較高的包埋率。而在模擬腸液中消化后,由于淀粉水解和乳液的破壞,大部分花色苷被釋放出來,從而實現腸道精準靶向遞送。

圖4 辛烯基琥珀酸藜麥淀粉穩定的雙重皮克林乳液示意圖[62]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double Pickering emulsion stabilized by octenylsuccinate quinoa starch[62]
5 復合遞送系統
單一的壁材并不能具備所有必需的特性,所以很多研究通過復合不同壁材之間的比例來改善包埋效果。Chotiko等[63]制備了4種不同花色苷的膠囊:包括果膠膠囊(1);覆蓋玉米醇溶蛋白涂層的果膠膠囊(2);果膠-乳清分離蛋白復合膠囊(3);涂有玉米醇溶蛋白的果膠-乳清分離蛋白復合膠囊(4)。研究選用具有結腸特異性的并且帶負電的果膠與帶正電的乳清分離蛋白之間形成復合物以改善果膠高孔隙率的情況,并在果膠膠囊上用玉米醇溶蛋白包裹整個膠囊,結果表明,與對照相比,復合壁材(2)~(4)均提高了果膠膠囊的包埋率,其中,復合壁材(4)的包埋率最高,為(68.77±3.46)%。當膠囊暴露在胃腸模擬體系中,復合膠囊有利于保護花色苷并實現其在腸道中的緩釋,但并未發現玉米醇溶蛋白對其的影響。Wang Shuo等[64]以殼聚糖鹽酸鹽、羧甲基殼聚糖和乳清分離蛋白為載體,將花色苷包埋在納米復合物中,該納米復合物具有較理想的粒徑(332.20 nm)和zeta電位(+23.65 mV)以及較高的包埋率(60.70%)。經過包埋的花色苷抗氧化能力強于未經包埋的花色苷。在模擬體外消化過程中,由乳清蛋白和殼聚糖衍生物交聯形成的雙層涂層和花色苷之間的結合提高了花色苷在pH值較高環境下的穩定性,防止了腸道消化過程中的降解。將納米復合物引入到咖啡飲料中,對功能飲料熱處理后,保留了較高的花色苷含量,與不含花色苷的咖啡相比,該咖啡具有更高的抗氧化活性。
除了運用微載體遞送系統進行遞送以外,有研究者將輔色作用和微載體遞送系統復合使用從而改善花色苷的穩定性。由于蛋白質-多糖壁材的眾多活性基團(如巰基、氨基和羧基)在聲空化過程中能夠形成殼層交聯的納米膠囊包裹水相,隨后通過改變pH值可以使非交聯蛋白直接沉積回壁材交聯表面從而形成額外的殼層,基于此,Tan Chen等[65]利用牛血清白蛋白和硫酸軟骨素開發了一種穩定、高效、多功能的核-殼-殼納米結構用于遞送花色苷。雙納米殼層水核納米膠囊的形成是由共價鍵和靜電相互作用通過連續的交聯和界面絡合來驅動的,硫酸軟骨素與牛血清白蛋白通過蛋白質間二硫鍵和酰胺鍵形成較強的交聯,增強了交聯殼層對花色苷的包埋。將輔色作用和包埋同時使用可以提高整個體系的穩定性。如圖5所示,通過將花色苷與沒食子酸乙酯以及硫酸軟骨素輔色作用形成分子間絡合物,與單獨包埋花色苷的包埋率((47.4±1.6)%)相比,運用輔色作用以后包埋率可以達到(54.6±1.4)%,粒徑為(147.0±0.4)nm,和單獨包埋花色苷的粒徑((149.4±1.2)nm)相差不大。并且這個體系對外界刺激(如pH值和氧化還原響應性釋放)有很強的響應能力。
6 各種遞送系統優劣勢比較
花色苷作為天然著色劑,目前最大的應用瓶頸在于其穩定性。本文綜述了目前研究較多的花色苷的幾種遞送系統,并對各種系統進行了描述和對比。各遞送系統優劣勢的比較如表1所示。以脂質、多糖和蛋白質等為材料制備的遞送系統在提高花色苷口服過程中的穩定性和生物利用度方面效果顯著,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從已有文獻報道可知,單一的多糖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實現很好的包埋,如殼聚糖易受到體系pH值的影響,不能在相對酸性的環境下存在,而海藻酸鈉在堿性條件下穩定性較差,使負載藥物易從顆粒孔隙中泄漏。多糖需要和其他材料如多糖、蛋白質、脂質體復合使用從而提高負載藥物的穩定性,實現在胃腸道中的緩釋。蛋白質雖然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但是由于表面電荷和疏水性的作用,其對某些環境因素(pH值、離子強度、溫度)的變化十分敏感[66-67]。傳統的脂質體由于自身的局限,穩定性較差,長期貯存易發生聚集、磷脂氧化、藥物泄漏等現象,開發新型的脂質體系統是很有必要的。復乳體系中皮克林乳液因包埋率較高,能起到緩釋的作用,并且符合現代人類飲食的趨勢,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但熱力學性質不穩定,會由于奧斯瓦爾德熟化、絮凝、聚集或重力作用而導致粒徑粗化,需要尋找合適的固體粒子來穩定界面。

表1 各種遞送系統優劣勢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delivery systems

圖5 花色苷共色納米復合物形成的示意圖[65]Fig. 5 Schematic diagram describing the formation of anthocyanin copigmentation nanocomplexes[65]
7 結 語
花色苷的精準靶向遞送是實現精準營養干預的關鍵。未來,選擇包埋率更高、成本更低、綠色安全環保的遞送原料將成為產業追求的目標。篩選不同壁材或結合使用多種物理和化學方法提高花色苷穩定性將會是未來關注的重點。納米技術的發展也為花色苷遞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于不同壁材構成的遞送系統與花色苷之間的構效關系、花色苷與壁材的結合位點等研究較少,而對于花色苷遞送系統的評價目前也主要基于體外胃腸模擬體系,未來需要進一步開展動物和人體實驗,研究包埋后花色苷在體內的藥代動力學,明確各種遞送系統的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為花色苷的產品開發提供基礎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