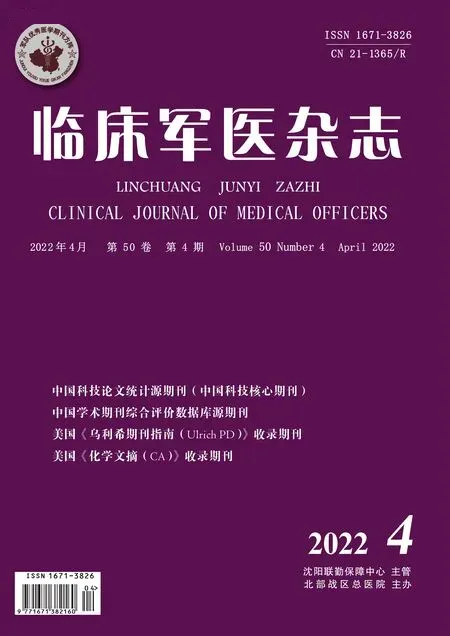介入技術在兒童先天性心臟病外科術后肺動脈分支狹窄中應用價值研究
鄧曉嫻,張剛成,沈群山,李云燕,鄭 璇
1.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湖北 武漢 430022;2.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湖北 武漢 430071
肺動脈分支狹窄(pulmonary artery branch stenosis,PBS)是兒童先天性心臟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外科矯正術后的常見并發癥[1]。不同CHD外科術后PBS發生率有所差異,法洛四聯癥外科術后PBS發生率高達40%左右,其他復雜CHD術后PBS的發生率為4.7%~21.4%[2]。CHD外科術后PBS二次外科手術治療風險高、并發癥多,因此,介入治療成為這類患者的首選治療方法。本研究旨在探討介入技術在兒童CHD外科術后PBS中的應用價值。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自2016年6月至2021年3月收治的6例CHD外科術后PBS患者為研究對象,所有患者均接受介入治療。6例患者中,男性4例,女性2例;年齡1~15歲,平均年齡6.2歲;體質量8.2~61.5 kg,平均體質量22.4 kg;外院動脈導管未閉結扎術后右肺動脈狹窄介入球囊擴張1例(患者1,1歲,8.7 kg),法洛四聯癥矯治術后左肺動脈狹窄介入支架植入1例(患者2,8歲,19.2 kg),肺動脈閉鎖矯治術后左肺動脈狹窄介入球囊擴張1例(患者3,5歲,15.0 kg),法洛四聯癥矯治術后左右肺動脈狹窄分別行左右肺動脈介入球囊擴張1例(患者4,1歲,8.2 kg),肺動脈吊帶矯治術后左肺動脈狹窄介入球囊擴張1例(患者5,15歲,61.5 kg),肺動脈閉鎖矯治術后左右肺動脈狹窄、左肺動脈介入球囊擴張、右肺動脈介入支架植入1例(患者6,7歲,21.5 kg)。所有患者術前均行心臟超聲或/和心臟CT增強掃描,診斷為CHD術后左或/和右肺動脈狹窄。本研究所有患者監護人對各類檢查方法和治療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治療方法
1.2.1 介入材料 球囊擴張導管為波科Sterling OTW球囊、波科Sterling Monorail球囊、百多力球囊,球囊擴張支架為波科SD支架、雅培Ominilink Elite支架,導引導管為8F波科MACH1。
1.2.2 介入方法及術后處理 在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下穿刺右股靜脈并肝素化(50 U/kg),常規右心導管檢查、肺動脈造影,確定狹窄位置及程度。檢查完畢后,根據病變特點選擇球囊擴張或/和支架植入。患者1選擇6 mm×20 mm波科Sterling OTW球囊擴張;患者2選擇6 mm×18 mm波科SD支架植入(圖1);患者3選擇8 mm×20 mm波科Sterling Monorail球囊擴張;患者4先后選擇8 mm×20 mm波科Sterling OTW球囊和10 mm×20 mm波科Sterling OTW球囊對左右肺動脈進行擴張(圖2~3);患者5選擇10 mm×20 mm波科Sterling OTW球囊擴張;患者6左肺動脈選擇8 mm×40 mm百多力球囊擴張(圖4),右肺動脈選擇9 mm×19 mm雅培Ominilink Eite支架植入(圖5)。所有患者手術當天給予靜脈抗生素預防感染,術后口服阿司匹林3~5 mg/(kg·d)6個月。

圖1 6 mm×18 mm波科SD支架(紅色箭頭)植入狹窄的左肺動脈

圖2 8 mm×20 mm波科Sterling OTW球囊擴張狹窄的左肺動脈

圖3 10 mm×20 mm波科Sterling OTW球囊擴張狹窄的右肺動脈

圖4 8 mm×40 mm百多力球囊擴張狹窄的左肺動脈

圖5 9 mm×19 mm雅培Ominilink Eite支架(紅色箭頭)植入狹窄的右肺動脈
1.3 觀察指標 比較介入治療前后的狹窄直徑和跨狹窄處壓差;觀察術后即刻的介入并發癥發生情況和隨訪中的不良事件發生情況。
2 結果
所有患者術后即刻無心跳驟停、心包積液、惡性心律失常等介入并發癥。患者1治療前后狹窄直徑分別為2.5 mm和6.0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46 mmHg和25 mmHg(1 mmHg=0.133 kPa)。患者2治療前后狹窄直徑分別為1.5 mm和5.0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50 mmHg和23 mmHg。患者3治療前后狹窄直徑分別為2.5 mm和8.0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34 mmHg和25 mmHg。患者4治療前后狹窄直徑分別為2.0 mm和6.0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74 mmHg和36 mmHg(左);狹窄直徑分別為1.9 mm和6.0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53 mmHg和49 mmHg(右)。患者5治療前后狹窄直徑分別為2.0 mm和6.0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30 mmHg和15 mmHg。患者6治療前后狹窄直徑分別為5.5 mm和12.5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21 mmHg和13 mmHg(左);狹窄直徑分別為3.3 mm和11.9 mm,跨狹窄處壓差分別為33 mmHg和17 mmHg(右)。介入治療后,跨狹窄處壓差由治療前的(42.63±16.70)mmHg降至治療后的(25.38±12.00)mmHg,狹窄直徑由治療前的(2.65±1.27)mm升至治療后的(7.68±2.92)mm。隨訪1~5年,平均隨訪時間2.5年,患者3在隨訪第4年因再狹窄于外院行支架植入,其余5例患者均未發生栓塞、支架移位或斷裂等,6例患者均存活。
3 討論
PBS是CHD(尤其是復雜CHD)外科術后的常見并發癥,與吻合口瘢痕形成、血管牽拉扭曲、內皮細胞增生等因素相關[3]。據文獻報道,復雜CHD外科術后PBS發生率為4.7%~40.0%[4]。北京安貞醫院統計報道,200例法洛四聯癥外科術后患者中,有152例出現肺動脈狹窄[5]。壓差明顯的PBS會引起患者右心壓力增高、肺動脈擴張、雙側肺血不匹配等,導致右心功能不全,從而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甚至危及生命。
二次外科手術風險高、并發癥多,且分支狹窄,外科手術難以到達,因此,介入治療成為兒童CHD外科術后PBS的首選治療方法。介入治療包括球囊擴張和支架植入。自Rocchini等[6]在1984年報道了球囊擴張技術在肺動脈狹窄中的應用后,該項技術在肺動脈狹窄中的應用日益廣泛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021年,Zsofia等[7]采用球囊擴張技術對法洛四聯癥術后60例患者的134條肺血管進行了擴張,除6條血管外,其余血管均擴大,最窄直徑中位數增加了1.0 mm,證實了球囊擴張對CHD術后PBS的改善作用。然而,由于血管壁的彈性回縮,球囊擴張存在再狹窄可能,該技術不能完全滿足臨床需求,因此,支架植入應運而生。國外學者O′Laughlin等[8]在1991年報道了支架植入在肺動脈中的應用。國內學者張智偉等[9]在1998年報道了國內首例行肺動脈狹窄支架植入的患者。此后,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證實了支架植入在PBS中的有效性[10]。同樣,支架植入也存在局限性,如嬰幼兒患者隨著肺動脈的發育而導致支架再擴張受限等。
有研究提出,支架植入優于單純球囊擴張[11-12]。但筆者認為,兩種介入技術存在各自的優缺點,需根據患者年齡、病情特點、狹窄長度和程度、各中心經驗等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支架植入在嬰幼兒中的應用較少、并發癥發生率較高[13],因此,對于嬰幼兒多行球囊擴張,盡量避免因患兒生長發育、支架不匹配而出現再狹窄。但對于局限單支肺動脈狹窄的年長患兒多行支架植入[14]。本組6例患者共處理8支血管,其中,6支行球囊擴張,2支行血管植入支架,行球囊擴張者年齡相對偏小,而支架植入者年齡相對偏大。本研究中,1例球囊擴張患者隨訪第4年因再狹窄外院行支架植入,兩種介入技術的互補應用和介入優勢最大化在該患者身上得到了完美體現。
本研究結果顯示:介入治療后,跨狹窄處壓差下降,狹窄直徑增大;隨訪中,除1例患者因再狹窄外院行支架植入以外,其余5例患者均未發生栓塞、支架移位或斷裂等,且6例患者均存活。這提示,介入技術對CHD外科術后PBS患者的治療效果顯著,其可有效擴張病變分支血管,降低狹窄段前后壓差,增大狹窄處最小直徑,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減少CHD外科術后不良心血管事件。
綜上所述,介入技術在兒童CHD外科術后PBS的治療中安全可行,可作為CHD外科術后PBS的有效治療方法。但介入技術目前仍存在局限性,如術后近期和遠期再狹窄等問題,有待于今后更先進技術和更理想器械的發明進一步解決;而對于球囊擴張和支架植入的選擇,需根據各中心經驗、患者年齡、病變特點等綜合考慮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