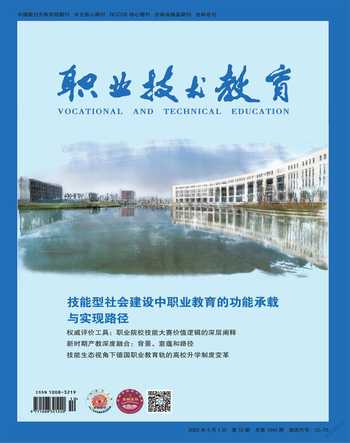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脈絡演進與變遷邏輯
賀艷芳 吳丹
摘 要 對職教教師教育政策文本的疏理發(fā)現(xiàn),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即注重教師專業(yè)技能階段、強調教師實踐應用能力階段、強化教師理實結合能力階段和推進教師多元能力階段。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雖然經(jīng)歷了不同的時代變化,但是總體發(fā)展趨勢基本遵循需求邏輯、宏觀邏輯和服務邏輯。站在新的時代起點上,深化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策略是:兼顧職教教師自身能力發(fā)展需求;倡導各主體共同助力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構建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體系;建立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監(jiān)督評估機制。
關鍵詞 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政策變遷;演變邏輯
中圖分類號 G7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2)10-0047-06
伴隨著我國經(jīng)濟進入高質量發(fā)展階段,職業(yè)教育開啟了提質培優(yōu)、以高質量發(fā)展為目標的新征程,而推動職業(yè)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關鍵在于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提升。一直以來,我國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內涵隨著時代發(fā)展的不同需求以及職業(yè)教育實踐的經(jīng)驗積累不斷變化。以國家關于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政策為依據(jù),國家對于發(fā)展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要求經(jīng)歷了從注重專業(yè)技能本身到強調實踐應用能力,再到強化理實結合能力和推進多元能力四個階段。本研究以政策文本為切入點,重點分析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脈絡演進,從而揭示我國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變遷邏輯,并以史為鑒,為當前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提出促進策略。
一、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脈絡演進
我國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經(jīng)歷初步確立、調整適應、重構發(fā)展以及完善深化四個階段,基于政策文本縱向疏理每個階段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要求,有助于明晰我國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演變邏輯。
(一)初步確立階段:注重教師專業(yè)技能
洋務運動是我國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起點,但是此時的職業(yè)教育以培養(yǎng)具體專業(yè)的技術技能人才為主,并沒有涉及到職教教師教育的范疇,直到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標志著職教教師教育在中國的正式誕生。其中,能較系統(tǒng)地揭示當時職教教師教育辦學要旨的文件非《實業(yè)教員講習所章程》莫屬,在入學條件方面,該章程規(guī)定“須年在十七歲以上,在初級師范學堂、中學堂或與同等以上之實業(yè)學堂畢業(yè)者,始為合格”[1]。也就是說,當時要進入實業(yè)學堂學習并成為一名職教教師,首先須具備最基本的文化知識學習能力。在專業(yè)選擇方面,講習所開設了農(nóng)業(yè)、工業(yè)與商業(yè)三種教員講習所,分別針對不同群體進行具體的專業(yè)理論知識講授和實踐能力訓練。每種專業(yè)門類下設的科目劃分明確,數(shù)量繁多,每類科目內容不僅涉及專業(yè)知識,還將“實習”明確規(guī)定在培養(yǎng)范圍之內,從側面體現(xiàn)了對職教教師專業(yè)能力以及實踐能力的重視。除此之外,在課程設置方面,依據(jù)《實業(yè)教員講習所章程》中對各專業(yè)具體科目的設定可知,人倫道德、教育學、教授法、英語和體操是所有職教師范生必須學習的科目,體現(xiàn)了對職教師范生道德素養(yǎng)、教育教學能力和身體素質的要求。
1915年10月,教育部頒布《實業(yè)教員養(yǎng)成所規(guī)程》,其中第五條提出“實業(yè)教員養(yǎng)成所之學科目,須參照相關專業(yè)學校的規(guī)章制度辦理,并要酌情增加教育學和教學法等科目”[2]。可以看出民國初期對于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要求大致沿用“癸卯學制”中所規(guī)定的內容,以職教教師的專業(yè)能力和教育教學能力為核心。1928年8月,教育部公布《實業(yè)學校教育令》,明確實業(yè)學校的宗旨:“以教授農(nóng)業(yè)、工業(yè)和商業(yè)中所需掌握的基礎知識技能為目的”,這與《癸卯學制章程》中的辦學目的基本相同[3]。
洋務運動至民國初期是我國職教教師教育初步建立與發(fā)展時期,對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規(guī)定更多的是依據(jù)社會實際需求、社會性別角色以及社會傳統(tǒng)觀念來制定的,教授方法也多以講授的形式開展。通過對這一時期政府文件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此時政府已經(jīng)開始注重對職教教師專業(yè)能力、實踐能力、教育教學能力、學習能力、身體素質能力提出要求與規(guī)定,但這些要求大多體現(xiàn)在入學條件以及專業(yè)課程設置中,并沒有單列出具體的職業(yè)能力標準與行業(yè)細則。此外,在政策落實層面存在很大不足,很多文件中提到的內容都沒有得到落實,因此當時培養(yǎng)的職教教師質量并不高,專業(yè)能力和教育教學能力都比較強的教師更是鳳毛麟角。
(二)調整適應階段:強調教師實踐應用能力
1922年,壬戌學制頒布,以職業(yè)教育制度取代實業(yè)教育制度,職業(yè)教育在學制中的地位得以確立,職教師資培養(yǎng)制度也就此確立[4]。此次新學制的標準發(fā)生了調整,其中“適應社會之需要;謀個性之發(fā)展;注意國民經(jīng)濟力;注意生活教育”都更為體現(xiàn)出新學制對于與人的生計相關教育的重視,而針對職教教師的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則還是基本沿用之前的政策規(guī)定。1927年,國家進入10年內戰(zhàn),職教師資的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更傾向于為戰(zhàn)爭服務,即注重培養(yǎng)教師的專業(yè)技術能力繼而為戰(zhàn)場后方培養(yǎng)各種專業(yè)技術人才和經(jīng)濟建設人才。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三民主義教育”宗旨,隨后職業(yè)教育宗旨也隨之改變,其中“人民生活、社會生存以及國計民生”等內容得以凸顯。《修正職業(yè)學校規(guī)程》規(guī)定,將具備職業(yè)經(jīng)驗作為初、高級教師任職的條件之一。1933年,教育部出臺《各省市職業(yè)學校職業(yè)學科師資登記檢定及訓練辦法大綱》,針對職業(yè)學校師資培養(yǎng)方式及訓練科目作出規(guī)定,其中訓練科目的占比如下:普通學科占10%;職業(yè)理論學科占30%;職業(yè)技術學科占50%;教育學科(如教育、教育心理、職業(yè)教育、職業(yè)教學法、教育實習等)占10%[5]。除此之外,為提升職教師資的專業(yè)能力,教師培訓也積極開展起來。一方面,政府出臺獎勵政策鼓勵教師參加進修,提升自我;另一方面,建立教師進修機構以及在假期開展各種工科、農(nóng)科專業(yè)的講習會來助力教師專業(yè)能力的提升。
總體來說,這一時期的職業(yè)教育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為戰(zhàn)爭服務以及為人民生活、社會生存和國計民生服務上。政府在此階段主要強調職教教師專業(yè)能力、教育教學能力、實踐能力、繼續(xù)學習能力和服務能力的發(fā)展。但由于戰(zhàn)亂頻繁,民國時期的職教教師教育處于不斷適應調整之中,職教教師的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內容也大體基于之前頒布的各項政策,以專業(yè)理論、專業(yè)技能、實踐經(jīng)驗以及道德素質為四大核心,特別強調專業(yè)技能和實踐經(jīng)驗在培養(yǎng)中的作用。
(三)重構發(fā)展階段:強化教師理實結合能力
1949年,新中國成立。此時的中國依然面臨著復雜的內外環(huán)境,各項教師教育政策多借鑒蘇聯(lián)經(jīng)驗,國家沒有具體就職教教師教育制定新的政策,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內容幾乎都零散地顯露在教師教育政策、職業(yè)教育政策以及相關會議紀要中。
此時政府明確規(guī)定,中等技術學校不僅要給學生以專門的技術訓練,還需要加強政治教育、基本文化知識教育、專業(yè)技術教育以及實習,并且還要建立與有關工廠、農(nóng)場的聯(lián)系,為學生提供實訓場地。1952年,教育部頒布《中等技術學校暫行實施辦法》,規(guī)定“中等技術學校應該有計劃地培養(yǎng)專業(yè)技術教師,加強其專業(yè)技術能力以及提高企業(yè)專業(yè)技術人員的學術水平,與企業(yè)定期交流合作,建立專業(yè)技術教師和專業(yè)技術人員的溝通機制”[6];1954年,政務院發(fā)布《關于改進中等專業(yè)教育的決定》,進一步強調“理實結合”的教學方法,重視生產(chǎn)教育在中等技術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要使生產(chǎn)實習的每一個階段服從于理論課程有關部分的學習”;此外,文件中還提到“教師在講授課程時應力求自科學技術的最新成就取材,作為教學大綱的補充”,體現(xiàn)出職業(yè)教育教師要有與時俱進、審時度勢眼光和能力,彰顯職業(yè)教育的特色。1985年,國務院提出要調整中等教育布局,治理專業(yè)技術師資緊缺的問題,強調“可以聘請技藝精湛的技師和技壓群芳巧匠來傳授技術手藝”;1987年,國家教委發(fā)布《關于職業(yè)中學專業(yè)課教師職務聘任工作的補充意見》,規(guī)定“在教師崗位聘用工作中,對教師任職條件的評定,要堅持理實并重的原則,主要考察教師的思想道德、基礎文化水平、理論學術能力、教育教學能力、工作過程能力和本專業(yè)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達到專業(yè)崗位標準的,可以予以聘用”[7]。
新中國成立后,職業(yè)教育肩負著為國家建設培養(yǎng)各行各業(yè)專業(yè)技術技能人才的重任。學術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都被加入到職教教師政策文件中,以完善職教教師的職業(yè)能力結構。但參考這一時期的實際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在計劃經(jīng)濟時期職教教師教育相關內容總體呈現(xiàn)出培養(yǎng)目標單一化趨勢,即只重視職教教師專業(yè)能力的培養(yǎng)與發(fā)展[8],而對于政策中所提到的許多職業(yè)能力都還只是停留在美好的藍圖中。當然,這一方面體現(xiàn)了職教教師教育對于教師專業(yè)技能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且逐步通過制度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也揭露出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單一性。此外,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標準和層次仍未能在政策中得以體現(xiàn),主要還是在宏觀層面進行把控。
(四)完善深化階段:推進教師多元能力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逐步由計劃經(jīng)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此時我國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也逐步向標準化、全面化和深入化發(fā)展。1995年,國家教委頒布《關于開展建設示范性職業(yè)大學工作的通知》,“雙師型”教師概念初次在國家政策文件中出現(xiàn),作為職教教師教育的培養(yǎng)宗旨,“雙師型”教師不僅強調理論教學能力,更強調實踐教學能力;不僅強調教育教學能力,更強調工作職業(yè)能力[9],充分體現(xiàn)了國家對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視。2000年,教育部印發(fā)《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yǎng)工作的意見》,提出不僅要使教師具備深厚的教學功底,還要讓他們擁有扎實的專業(yè)實踐能力和豐富的實際工作體驗,在教育教學工作的每個環(huán)節(jié)中都積極滲透對職業(yè)能力的培養(yǎng),對追求終身性學習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的教師給予物質鼓勵。
2002年,教育部辦公廳頒布《關于加強高等職業(yè)(高專)院校師資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為了順應信息化時代的到來,要大力提升教師現(xiàn)代化教學技術的應用能力,勉勵和支持教師靈活運用現(xiàn)代化信息技術手段提升課堂教學質量與效率。2006年,教育部頒布《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yè)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要求派遣專業(yè)教師走進企業(yè)開展頂崗工作,積累工作過程知識和經(jīng)驗,提高實踐教學能力,并在此基礎上深化科技創(chuàng)新與開發(fā)服務、企業(yè)服務和社區(qū)服務等職業(yè)能力。2011年,教育部和財政部共同發(fā)布《關于實施職業(yè)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的意見》,將提高教師的教育教學水平特別是實踐教學和課程設計開發(fā)能力作為這一時期的目標任務,塑造一大批以能力為本位的“雙師型”專業(yè)骨干教師[10]。2013年,教育部發(fā)布《中等職業(yè)學校教師專業(yè)標準(試行)》,強調教師要優(yōu)化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培養(yǎng)終身學習與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具有與實習實訓單位溝通合作的能力等。
2015年,教育部頒布《高等職業(yè)教育創(chuàng)新發(fā)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要求“將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歸納到教師考核評聘的標準之中,并要求提高教師的國際語言交流能力”。2016年,教育部和財政部發(fā)布《關于實施職業(yè)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2017-2020年)的意見》,在專業(yè)帶頭人領軍能力研修的部分強調要重點提升教師的團隊合作能力、應用技術研發(fā)與推廣能力、課程開發(fā)技術、教研科研能力和管理協(xié)作能力,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實際問題;此外,文件中還提出要提高職教教師的培訓需求診斷能力、課程與數(shù)字化資源開發(fā)能力、教學設計實施能力、核心技能創(chuàng)新與推廣能力、績效考核評估能力和工作室(平臺)主持能力[11]。2019年,教育部等四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深化新時代職業(yè)教育“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改革實施方案》,提出“推進國家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加速培育一批具備職業(yè)技能等級證書培訓能力的教師”,將雙師素質納入教師考核評價體系,并以此作為聘任考核、晉升考核、績效考核的重要參考[12]。
通過對20世紀末至今我國有關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政策文本的分析可知,這一時期我國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相關政策中反復提到教育教學能力、專業(yè)實踐能力、信息化教學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突顯了新時代職業(yè)教育教師的核心特質;而服務能力、外語交流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管理協(xié)作能力、課程技術和資源開發(fā)能力、科研教研能力等則是隨著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而陸續(xù)增加的職業(yè)能力,體現(xiàn)了職業(yè)教育順應時代潮流發(fā)展、與時代潮流緊密聯(lián)系的特性。
二、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變遷邏輯
從洋務運動發(fā)展至今,隨著我國經(jīng)歷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征程,職教教師教育也完成了螺旋式上升的四個階段,其中對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要求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更為全面化,在職業(yè)教育邁向高質量發(fā)展的演進中發(fā)揮著關鍵作用。結合政策變遷歷程,可以從需求、宏觀和服務的邏輯中窺見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蹤跡。
(一)需求邏輯:順應各時期社會發(fā)展對職教教師的現(xiàn)實需求
“人類歷史是一部不斷追求社會需求和諧的歷史。”[13]國家每一次重大時期的轉折都會產(chǎn)生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作為與時代需求緊密銜接的教育類型,開拓職教教師資源、傳授給國民謀生技術、助力國家經(jīng)濟建設發(fā)展是每一時期職教教師教育給予社會需求的回應。
洋務運動至民國初期,我國職教教師教育開始初步發(fā)展,在遭受外部勢力侵略,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之時,急需大批技術技能人才來振興國家實業(yè),而培養(yǎng)一群優(yōu)秀的職教師資繼而培育出專業(yè)的技術技能人才,以挽救處于生靈涂炭之中的國家成為必然選擇。基于此,政府開始探索新學制,強調以實踐能力與教育教學能力為核心來培養(yǎng)職教師資。民國中后期至新中國成立,這一時期國家對職教師資的需求分為兩部分,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職教師資的職責是為戰(zhàn)場后方培養(yǎng)各種技術技能型人才,為戰(zhàn)爭勝利提供人才需求補給;新中國成立之后,恢復和重新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成為了這一時期的課題,職教師資也逐漸由為戰(zhàn)場后方培養(yǎng)技術技能型人才轉變成為國家培養(yǎng)戰(zhàn)后恢復和建設而服務的應用型人才。1949-1995年,國家逐漸從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中走出來,開始大力建設國家事業(yè),急需培養(yǎng)各行各業(yè)的應用型人才,為此,國家開始規(guī)劃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的美好藍圖,不僅重視教師職業(yè)能力在廣度上的拓展,還重視教師職業(yè)能力在深度上的優(yōu)化。1995年至今,隨著改革開放、全球化的進一步推動,各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逐漸與國家戰(zhàn)略布局息息相關,社會對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層次的要求也進一步升級。以建設“雙師型”教師隊伍為開端,政策文件逐步體現(xiàn)出對職教教師質量的重視以及對教師職業(yè)能力多樣性的要求。
(二)宏觀邏輯:政府從宏觀上進行總體布局
通過疏理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相關政策脈絡可以發(fā)現(xiàn),其過程明確體現(xiàn)了以政府為主體,從宏觀上進行把控,再從上而下進行落實這一路徑依賴,每個時期的政策出臺主要都是以政府為主體來推進,表現(xiàn)出較強的宏觀邏輯。
首先,在初步確立階段。面臨國破家亡的處境,面對敵人的船堅炮利以及各種先進技術的涌入,清政府開始意識到過往那種“重學輕術”的教育對于拯救國家顯然已軟弱無力,發(fā)展實業(yè)才是“對抗”的有效手段。而實業(yè)、教育、教師正如漣漪效應般層層暈開,環(huán)環(huán)相扣,要想實業(yè)發(fā)展最終還是要落到教師發(fā)展上來。因此,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開辟了我國職教教師培養(yǎng)的先河。其次,在調整適應階段。伴隨著清朝政府的完結與南京國民政府執(zhí)政的開始,常年遭受外部戰(zhàn)爭與內部戰(zhàn)爭輪番交替的境況早已使得民不聊生,為此南京政府依據(jù)國情調整新的教育政策,提出“以培養(yǎng)青年生活之知識與生產(chǎn)技能”為此時的職業(yè)教育目標,從宏觀上引導職業(yè)教育在注重培養(yǎng)工業(yè)、農(nóng)業(yè)方面專業(yè)人才的同時也培養(yǎng)生活生產(chǎn)方面的專業(yè)人才,以維持社會生存與國民生計。再次,在重構發(fā)展階段。新中國的成立使得國家可以將重心放在發(fā)展國家經(jīng)濟建設上。但由于當時我國實施計劃經(jīng)濟體制,資源的生產(chǎn)、分配以及消費都是由政府按照事先制定的計劃進行調控。因此,職教教師也是由國家進行統(tǒng)一計劃與管理。最后,在完善深化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逐步由計劃經(jīng)濟轉化為市場經(jīng)濟,但出于對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慣性”和對“市場失靈”的擔憂,政府仍然是推動眾多政策變遷的主導力量[14]。這一時期,政府根據(jù)國家戰(zhàn)略需要以及國際形勢發(fā)展不斷出臺政策,對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提出新要求,推動了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朝著專業(yè)化、多元化、深遠化方向發(fā)展。
(三)服務邏輯:服務于國家戰(zhàn)略、社會經(jīng)濟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
從洋務運動至今,職教教師一直作為我國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順應時代需求逐步完善。洋務運動時期,面對“喪權辱國”的國情和“自強求富”的渴望,軍事工業(yè)與民用工業(yè)開始發(fā)展起來,但苦于當時專業(yè)師資與技術匱乏,國家發(fā)展難有起色。為早日擺脫屈辱的命運,急需培養(yǎng)大批服務于軍用企業(yè)與民用企業(yè)的專門人才,職教教師教育應運而生;民國時期,頻繁的戰(zhàn)爭使得國家對于戰(zhàn)場后方各種技術人才和經(jīng)濟建設人才的需求激增,為更好地服務于戰(zhàn)爭的需要,這一時期對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提出了為戰(zhàn)爭勝利與國民生計服務的要求;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進一步鞏固政權,更好地促進戰(zhàn)后經(jīng)濟恢復和發(fā)展,國家實行了計劃經(jīng)濟體制,并開始培養(yǎng)各類技術技能人才為國家建設與改革服務;改革開放以來,全球競爭、合作與發(fā)展日益緊密,國家對專業(yè)技術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加強了社會對于職教教師數(shù)量和質量的重視。教師職業(yè)能力標準也向國際標準看齊,信息技術能力和外語交流能力日益成為職教教師的基本職業(yè)能力,為現(xiàn)代企業(yè)和行業(yè)培養(yǎng)更具國際適應性的技術技能人才服務。此外,在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進而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實現(xiàn)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時期,培養(yǎng)更多優(yōu)質的定向公費職教師范生服務鄉(xiāng)村、振興鄉(xiāng)村也深刻體現(xiàn)了這一強大邏輯。
三、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的促進策略
教師振興是教育振興的關鍵,教育振興是人才隊伍振興的關鍵,人才隊伍振興是鄉(xiāng)村振興、國家復興的關鍵。推進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發(fā)展既是提升職業(yè)教育質量的重要措施,又是解決當前國家對于高級技術技能人才需求的突破口,意義深遠。
(一)兼顧職教教師自身能力發(fā)展需求
社會需求與社會服務是推動職教教師能力深化發(fā)展的有力推手,社會需求的更新與社會服務能力的提升,往往會驅動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的方向。而教育作為一種與人類社會發(fā)展共生的產(chǎn)物,其既依附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也有其獨立發(fā)展的體系與內核。一味地追尋社會需求和效益,迷失教育的本質也是對教育資源的一種損耗。因此,在以社會需求、服務為導向的同時兼顧職教教師自身能力發(fā)展需求是沖破當今社會“需求縱橫”境況,永葆職教教師教育本質的有效路徑。職教教師發(fā)展核心需求總體可以歸納為四個方向,即道德、知識、能力和態(tài)度,這四方面猶如四根支柱共同架構起職教教師教育專業(yè)發(fā)展的樓宇。其中,職教教師職業(yè)核心能力包括職業(yè)教育教學能力、專業(yè)實踐能力、專業(yè)發(fā)展能力、應用型研究能力、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將核心能力作為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根基,再以此為基礎順應時代潮流以及不同專業(yè)的實際需求去完善職教教師其他能力發(fā)展是進一步科學提升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的有效策略。
(二)倡導各主體共同助力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
首先,政府、企業(yè)、學校和社會應該積極參與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的相關政策與標準制定。除政府以外,企業(yè)、學校和社會都是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的利益相關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教教師教育的管理體制從中央政府集權逐漸轉變?yōu)檎艡唷⒌胤椒謾啵粩鄬⑸鐣蟊姷男枨笈c市場滲透納入職教教師教育的多元話語體系中[15],各主體應該借此“東風”積極參與到推進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中,制定職教教師能力標準與細則,完善職教教師能力體系。其次,政府、企業(yè)和學校應該加強聯(lián)系與合作,了解在當前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進程中,職教教師需要具備怎樣的能力、如何培養(yǎng)職教教師的能力,特別是在職業(yè)院校工作的職教教師,更應該加強對企業(yè)的了解及與行業(yè)的互動,在提升自己實踐能力的同時繼續(xù)完善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此外,政府、企業(yè)和學校應鼓勵和推動職教教師能力的快速升級,落實企業(yè)實踐、教師培訓等相關政策,為職教教師提供能力發(fā)展的機會,并適當對積極參與培訓,不斷提高自身能力的職教教師給予獎勵,永葆職教教師對自我能力提升與發(fā)展的熱情。最后,各主體應大力宣傳技術技能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扭轉“重學輕術”的局面,將職教教師能力提升到與“大國工匠”同樣的高度去重視,增強職教教師對職業(yè)能力的認同感,提升民眾對職業(yè)教育本質的認可度。
(三)構建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體系
隨著時代深入發(fā)展,社會對于教師專業(yè)性的要求越來越高,職業(yè)教育作為以“能力”為本位的教育類型,其教師所具備的能力越全面、越專業(yè),學生的能力構建則越完善。此外,由于職教教師工作環(huán)境更為復雜,工作內容也更為豐富,這也對他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制定職教教師能力框架體系。依據(jù)實際工作所需將職教教師職業(yè)能力分成若干板塊,如教育教學能力、專業(yè)理論能力、專業(yè)實踐能力、其他工作能力等,再針對每一種能力進行延伸,并細分下一級能力,如教育教學能力可以細分為教育能力和教學能力,而教學能力還可以細分為教學設計能力、課堂組織能力、課堂評價能力等等,通過這樣的逐步疏理,構建出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的框架體系。其次,基于職教教師能力框架制定能力標準。如果說構建能力框架是為了解決“職教教師需要什么樣能力”的問題,那么對能力制定標準則是解決“如何發(fā)展職教教師能力”的問題,通過對不同水平的教師制定不同層次的能力標準,即對新手教師、骨干教師、專家教師制定出不同的能力要求,以期提供給他們明確的上升方向與空間,并以此作為他們考核或晉升的標準,激勵他們重視自身能力的發(fā)展。最后,多主體制定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標準。由于職教教師工作的特殊性,特別是專業(yè)課教師,很多能力都需要在企業(yè)中去歷練,企業(yè)的設施設備換代以及技能技術的更新彰顯出社會發(fā)展對人才要求的不斷升級。因此,要了解行業(yè)發(fā)展動態(tài),培養(yǎng)企業(yè)所需的應用型人才,加強企業(yè)和學校的溝通。而政府作為宏觀層面的主體,不僅緊握國家戰(zhàn)略以及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的船舵,且更能有效架起校企合作的溝通橋梁,因此,三方共同參與職教教師能力標準的制定和完善,能為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保駕護航。
(四)建立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監(jiān)督評估機制
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離不開科學、有效的監(jiān)督評估機制,能力標準的制定和評定也只有通過監(jiān)督評估才能將其意義發(fā)揮出來。首先,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評估機制要注重發(fā)展性和多維性原則,能力發(fā)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每個人的能力發(fā)展速度有快有慢,能力的呈現(xiàn)方式也各有所異,需要用發(fā)展的眼光來看待教師能力的成長,注重個體能力發(fā)展的差異性。此外,基于職教教師工作內容的復雜性,在對教師能力做出評價時,應全面、多維地看待教師能力發(fā)展,如可以從教學維度、學習維度、實踐維度、創(chuàng)新維度等方面入手來綜合評價教師的能力發(fā)展。其次,在選擇評價方法時,由于每一種能力的呈現(xiàn)有隱性與顯性之分,在評價時應注重采取形成性與過程性聯(lián)合評價的方式,特別需要正視過程性評價在教師能力形成中的作用。此外,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也是全面、科學評價教師能力的有效方法。再次,建立多主體評價組織。延續(xù)多主體制定職教教師能力標準的做法,在評價環(huán)節(jié)也應該采取多主體評價機制,即建立第三方組織,組織成員可以從教育部門、企業(yè)、學校中按比例分別選取研究員、一線技術技能人才以及專家教師組成,依據(jù)制定的標準對職教教師能力進行綜合評價。最后,將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評價結果與獎勵機制掛鉤。滿足教師需要是保持內力、促進教師發(fā)展的手段,更是實現(xiàn)教師評價目的的保證[16]。參照評價結果,對符合標準,甚至超過標準的教師給予獎勵,將晉升、評職稱、評優(yōu)評先的占比向能力超群的教師傾斜,是鞭策職教教師能力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
參 考 文 獻
[1]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冊)[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0:110.
[2][3][4][5]孟慶國,曹曄,楊大偉.中國職業(yè)技術師范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6:21.17.22.29.
[6]曹曄,劉宏杰.我國中職師資隊伍培養(yǎng)培訓主要政策60年演變進程綜述[J].職業(yè)技術教育,2010(25):18-24.
[7]曹曄,母華敏.我國中等職業(yè)學校教師職務制度的歷史與現(xiàn)實[J].職業(yè)技術教育,2010(32):61-66.
[8][15]湯秋麗,趙英.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職教教師教育政策的變遷分析——基于歷史制度主義視角[J].現(xiàn)代教育科學,2021(3):91-97.
[9]李曉東.基于崗位能力視角的高職“雙師型”教師認定標準及培養(yǎng)路徑研究[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19(8):76-81.
[10]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yè)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的意見[EO/OL].(2011-11-08)[2021-10-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1111/t20111108_128045.html.
[11]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yè)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2017-2020年)的意見[EO/OL](2016-11-03)[2021-10-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1611/t20161115_288823.html.
[12]教育部等四部門關于印發(fā)《深化新時代職業(yè)教育“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EO/OL].(2019-09-23)[2021-10-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1910/t20191016_403867.html.
[13]鮑宗豪.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需求理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9):64-73.
[14]鐘云華,劉姍.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畢業(yè)生基層就業(yè)政策變遷邏輯與發(fā)展理路——基于1949-2020年政策文本的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21(2):114-124.
[16]陳建超.試論素質教育背景下教師評價機制的構建[J].當代教育論壇,2005(8):38-39.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 polic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professional ability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namely, the stage of emphasizing teachersprofessional skills, the stage of emphasizing teachers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the stage of strenthening teachersability to integ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stage of promoting teachersdiversified ability.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teaching ability has experienced different era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s basically follow demand logic, macro logic and service logic. Standing 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to deepe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ability: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own ability; advocate social institutions to help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ability development; construc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ability development system; establish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teachersability.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policy changes; evolution logic
Author? He Yanfang, lecture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Wu Dan, master stud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