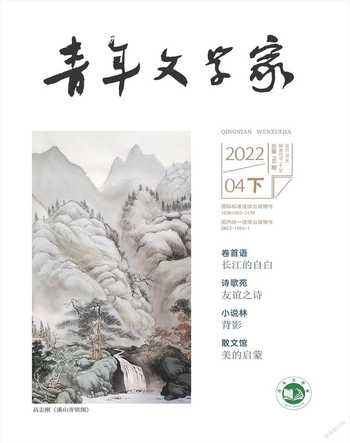一枕秋霜
高偉俊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白山湖濕地的蘆葦,一到白露時節就開始枯黃,湖區呈現一派蒼黃、凄涼的景色。
西域的季節,春夏較短,秋冬尚長。十月,湖邊的矮草上就開始綴滿了白花花的晶霜。早起時,我在湖邊散步,可以看到那秋霜如一攤攤白花花的細鹽,撒在墨綠色的草坪上,它們和鹽堿地的顏色一樣,亮晶晶的。此時此刻,一股凜冽的寒意從地下冒起,鉆入身軀,肌肉不禁有些瑟抖,膝蓋骨如被冰刀刺了一般,隱隱作痛。當高原的晨陽射出一股金燦燦、明晃晃的陽光時,那份深秋的寒意才開始消散,地上的冰霜融化成水滴,滲入到草根下的鹽堿土壤里了。
深秋的晚上,白山湖上空的月亮也格外皎潔明亮,也許地上的水汽正在這皎潔的世界中悄然凝結成一朵朵霜花。湖的四周一片寂寥、沉靜。大片的蘆葦叢,全被水汽彌漫著,霜氣慢慢浸黃了它們夏季青綠的身軀,讓它們的莖稈變得更加結實耐折。仿佛在一夜之間,所有的蘆葦,都在秋霜中枯黃了、變老了。但蒼白的蘆葦花更飄逸了,在夕陽的映照下,顯得愈加凄美、蒼莽。
我在新疆克州阿克陶縣援疆支教已有一年多,也漸漸適應了這邊高寒干燥少雨的氣候。只是因為時差的緣故,我很少在凌晨一點睡下。深秋時節,也是一個愛思念的季節。特別是在一個月光皎潔、澄凈寂寞的異地夜晚,那思念的情緒陡然化成一枕秋霜,頓時染亮了少時的夢鄉……
年少時,我總喜愛站在高崗上,俯瞰那被白霜覆蓋的田野,碧綠的菜葉上點綴著一團團白晶晶的霜花,時隱時現,滿地一片蒼涼。身邊的白狗,一溜煙兒跑到那一片菜畦中,“唰唰”的聲響,它抖落了夜晚凝結在菜葉上的霜花。這時,我看到祖母佝僂著身軀,拿著一只竹籃,在那布滿白霜的田野中采摘一顆顆圓滾滾的圓白菜,經霜打過的圓白菜,吃起來才甘甜有味。
祖母采摘好圓白菜后,徑直朝屋后沙丘壟上走,她粗糙的右手握著一把小鋤頭,左臂上挽著那一個有些枯黃的竹籃。竹籃被祖父編制成時,也是翠綠的顏色,但常年掛在屋檐下,經歷多少風霜,終于收斂了那青春的氣息,也呈現出祖父臉色那一樣的枯黃。祖母小心走到一棵樟樹下,樟樹根部是黃黃的細沙,細沙底下埋著從地里挖來的紅薯,一顆顆濕潤的紅薯埋在沙洞中,深秋的霜氣透過沙隙,把紅薯身體內的淀粉慢慢化為糖分,經霜的紅薯也甘甜如蜜。
小時候,沒有零食裝在口袋中,中午上學時,祖母總要把幾個煮熟了的紅薯放進我的書包內,叮囑我下午餓了就可以當零食吃。那有些冰涼的紅薯,吃在口里,甜甜的味道漾出一點一滴的幸福。
深秋和初冬季節,是鄉村豐收的季節。很多食物經歷了秋霜之后,仿佛變得更加濃郁香甜。如果說,雪是天上飛舞的公主,霜就是地上釀造甜蜜幸福的催化師。雪,可以漫天飛舞,讓人感受到眼前銀裝素裹的景色;而白霜猶如沉默低調的農夫,只默默把自己的身軀涅槃成甘露,滋潤著秋后的蔬菜和果品。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在少年時,不諳世事,感覺不到深秋下霜后的寂寥和悲涼,只覺得下霜的日子也是甜蜜和熱鬧的。
還記得那時上村小讀書,秋季的早晨,我最喜歡穿過一片布滿霜露的田野,踩著田埂上有霜露的小草,霜露沾濕了一雙破舊的解放鞋。我邊走邊看那一片蒼涼冷落的殘荷,它們低著頭,好像犯了錯誤的學生,橫七豎八地站在被秋風吹起皺紋的清水塘上。
到了有月光的晚上,吃好晚飯,邀幾位發小,走幾里田埂路,前往隔壁村的廣場上觀看露天電影;或者隨著幾位鄉村長輩,夾著一張小板凳,跑到村頭新筑鄉屋的村人家聽一番家鄉的“鼓書”。
如今,我年近半百,不知哪天早起,看到洗漱間的玻璃鏡中,自己的雙鬢已染上點點如霜的白發,感覺時光流逝如飛,知道自己已快到“知天命”之年,內心涌起的不再是一種沖動和興奮,而是一股如霜花般的蒼涼感。
人生如四季,中年已到,塵世的秋霜染白了黑發。但在一個清寒的季節里,踏霜奔向遠方,內心依然煥發出年輕時的那一股沖天豪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