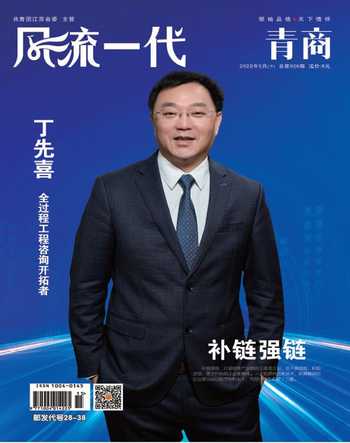后疫情時代的“穩就業”
本刊編輯部


當前就業形勢企穩,除了得益于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間出臺的一系列促進就業政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就業模式的發展。
兩年多前,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這場讓整個世界都毫無準備的疫情在短期內對全球的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此后,在我國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勞動力市場、就業形勢逐漸趨于穩定。如今,在后疫情環境下,全球的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呈現出新的形態,我國在這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比如以平臺就業為代表的新就業模式得到發展,又比如年輕求職者在就業壓力下選擇“慢就業”。
無論模式如何變化,關系到民生的就業在我國“穩就業”的政策保障下,成效可圈可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全國就業人員74652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46773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員比重為62.7%,比上年上升1.1個百分點。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269萬人,比上年多增83萬人。這其中,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網絡技術對穩定就業發揮了極大作用,以平臺就業為代表的新就業模式尤為突出。
就業市場受疫情沖擊
由于事發突然,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內給我國的就業市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在2020年初,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創2018年1月以來新高,城鎮調查失業率在2020年2月達到最高值(6.2%)。在此期間,一般城鎮就業人口下降2640萬人,大量的勞動力退出了市場。國家統計局當時公布的數據顯示,整個就業人口中有約7568萬人處于休假未上班的狀態,占總就業人口的18.3%,整個一季度受到影響的就業人口超過1億。
在2020年一季度,疫情對就業的影響可以分為三類:第一,失業人口增加,按照調查失業率同比上升約一個點計算,新增了400萬人左右;第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增加,城鎮就業人口下降6%,大約2640萬就業者退出勞動市場;第三,受此影響的就業人口中大約有7568萬人處于休假未上班狀態。
從疫情對各個群體就業的影響情況看,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疫情下我國就業形勢與就業模式變化》顯示,農民工群體受疫情沖擊的時間短,就業形勢從長期來看較為平穩,波動幅度較小,目前已經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年輕群體和高校畢業生在疫情期間就業受到沖擊較深,持續時間長,波動幅度大,目前來看影響還未完全消除,所以需要在經濟層面探索適合他們的就業模式。
盡管短期內疫情對就業市場的沖擊不小,但從整體來看,我國的失業率將長期呈現平穩下降的趨勢。從失業率的波動幅度來看,疫情初期失業率波動幅度較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失業率波動幅度逐漸減小。從持續時間來看,疫情對失業率的沖擊持續了一年左右。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顯示,從長期來看,就業市場景氣回升速度快,在2020年第三、第四季度回升最為明顯。雖然疫情造成就業市場出現波動,但對我國就業形勢整體處于平穩向上這一趨勢并沒有影響。
“穩就業”面臨不小壓力
雖然后疫情時代失業率長期處于平穩下降的趨勢并沒有改變,但受疫情零星反撲、國際局勢日趨復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影響,國內就業形勢的穩定仍舊面臨著不小的挑戰和壓力。
2022年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到1076萬人,比上年度增加167萬人,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招工難”“求職難”等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緩解,而部分行業和企業的生產經營可能受到疫情的影響或沖擊,用工需求仍將出現波動。
總體而言,當前我國就業形勢較以往更加嚴峻,壓力既來自突發疫情的沖擊,也來自我國一直存在的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
從需求側來看,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傳統產業衰退使得企業用工萎縮;而新興產業發展所需要的高層次、高技能、創新型人才匱乏。人社部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聯合阿里巴巴釘釘發布的報告顯示,包括云計算工程技術人員、物聯網安裝調試員、電子競技員、數字化管理師等在內的新職業人才缺口超千萬。從供給側看,勞動者的技能和素養難以適應崗位要求,尤其是幾大重點就業群體更為明顯:高校畢業生文化水平及其對工作的要求相對較高,但社會經驗少,實踐技能不足,專業選擇與實際需求存在著結構性錯配,熱門專業畢業生供過于求,而冷門專業和技術類專業畢業生供不應求;農民工群體的文化層次普遍較低,且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劇;去產能企業職工往往技能單一,文化水平偏低,年齡偏大;退役軍人專業技能與社會需求匹配度不高。
新就業模式蓬勃發展
當前就業形勢企穩,除了得益于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間出臺的一系列促進就業政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就業模式的發展。
所謂的新就業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網絡技術,伴隨著數字經濟平臺而產生的新的工作組織形式。它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組織方式依托網絡平臺,因此具有靈活性、分散性;第二是勞動者與工作崗位的結合方式發生了變化,由此衍生出新的依托于平臺的勞動關系,第一種是自雇(創業),第二種是較為有彈性的平臺雇傭關系;第三種是工作狀態發生變化,在時間和空間上更具靈活性。
就業模式通常受到技術的影響。我國正在經歷第四次新技術革命,新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就業模式,進而影響到勞動市場就業數量和就業結構的變化。比如在疫情之下,傳統就業模式受到的影響較大,以技術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就業模式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
當前我國存在著包括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不同類型的新技術,不同的技術會產生不同的就業模式,但就目前來看,對就業穩定發揮最大作用的就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網絡技術。
《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疫情下我國就業形勢與就業模式變化》顯示,新就業模式在疫情期間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疫情之后,以阿里巴巴、抖音、美團等為代表的經濟平臺提供的工作資源達到1億個以上,其中抖音平臺的工作機會增加了3000萬個以上;美團方面的數據亦顯示2020年上半年美團平臺的騎手人員相比于2019年上半年增加了41.6萬。
從數字經濟招聘占總招聘規模的比重來看,經濟水平越發達的地方,數字經濟對就業的貢獻越大,比如廣東、北京、上海數字經濟招聘占比分別高達26%、18%和12%,這也說明數字經濟就業模式是未來的一種發展趨勢。
新就業模式下雇傭關系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目前國內個體工商戶已達到2.3億,且這一數據還在上升,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平臺就業。對于平臺就業,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副主任王衛東表示,預計10年之后平臺就業的比例會越來越高。盡管新就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但由于其處于發展初期,因此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杜鳳蓮表示,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的關系,需要以政策和制度進一步明確,否則存在風險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