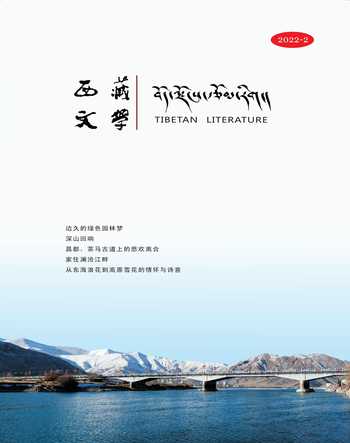深山回響

赤列索巴,筆名零。西藏芒康人,90后母語小說寫作者。1993年出生在昌都市芒康縣徐中鄉布查村,布查村屬于半農半牧地區。2012年開始詩歌創作,2014年藏語小說處女作《瀾滄江邊的情歌》發表在刊物上,2016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2015年起作品發表在《民族文學》《西藏文藝》《貢嘎山》《青海湖》等報刊雜志上。
我年滿十一歲的那天,看到父親在打開他的鐵皮箱。每次父親打開鐵皮箱,箱子里安睡的糖,得以重見天日,落入我的手掌里。以前家里人不在的時候,我想辦法打開掛在箱子外面的鎖,鎖沒能打開,自己卻累趴了。父親腰上戴著的那把小巧的鑰匙,只要輕輕插入鎖孔里,清脆悅耳的“咔嚓”聲一響,箱子便打開了。今天我跟往常一樣,走到父親跟前伸手,等待那些五顏六色的糖離開父親的手,落到我的小手中。父親從箱子里拿出的不是糖,是黑布罩著的沉重的東西,父親小心翼翼地把黑布解開,里面亮出的是一把手槍。
父親說:“你爺爺到十一歲的時候,用這把槍去仇家的村落里搶來了牛羊;你父親十一歲的時候,帶著這把槍,去山上打獵;現在我的兒子,你已十一歲了,不能整天想著玩泥巴,應該做一些男子漢該做的事情。”我接過父親手中的槍,帶上一袋子彈,到田野里玩槍去了。從此,糖不香了,玩泥巴也沒啥意思了。
我出生的時候,既不能做強盜,又不能上山打獵,連無惡不作的狼都保護起來了。每每,狼追山羊的時候,我們布查村的人都來到屋頂上,大聲地叫喊,起初狼聽到人的聲音就灰溜溜地跑。但是時間一長狼也慢慢明白過來,人們不過是在虛張聲勢,不能把它怎么樣。現在我們一叫,狼追起羊來更起勁,我們是在為它加油打氣似的,狼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把羊追得跑不動了,不緊不慢地咬羊的脖子吸血,吸完了這只再吸另外那只,羊群累得已經沒了抵抗能力。
看到羊一只一只地死去,以前的打獵能手,阿古曲杰氣不過,拿起已經積著灰塵的長槍來,裝上子彈,來到屋頂,給那只狼開了一槍,我們看見那只狼從山上掉下來,落到公路上。
“打中了,打中了!”我興奮地叫起來,準備跑出去一睹究竟。但我的父親說:“叫什么叫,耐心一點,如果狼沒死的話,就有你好看的。”說的好像放槍的就是他似的。
半個小時后,父親小心翼翼地沿著公路走過去,到了那邊給我們做了個手勢,意思是狼已經死了。我跑出去,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跑出來,那只狼灰頭灰臉地掉落在公路上,血流不停,毫無尊嚴可言。平時,布查村的人連螞蟻也不忍踩,如果不小心踩到,要念瑪尼,吹氣,將尸體放在路邊。今天看到惡狼斃命,沒有一個人發慈悲心,我們大家吃被狼殺死的羊肉吃得都膩了,全村人的身上散發出羊肉的膻味,村人之間感覺不到,一旦到了其他村,同沒吃過羊肉的人一見面就能聞到,別的村把布查村人的汗水味中滲著羊肉膻味的獨特味道叫做“布查村之味”。在布查村,家家都養山羊,但不是為了吃肉,而是為了豆狀的羊糞。據說,田里施了羊糞肥料和沒施羊糞肥料,一看就能分辨出來,長出的青稞顆粒大小不一樣,勇瑪(圓根)的大小都不一樣,施了羊糞肥的田里長出來的青稞秸稈粗長、葉子深綠;勇瑪的根部龐大,葉子綠里透黑,所以在布查村里羊的死去,意味著莊稼收成的減少。
這時候,阿古曲杰也得意洋洋地跑來了,他說:“怎么樣,準吧?打獵高手不是白叫的。”
過后,野生動物保護站工作人員聞聲而來,阿古曲杰夾起尾巴跑了。他們先對死狼檢查、拍照之后,尸體放到汽車里,好像狼的尸體是個有用的寶貝,既可以吃,又可以喝似的。
領導給手下說了一句干澀難懂的話:“把嫌疑人抓回來,沒收犯罪工具!”
我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們布查村人就叫“領導語”,領導說領導語的時候,我們只能從他的手勢和表情中,做一些大概的判斷。
手下對他的手下說:“聽到沒有?領導說了,把嫌疑人抓回來,沒收犯罪? ?工具!”
手下也想對自己的手下下達同樣的命令,但他看到自己是最下級,他決定自己去執行的時候,汽車司機下了車,手下的眼睛明亮了起來。
手下對汽車司機傳達了同樣的? ?命令。
汽車司機是個非常精神的小伙,當然他比我大很多,但是布查村的老人們看到能干的年輕人就會這樣說:“非常精神的小伙。”我也想盡快成為精神小伙,但山谷里的時間走得慢,個子長不快。汽車司機把瘦長的羊腸小道用一分鐘跑完,還沒到下一分鐘,就帶著阿古曲杰和長槍回來了。確切地說,汽車司機帶著槍,槍帶著阿古曲杰。
我們才明白過來領導語的意思,所謂“嫌疑人”原來是阿古曲杰,“犯罪工具”其實就是槍。
阿古曲杰沒了之前的得意神情,他說:“你們抓我干嗎?這狼的命數已經到了,今天我只是嚇唬一下它,槍沒瞄準就開了,結果一命嗚呼。不是很明顯么?你們也知道嶺國的加嚓西嘎命數一到,失手落到德青星巴的長矛上去的。”工作人員沒理他,把他推進車里,車屁股后揚起塵埃走了。
十天后,阿古曲杰回來了。我們問他:“在看守所里生活得怎么樣?”他一句話也不說,如此一來,知道問不出什么東西,別人就不問了。
那天,山上又出現了狼,這次有三匹狼,這三匹狼把羊群包圍起來,它們相互協作,有目標、有步驟地抓起羊來,我們布查村的人都來到自家的屋頂上喊叫。阿古曲杰除外,他坐在自家的屋頂上,瞇起眼,有滋有味地看狼吃羊。
白天與黑夜交織的間隙中,阿古曲杰從我家的門口探出頭來。他對離門口最近的我說:“好久沒有吃蜂蜜了,好侄子,給我倒一碗蜂蜜。”他舔了舔自己的嘴巴,好像我家的空氣里飄蕩蜂蜜似的。
我拿了碗,跑到倉庫里從大桶中挖了一碗蜂蜜。他每次見到我就叫我“好侄子”,但我是不是他的侄子無從考證。我家與布查村的其他八戶人家有點親戚關系,不是媽媽的親戚,就是爸爸的親戚。不是爸媽的親戚,就是爺爺奶奶的親戚。
阿古曲杰想吃蜂蜜的時候會到我家來坐坐。我們家養著三十多箱蜜蜂,家人都不愛吃蜂蜜,一大箱一大箱的蜂蜜存在倉庫里,大部分已經變成了冰雪一樣的固體。很多人一看到蜂蜜就會流口水,沒有明顯地向外流,但舌頭和牙齒之間已經充滿了口水,等著咽下去,但是我不喜歡這種過甜的東西。我觀察發現,家人給的東西不好吃,但自己偷偷摸摸取得的東西又顯得異常地好吃,在家里吃雞蛋的時候沒什么味道,偷偷弄出去,在山上放羊的時候吃的話,又變得異常地好吃了。阿古曲杰給我傳授過偷吃蜂蜜的技巧,柳樹枝插到養蜂箱里,拿出時樹枝上粘滿了蜂蜜,那是非常便捷的取蜂蜜的辦法。
布查村人看到我們家周圍布滿了蜜蜂箱,就說我的爺爺有蜜蜂養殖的絕技,其中的一小些傳給他們的話,布查村的每戶人家都會有蜂蜜吃。
幾年前,阿古曲杰從我家拿走了三箱蜜蜂,說是他要把蜜蜂養得天天有蜂蜜。那天爺爺、阿古曲杰、我各背著一箱蜜蜂箱,踏著青稞田間的小道向他家的方向走去。
爺爺說:“養蜂要給蜜蜂留一口,自己吃一口,不能一下全挖走了。”
阿古曲杰說:“知道了。”
爺爺說:“春天荊棘花開完后有荊棘蜜;夏天油菜花開后有油菜花蜜;冬天有冬蜜。提前要敲敲蜜蜂箱,響聲空洞說明沒有蜜,響聲沉悶可以開箱挖了。”
阿古曲杰說:“明白。”
一個月后阿古曲杰跑過來說:“蜜蜂全跑了。”
我爺爺生氣地問:“怎么搞的?”
阿古曲杰說:“我把蜂蜜全挖了。”
我爺爺罵道:“你這是怎么搞的!”
“我挖到一半,切口上流著深黃的蜂蜜呢,怕浪費,忍不住全部挖了。”
爺爺說:“你回去吧,跑去的蜜蜂我也沒辦法叫回來了。”
阿古曲杰瞇著眼吃罷蜂蜜說:“縣里招待所(賓館)里不知是啥味,有塵土上灑了水后的那種味道。”說起縣城不說被關的事情,話題永遠離不開招待所。
“深夜口渴,開了他們故意放在床頭柜上的水瓶。按他們的話說,早上退房的時候,退房不知道是啥意思,房子也可以退回去?那時候他們要我多交三十塊錢,我說為啥?他們說因為你喝了水。”
走前,爺爺挖了一團蜂蜜給他。過幾天爺爺笑著說:“送給阿古曲杰的那團蜂蜜在他家水桶中消失不見了,他以為蜂蜜也像酥油一樣在冰水中會變得更加堅固。”
布查村的羊越來越少了,有些人家,把剩下的羊賣給開著東風車來的商人。但是到城里打工回來的哥次扎說:“東風車會把羊運到工廠里,羊從機器的入口趕進去,出來的時候,羊的肉已經做成了火腿腸,毛做成了帽子和圍巾,羊的皮已經做成了熱乎乎的皮鞋。”
布查村的人們都說:“和機器相比,狼是仁慈的,它只喝血,肉留給我們。”
東風車的喇叭聲,把家里的窗戶震得嘶嘶響,但我們當做沒聽見,羊群在山里自生自滅。過幾個月后,山羊從布查村的歷史舞臺中退了出來,布查村的青稞和勇瑪綠油油地在田里照樣生長。
在這樣背景下,我年滿十一歲,擁有了那把槍。阿古曲杰主持正義的槍聲中,我聽到了殺生的快感,不能打獵,也可以讓槍發出聲音來,“噠”一聲,可以用來驚嚇一群吃飽喝足的鹿群,讓它們在森林里到處亂跑,給死氣沉沉的森林,增添一份生機。因環境所迫,我不可能成為“噠”的槍聲一響,讓一位茶馬古道上的巨商從馬背上落下的強盜。但用我的這把槍,可以把那些給天空噪聲的烏鴉,打掃干凈。當槍聲響起,布查村天空會得到片刻的寧靜,沒了烏鴉厭人的叫聲。我用手槍殺了烏鴉,殺了那些將來春天會吃蘋果花的,喜歡自作聰明的小鳥。生來膽小如鼠的我,有了槍膽子大起來;有了槍,感覺自己是個傳奇強盜或者打獵能手,只要看到有生靈在動,某種沖動從內心轉到手指,就想來一槍,對準,讓槍口冒煙,發出“噠”的聲響。
在布谷鳥的叫聲中,一個酸溜溜的夏日,落入布查村所在的山谷中。核桃樹茂盛,烏鴉和小鳥們隱形于樹葉之中。沒了目標,我手中的槍變成了一塊廢鐵。我無所事事,坐在核桃樹的暗影中,太陽越毒,深山蟬叫得越響。蟬聲無處不在,沒辦法,我只能當做沒聽見。但心煩意亂,只能用半濕的布不斷擦槍來打發時間。擦得亮油油的,拿到手里,感覺槍順手了很多,想給天空放上一槍,但是無濟于事的,要知道,深山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話癆,做什么也影響不了它們盡情尖叫,我只能盼望著下雨、盼望著天黑,一下雨、天一黑,它們就變成了啞巴。
“喵喵——”
一只黑貓,輕手輕腳地走過來,停在四五步之外,謹慎地觀察我。玻璃球一樣的眼珠在陽光中泛光,我看不到它臉上的表情。這一點,貓和狗之間,有天壤之別,如果是狗,它會模仿主人的表情,知道主人喜歡什么樣的表情,看見主人,就搖著尾巴,做出可憐巴巴的神情來,久而久之,受到主人的影響,狗就有了主人的性情。看那只阿古曲杰家的藏獒,以前是那種準備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情的表情,現在卻變成了看熱鬧不怕事大的神情。這個變化肯定與阿古曲杰去看守所前后性格轉變有關。我偷偷觀察過狗,發現只剩下它自己時,臉就會拉得很長,變成憂心忡忡的樣子,表情也消失了。貓呢,沒有表情,時時刻刻處于戰時狀態,都保持著謹慎。它覺得我沒有威脅性,向前進行試探。我又不是老鼠,不精于貓鼠游戲,發亮的槍對準它,按下扳機。
“噠”一響,它的玻璃球一樣的一只眼不見了。它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目瞪口呆地站了片刻。
一秒鐘后,尖叫一聲,飛速逃走了。
過了一天,村人都在說阿古曲杰家的貓挨了子彈,他們沒有明說,但心里知道是我干的。
之后我看到它出沒于田間地頭,我拿著槍,輕手輕腳地去找它,打算把它的另一個玻璃球也給打爛。它也吸取了教訓,變聰明了,只要田里有了我的氣息,就沒了它的蹤影。
幾年后,有人在玉日神山的山洞中看到了那只貓的尸體,說是空洞洞的眼里擠滿了肉蟲。
幾年后,那些啄蘋果花、梨花、桃花花苞的無惡不作的小鳥和鳥類中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烏鴉都成了保護動物。我們看著水果的花苞還沒綻放之前被小鳥給啄光了。
清晨,天還沒有亮透,它們在果園里忙碌起來,果園里花沒開之前,它們來秋收了。誰家的屋頂上有風干牛肉和奶酪,機會主義者們趁機而動,在主人的注視下,成群結隊地來,明目張膽地搬動起來,好像這些都是它們的勞動成果似的。這些機會主義者小腦袋中裝著比人類還復雜的腦神經,誰家的牛死在山上,如果有傷口,它們不吱聲,偷偷摸摸地吃起來。如果沒有傷口,它們吃不動,方圓十里都有它們的尖叫聲,好讓所有的肉食動物都能聽得見,它們有計劃、有組織地飛往周圍的村落。
很久以前就保護起來的猴子、灰熊、狼帶著自己肥胖得變了形的身體,到村子里來散步了,散步者里最具代表性的有兔猻、猞猁、雪豹,我們布查村的老人們說它們三個是兄弟,老大兔猻舍不得吃好吃好喝的,都讓兩個弟弟吃,自己由于營養不足而長得矮小丑陋;雪豹是老三,有兩個哥哥寵著長得白凈,高大威武;猞猁位于中間,前面有老大,后面有小弟,不高不低,不丑又不俊。老大兔猻從不來村子里散步,只是到離村不遠的草地上做了什么錯事一樣偷偷摸摸地走來走去,聽到有人叫的時候,會回頭看看,它的表情永遠是不開心似的哭喪著臉;老三雪豹偶爾到村里轉一圈之后在山上消失掉了。后來我們才知道其貌不揚的老二猞猁喜歡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當深夜降臨它就出現了,它最喜歡吃蜂蜜,我家養殖的蜜蜂箱就遭殃了,連蜜蜂也被當成了點心和蜂蜜一同吃光了。
我們只要跑到屋頂,看一下布查村的全景就知道,布查村已經成為不需要門票的動物園。它們中特點最突出的,當屬白額頭灰熊。照理說,白額頭的灰熊極少或者不會有,但是布查村散步的灰熊中就有一個,它個頭跟牦牛一樣,從前面看有點可愛,從后面看肉墩墩的有點可笑。我們布查村的有些人說,白額頭灰熊是祥瑞之獸;有些人說,白額頭灰熊代表著末日之兆,是自然界亂了套的產物。只有我看出白額頭熊來者不善,也許別的灰熊來布查村純屬是散步的,但我從白額頭灰熊泛著賤光的眼神中,看到它有其他目的,也許散步是它的副業。前幾個月,我們鄰村一名小伙,晚上去田野里解手的時候被熊給吃了,我猜準是這頭白額頭灰熊干的。因為村里的老人們說過,熊吃過人肉之后會上癮的。白額頭灰熊已經成為布查村不可缺少的一員,村人看似不怕它,不在意它的存在,但大家心里清楚,它是肉食動物,所以晚上一人要上廁所的時候,家中三四個人陪著去,或者盡可能地天黑之前去解決。上廁所容易被熊吃的原因在于,布查村里根本就沒有廁所,解手必須在田間地頭解決。布查村人一進縣城,這種習慣也帶到縣城去,在布查村里田間解決,有利于田里的禾苗,核桃樹下解決,有利于核桃樹的生長,但縣城的街道邊整整齊齊的綠化帶和大紫大紅的花園里隨地大小便的時候,縣里人會向我們吐口水,臉上盡是不屑的表情,如此看來大小便對城里的花草樹木是毫無用處。
話說回來,身邊的一切動物,都成了保護對象,我的槍變得毫無作用。我無聊地把槍拆解,再也沒有重組起來。
不久動物保護站工作人員和警察進入布查村,一家一戶地查起槍來,說私藏槍支是犯法的,每家每戶在沒查之前,就將生銹的那些槍主動交了上去。看著大人們嚴肅的表情覺得好玩,我也找自己槍的零件來,槍沒找到只找到了半袋子彈,我把這些子彈交給警察叔叔手里,警察叔叔把鐵珠子彈倒在手里檢查了一會,然后,笑著說:“小兒科。”子彈袋子向我拋了回來。
阿古曲杰老了很多,自從殺狼事件之后,話變少了,但還帶著以前話多的后遺癥,主要表現在怕冷場上,和別人待在一起,無話可說,落入寂靜的時候,他的雙手不斷地摩擦,坐立不安。他沒話找話,說出槍聲和時間,這正是他不愿意談的話題,槍聲和時間傷害過他,一直藏在潛意識深處,不得不說話的時候才脫口而出。 他說:“啊!這個長槍的聲音多響!”別人問他“槍聲在哪個方向響?”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為根本就沒有槍聲,只有寂靜,槍聲是無中生有的。他只是想打破可怕的寂靜而已,但引來了別人的嘲笑,人們叫他“長槍”。
阿古曲杰老了之后,他對我說:“好侄子,時間變了,你感覺到了么?”
我說:“我沒什么感覺,時間按照原樣在走呢。”
他說:“所有的生靈都在時間的長河中漂流著,如果時間改變了方向,會把所有的生靈都帶到另外一個方向去,誰也反抗不了。因為我們靠時間而生存,沒人能逃到時間之外。”
他又神秘兮兮地跟我說:“知道嘛,我們隔壁德西村后山深林里發現了金絲猴,說是整個村要生態移民呢。知道嘛?次扎從成都打工回來,說是很多動物開始穿衣服嘞,他說還看到了動物醫院。”
我沒有感覺到時間在改變方向,而是強烈地感覺到時間流得越來越快了。那時候我才剛剛觀察、思考時間的存在,以前對我來說時間只有兩種:吃飯的時間和睡覺的時間。但現在我發現今天吃完后明天得繼續吃,今天睡完后明天得繼續睡;發現一年有四季,春季布查村在重復往年春季做過的事情,種子灑向大地,到秋季時和往年同樣的動作,收回種子的果實。時間像河一樣流向所有東西的內核。時間淹沒了我的槍,洗去了記憶中左眼黑洞洞的貓。時間流去之后,本來在時間深處的一些東西露出真面目來。比如我的槍在手里的時候,是實實在在的一把槍,壞了、丟了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槍不過是仿真槍,它會發聲,它有鐵珠子彈,它能射得很遠,它能殺死烏鴉,但和真槍比起來不過是玩具槍。我初次明白這些道理的時候,如同第一次看露天電影后,聽到見過世面的哥次扎說:“那是演的,是假的。”
十三歲那年,我到鄉中心小學上學。因為個子高,四肢發達,一入學就直接弄到了六年級里,說是六年級里學生人數不達標。六年級的學生都比我高大,比我發達,我的到來如同誤入綿羊群里的山羊一樣突出。死氣沉沉、塵土飛揚的教室有了一絲的生機。他們首先要給我介紹女生,我不知道介紹是什么意思,我看到只要塊頭非常大的那個女生走進教室,男生都叫:“索巴和措央。”索巴是我的名字,措央是那個女生。名叫措央的大塊頭女生,惱羞成怒,誰叫跟誰急。用木板搭建的簡陋教室里,腳下都是沙石。大塊頭女生把男生們一追,教室里雞犬不寧,塵土飛揚,上課后空氣中的塵埃才落定下來,落滿頭發上、桌子上、作業本上,進到嘴里牙齒之間沙沙作響。
老師進來之前,他們把我的腳綁到凳子上,老師一進來說:“同學們好。”
同學們站起來大聲喊:“老師好!”
我站不起來,之后由于強行站立,凳子的腳壞掉了。每一次上課,我好像坐在空氣上一樣,膽顫心驚,黑板上千奇百怪的文字,一個也記不進去。有天,一下課,我抱著凳子直接走到從徐中鄉流向布查村的無名河邊,拿來了石頭、干樹枝、舊衣物,把凳子綁得異常結實。我坐在這張結實的凳子上,懸在空中的心落入我的身體里,每次上課鈴聲一響我就舒舒服服地進入夢鄉。但藏文老師除外,在藏文課上,全班同學沒有一個敢在凳子上挪動一下身子,鴉雀無聲,有的同學不敢出氣。而我往自己的眼皮上不斷抹著口水,以免眼皮覆蓋眼珠而進入夢鄉。每次我在自己眼皮上抹口水的時候,藏文老師會說:“看!小貓咪要睡覺了,在洗臉呢。”但是我身在戲中不知戲,不知道說的是我,同學們笑的時候,我也跟著笑。長大后,有一次仔細觀察了貓咪洗臉的過程,和自己往眼皮上抹口水的動作如出一轍,才明白老師說的是誰。
同學們都要我出洋相,我也在老師面前出洋相,在女同學面前出洋相。起初我出洋相出得特別真實,洋相出的越多,越來越有些夸張了。一些眼尖的同學開始發現我是在演,而不是在真的出洋相。對我出洋相這件事,越來越不感興趣了,教室里經久飄揚的塵埃也落定了下來。
我雖上到六年級,但依舊和低年級的學生住在一起,我發現他們喜歡做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來。常常想家的小羅鄧被窩里取出一只跳蚤,我們要他立刻殺掉,他卻說:“它好像昨天是從家里帶過來的。”然后把跳蚤放進自己腋下放生了;睡上鋪的扎森常尿床,下鋪的尼瑪桑布深受其害,就把我們布查村常用的諺語“天快要亮時不尿床”掛在嘴邊;桑培諾布由于沒做作業,老師讓他在教室外面站著上課的時候,師生們發現他睡著了,怎么叫也弄不醒。從此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洛尼”,意思是站著睡覺的人;我呢,喜歡一直背著父親給我做的書包——牛皮袋。玩的時候背著牛皮袋,上課的時候背著牛皮袋,睡覺的時候也背著,連上廁所也背著,所以同學給我起了個外號叫“牛皮袋”。我恨死了我的外號,也恨死了牛皮袋,但我不得不天天背著。一是我確實沒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書包;二是我從家里出發時父親教導我說:“兒啊,你要保護好我給你做的牛皮袋,這種精美的東西不能被別人偷了。”
星期六、天回到家,我的父親見人就說:“我的孩子年紀輕輕就要小學畢業了。”
“上學這件事上,越年輕越好。”這句話,不知道是誰給他說的,只要有空,父親就不斷地重復著。我偷聽到他從十三數到二十二。
十三到二十二不難數。我沒上學之前,不用手指也能數清。不明白父親為什么要計算這么簡單的數學題。我終于忍不住問:“爸爸,你這是在數什么?”
我從父親的眼中看到了平時看不到的光,父親說:“兒子啊,我算了一下,你到二十二歲就能大學畢業了。”
我沒聽說過大學這個詞,打賭我們布查村里,除了常常到外面打工的哥次扎和我的父親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大學這個詞是什么意思。因為布查村里數哥次扎和我的父親見識最廣。哥次扎去過外面的世界,而我父親一輩子沒出過布查村。我不明白在一樣的環境中,父親為什么比別人聰明,比別人有智慧。我經過長時間的觀察研究,發現父親變聰明的秘訣,父親有事沒事都最大限度地嗅著空氣。看到他的鼻子里很多塵埃進進出出,這些塵埃有些來自山的那邊,也就是哥次扎去打工的外面世界。父親在布查村里的空氣中,嗅出外面世界的信息來。哥次扎千辛萬苦地到外面的世界,又跋山涉水地回到布查村,準備給村人講外面世界的精彩的時候,才發現他要講的事情都被我的父親講過了。布查村人最不喜歡已經知道的事情被重復地講。我的父親還能嗅出從未來漂浮而來的塵埃的味道,嗅出今后將要發生的事情來。現在我看見父親的鼻子動了一下,從我的頭頂飛過去的問號被吸進去了,我沒開口之前,父親已經知道了我的問題——“什么是大學?”
“大學畢業后,就能成為干部。”父親回答說。
“爸爸,如果成為干部,像上次到村里的名叫工作組的那些人一樣,可以穿西裝?”
“不僅可以穿西裝,還不用干農活。”父親說。
之后,我成為布查村里的第一個初中生。
父親讓我騎我家的老白馬,他牽著馬,我們越過雪山,到鹽井去上中學。路上我問父親:“我倆為什么要自討苦吃,待在家里不好嗎?”
父親說:“我們家里人太多了,牛太多了,你長大后家里就容不下你了。最好不要圖舒服,你的前面只有一個路子,那就是上學。”
父親這么一說,我第一次算起家人來,我們家總共有十六口人。平時為什么覺得人不多呢?為什么一家人待在一起的時候不擠呢?因為我還沒有長大,我想。
記得前些年,灰熊、狼、雪豹在村子里出沒的時候,我父親用很低的價格買來布查村里的所有犏牛和牦牛。我們家的院子里一下子有了八十多頭牛。大哥和叔叔、我,把這些牛趕到高山草地上,遠離灰熊、狼、雪豹出沒的村落和森林。我們仨一年四季在高山上,逐水草而居,三名農民突然變成了三個牧民。每月把酥油、奶酪、牛肉干送到山下的家里,我們家里實在放不下的時候,高價賣給那些開東風車的商人。我們仨為這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有一天我高高興興地下山來到村子的時候,我父親正在發酒瘋,說他一手造就了這個家,但我這個小牧童不同意這句話。
之后,我成為布查村的第一個高 中生。
快要高考的時候,我夢見了神山玉日山洞里的死貓,高考越近,夢越逼真。它在給我展示沒有眼珠的左眼,說:“你殺了我的一只眼睛,我身上的一部分死掉了,所以我不想活在世上,這個世界本是完整的生活叢林。死后才發現更需要完整,死后我的左眼依舊瞎著,沒有因死而修復、因死而圓滿。死后,我的靈魂依舊瞎著!”
一直以來,學習、考試都順順利利,我相信自己所有考試閉著眼睛也能通過。因為夢,我變得慌張,疑神疑鬼,害怕路邊的花和蝴蝶。走在路上,從樹上掉下的一片葉子都能讓我驚叫。以父親生病為由,向學校請了一個星期的假。
一到家,看到父親臉上憂慮的神情,我給父親解釋道:“學校讓我們休息一個星期,放松身心,迎接高考。”父親臉上繃緊的肌肉放松了下來。有一天,家人都出去了,只留下我一個在家,我趁這個機會,實施起這次回來的目的。
我將洗得干干凈凈的青稞、小麥、大米摻雜在一個小包里,帶著一瓶水爬上了神山玉日。
到山腰,回頭看了看布查村。這時,太陽把布查村分成兩半,一半在太陽里清晰明亮,一半在陰影里模糊不清。以前,每一寸地、一塊石頭都覺得特別的大,現在布查村縮小了。在山谷之間夾著,顯得狹長,好像一條死蛇落在那里。以前灌溉用的水渠上,已經建起了瀝青路。盛夏的布查村是山谷中的一抹綠,核桃樹葉舒展,田地里的青稞、小麥結出穗子來,空氣中到處都是稞苗氣味。由于缺水,到了秋天,布查村的核桃只有豆子那么大,村人不喜歡這種核桃,但松鼠們可喜歡了,沒人跟它們搶食,運起來又輕便。看完了無生氣的布查村,爬起山來更沒勁了,感覺到自己的心變重了很多。手機相機開啟全景模式,想給布查村拍個全景,但拍到我家的時候,拍不到鄰居家,很多重要的地方,被石頭和樹木擋住了。
平時回到沒有信號的布查村,手機就變成一塊廢鐵,心里常常想有沒有重要的信息發過來?爬上神山玉日,爬到山腰有信號的地方,手機鈴聲就會響起來,每次重要的信息一個都沒有,都是一些不重要而無聊的信息。之后,我也借著信號,給遠方的朋友說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下山去。
神山玉日山頂有供養煨桑的地方。
我采完松柏枝,站在神山玉日的峰頂,風中五彩的隆達在嘶嘶響。我在桑爐中堆滿干荊棘枝,最下面放上助燃的一團雜草。火柴劃了三次,前兩次被風吹滅,后一次勉強點著了。空氣中飄著火柴和干草混合的氣味。火柴點燃了干草,干草點燃了樹枝,上面放上一團松柏枝。煙霧中我祈愿:“愿盡快消除惡夢,愿早得清凈心!”聞到煨桑味的小鳥們,嘰嘰喳喳叫著,在附近的樹枝上飛來飛去。
我走上了回校的路。出發前,家人要我多待幾天,他們說:“你的臉色像豬肝一樣,紅里透青。”我想盡快地離開這里。
之后,我成為了布查村的第一個大學生,成為北京某所大學里年齡最小的學生。
畢業后,我成了布查村唯一的公務員和城里人。
大四那年,家里的事情都稱心如意,我的父親最喜歡的事情是去山上放牧,自從我上學之后,他替叔叔和大哥放牧,叔叔和大哥在山谷里替他干農活。父親在山上放牧之余與來山上買酥油和奶酪的商人進行交易,從他們那兒除了錢,還會得到一些生活用品,其中就有父親喜歡的白酒。父親喝酒的原因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拉肚子喝點酒就好,一發不可收拾;天氣冷了喝點酒暖暖身子,一發不可收拾;放牧回來,遇到好友在喝酒,好友一般會說:“來嘗嘗,干活后喝的酒味道會有所不同。”之后一發不可收拾。喝酒的父親變成不喝酒的父親的反面,一個有智慧的人一下子變成了愚蠢的人。喝酒喝的有多猛,酒后就有多痛苦,嘔吐、頭疼、后背痛、腰痛,全身上下沒有一塊是不痛的。父親病懨懨地躺在床上,不斷罵著酒水。罵完后,說要戒酒。父親要戒酒時想到了離布查村不遠的高地上修行的空行母。
到空行母那邊戒酒的那幾天,心里想的都是酒,吸入鼻孔中的塵埃里只有酒的味道,父親正心煩意亂地坐在帳篷中,在三石灶的火灰上煮起了酥油,平時酥油融化的芬芳香氣,現在一入鼻就感到陣陣的惡心。酥油融化,正沸騰的時候,阿古曲杰背著大牛皮袋,手里拿著斧頭,進入了帳篷。父親看到牛皮袋,想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一瓶酒睡在牛皮袋里面,父親的眼睛發亮了。阿古曲杰坐下,從牛皮袋中拿出木碗、青稞餅、辣椒等一大堆無用的東西,就是沒有酒。阿古曲杰說:“我不喝熱酥油,對肝不好。”那是反話,布查村人都喜歡吃蜂蜜,喜歡喝熱酥油。但布查村人到別人家吃飯的時候要客氣,這個不吃,那個不喝的,這已經變成布查村里約定俗成的習俗。所以阿古曲杰想喝熱酥油也說肝不好,其實他的肝好著呢。在阿古曲杰的牛皮袋中,父親沒看到自己想要的酒就賭氣地說:“你不喝,就讓佛喝吧。”他把酥油都倒入酥油燈中,看到此情,阿古曲杰的臉都紅了。
傍晚阿古曲杰,從牛皮袋里拿出一塊肉,放到三石灶邊的火灰上烤。我父親說:“高山上不要烤肉,容易引來非人。”但早上沒倒酥油的緣故,阿古曲杰沒有拿回肉的意思,肉在火灰上烤著,白煙裊裊,肉香四溢。阿古曲杰在青稞餅上用刀割成小塊,有滋有味地吃起來。父親不斷咽口水,但是沒有開口要,他知道開了口也無濟于事,阿古曲杰不會給的。
“阿若,阿若。”
半夜阿古曲杰叫醒了我父親。我父親突然被叫醒,心有不快,問道:“什么事?”
“聽,森林中有個野獸,一直在走來走去!”父親靜心一聽,森林中果真有動物走來走去的,不時發出樹枝折斷的聲響。牧圈里牦牛跺著腳,鈴聲嘈雜成一團。門口的小狗對著森林狂叫。父親拿著電筒,在牧圈里巡邏了一遍,森林里的聲響停止了,啥都沒看見,他對著森林大聲叫了三遍,回到帳篷繼續睡。不久,森林里又有響聲。“不好了,你烤肉引來了不干凈的東西。”父親說著往火灰里倒了熏香,帳篷里的烤肉味一下被熏香代替。熏香燒完,三石灶間放上干樹枝,把灰炭吹了幾次火就燃了起來。帳篷中燃起熊熊的烈火,火光照亮了牧圈的一半。但森林里的響聲沒有走遠,反而更近了,因為害怕加之火堆起作用,他倆滿身都是汗水,從帳篷門口瞄去看到有個東西已經進入牧圈里,它好像帶著手電筒,前面白花花一片,牦牛們不斷跺著腳,鼻子里吹著氣,小狗瘋狂地叫。過后它的聲音戛然而止,站在了門口,它像人一樣站著。它只有一只眼晴,眼球像手電筒,他倆抓起燃燒的樹枝打下去,它的身體像霧,打到身上不停留,火落入它身后的牧圈里。它進入帳篷里,他倆用被子蒙臉瑟瑟發抖。它不斷攪著火灰,呼呼吸著氣,吸了很久后離開。他倆從被子里伸出頭的時候,看到外面的天已經亮了。門口留有六個爪子的腳印,小狗全身濕淋淋地死在牧圈的中央。布查村人說它是神山玉日的看門神靈,名叫黑孽。之前,一些布查村人在高山上烤肉的時候見到過,那時候,它有兩個像手電筒一樣的眼球。但是我父親看到它的時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只有右眼,沒有左眼。
自從見到黑孽后,父親變得心神不寧、疑神疑鬼,無法一個人待在山上,大哥替他去放牧,我父親回到了布查村。在家里,他一有空就翻這翻那找他的酒瓶子,把家里的東西弄得亂糟糟,以前放鞋子地方現在放著上衣,家人要去干活的時候工具都找不到了。他在家里找不到酒瓶就往親戚家、鄰居家跑。回到家,醉得不省人事地說:“箱子的鑰匙丟了。”用斧頭、石頭、木棍把放糖的巨大箱子亂砸一通。
在父親醉得不省人事的某一天,我爺爺把他綁到我們家老白馬背上,帶到空行母跟前去。空行母說:“正是時候!”并為父親念了《無量壽陀羅尼》,把去往死亡路上的靈魂拽回來。空行母在父親頭上撒水撒五谷時清醒了過來,他發誓要戒灑。空行母念完經后說:“再喝,我就救不了你。”爺爺在空行母那邊了解到事態的嚴重性,到附近的寺廟里去叩頭,讓酒醒后的父親牽老白馬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父親感覺頭痛欲裂,不喝點小酒,頭疼永遠好不了!這個念頭從心里泡沫一樣不斷冒出來。到了布查村和卡布村的交界處,我家親戚崗布家附近的空氣中彌漫著熱乎乎的醇香,父親貪婪地嗅著,然后不由自主地跟著醇香走。到了崗布倉院子里,父親看到女主人阿瑪玉洛正在院子里制酒,鍋底下的青岡木在熊熊燃燒,火舌舔著大鍋,大鍋里的水在沸騰。阿瑪玉洛正在制酒的時候,我父親的鼻像老鼠的鼻子一樣不斷動著過來了,阿瑪玉洛不知道父親剛剛戒了酒,就說:“來喝一杯,看看我制的酒怎么樣!”父親說:“好!”后來,我家的那匹老白馬牽著父親回到家中。父親醉酒后的夜晚看見了鬼魂,之后白天也能看見,父親的身子一半在人間,一半已經在中陰界,直到父親死于酒后的意外。在冬天光禿禿的田野里父親火葬的那天,布查村的男女老少都聚在我家,吃肉喝酒。
我在城市的公園里散步,其實公園里沒什么好看的,不過是一些半死不活的花草,種在花盆里的松柏樹從小就人為地彎曲,變得蒼老不堪。城里人都喜歡到公園里鍛煉身體,鍛煉身體是城里人的說法,其實鍛煉身體就是為了消化肚子里的魚、羊、牛、蝦等各種動物的尸體罷了。我的身體在公園里散步,心識卻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漫游。在城市里我每天都要回答兩句話:“哪里的?”和“吃了沒?”回答“吃了沒?”非常簡單,如果你不想跟很多人一起聚會喝酒,沒吃飯也應該回答“吃了。”就能和問話的人就此別過。但回答“哪里的?”有點難。
城市里的朋友們問我是“哪里的?”我回答說:“布查村的。”但他們不知道布查村在哪里,又問:“布查村是在哪里?”我回答說:“布查村是芒康的。”他們又問:“芒康在哪里?”我說“芒康是昌都的。”他們又問:“昌都是哪里的?”我就說:“西藏的。”
他們才明白了我的故鄉,“啊,你的故鄉是西藏!”
別人的故鄉越問越小,而我的故鄉越問越大了,布查村消失了,西藏成為了我的故鄉。城市里生活得越久越喜歡回答“吃了”和“西藏的”之后,獨自一個人沿著沒意思的小路散步一會,想一些沒用的事情、玩手機。在手機短視頻平臺上輸入“布查村”三個字,但看不到布查村人熟悉的面孔,他們永遠隱藏在網絡世界之外。但白額頭灰熊進入芒康縣城的視頻在網上爆炸了,白額頭灰熊一出現在網上就成為了網紅熊,視頻中白額頭灰熊在街上翻著垃圾袋,有滋有味地吃起了殘羮剩飯,第一次嘗到人類食物味道的情形中,我清晰地感覺到人肉不香了的神情。白額頭灰熊坐在街邊成為景觀,人類的食物不斷出現在它的身邊,嘗到千萬種的人類食物的滋味之后,它在布查村時發光的雙眼暗淡了下去,對人類一點也不感興趣,只等著他們手里的東西落在自己的腳旁,拿起來消滅掉。不久拍照的時候會咧嘴笑,按照投食的要求,會跳一段裝模作樣的弦子舞。它的周圍擠滿了主播和記者,白額頭灰熊的毛發立起來的時候,他們解釋道那是它想遠方的森林里的家了;它來不及咬就直接吞一個大蘋果,被嗆得淚水直流,他們說那是它在想家里的崽子了;它吃飽后,心滿意足地坐起來,用舌頭舔著鼻子,他們說那是在對那些穿得少的美女游客說俏皮話呢。拍照的人越來越多,投食的越來越多,引來了動物學家。動物學家們把白額頭灰熊關進籠子里,量體重、抽血、拍照,折騰了一個星期,我們的熊變得皮包骨,看到人雙眼放出恐懼的光來,動物學家在芒康待了近一個月,天天泡曲孜卡溫泉,天天喝鹽井的葡萄酒,把自己養得白白胖胖的像某種動物,不斷敲打從襯衣下快要爆炸出來的肚子。他們回到大城市去了,走之前沒有留下什么結論。有人說:“動物學家們早就得出了結論,白額頭灰熊其實是大熊貓和灰熊雜交的產物,不久他們會把白額頭灰熊帶到大城市里去,我們的白額頭灰熊會像大熊貓一樣享福。”有人又說:“動物學家研究發現,白額頭灰熊其實是全球氣候變暖的產物。”白額頭灰熊在街上整天像狗一樣地嗯嗯叫個不停,縣城里一半以上的人得了失眠癥,其余能睡得著的人都噩夢不斷,所以,芒康縣里懂生態政策的一個人說:“白額頭灰熊想念大自然了。”動物保護站的工作人員,把它運到紅拉山自然保護區。看到白額頭灰熊被帶走了,人們又開始傷心起來。三天后,它不動聲色地出現在了芒康縣城里,和一群流浪的哈巴狗一起撿垃圾。這是我在短視頻平臺上最后一次看到它,比以前更瘦了。之后它在網上消失了,布查村的人、布查村的動物、布查村的特色產品都再也沒有出現過。但鄰居家的兒子桑培諾布只要布查村里有信號,就會給我打電話。當他說:“阿若,在做什么?”我能想象的出來,電話對面的他臉上掛滿了笑容,充滿喜悅地說著當前布查村人在做什么,布查村里有什么新聞。但他從來不說自己在干什么,有什么打算。關于他的消息,另外一個布查村人給我打電話說的,他說布查村里以前有過打工熱,這個你知道的,現在已經冷卻了,現在正興起跑拉薩熱。他說:“你家鄰居家的桑培諾布也跑拉薩去了。”
我問:“他現在在拉薩嗎?”
他說:“跑拉薩后,發現拉薩沒有什么,幾個月后就回來了。”
但桑培諾布給我打電話的時候,他跑拉薩的事一句話也沒說,相反他喜歡說其他人的事,說阿古曲杰的事情。我知道他和阿古曲杰沒一點親戚關系。他說阿古曲杰戒煙戒酒了,還說了阿古曲杰戒蜂蜜的事,從而我想到小時候看到阿古曲杰走在田間,吸著野花的芳香,那時候我覺得阿古曲杰前世一定是個辛勞的蜜蜂。現在這些動作和習慣都戒了,這好像一個無所事事的人戒了生活必需品,只能更快地走向死亡之路。
“嗡嗡嗡嗡——”
我的手機放在襯衣口袋里,正好貼著心臟,突然一震動,把我嚇了一跳。
“喂?”
“我是次扎,今天到城里了,晚上一起去喝酒。”
“你定個地方。”
從公園的西門進去不到十來分鐘就出了東門。哥次扎來電話說,他在無刺玫瑰酒吧里等我。
無刺玫瑰酒吧位于城市的不夜城里,是富二代們聚居的地方,哥次扎怎么變成了富二代?
我帶著很多問號,進入無刺玫瑰酒吧里。
去包間的路上,哥次扎給我說了很多家鄉的冷笑話,但是我沒有笑。來來去去的富二代們看著這位身材高大,皮膚銅紅,滿身是黃金,走起路來好像腳底下安裝了彈簧一樣的異類。哥次扎很享受自己變成別人眼中焦點的這種待遇。我看到富二代們鄙視的眼光。
進入包間,我坐在透明的沙發上,沙發是某種塑料那樣無法滲透水的材料做成,裝在沙發里的水在流動,能聽到沙發下有動靜,深不見底的玻璃地板下面出現了很多五顏六色的小魚,它們好奇地睜大眼,游到沙發里來,它們在我的屁股下游來游去,好像丟了什么似的,最終沒找到又回到水的深處去了。我倆置身于海的中心,透明的玻璃和水融合在一起。鋼琴曲輕輕響起,一只巨大的魚在玻璃墻上摩擦著肚子玩起來。服務員拿來了酒和一些小吃放在透明得幾乎看不見的桌子上,小魚們又來到桌子下面,小嘴撞著酒瓶底,你推我搡地搶起來,最終又沒吃到什么,游到海底去了。音樂聲撞到海的切面上又彈回來,無數個音符在我的身體上交叉起來。杯子里還沒倒上酒之前,醉意飄飄然了。
我拿起一瓶葡萄酒,看了一下牌子,沒寫是什么牌子的,只寫了生產日期,一百年前的。“砰”開瓶時響起開槍一樣的聲音,塞子飛了,瓶口流出了泡沫,隨即變成了一團白氣,白氣又化作滿屋醬香氣了。
一杯下肚后,我問他:“怎么突然成了暴發戶?”
他說:“什么話,暴發戶不就是突然成的嘛,暴發戶的靈魂就在‘暴發’兩個字里,如果慢慢成了富翁,就不叫暴發戶了,那叫地主。”
我也覺得他說的沒錯,就換了話題:“怎么突然有錢了?”
他說他在做蟲草生意,還說蟲草行業是暴利行業,暴發戶輩出的行業。但是我就是半信半疑。
“這酒真好喝,城里人到底在里面加了什么東西?”他把酒瓶舉起端詳。酒瓶里沒有什么奇怪的東西,我的眼光越過酒瓶,看到了天花板,天花板上很多烏龜伸出頭,好奇地看著我倆。
以前,哥次扎一次兩次地往外面跑,沒人說,但三次四次地往外面跑,布查村人都很好奇。哥次扎跑成都回來,布查村人問:“成都有什么好?”
哥次扎說:“成都沒什么好,就是 人多。”
哥次扎跑拉薩回來,布查村人問:“拉薩有什么好?”
哥次扎說:“拉薩沒什么好,就是人多。”
哥次扎這么一說,年輕人喜歡熱鬧,哪里人多就喜歡往哪里跑,當布查村的年輕人一波一波地往外面跑。哥次扎卻不再向外面跑了,待在家里放起了羊。
布查村年輕人跑外面回來問:“布查村有什么好?”
哥次扎說:“布查村沒什么好,就是人少。”
哥次扎和后來向外面跑的那群年輕人完全不同,哥次扎回來的時候賺到了一筆錢,而這些年輕人回布查村卻收獲了愛情。帶回了錢,一個人變富,對布查村人整體生活沒什么影響,但帶回了愛情就大不一樣了。之前,布查村里根本沒有愛情一說,以前在布查村,只有雙方的父母們安排,你就照著走就行,每個人的婚姻會順水順舟。但現在變了,愛情像病毒和風一樣,從成都吹到拉薩,從拉薩吹到芒康縣,從芒康縣吹到徐中鄉,從徐中鄉吹到吃飽喝足后的布查村里。平時靜悄悄的夜里,首先有了夫妻吵架的聲音,然后有人在砸打工買來的精美家具,小孩在哭,老人在勸架,每個家庭弄得像開朗瑪廳一樣熱鬧。次日,老人們聚在白塔邊曬太陽的時候,睡眠不足的老人看著身邊像自己一樣腫著眼睛的老人,像念經一樣不斷說著:“一代不如一代啊!”
“次扎,外面的世界不是很精彩嘛,怎么不去了?”一輩子待在布查村的老人們挖苦。
哥次扎說:“外面的世界精彩是精彩,但餓鬼一樣跑來跑去,找這找那,有啥意思呢,還是待在家里舒服,餓了有糌粑吃,渴了有酥油茶喝,人活在世上,還需要別的什么呢?”關于餓鬼,布查村有個說法,神山玉日的一半是松柏等常青的樹林,一半是落葉喬木的樹林,一到秋天落葉喬木的樹林變得漫山遍野的紅,遠遠望去,好像著了火一樣。布查村的老人們便說:“每當到了秋天,餓鬼們在森林里跑,口中歡喜地叫著,‘血血!肉肉!’”它們以為紅葉就是血和肉,所以在布查村,常常用餓鬼來比喻不知足的人。
羊在布查村里絕跡之后,哥次扎用打工的錢,買回一大群的羊。布查村里每家都有羊的時代里得利者是狼群,羊消失之后,它們餓得只剩下包皮骨,狼不得不相續遷出,在別處尋找活路。布查村的狼們絕跡后,灰熊、雪豹也不來散步了,因為他們發現布查村里什么也沒有,散完步又要爬山回森林,那頭白額頭灰熊發現看似懶散的布查村人,心頭弦永遠不會松,對它時時刻刻保持著警惕,吃人肉的愿望變成遙遠的奢想,就遠離布查村,沿著新建的公路往縣城的方向走了。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哥次扎帶回了一群羊。由于多年沒有放牧,喜鵲頂滿是白花花的雜草,以前放牧生火的三石灶,已經消失在瘋狂生長的雜草之中,以前放牧的那群小孩已經長大,而他們的孩子到三歲就去讀書了,他們已經不知道何為放牧,不知道羊長什么樣,說羊有角的時候他們覺得羊是動畫片里恐怖的獨角獸,而熊都是保護森林和平的“熊大熊二”。以前熱鬧的神山玉日,已經變成了沒有人跡的荒漠,哥次扎在荒漠中開辟一塊空地,費了很大功夫找來三塊石頭,變成了嶄新的三石灶,用一些干枝生起了久違的火。早上最初的暖陽照到布查村的白塔上,布查村的老人們像以往的所有早上一樣,聚到白塔邊曬太陽,他們看到神山玉日上升起灰白的炊煙直升空中,他們的心也變得暖洋洋,已經變成荒漠的大山里,看到了一絲生機。
羊群沒在雜草里,它們一整天睡在一個地方,眼前的草吃完后,轉過頭吃另一邊,它們不停地動著小嘴,邊拉出藥丸一樣的羊糞來,羊糞是絕好的料,有利于草的生長。草經過羊們的肚子變成了羊糞,羊糞又經過土壤變成了肥料,如此良性循環,經過三年的時間,羊群無限繁殖著,最先的一百多干瘦的羊變成了三百多只胖羊,神山玉日山上的亂糟糟的草沒有了,如同一個人剪了頭發,遠遠望去,神山玉日的山坡充滿了生機。夏日雨后,以往滿山遍野的雜草腐爛味,現在已經變成了草香味兒;以往冬日白花花的干草像汽油桶,火一點就滿山著,現在雜草里冬眠了很多年的石子們重見天日了。
布查村人放羊的時候,哥次扎在打工;布查村人出去打工時,哥次扎又放起了羊,一來二去哥次扎成為布查村的致富帶頭人。早上布查村的這位萬元戶,趕著三百多只羊來到喜鵲頂,喝完酥油茶,睡在雜草里,這里狼已經消失,水草充足,羊一天都會待在同一個地方,哥次扎睡了一天,也能照樣在母羊身上賺了奶,公羊身上賺了肉。
布查村的好事者看到哥次扎的放羊生活過于舒服,就提議道:“羊一天都待在一個地方,為什么你非要到山上去呢,早上把羊趕山上,下午去收回來不就得了,為什么非要在喜鵲頂待上一天呢?”
對此哥次扎回答說:“待在山谷里太悶了,向左轉是山,向右轉是山,向前轉是山,向后轉還是山。待在喜鵲頂就不同了,向左轉能看卡布村的全景;向右轉能看到門巴村的全景;向前轉能感受到從神山玉日的密林深處吹來的習習微風;向后轉能看到無數個山頂從云霧里出現又消失;待在山谷中沒有向下看這種說法,如果有的話也只能看到自己的腳,但喜鵲頂向下一看能看到布查村的全景,能看到村人在做一些無用功,向下一看,山谷里的布查村其實像城市里人看的小電視,很多人在那里演出,很有細節。”
聽完,好事者覺得怪,以前的次扎傻里傻氣,現在一本正經地講起道理了,是不是人一變富,見識也長了?帶著問號回家的路上,遇到另一個正在曬太陽的好事者,就對那個人說了哥次扎的情況。
那人回答說:“這很正常,人吃飽喝足了,腦袋就會餓起來,怎么說呢,胡思亂想,奇思妙想,啊,就這樣。”
有一次,哥次扎在雜草里睡了一陣子,醒過來,羊群還在原來的地方,天空晴朗。突然,天空中傳出爆炸聲,一道閃電落在喜鵲頂巨石上。吃飽喝足而變得懶洋洋的胖羊們,機靈起來,鼻子里發出“噗!噗!”的聲音。哥次扎意識清醒過來,空氣里彌漫著白霧,嗅出錘子敲打石頭時閃現的白煙味,布查村民就叫“石頭燃燒的味道”。丑陋的巨石被燃沒了,或者炸沒了,喜鵲頂上多出了一道凹下的土坑。哥次扎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到處都是閃閃發光的石子,最先以為石頭被閃電點燃了,到近處一看不是紅的,是金色,用手摸下也不熱。
“金石!”
哥次扎叫出來的時候,不是驚喜,而是驚慌。“千萬不要讓別人發現。”他想。碎片都撿起來,丟到土坑里,上面填上土,放上雜草。布查村人養成了運道好時,不聲張的良好品質。哥次扎找到金石時,第一個想到的是藏起來,藏是藏起來了,但問題又出來了,以前毫無用處,又無人不知的巨石,突然消失了,誰都會注意到。哥次扎想到這,跑回家去,背個籃子背回家。那天,布查村人看到,哥次扎背著籃子上山下山,跑了五六趟,布查村人好奇歸好奇,都在想:“人一旦變得富有了,腦袋就餓了。”沒人去問個究竟。
后來布查村的好事者終于忍不住了,跑出來攔住滿頭大汗的哥次扎問:“跑啥呢?”
“咋的,礙你的事嗎?”哥次扎這樣回答,他們覺得問法不太對,又問:“背啥呢?”
哥次扎回答:“背羊糞呢?”
“背羊糞要跑得這么歡?”
“鍛煉身體呢。”
聽到這個答案好事者無話可說了。回去跟別人說:“次扎在鍛煉身體呢。”
布查村的老人們閑聊說:“以前為了找食物而跑步,現在為了消化食物而跑步,這不是反了么?”
“反了。”有人回答。
哥次扎來回跑了十六次,將全部碎石倒入糧倉中。知道山上沒剩下什么,他喝足青稞酒,睡了整整三天后,發動了經久沒有聲響的拖拉機,在拖拉機的突突聲中一半是糧食,一半是碎石的袋子運到城里去了。糧粒從拖拉機里漏出來,一直在研究空氣味道的豬和驢們,第一時間嗅出了糧食的淀粉味,都聚在瀝青路上,追著大吃一頓。布查村的嗅覺靈敏者,在拖拉機留下的黑煙中,嗅出了珍貴金屬的味道,來到公路上的時候,肚子龐大的驢們睡在路邊,看到人就咧嘴笑,好像在說:“你們來晚了,哈。”嗅覺靈敏者隨后爬到喜鵲頂看情況去了。他看到吃飽了睡,醒了又吃的胖羊群,之后嗅出“石頭燃燒的味道”,看到喜鵲頂那個丑陋的巨石消失不見了,剩下一個土坑,土坑中黃金渣在閃閃發光,沒有留下哪怕是豆子大的金石。他回到村里,宣布了這一重大的發現。不久神山玉日的山坡上滿是“叮叮當當,叮叮當當”錘子敲打石頭時發出的悅耳聲音,在布查村的山谷中回響,演奏出一場日夜不息的打擊樂。哥次扎賣完金石,開著東風車回布查村的路上,遠遠地聽出了從神山玉日山坡上傳出的樂聲,他才想起了自己的羊群。
哥次扎找到金石后不久,就像我所預見的那樣,下來到了山上不能生火抽煙的時代,哥次扎說這個時代來得剛好,來得快一點他就不能放羊,不能放羊自然不會找到金石。我給他說了小時候我的腦子里“叮當”一聲,突然開悟的情況。他說:“如果有這種情況發生,應該第一時間對身邊的人說,如果那次你說出你的發現的話,說不定現在你已經是活佛了。”那天哥次扎回到布查村,第一件事就是去慰問擔驚受怕的羊群,羊群依舊是胖的。哥次扎把羊群趕到山谷中,跟布查村里的九戶人家平分了,對此沒有一個人表示感謝,很明顯布查村人想要的不是羊而是金石。
哥次扎在無刺玫瑰酒吧中跳起家鄉的弦子舞,左手拿著的空酒瓶當成弦子,右手拉起馬尾來。背景音樂和跳舞節奏不搭,我看著不舒服,他跳著也不舒服,很快就累了。“破弦子,不對調。”他把破弦子,也就是空酒瓶扔到垃圾桶后,好像做完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樣,鄭重地喝起酒來。
一杯下肚后他說:“我知道你們這些城里人看不起自己的家鄉,對于你們來說家鄉不過是滿是石頭的山谷。但對于我來說家鄉意味著一切,故鄉是由寶石組成的山谷。”
他又說:“我越來越不喜歡城市了,但不得不來城里,因為機器是沒有種子的。如果有機器種子,那么鄉下也會不斷生長出機器,眼下需要機器的時候,不得不往城市里跑一趟。”
我問:“你要機器干嗎?”
“我在家鄉成立了一家公司,”他停頓片刻后說:“名字叫布查神山玉日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我問:“神山玉日里有金礦?”
他說:“你們學了一腦袋知識,反而對于家鄉的小知識給忘掉了。老人們說神山玉日是騎著像玉一樣的綠馬,住在用玉打造的宮殿里的‘綠人綠馬’的神山。”
我問:“這個又能說明什么?”
他不耐煩地說:“神山玉日里面有玉礦呀。”
說到神山玉日的玉,我想起了神山玉日與玉的故事。從前神山玉日的巖石都變成了玉石,泉水里長出高大的珊瑚樹,樹上長滿了大片大片的珊瑚。第一個發現者是名叫多果的布查村人,他把所有的珊瑚都摘掉后,又日日夜夜地挖起玉來。神山玉日看到人的欲望是沒法滿足的,就把玉和珊瑚都收回了,玉石又變回巖石,珊瑚干枯、消失了。布查村人多果拿著石頭:“看!我找到了玉。”拿著樹葉說:“看!這是珊瑚。”他徹底瘋了。
哥次扎說:“我找到金石就滿足了,但很多寶貝在神山玉日里面不增不減地待著多可惜,拿出來富足一方是多好的事情。”
我笑了。
“有什么好笑?”
“神山玉日不是個騎著像玉一樣綠馬的神山。神山玉日里有很多寶貝的說法也只是傳說而已。”
“怎么說?”他問。
我猶豫了一下,但酒精的作用下,腦袋一熱就說道:“神山玉日是我開槍打瞎了的那只黑貓”。
“什么?阿古曲杰家的那只瞎貓是神山玉日?”
我發誓道:“神山玉日!”將上次煨桑時所見所聞都說了出來。
見我發誓,他有點恐慌。他在自言自語地說:“我買這么多機器圖啥呢?”之后急忙給司機打電話。不久司機從門口探出頭來說:“走吧,一切準備就緒。”我的話像一盆冷水潑在哥次扎的頭上,酒就徹底醒了,給司機示意無需幫忙,筆直地走下去了。
我感覺自己在渾渾噩噩地穿過走廊,汽車的聲音、行人的聲音、各種光線落地的聲音交織在耳中。當咔嚓一聲關了車門,這些聲音都關在外面的世界里,像蚊子一樣嗒嗒地撞在車玻璃上。有人在問我:“你住什么地方?”我拿出身份證,有人取走了,我睜大眼睛看著那個人,但看到的只有黑暗,我自己慢慢落入無底的黑暗中,過去和現在、未來凝聚在一處。
早上醒來,我發現自己睡在自家的床上。
“噠——”我心里響起一聲久違的槍聲。
我起床走到鏡子面前,看眼里是不是進了塵埃。照鏡子的那一刻,我嚇得驚聲尖叫起來,左眼的眼珠子昨晚弄丟了,只剩下黑洞洞的,所有的光線在那里消失不見了。
我在房子里來回踱步,尋找著某個東西。意識到自己其實在尋找著一把槍。“噠”地對準自己的額頭扣下扳機全部完事。但是現在是不能私藏槍支的時代,這個時代來到這個世界已經有很長時間了。
“噠!噠!”
編輯導語:回響,源自于深山里的一個小村鎮。
“我”的成長過程正好是鄉村嬗變的整個歷程,從每一個點滴細節的描述,映射出的是西藏山村一絲一毫中的循序漸進,這當中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變化。小說以自傳體式的架構,用調侃、譏諷的文筆,讓我們回望幾十年前的西藏山村樣貌,體會變遷中的無奈與希望。
責任編輯:次仁羅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