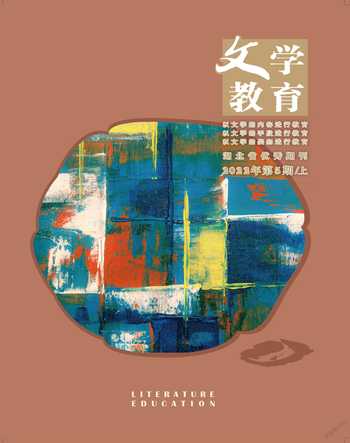保羅·奧斯特《紐約三部曲》的后現代迷思
潘若曈
內容摘要:保羅·奧斯特在現代美國文壇中以奇異、詭譎的寫作風格獨樹一幟,得到大批讀者和評論家的肯定。但對于他究竟屬不屬于后現代一派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盡管奧斯特自認是“現實主義”的,但他的代表作《紐約三部曲》展示出濃厚的后現代性,本文試圖從人物、情節、語言三方面做出分析,并認為這是奧斯特從傳統走向后現代的一次探索。
關鍵詞:保羅·奧斯特 《紐約三部曲》 后現代 后現代性
保羅·奧斯特是當代美國文壇最炙手可熱的作家之一,他以奇異、詭譎的寫作風格自成一派,受到大批的讀者和評論家追捧。同時他獨特的個性和寫作風格也吸引了諸多國內外學者對他作品的關注和探討。而他的經典之作——由《玻璃城》《幽靈》和《鎖閉的房間》三部偵探小說合成的《紐約三部曲》引起了最多的反響和研究,小說中令人捉摸不透的后現代迷幻風格令人為之眼前一亮,給研究者們從各種角度進行闡釋的廣闊空間。
一.保羅·奧斯特無法被定義的“紐約傳奇”
國內外諸多學者對保羅·奧斯特的《紐約三部曲》開展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約翰·齊克斯基在《作者的報復:保羅·奧斯特向理論挑戰》一文中,以奧斯特的《紐約三部曲》為例,論證了由其開創的玄學偵探小說的屬性。他認為“三部曲”不是有關犯罪的小說,而是對作者和寫作本身的書寫。而史蒂文·奧爾福德則關注到奧斯特小說中的空間敘事,在《間隔:保羅·奧斯特〈紐約三部曲〉中的意義與空間》一文中,借《紐約三部曲》里的行人空間、繪制的空間和烏托邦空間這三類空間探討了自我、空間和意義的關系。國內則有學者就奧斯特的城市書寫展開討論,齊碩在他的《烏托邦的消逝——保羅奧斯特早期小說中的城市書寫》中從代表著欲望與野心的紐約都市入手,認為奧斯特從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向混亂無章的城市提出挑戰,從而達到自我的詩意棲居。除對奧斯特的小說體裁,空間問題、城市書寫等的關注以外,還有學者從其作品中體現的猶太性入手,亦或是聚焦于小說中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在諸多的闡釋角度當中,引起最多探討和爭議的要數奧斯特的后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定性,盡管他本人曾表示自己是“現實主義”的,他所描繪的紐約即他眼里所看到的真實的樣子。與“現實主義”的徹底決裂似乎一度成為了后現代小說的主要標志之一,但對于奧斯特來說,他所指的現實主義可能有比通常想象的更大的界限,如今,甚至有人認為,后現代小說只不過是現實主義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發展或產物。同時還一部分學者毫不猶豫地將他劃入了后現代主義的陣營當中,奧爾福德斬釘截鐵地指出其就是后現代主義,因為“他使用了一種流行文化的形式來反思比‘偵探小說’更深刻的問題。”大多數批評家則致力于分析他的后現代性,而并沒有對奧斯特究竟應歸屬于哪一流派持明確立場。關于《玻璃城》的文章結尾,克里斯·泰什總結說,這部小說夾在“巴別塔式的混亂以及現代性的衰落”和“后現代主義的再現危機”之間,他敏銳地回避了這個“二分法”問題,因為他認為奧斯特本身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處于一個停滯的狀態。威廉·G·利特爾同樣中立地承認《玻璃之城》是“對一種現代的、世俗化的經驗觀念的回應,這種觀念是支離破碎的、武斷的和不連貫的。”
不論如何,后現代主義本身就是一個由多義、模糊、開放等概念勾勒的復雜范疇,它是一場由“不確定性”構成的狂歡,而“不確定性”也是奧斯特小說中最突出的主題之一,對奧斯特的分類遠不如展示他是如何通過他的角色來探索不同的文學和審美情感重要。事實上,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去質疑奧斯特是否是一個后現代作家可能是無關緊要的。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某些時候,給作者貼標簽可能是必要的(或流行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現在被認為很有必要的范圍。因而筆者無意將奧斯特的文風進行一個歸類,而是著重探究其《紐約三部曲》中的哪些方面透露出其后現代風格,我們大致可以從其小說中的人物身份、敘事語言與情節安排三個方面來看。
二.《紐約三部曲》的后現代性
1.丟失的身份
《玻璃城》中的主人公奎因幾乎沒有擁有過一個確定的身份。當他窺探斯蒂爾曼的照片時,他希望“能有所頓悟,醍醐灌頂般了解這個人”,就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個單子,一個連貫的自我。后來,當他觀察從中央車站的火車上走出來的人群時,他驚訝于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可還原的自己”。奇怪的是,奎因發現了兩個完全相同的斯蒂爾曼,從而與他所有先前的假設相矛盾,并面臨著一種后現代主義的情況,他不得不被迫選擇一個,最終屈服于后現代的沖動,追隨最不可能的斯蒂爾曼。但奎因意識到,他正屈從于偶然和一個完全武斷選擇的世界,“不確定性將始終與影隨行地跟著他”,從而放棄跟隨他第一選擇的斯蒂爾曼。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認為,后現代主義的特征是一種“取消自我”的過程,因而更熱衷于慶祝身份的流動性,且許多評論家也認為《玻璃城》強調的就是對一個穩定的、始終如一的身份的追尋。奧斯特的書寫確實地揭露了自我及自主性的虛構。事實上,奎因三次出現在斯蒂爾曼面前,每次都假裝用不同的身份。對奎因來說,這只是一個偵探有權使用的偽裝,但斯蒂爾曼欣然接受了他流動的身份,并通過評論“人會改變,不是嗎?前一分鐘我們是一回事,后一分鐘我們是另一回事”來做出回應。我們可以發現,與試圖以一種更深入、更徹底的強度接觸個人自我的現代主義相反,后現代主義否認個人作為獨特自我的東西,這種獨特自我將個人與其他個人區分開來。其實一開始奎因是有確定身份的,委托人打來電話找偵探保羅·奧斯特時,他一心想保持自我的獨特性,因此他明確表示自己并非此人,就要掛斷電話。但是打電話的人不在乎他是不是保羅·奧斯特,仍然請求幫助。在一個身份流動的世界里,區分“真實的”自我和“虛假的”自我不再重要,現代主義自我的構成從一開始就有如此多的虛假。但從他頂替奧斯特身份介入案件開始,他的自我逐步被后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所裹挾,甚至于到他需要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記住你是誰”來不斷提醒自己,因此,這個故事看似是對真相的追尋,實際卻演化成了一場現代人掉進了沒有真相的后現代主義漩渦之中的鬧劇。
在《紐約三部曲》中,有關人物的身份描寫互為蹤跡,互為替補。人物舊身份的數次分裂與新身份的不斷形成相互裹挾,卻終究難以確定下來。不僅是奎因,還有《幽靈》中的布魯和《鎖閉的房間》中的敘述者“我”,他們都有身份的迷失,這些人物習慣于游走在紐約這個他們所熟知的城市,然而迷失卻成為他們的日常,如作者奧斯特所言:“迷失,不僅摸不清這個城市,而且也找不到他們自己了。”
2.破碎的語言
在《玻璃城》中,作者保羅·奧斯特借老斯蒂爾曼之口表達了現今“詞語退化為某種隨心所欲的符號的集合”的觀點。世界變成碎片,語言脫離了現實,似乎只是指它自己,詞語不再與世界相對應。《幽靈》中的布魯試圖證明語言仍是一種有效的工具,“他看到床,對自己說,床。他看到筆記本,對自己說,筆記本。他想,把燈叫做床是不行的,把床叫做燈也是不行的。不,這些話與它們所代表的東西貼合在一起,布魯說出這些話的那一刻,他感到一種深深的滿足,好像他剛剛證明了世界的存在。”當世界完整時,我們相信我們的語言可以表達出來。但漸漸地,當世界分崩離析,支離破碎,陷入混亂時,語言依舊維持原樣,這樣就會“隱藏起它本應表達的意思”。
與奎因一樣,布萊克也是一位作家,他化名懷特雇傭偵探布魯去跟蹤監視他自己。文中的他沉默寡言,僅有的語言交流也只與喬裝打扮后有意接近他的布魯發生。然而,在他們的對話中出現一個奇異的現象:上一次對話的內容毫無例外都會被下一次對話輕易推翻。奧斯特在此有意淡化語言的表意功能和邏輯原則,布萊克與布魯交談間所使用的話語缺乏語言應有的邏輯性和條理性,滿含戲謔成分。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奎因與小斯蒂爾曼的第一次面談當中,小斯蒂爾曼說道:“我的父親離開十三年了。他的名字也是彼得·斯蒂爾曼。很古怪,是吧?這兩個人的名字是一樣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實的名字。但我覺得他不是我。我們兩個都是彼得·斯蒂爾曼。但彼得·斯蒂爾曼不是我真實的姓名。所以也許我不是彼得·斯蒂爾曼。所以也許我根本不是彼得·斯蒂爾曼。”如果斯蒂爾曼是后現代主義中某種語言觀點的代言人,他的兒子小斯蒂爾曼就是這種觀點的可悲后果,在他對奎因的長篇大論中,他不會承認任何問題,沒有最終的答案,只能提供有限的、部分的、可能令人懷疑的真相。在這里,奧斯特向我們展示了后現代主義風格的敘述話語前后矛盾,相互否定,“每一句話都抹去了前面那一句,每一段文字都使下面的文字段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說,《紐約三部曲》中的每一句話都似乎想要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之后卻又提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以至于讀者始終無法探清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作者則致力于將“破碎的語言”貫徹到底,如上所述,既然詞永遠無法達意,那么語言背后的“意義”就變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語言本身。
奧斯特借助作品中人物的花式語言,建構了一套自己獨特的游戲規則,他的語言游戲給讀者帶來了全新的感受,把作品意義推向了不確定與虛無。正如德里達所言:“事實上,這種對于話語新地位批評追索最令人神往之處,就是它公然申明放棄對中心、主體、地位特殊的意義、本源、乃至絕對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義。”這或許也是吸引無數學者加入奧斯特這場“后現代風”語言游戲的原因所在。
3.斷裂的情節
后現代作家慣來對傳統小說情節的封閉性、連貫性和邏輯性持批判的態度。在他們看來,現代主義的那種意義的連續性、人物行動的恰當的邏輯性、情節的完整統一是一種“封閉體”(closed form)寫作,并沒有建立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只是現代作家們一廂情愿的構想而已。于是,他們主張沖破這種封閉,并倡導采用“開放體”(opened form)寫作來取而代之。在《紐約三部曲》中,奧斯特也將互不連貫的情節與片段編排在一起。現實、回憶、幻覺三者相互交纏,情節分散零亂、雜亂無章,在故事主線的行進過程中,悄然地穿插進各種小事件,讀者在眾多的線索和繁雜的信息面前感到一籌莫展,難以獲取真正的有效信息。其實不只是讀者,就連文中的三個偵探:奎因、布魯和“我”都同樣被困其間,了解到的信息越多,知道真相的可能性反而越低。《幽靈》中曾不止一次的出現與故事主線毫無關聯的情節來阻礙故事的發展進程。如文中莫名插入的費城小男孩兇殺案,這個費城小男孩的故事,與布魯監視的布萊克的案子毫無瓜葛,作者卻用了很大的篇幅進行敘述。且這個故事的某些片段還在時不時出現在主人公布魯的腦海中,并作為插入情節突如其來的擾亂了故事主線的進展:“他端量著自這個案子以來定在墻上的各種圖片,一幅幅地研究著,對這一幅圖片盡可能琢磨出什么意思,然后轉向下一幅。這是那個費城驗尸官戈爾德拿著那個小男孩的遺容面模的圖片。”此時讀者不禁會對這個出場次數頗多的“編外”故事傾注大量目光,試圖尋找到兩起案件之間的某些關聯,但奧斯特又一次向讀者展示了他的戲謔智慧——這個故事除了會突如其來地打斷情節的連貫性以外與案件根本毫無瓜葛。而這樣的情況在小說中還有很多,如布魯克林大橋設計師父子的故事、電影《漩渦之外》的故事情節、主人公布魯多次對色彩展開的聯想等等,顯然,這樣的寫法是作者在創作時的有意為之。同樣,《玻璃城》中奎因會不知緣由地與餐廳廚師大聊特聊起棒球,《鎖閉的房間》中突然敘述起“我”與妓女之間的一段短暫情緣,這些都可視作奧斯特為他的“吊詭情節”所設置的巧思,也是為讀者閱讀所設置的一種障礙,讓讀者長久以來習慣性的連續閱讀戛然而止,這既令人困惑,又是奧斯特小說的魅力所在。
《紐約三部曲》的故事情節,雖然看似明確,實則充滿了不確定性且帶有意識流色彩,文中的情節散亂無序,前后之間并不連貫,敘事時空隨意跳躍,從而構成了小說表面凌亂無序的狀態。但在奧斯特的小說世界里,“敘事和消解其實是同質的,敘事總是處在無效的邊緣,因為正是過度的敘事導致了存在的缺席。”奧斯特有意切斷故事的邏輯性和連貫性,使用大量碎片化情節來干擾故事的主線劇情是將作品的不確定性和多元化推向最佳效果的一個有效策略。
《鎖閉的房間》的敘述者曾提到,三部曲中的三部小說“最終是同一個故事,但每一部都代表了我對它的認識的不同階段。”“我很久以來一直在努力與某件事告別,這種斗爭才是真正重要的。故事不在文字里,而是在斗爭中。”這場斗爭或許可以看成記錄了作者保羅·奧斯特走向后現代主義的旅程。這位小說家的主要探索是對風格的探索,在這股強大的后現代風潮之中,他既不拋棄也不完全擁抱任何東西,而是總是在尋找,總是在試驗。奧斯特一直持有一種開放的心態邀請讀者們與他共同完成文本的終極意義,或許他會與愛默生所說的話產生共鳴:“對我來說,沒有什么是神圣的,沒有什么是褻瀆的,我只是實驗,一個無止境的探索者,背后沒有過去。”愛默生的背后雖然沒有過去,但在奧斯特的書寫中,“過去”是一直他的一個愉快的旅伴,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他的小說無疑會受到當代情感的影響,關注當前的問題和理論爭論,但同時也會包含著傳統的敘事結構和形式,時不時展現出與“過去”的互文性,承接著千百年來順流而下的文學傳統。不論他的人物、語言或情節有多么匪夷所思,它們的腳下一定是傳統文學的影子,踩出的是一連串悠長的后現代迷思。
參考文獻
[1]Steven E.Alford, “Mirrors of Madness: Paul Auster’s The New York Trilogy”[J].Critique,1995.
[2]William G.Little, “Nothing to Go on:Paul Auster’s City of Glass[J].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97.
[3][美]保羅·奧斯特.紐約三部曲[M].文敏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
[4]王逢振等編.最新西方文論選[M].桂林:漓江岀版社,1991.
[5]RichardF.Patteson,“The Teller's Tale:Text and Paratext in Paul Auster's Oracle Night”[J].Critique,2008.
[6]Ralph Waldo Emerson,“Circles”, in The Portable Emerson[M].ed. Carl Bode,New York: Penguin,1981.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