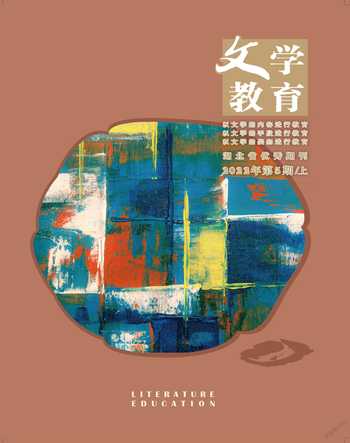論歌妓文化與晏歐詞的書寫
方興
內容摘要:在詩詞高度發達的古代中國,歌妓與文人們聯系緊密。而宋詞的創作方式也主要是倚聲填詞,且依靠歌妓們的傳唱得以影響深遠,此二者交織發展,從而形成宋代獨有的文學和文化景觀。宋代歌妓文化發展至頂峰,對當時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學等諸多方面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北宋初年,以晏殊、歐陽修為代表的詞人們在延續了南唐詞風的基礎上,受到歌妓文化進一步發展的影響,晏歐詞派的文人們在心態和創作方法上較前代均有所不同,體現出獨有的精神風貌和文化意蘊。
關鍵詞:晏歐詞 歌妓形象 城市經濟 文化內涵 心理刻畫
詞至宋代,已然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樣式,再加之詞本就是文學和音樂結合的產物,即兼具兩種內蘊的藝術作品,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唐宋時期歌妓制度和文化發展完備,歌妓的發展歷史悠久,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宗教崇拜中的歌舞表演,在《尚書·伊訓》中就有記載“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這些在宗教儀式中表演的女性可以看作是歌妓的前身。隨著社會的發展,歌舞表演逐漸擺脫宗教元素,走向純娛樂化。
尤其到了宋代,在宋太祖“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的號召下,市井經濟的蓬勃發展促使了勾欄、瓦肆等一系列娛樂場所的興起和繁榮,從而給歌舞樂妓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這一時期,歌妓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均已達到了空前絕后的狀態。而享樂主義的盛行讓宋代文人與歌妓間的交往成為一種風尚。如此一來,歌妓與宋詞的結合更為緊密,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宋詞的題材,擴充了精神內核,提高了詞的審美趣味;也讓歌妓詞逐漸成為宋詞中無法忽視的重要內容。晏、歐二人在繼承了晚唐五代以柔情婉媚為創作風格的基礎上,對婉約詞有了更深的開拓,尤其是在對歌妓形象的描繪上一改前人過于香艷的指向,進而凸顯出一種獨特的精神內涵和價值取向。
一.靈感源泉:歌妓文化促進詞之發展
在五代十國戰亂不斷的分裂局面結束之后,北宋迎來了統一,農業與手工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良好的經濟基礎促進了城市的發展,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汴京城內有商鋪“一百六十多行、六千四百多家”。[1]強盛的國力讓百姓們有了安定祥和的生產和生活環境,“重文輕武”的政治導向極大程度地保證了文人們的生存權利,對于文人的種種優待一方面使宋代文人數量激增,另一方面對自身生活的挖掘與探索開始成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重心;因此,娛樂行業便自然而然得到了發展。根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所記載,當時汴京城內“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地,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2]由此可見,城內最為興盛的行業就是酒館和妓館,這些場所的大量出現為歌妓提供了得以安身的場所,同時也促進了音樂和歌妓制度的發展,而此類行業的興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北宋經濟的繁榮,所以將北宋經濟的浪潮說成是“花潮”則一點也不為過了。
北宋時期歌妓制度趨于完備,且大體上承襲了唐代,根據歐陽炯《花間集序》中所描述的“有唐以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3]就足以反映出當時歌妓制度和文化的繁榮景象。歌妓一般可分為三類,即官妓、私妓和市井妓,這些歌妓都是以自身才藝表演為主要的生存手段,即賣藝不賣身。歌妓們大多出生貧寒,地位低微,即便是官妓也同樣如此,唐宋時期教坊樂工中的歌妓均無正式身份,并且常被視作“奴婢賤人”,因此無論是受盡寵愛或是被厭棄,歌妓們都難逃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不幸境遇。盡管歌妓們在社會中處于下層地位,但姣好的面容、超群的藝術技藝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學素養讓她們常表現出有別于社會底層人的見識與修養,這樣一來,能歌唱能做詩寫詞的她們成為了文人士大夫最為親密的朋友,也成為了歷代文學作品中常出現的文學形象。
唐中期以后曲子詞開始流行,不少文人都嘗試依曲填詞,到了宋代更是如此,正如王炎的《雙溪詩余自序》中就評價了詞是“長短句宜歌不亦誦”,而歌妓們的演唱則進一步凸顯了詞的音樂性,也就有了“非朱唇皓齒,無以發其要妙之聲音”的說法了。在繼承了婉約派好寫物,善描摹的基礎上,宋代文人們大力創作歌妓詞,開始將歌妓們的生存狀態、面容服飾、聲腔體態以及內心情感等作為他們創作的靈感和材料,以這些材料入詞無疑是豐富了詞的內容和文化內涵;如蘇軾就創作過不少歌妓詞,據有關學者研究統計,在蘇軾的三百五十多首詞中,其中大約有一百八十多首直接或間接的涉及到歌妓,這些詞在一定程度上也彰顯了蘇軾的審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詞人們在作品中展露的真情實感引發了深陷苦楚中歌妓們的共鳴,于是她們通過自身演唱這種娛樂活動,將詞人們的作品傳播得更廣,從而擴大了詞的影響力。由此可見,歌妓們與詞人們相互成就,難以割裂,詞一旦失去了歌妓們的演唱詞就失去了最好的傳播媒介及音樂性;而歌妓沒有了能與其共鳴的詞人們的關照也就缺少了讓世人們關注和剖析其內心世界的視角,也很難在文學上留下屬于她們的重要痕跡。在這樣寬松的文化氛圍中,詞即是詞人們與歌妓們在推杯換盞與交流唱和間最鐘愛的“歌曲”。由此可見,宋代歌妓制度和文化的發展極大程度上的刺激了詞人們的創作熱情,豐富了宋詞創作的內容,歌妓詞的創作儼然成為一種文學風尚。以晏殊和歐陽修為代表的婉約派詞人們也深受影響,創作了一些以歌妓為題材的作品,且憑借其區別于以往同類作品的獨特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和意義。
二.創作方式:心理刻畫輔之容貌描繪
毫無疑問,宋詞沿襲了前朝華麗有余,卻落于內涵空洞之窠臼,蘇軾、晏殊以及歐陽修等人所創作的歌妓詞在承襲綺嫵媚的特質之外,將生動、率真以及清新之風注入其中從而使歌妓詞呈現出不同的審美和藝術風貌。與詞發軔之初注重描繪歌妓舞女們的容貌、服飾,甚至于色情的低俗格調不同,晏殊、歐陽修詞中的歌妓們則展現出更多方面的特點,除了在容貌與歌唱彈奏技藝上詞人們精心雕琢,無一例外的,晏歐二人開始對歌妓舞女們的內心進行探索,從而挖掘她們的心靈世界,顯示出不同于傳統艷情詞過度沉溺感官描寫的取向,更有意蘊和深度。
“富貴宰相”晏殊一生與歌妓結下不解之緣,根據周召在《雙橋隨筆》中所載:“晏元獻雖早富貴, 而奉養極約。唯喜賓客, 未嘗一日不宴飲……亦必以歌樂相佐, 談笑雜初。”[4]由此可見,在晏殊宴請賓客的席間歌舞表演是必不可少的“佐料”,而歌妓們作為表演的主體自然就成為晏殊筆下描寫的對象。晏殊平生創作了大量的歌妓詞,這些詞作在一定程度上雖難以擺脫其身份地位帶來的桎梏以及晚唐五代艷詞的影響,但晏殊詞中對于歌妓的描寫更顯尊重和欣賞,有一種“遠觀不褻玩”的距離感;如“春蔥指甲輕攏捻,五彩條垂雙袖卷”“淡淡梳妝薄薄衣,天仙模樣好容儀”等,詞人以旁觀者的角度來描繪歌妓的美好,在他的描摹下歌妓詞中的女性們別有一番韻味,這些女性們均以淡妝展現出清麗的面貌,甚至有一種超脫凡俗的氣質,這樣的精心雕琢足以顯示詞人對歌妓們的欣賞與憐愛。且晏殊筆下的女性形象更多作為一個客觀對象或是與景物描繪雜糅在一起形成統一的整體,但形象和背景并不作為詞中的重點,而是作者表達情緒的載體,如《鳳銜杯》篇就完美地演繹了晏殊的創作方法,此篇主要通過描繪歌女在濃郁春色中因青春歲月轉瞬即逝而產生了無盡的煩惱,以歌女和春色為背景著重凸顯詞人對歲月匆匆的感嘆;又如《更漏子·菊花殘》中詞人雖描寫歌妓美好的體態以及曼妙的舞姿,但詞的落腳點在于對時光易逝的嘆息和要及時行樂的價值取向,諸如此類的詞還有很多。由此可見,晏殊對歌妓的描繪更多從第三者的角度出發,給予同等的尊重與理解,且不將其視為創作重心,更多是以這些人物形象作為表情達意的載體或手段。
歐陽修作為北宋文壇上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學上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毋庸贅述,但他也有著宋代文人士大夫多情風流的一面,在宋代筆記小說中就記載了不少歐陽修與歌妓交往的韻事,如在錢愐的《錢氏私志》就寫了歐陽修因與歌妓幽會而在宴會上遲到之事,而其名作《臨江仙·柳外輕雷池上雨》就是歐陽修在宴會上所做;且此事在《古今說海》《詞苑叢談》等多部典籍中均有記載。根據史料可知,歐陽修初入政壇之時,就曾寫下自己與歌妓“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在其代表作《采桑子》十篇中還能看到他與歌妓舞女們共游西湖的場景,因此,與歌妓舞女交往頻繁的他也創作了一定數量的歌妓詞。歐陽修筆下的女性形象眾多,而歌妓只是其中一類,卻是無法忽視的經典。在這類詞中,詞人對于歌妓形象的描寫體現詞人獨特的審美觀。與晏殊相同,歐陽修寫歌妓舞女時更多著墨于歌女們動人的女性特點,如“玉如肌,柳如眉”,詞人以美玉和柳枝來凸顯歌妓們天然去雕飾的美貌。其次,歐陽修善于描寫歌妓們絕佳的演唱技巧,如在《減字木蘭花·歌檀斂袂》中就寫到“歌檀斂袂。繚繞雕梁塵土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線穿”,詞人借以韓娥余音繞梁三日不絕和虞公高亢清越之音震動梁上灰塵來凸顯歌妓們歌唱效果和技藝,同時又以百串明珠來比喻歌妓們聲音之悠長與圓潤,這樣的技藝不得不令人折服。此外,在其創作的歌妓詞中,詞人多嘗試用細膩的筆觸來刻畫歌妓們純真的內心世界。以《訴衷情》為例,在這首詞中,歐陽修筆下的女主人公早起梳妝,將眉毛畫作遠山狀,以此表達對情郎的思念,一句“都緣自有離恨”點名分別的愁緒,正因為這種離愁別緒縈繞在心頭以至于在演唱之時都要“擬歌先斂,欲笑還顰”,如此一來,詞人將歌妓內心中對情人的思念,那種愛而不得之感刻畫得淋漓盡致。總而言之,歐陽修雖較少創作艷情詞,但他在艷情詞上的創作逃脫了花間詞人的藩籬,以一種無關風月的情感狀態來描繪歌妓這個特殊的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歌妓詞的審美內涵。
三.思想內蘊:借歌妓口吻以表情思
宋人尤重女音,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從皇宮貴族到平民百姓均能創作詞,尤其是女性成為了宋代文學活動的重要參與者,由此,便奠定了宋詞以婉約為美的基調以及善用寄托的創作特點。中國古代文學總體而言是由男性所主導的文學,因此一些細膩的情感體驗常需要借助女性的口吻來表達。歌妓們作為社會的邊緣人物,她們依賴青春容顏生存,無奈容顏易老,身份卑微卻對愛情有著無限的憧憬與向往,又在求愛不得后又落入無盡的失落與悲傷;以上種種均能引發與她們交往頗深的上層文人士大夫對自我人生的深沉思考,于是文人們將其寫入詞中以此寄托自身情懷。
古言有云“女為悅己者容”,足以見得女性對于美麗的追求,而容貌作為歌妓們賴以生存的因子,其重要性則不言而喻,但華美青春終是短暫的,于是詞人們從歌妓們對于容顏衰老的哀嘆中發現人生哲理,抒發獨屬于自身的人生體驗,如晏殊的“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又如歐陽修所寫的“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春風容易別”,這些詞句均表達了詞人們對于人生苦短多缺憾的思考。歌妓們身世凄苦,一生漂泊無定,這常引起處在被貶謫境遇中詞人們的共鳴,如在宋仁宗皇祐二年,正值晚年的晏殊遭遇了晚年流落異鄉的痛苦,輾轉各地。在這樣的情況下,晏殊創作了一篇《山亭柳》,他借助歌妓的口吻來表明自己的遭遇,先是描寫了歌妓年輕時紅極一時,而年老色衰之后,人去樓空,只能靠在街上賣藝,以“殘羹冷炙”來糊口。這與晏殊《珠玉詞》中其他贊美歌妓的詞不同,在此篇中有他對歌妓不幸命運的深切同情,而更多的是表達自己漂泊的憂愁。還如《破陣子·燕子欲歸時節》中通過描寫獨自佇立在高樓上的女子來比擬自己家道落寞時的悲傷。同樣是寫歌妓的悲慘,歐陽修則更多著眼于對當時整個社會現實的反思,如在《漁家傲·為愛蓮房》中就有寫多情女與薄幸郎之間的愛恨糾葛,“妾有容華君不省,花無恩愛猶相并。花卻有情人薄幸”,在他的筆下,歌妓們的悲慘遭遇和對愛情的渴望是對當時社會婦女地位低下以及情愛生活艱難的真實關照。
自古以來,就有以男女之情來寄托政治之思的傳統。從屈原的香草美人說開始,歷代文人們在經歷被貶謫,被去官之時都常以女子自比。顯然,這與古代君臣關系有著必然的聯系,在封建專制的社會中君主處于至高的地位,因此即使是男子,在君主面前都只能呈現陰柔的心態,此時他們的內心對于君主賞識的強烈期待與女性對于情愛的深切向往有著高度的重合,而借男女之情表達對于君主的尊敬更顯忠厚與溫柔。從而,詞人們流離失所之苦悶與歌妓愛而不得之傷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用文人劉克莊之言總結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論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5]這樣的表達在晏歐二人的詞作中也常有,如“當時清別離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就是寫于晏殊被貶至宣州之時,他將圣上比作“意中人”,以一種極為悲傷的口吻書寫了自己一路上的復雜心情,以及難見“意中人”的孤獨之感,此類作品中的形象和情感表現細致,均是上乘佳作。如上文所言,詞本身就擁有含蓄蘊藉,便于寄托的重要特征,而古代君臣之間的微妙關系決定了含蓄是詞人們諫言獻策最為妥帖的表達方式,因此詞人們常借助女性口吻傳遞內心的政治情思。總之,歌妓們悲慘艱辛的身世和生活,與愛情的分離以及身份地位的地下都讓她們情感體驗豐富而又真實,這些獨特感觸與詞人們的內心情感不謀而合,因而使得詞人與歌妓這二者間的關系升華為一種同呼吸共命運的情感。
林語堂先生在《中國人》一書中就曾強調過歌妓在中國古代的愛情、文學、音樂甚者于政治方面的影響是無法忽略的,因此對于宋詞的研究也無法避免要對歌妓這類特殊群體進行關照。宋代歌妓制度與文化發展至頂峰,她們影響著當時的經濟狀況、社會生活以及文學風尚。在歌妓與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交流唱中,宋詞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等方面均得到了提升,從而加深了宋詞的文化和文學價值。晏、歐二人作為北宋初期文壇的領袖人物,在繼承花間婉約詞風基礎之上,將自身獨特的藝術視角、敏感多情的藝術氣質以及宦海沉浮的人生經歷灌入歌妓詞的創作中,創作出不同于前人的,充滿生命力的歌妓形象,賦予了其新的審美和精神內涵,對之后婉約詞的發展和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孟元老.東京夢華錄[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3]李一氓.花間集校[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4]郭預衡.中國文學史長編:第三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2.
[5](宋)劉克莊跋劉叔安感秋八詞[A].全宋文[C].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作者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