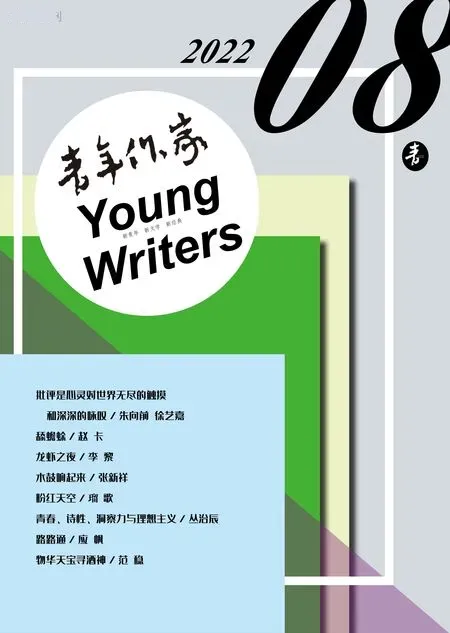老兵遁走山林
高滿航
我不得不交出半張白卷,內心悲壯如即將開啟多舛的命運之門。
那是新兵訓練結束后的第一次選拔考試,如果成績優異,我就能如愿成為發射營的兵。帶我們的班長經常講,你們要真有本事,就考到發射營去打導彈,打得好就能立功,提干指標也多,考軍校還有加分政策。
當兵前,我是一所非985和211大學的大三學生。家里憂慮我畢業后的出路,聽取曾在部隊當過營長的舅舅建議,讓我從所在大學報名入伍,到部隊當兵去。我之所以同意,并不是受了他們說的退伍回校后有國家資助學費、研究生考試加分等等看得見的好處誘惑,而是打心底里對一成不變的大學生活厭倦透頂,決定順水推舟,離開學校換個活法。
剛到新兵連那會兒,我覺得帶我們的下士班長威風得很,打定主意將來像他那樣轉士官。后來見了排長連長和營長,就又立志成為軍官。
聽到選拔考試消息時,我認作機會,摩拳擦掌欲作一搏。遺憾的是,那些機會都歸了我同批新兵里那些貌不驚人卻出類拔萃的學有所成者。
那年十二月底,我不得不去導彈旅最東北角的哨所報到。
山里剛下了一場大雪,到處白茫茫一片。風從寬闊的河道滾來,一陣又一陣,卷起冰冷的雪片抽打在我臉上。我無處躲藏,面冷如心,扛著背囊,拎著行軍包,垂頭喪氣跟在警衛營文書身后。走到一處岔路口,風又來,雪也起,他在風雪中抬手指著通往山里的方向,說他還有緊急的事要提前回去,讓我順著山腳一直往前走,無路可走時就能看到哨所。他已走出十幾米,又轉身大喊著讓我到了給他說一聲。我還沒來得及問怎么給他說,他就轉過山的拐角不見了蹤影,只留下雪地上一串腳印。
我不得不獨自去哨所。
藏在雪下的山路可真不好走。左邊是長滿雜木枯枝的陡峭山坡,稍不留神就戳到頭,右邊是被山洪沖毀護堤的河道,時時得提防著不滑下去。冰凍的河面看似平靜,冰層下的流水卻嘩嘩作響,聽得人心里發毛。
我一邊謹慎踩著腳下的路,又不得不時時朝山上張望。
我在新兵連聽那些待過哨所的班長講,走山路遇到野豬是常有的事。他們還說,那些膘肥體壯的野豬尋仇似的,專在隱蔽處等落單的官兵襲擊。他們給我比畫見過的野豬有一摟粗的脖子、一尺長的拱嘴,沖著人來時哼哼叫著,就像射過來嘯叫著的炮彈。班長們還說,山林里動物的戰斗力排名順序是一豬二熊三豹子,野豬能把胳膊粗的樹一口咬斷,更不要說咬人了。班長們的本事倒是一點兒也不比野豬差,他們都完美躲過了野豬襲擊,有的是爬到樹上,有的是跳進河里,還有的是躺平裝死。
我愈加強烈的恐懼不只是遇上野豬,更是弄不清到底哪種方法管用。
行走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我很快就大汗淋漓,全身濕透。
我的腳疼到即將麻木。前面沒了路,果真就看到了哨所。
我畢生難忘那一抬頭所見的情景。
二十幾個兵在哨所門口分兩排站立,軍犬也在隊列尾部蹲得筆直。我踏上亂石拼鋪的臺階時,就已看見了他們噴薄而發的激動。我剛站上哨所前的水泥廣場,掌聲就嘩嘩響起,我心頭一熱,眼淚止不住涌出來。
我站上廣場的同時,朦朧看見老兵昂首走出哨所大門。
整齊列隊的哨所官兵不是歡迎我,而是歡送老兵。
老兵神情肅穆,眼含熱淚,他情深意切地和每個人握手、擁抱。他們說等他回來,他也答應他們一定回來。老兵最后也和我握了手,并且和我擁抱。他的臉上綻出笑來,夸我能來哨所了不起,讓我也等他回來。
老兵向大家揮手告別后,背著他的背囊向山下走去。
我喊住老兵,讓他小心野豬。那一刻,我就如同把充斥大腦的恐懼傳遞給了老兵。他卻沒有絲毫緊張,只是沖我咧嘴一笑,然后瀟灑而去。
我后來才知道,我對老兵的提醒完全多余。
老兵是剛卸任的代理哨長,他那天是去哨所的上級單位警衛營報到。
關于老兵的更多故事,我是后來斷斷續續聽哨所的戰友們講的。他們說,老兵就像鐘情自己的初戀一樣熱愛哨所巡守的三十里山林。他們說他的身手比山林里的獼猴更加矯健,他的嗅覺比德國血統的軍犬更加靈敏。他們還說老兵曾徒手擒獲一頭偷襲他的野豬,不過他倒沒有傷害它,而是放歸山林。老兵就像對待自己的家人一樣寵愛山林里的飛禽和走獸。哨所每一個戰友都無數次對我講,與其說老兵是哨所的兵王,莫若說,他天生就是哨所巡守的三十里山林禁區的一部分。在這三十里山林,他是太陽,是月亮,也是風和雨,是白天的雄鷹和晚上的貓頭鷹。
我不理解他們的比喻,更疑惑天生屬于山林的老兵為何離開哨所?
他們說,老兵不會離開哨所。他們還說這些年里,老兵固守哨所的信念從來都是堅若磐石。他通過了發射營選拔考試,卻沒去報到。他軍事比武拿了多個第一,卻放棄提干培訓。他符合預考軍校的苗子班條件,也是一次沒去。老兵堅守哨所七年,從列兵到中士代理哨長,繼續前進的道路卻不通了。哨長是排長編制,要么少尉或者中尉軍官擔任,要么士官代理,但哨所的士官編制最高到中士,老兵明年就中士屆滿,再沒法留下來。老兵倒是符合士兵提干的所有條件,所以他不得不踩著二十五歲的年齡門檻,晉升培訓后轉換士兵身份為軍官,然后再回山林來。
哨所的每名士兵都知道,老兵一年后就會歸來。那時,老兵將從中士代理哨長成為名正言順的少尉哨長,又和以前一樣,攜槍帶犬巡守山林。
誰也沒想到,才過半年,老兵就回來了。
老兵沒帶任何行李,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旅里的保衛科長。
那天,哨所每個人都憂心忡忡,只有我不清楚發生了什么。我又一次見到老兵格外興奮,向他問好時,看到他臉上綻出笑容。我問他是不是已經成為少尉軍官,這次回來就再不走了。老兵點頭說不走了。保衛科長滿臉愁容,我聽見了他一根接一根抽煙間隙里的沉重嘆息。除此之外,他還一遍遍重復地問老兵:“你怎么可以這樣,你不應該這樣呀?”
老兵更多的時候并不答話,只是陷在心事重重的沉默里。
老兵向接替他的代理哨長借值班哨一用,說要到山林里走一遭。保衛科長警覺起來,他讓代理哨長跟老兵一起去,老兵卻點了我。他說我是哨所唯一沒跟他巡守過山林的兵。保衛科長顯得為難,但還是答應了。
老兵得到應允后,歡快地將哨子銜在唇間。他沖出哨所院外的籬笆門后,一個大跨步就輕松越過河道,然后敏捷地攀上陡峭山坡。我氣喘吁吁跟在他身后,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也不清楚保衛科長給我使的眼色是什么意思。老兵沖上山脊后,倒是慢下來,他銜在唇間的哨子卻響個不停。他長吹一聲說,這是找你,短促吹兩聲說,這是有危險,悠揚吹三聲說,這是平安無事。他問我記住沒有,我點頭說記住了。為了讓他相信我的記憶力,我又復述了一遍。老兵高興極了,歡快地向著山脊更遠處跑去,他在中途停下,轉過身來向我揮手,夸我能來哨所了不起。老兵再轉過身去后,就迅即隱于密林,沒了蹤影。我沿著他奔跑的方向追去,卻什么也沒看見,什么也沒聽見。他就像是一陣風,從無處歸于無處。
我正猶豫要不要獨自回去,這時,在弧形山脊的另一頭,傳來三聲悠揚的哨聲,緊接著,在山脊弧頂的樹上和山腳的泄洪河溝,同樣傳來三聲哨響。我確定了老兵還在山林,他并沒有走遠。我獨自返回哨所。
老兵到晚上也沒有回來。保衛科長一根接一根抽煙,不斷重復說:“想盡辦法,必須找到。”上山去尋老兵的戰友陸續歸隊,他們沒能發現關于老兵的任何一點線索。每個人都替老兵憂慮,他們懷疑老兵墜入山崖,遇到猛獸,或者迷了路,但這些臆測又被提出者之外的其他人推翻。
哨兵失蹤是哨所幾十年從沒有過的事,現在卻發生了。
每個人都眉頭緊鎖,哨所持續發酵著關于老兵去向的種種推測。
保衛科長又抽完一包煙后,小心翼翼給上級打了幾通電話,然后在哨所住下。他也帶著士兵和軍犬上山尋過幾次,同樣沒有任何結果。他回來后倒是再沒說必須找到的話,卻愁眉不展,又開始一根接一根抽煙。
有士兵竊竊私語討論,聽說老兵大概是在警衛營犯了嚴重錯誤。我也是那時才知道,老兵已經辦理完退伍手續,這次回來本是和哨所戰友作最后的告別。有戰友推測,老兵是不服從組織對他的處理決定才以隱身山林作為抗爭,也有一種說法,老兵是在兌現之前對于某個人的諾言。
沒人知道某個人是誰。也沒人知道諾言的內容。
時間一天天消融于日月的光芒。久不見老兵,有戰友推測他有可能穿過山林回了老家,也或者去了其他地方,重新開始退伍后的嶄新生活。
各顯神通的戰友們在山林那些必經之處拉上細線、撒上排列整齊的米粒,或者布設標記號碼的紙質粘板。他們希望獲得老兵的蹤跡,但一切的精心設計都未見成效。老兵蹤跡全無。大家認定老兵早已離開山林。
保衛科長離開后又很快回來。他已不信任我們哨所的軍犬,不知從什么地方帶來八條軍犬和八個馴犬員。保衛科長和他的隊伍午飯后上山,到晚上才回來。他們筋疲力盡,垂頭喪氣,仍舊沒有找到老兵。又過了幾天,保衛科長帶來一架裝有微型攝像頭的小型無人飛機。無人飛機一次次飛走,又一次次飛回,卻連老兵的半個影子都沒有拍到。保衛科長終于認定老兵已經離開山林。他在哨所給上級打電話時也是這么說的。
我最清楚他們做出了錯誤判斷。
每天早上的起床號前和熄燈號后,我都能聽見三聲悠揚的哨響。有時在山巔,有時在河溝,有時就近在哨所門前廣場的臺階下。我知道老兵游走在哨聲響起之處。我并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對老兵的行蹤秘而不宣。
直到有一天我正站哨,接連幾次聽到一聲長長的哨音。我下哨后循著哨聲,在我們上次分別的地方找到老兵。老兵虛弱地靠著一棵樹皮已經斑駁脫落的老樹,一只腿蜷著。他見我來,臉上綻出燦爛笑容。他小腿脛骨處受了傷,雖用揉爛的刺薊敷裹,卻不斷滲血。我跑回哨所拿藥時,代理哨長不但準備好了止血藥,還有紗布、酒精、雨衣、蚊帳和衣服。老兵只收下了止血藥。他笑著和我告別后,一瘸一拐地走向密林深處。
哨所戰友都知道老兵游走在山林。我們誰也不說,就像每個人都密密實實地捂著一個人盡皆知的秘密。我們有時覺得老兵就在哨所,事實上他一次也沒有回來過。我們不知道他怎么吃飯、怎么喝水、怎么睡覺,大雨之夜何處避雨,烈日之晝哪里避蔭。我也不知道他的腿傷是否痊愈。我確定的是老兵還在山林。三聲悠揚哨響一早一晚準時傳來,有時很近,近在眼前,有時很遠,遠在天邊。哨所寂靜,我每次都聽得一清二楚。
老兵隱身山林,斷絕了和我們的聯系,但我們忍不住又常提起他。一班長說起老兵訓哭他的事時,又哭了。我之前聽說,誤哨事件后,他脫胎換骨像完全變了個人。二班的賈大壯打小怕狗,因為軍犬在,他幾次鬧著要離開哨所。賈大壯從沒透露老兵教他和軍犬相處的絕招是什么。他動不動就摟著軍犬問:“想老哨長不?”我們知道是他想老哨長。不止他,我們都想。老兵似乎一點也不想我們這些想他的兄弟。我更想不通,老兵已經辦完退伍手續,他為什么不遠走高飛,而是游走于三十里山林?
老兵成了哨所待解開謎底的謎面。因為他,我們巡守禁區時不再走固定路線,有時穿越嶙峋亂石,有時鉆過密布藤蔓,也有時從山巔直插河溝,卻仍舊沒發現他在山林里的蛛絲馬跡。就在不抱希望時,我們循著他的哨音撲滅了一起山火,抓住一個形跡可疑的闖入者。慢慢的,我們習慣了一早一晚的三聲悠揚哨響,也期待揭曉藏在他身上的無盡秘密。
接替老兵的代理哨長考取了軍校。他在我們為他舉辦的歡送會上盡力克制著情緒。他回憶了和我們每個人相處的點滴往事,也談到自己這幾年的成長進步,最后提到要感謝的人時卻號啕大哭。他哽咽得幾乎說不出話,但我們都知道他最感謝老兵。老兵治愈了他的自大和自卑。代理哨長的大哭也引燃了我們的悲傷。我們在夏天的空調房里不知道老兵如何對抗酷暑,在冬天的暖氣室里不知道老兵如何忍受嚴寒,他怎么洗澡、怎么刮胡子、怎么剪指甲、有沒有換洗衣服?我腦中的老兵渾似一條被水澆過的蒼老瘦狗。他雖然直挺挺站立,卻隨時有可能一倒不起。
我們巡守禁區時,在老兵受了腿傷的地方放下壓縮餅干、簡易帳篷、薄厚衣服和能夠簡單處理外傷的紗布、藥物。我們再次經過時,偶爾會發現少了一些紗布和藥物,那些餅干、帳篷和衣服卻原封不動。
老兵隱身山林半年之后的年底,與他同年入伍的一班長即將退伍。一班長堅持和老兵告別。他穿著卸了軍銜的軍裝面向山林。一班長大喊老兵的名字,沒有應答。他一張張拿起和老兵的合影,說起以前的往事。他說完一張,新任哨長就給他換一張。他呼喚老兵應為每件事大醉一回。情深意重的一班長被前塵往事感動得哽咽不能言,山林里卻沒有一絲回應。一班長傷心得癱坐在地上,我們扶他回哨所,所有人一路走一路哭。
一班長走后一年,三班長也退伍,緊接著就是二班長。時間就像滴落在流水里的墨汁,瞬間便蹤跡全無。哨所每年都有情同手足的戰友陸續離開,也有新兵源源不斷補入。待我無人可喊班長時,才發現自己成了哨所最老的兵。這些年里,我再沒參加發射營的選拔考試,退出了旅里軍校苗子班的預選,也放棄去士官學校進修。我拒絕所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心甘情愿堅守高山哨所,似乎就是為了解開老兵這個謎面的謎底。
無所不能的老兵,笑容暖人的老兵,他何以錯失了提干而突然退伍?他又為何年復一年隱身山林?我這些年見人就問是否認識老兵,又不遺余力在認識他的人里打探關于他的一切。有一年,來哨所維修電纜的上士技師在我送他一對山核桃后告訴我,老兵重返哨所前一晚喝了很多酒,對同飲的營部文書說了很多話,營部文書應該知道我想了解老兵的秘密。我高興極了,以為一切都將有答案,并且知道技師所說的文書正是當年送我到哨所山口之人。可是自那之后,我再打探不到文書的任何消息。他退伍多年,沒人知道在什么地方,也打聽不到任何聯系方式。
每當新聞上播報世界各地的間諜案件,哨所的戰友都會自信滿滿地說,連我們自己人都不知道消失的老兵隱身何處,哪個外人又敢擅入三十里山林?也有人說,外國間諜早就謀劃從三十里山林進入我們的導彈旅禁區,老兵是領受了上級布置的秘密任務才潛伏山林,只等抓諜立功。
不管真相是什么,我都相信老兵不會有錯。
八年后,我中士第三年。也到了士兵在哨所服役的最高年限。
加之我的所有過往就像一場半睡半醒的夢,我常在夢里委屈得淚流滿面。老兵一去不回到底跟我有什么關系?為什么他出走山林席卷了我的整個軍旅生涯?我遇老兵時是哨所最新的兵,和他只不過相見三面。
四季輪回里的風霜雨雪更新著三十里山林,一切如故,一切又都是新的。我的頭發被山風吹掉了大半,容顏蒼老。我的腿巡山時被落石砸斷,皮肉雖痊愈,骨頭卻落下殘疾。嚴重的頸椎變形讓我整日頭昏腦漲心煩意亂。我厭倦日復一日重復巡守山林,我極度渴望換一種新的活法。
可是老兵呢?我常記不起他的容貌,不得不到哨所的榮譽室里緊盯著他的戎裝照片,才能在腦中緩慢還原那個臉上綻著笑容的陌生故人。老兵一年又一年就像山林里的野獸一般獨自生存,卻又沒有野獸那樣強壯的身體。我有時殘忍地想,老兵是不是早已暴死山林。哨聲依舊一早一晚響起,他還活著嗎?我有時寧可相信哨音是我頭昏腦漲產生的幻覺。我自己和自己掐架,激烈爭論老兵的生死。他在我半睡時死去,又在我半醒時活了過來。我不知道哪一個我是對的,也不確定他是死還是活。
我長久地癡望山林自言自語,才不到三十歲的年紀,卻頹喪得像個病入膏肓的老人。新到任的中尉哨長溫和地勸我最好不要夜晚獨自上山。我驚訝地望著他,知道他知道我半夜夢游。他維護著一個哨所老兵最后的尊嚴,并沒有那樣說。哨所沒有夢游者,或許每個人都有夢游的夜晚,但沒有人說別人夢游。我也鬧不清那是白天還是黑夜,睡去還是醒來。我還不到三十歲,耳朵靈敏,在月光擊打玻璃的嘈雜聲中捕捉到那一聲長長的哨音。我知道老兵找我。我披衣起床,循著哨音步入山林。我在老兵受傷的地方看到一個黑影,我走近,黑影卻跑開。那黑影就像另一個我,我動他也動,我停他也停。我知道我是我,黑影是黑影,那是老兵在我面前的投射。我急于知道他長久隱身山林的謎底,更想勸他走出山林。我還像八年前那樣稱他哨長,我說:“不管您在這里堅守什么,都已經太久了,離開吧,您還沒有老到埋骨山林。我和您當年一樣,現在是哨所最老的兵,我來接替您吧,您去重新開啟自己的生活。”黑影定在那里一動不動。我繼續說:“放心吧,您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我說出這些話的同時就后悔了。我只想勸服老兵,他在這片山林待得太久了,也到了該離開的時候。我也不再年輕,即將卸下軍銜失去軍人的身份。
我沒動。黑影動了。
我看見老兵走近我。他蒼老的臉上綻出歡快的笑容。
我沒想到老兵會相向而來,更沒想到他同意了我的建議。我站在叢林之中,看到老兵向著哨所的方向走去,他跨過河溝到了哨所門前的廣場,哨兵沒有發覺,軍犬也沒有吠叫。老兵朝著哨所敬了個軍禮。他下了臺階走向唯一的出山小道。我看見他在月光的照耀下越走越遠,直到蹤影全無。我突然沉陷在無邊無際的絕望里。我即將三十歲了,到了中士第三年,我馬上就要退伍離開哨所,開始新的生活。我在山林里狂奔,我相信老兵只是出現在我的夢里。我故意撞向樹干和石頭,我知道夢里沒有疼痛。就算明知是在夢里,我也急于收回我對老兵說過的每一句話。
新任的中尉哨長默默地給我拿來了治療外傷的藥物,又一次勸我最好不要夜晚獨自上山。嘹亮的起床號響起,我卻沒有在此之前聽到悠揚的三聲哨響,我在漫長的白晝里急躁等待,夜晚降臨,熄燈的軍號聲止住后,我仍沒有等到悠揚的三聲哨響。老兵走了。我沖出哨所,站在廣場望向山林。風止林靜,月光如灑,就像萬千將士屏息等待我的統領。
老兵走后,再沒人見過他,就連曾經隨風飄蕩的關于他的傳說也蹤跡全無。老兵在哨所榮譽室留下一張戎裝照片,那是他真實存在的見證。
我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癥,夜不能寐,晝則渾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