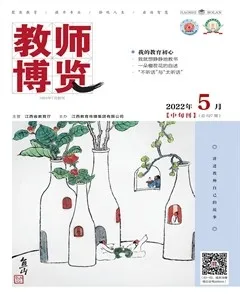教育,就是讓我把曾經需要的給學生
一
夜已深,楊聰老師的《插班生林可樹》也即將看完。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不斷被楊聰老師感動,不斷產生共鳴,也不斷在書的邊縫寫下自己的感受。
就在將要看完、放下書本之時,我讀到了楊聰老師這部“教育敘事”的最后一句話——
我曾經也是學生,也渴望著老師的溝通、理解、鼓勵、寬容和賞識……教育,就是讓我把曾經需要的給學生!
我瞬間熱淚盈眶,緊接著號啕大哭。熟睡的妻子被我突如其來的哭聲驚醒,問我怎么回事。是啊,怎么回事?
小時候,我是一個不聽話的學生,受老師的傷害很深;成為老師之后,我卻想對學生好,成為一名好老師。原先總以為自己是為了“報復”,到現在才知道沒那么復雜——我只是不想讓自己受過的傷再讓學生受一遍。用楊聰老師的話來說,就是“讓我把曾經需要的給學生”。
而在此之前,我已經被這種因“恨”生“愛”的復雜心理困擾多年。
二
1995年,我以3分之差,與重點高中失之交臂。分數線公布之后,班主任就找我談話:“朱勝陽,報考師范專業的話,英語成績不用算。你就去讀師范吧。”我點點頭。英語總分120分,我只能考60多分,不報考師范還能干嗎?再說,報考師范除了文化科目考試,還要進行美術、音樂及普通話的考試,我普通話雖一般,但美術和音樂都比較有優勢。所以在班主任眼中,師范似乎是給我“量身定做”的。
選擇讀師范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我喜歡班上的一位女生。但我身材樣貌一般,才華能力一般,家境條件一般,所以連追求她的勇氣也沒有。可如果我能考上師范,不但將來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當時師范畢業生的工作包分配),還可以把我的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而“農轉非”當時在我們農村相當于是“鯉魚躍龍門”。這樣的話,我追求這位女生時可以稍微有一點底氣。因此在接下來的文化課復習和素質考試集訓過程中,我都非常努力。最后我如愿以償,考上了浙江省上虞師范學校(今紹興文理學院上虞分院)。
說這么多,只是想表明我當初選擇讀師范,不是因為理想,也從來沒有這樣的志向,純粹只是命運使然。
三
雖然當老師不是我的理想,但1998年師范畢業參加工作之后,我也想把學生教好,使自己成為一名受學生歡迎的好老師。
但我想成為一名“好老師”的出發點很“陰暗”——我是為了“報復”,或者說是“報仇”。因為我上學時是一個特別頑劣的學生,除音樂老師、美術老師和數學老師稍稍對我有點好感外,其他老師基本上都討厭我,特別是班主任——從幼兒園開始到師范畢業,沒有一個班主任喜歡我。在我上學的生涯中,基本聽不到表揚,也得不到關注,關心就更不用說了。我很清楚這些教我的老師把我歸為哪一類學生。但難道像我這類學生就不需要老師的表揚與鼓勵嗎?就不需要老師的理解與寬容嗎?
所以現在自己也當老師了,我就想要“報復”——做一名好老師:以前教我的那些老師越是對我不好,我現在越是要對自己的學生好;以前教我的老師不關注我這類學生,現在我越是要關注班級中那些其他老師很少去關注的學生。可以說是“恨”的力量在不斷促使我去“愛”自己的學生。感覺很別扭,但我的確是這樣一種心態。
我的經歷,造就了我對學生病態的“愛”。
四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自己用心的付出,學生越來越喜歡我。我也在與學生相處的過程中,找到了做老師的快樂與幸福。但隨著相互之間的關系越來越融洽,我的心不知怎的,越來越感到不安——特別是在柯巖永紅小學的那段時間。
那時我剛從湖塘中心小學調到柯巖永紅小學,學校安排我教五年級語文兼任一個班的班主任。我上任沒多久,就打開學校圖書室,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為學生們淘出一批比較優秀的圖書,供全班學生閱讀。據班上的學生說,他們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還從來沒有老師為他們向學校的圖書室借過書,我是第一個。課堂上聽學生朗讀課文時,注意到他們沒有節奏、不講停頓,只是簡單地把字念出來、讀下去,聽起來機械、冰冷,所以我又想辦法為學生借來磁帶和錄音機,從零開始教學生們朗讀。春暖花開的時節,我又組織全班學生到操場上去放風箏,感受春天……所以這個班的學生越來越喜歡我這個新班主任。
但學生們越是喜歡,我越是不安。好像有塊沉重的石頭壓在心頭。我想:可能是我對學生的“愛”動機不純所導致的吧!但我又想不出為自己開脫的辦法。相反,越是思考這個問題,感覺自己越是卑劣,心情也越是壓抑。看著學生們那天真無邪的笑臉,我甚至有點不敢面對他們……
日子一天天過去,心頭的這塊石頭,變得越來越沉重。我身陷泥淖,無法脫身——直到看到這句話……
五
“教育,就是讓我把曾經需要的給學生。”
回想這么多年的教書經歷,我不就是這樣在教自己的學生嗎?自己書看得少,就建立班級圖書角,鼓勵學生多看課外書,從小愛上閱讀;自己古詩詞積累得不多,就讓學生多背古詩詞,變著法子獎勵他們;自己字寫得差,就讓學生買來字帖,我們師生一起練字;自己討厭老師布置的作業多,討厭機械的作業,現在我就少布置一些作業,布置的作業盡量多一些趣味性與實踐性;自己讀書時不受老師關注,現在就關注班級中的每一個學生;自己讀書時老犯錯誤,得不到班主任的寬容,現在學生犯錯時,我會多想想當年的自己,多站在學生的角度來思考他們的錯誤……
我跟妻子說,我在書中讀到一句話,“教育,就是讓我把曾經需要的給學生”。原來我所做的一切只是為此,原來這才是我的教育初心。
(作者單位: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實驗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