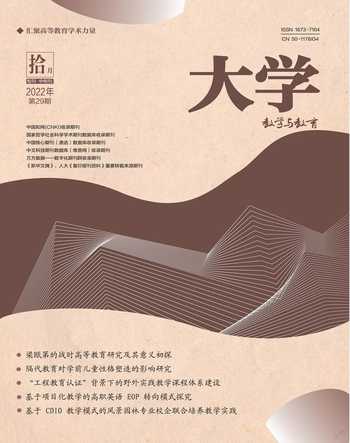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意義初探
侯波
摘? 要:梁甌第是我國本土培養的第一代教育學者和教育家,主要專注于邊疆教育研究和實踐。抗戰爆發后,梁甌第轉向對一戰時期英、法、德、美四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為抗戰前期興起的戰時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文章主要運用歷史文獻法,詳細解讀梁甌第《戰時的大學》《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歐戰時美國的大學》二書,系統論述其戰時高等教育研究的緣由、內容與觀點。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研究雖不乏過激之論,但反映了抗戰爆發后一代青年學人對國難日亟形勢下中國高等教育現狀與前景的深刻思考。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研究闡明了“大學興廢關系國家存亡”的道理,對當今中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梁甌第;戰時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高等教育史
中圖分類號:G649.29?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2)29-0001-04
梁甌第,1910年生于福建建甌,1937年畢業于我國近代第一所教育科學研究機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后簡稱“教研所”),系該所培養出的首位教育學碩士。1937—1949年,梁甌第先后任大夏大學教育學系主任及總務長、貴州師范學校校長等職。作為我國本土培養的第一代教育學家,梁甌第主要致力于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的研究與推廣,撰寫多部探討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的論著,在中國邊疆教育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對于梁甌第的邊疆教育研究,國內學者已有初步探討[1-2]。不過,在梁甌第的教育學研究成果中,有兩部問世于抗戰前期的論著——《戰時的大學》《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歐戰時美國的大學》尚未引起足夠關注。這兩部論著一反梁甌第早期的邊疆教育研究旨趣,轉而探討起一戰時期歐美四國高等教育。雖已有研究對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二書進行簡介[1-2],但并未對其個中緣由、觀點和意義詳加探討。本研究擬從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二書入手,闡述梁甌第轉向戰時高等教育研究的緣起、內容和觀點,由此管窺抗戰爆發前后中國青年學者的心路歷程。
一、梁甌第轉向戰時高等教育研究的緣由
梁甌第于1930—1937年間就讀于中山大學教育系、教研所,完成了從學生向青年學者的成長。梁甌第完成學業時,正值抗戰爆發,其研究旨趣遂從原先的邊疆教育轉向一戰時期歐美四國高等教育。這離不開日漸嚴峻的時代局勢,也同梁甌第所受的學術訓練以及前輩學人的影響緊密相關,包括以下因素:
其一,中大教育系創始人莊澤宣所倡導的比較教育研究。作為1927年創辦的中大教育系首任主任,莊澤宣強調以外國教育為參照來研究中國教育,以外國教育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教育改革提供借鑒。1929年,莊澤宣著《各國教育比較論》[3],對英、法、德、美四國學校與教育制度進行比較,是中國最早研究比較教育的專著。在莊澤宣的倡導下,中大教育系于1932年于全國率先開設“比較教育”必修課,對英、俄、德、法、美、日、意、土八國教育狀況加以介紹與比較。同時,依托于教育系的教研所也出版了一系列介紹各國教育教育動態的比較教育論文、叢書。至1937年,教研所在所刊《教育研究》上刊載比較教育論文58篇,出版比較教育論著10種。其中崔載陽的《世界戰時的學校動員》對梁甌第產生了直接影響[4]。此書論述了一戰期間英、俄、法、美、德五國的各類學校及其師生踴躍參戰、為國效力的情況。
其二,讀研期間教研所所長崔載陽所主張的教育“民族化”。1934年7月梁甌第升入中大教研所讀研時,崔載陽接替莊澤宣出任所長。崔載陽力主教育“民族化”,呼吁在“風雨飄搖國家地位日久危急的嚴重時代”,實行“民族主義的‘明恥教戰的教育方法”[5]。崔載陽后來進一步闡發了教育“民族化”之主張,稱為“民族中心教育理論”[6]。1935年,日本策劃華北自治,崔載陽組織包括梁甌第在內的中大教研所師生,在當年冬制定了中國第一份“戰時教育工作計劃”,對國家戰時教育方案進行了詳細周密的討論,以備戰時之需。“大學戰時工作計劃”是其中主要內容之一,提出“戰時大學應變成工廠化、軍營化,以養成戰時各種工作領袖為宗”[7]。
其三,抗戰前夕梁甌第所進行的國難教育調查。在崔載陽的影響下,梁甌第在中大教研所求學期間便關注起國難教育問題。1936年2月,他在《教育研究》發表了一篇學術綜述性的論文——《八年來中國國難教育之研究》。1937年5月至11月間,梁甌第與同學富伯寧從廣州經上海、無錫到南京,對四地的大學生與高中生的國難教育現狀進行調查,完成《中上學生國難調查報告》[8]。在此過程中,梁甌第從暫時太平的廣東來到戰火已至的蘇滬,目睹了南京、上海諸多大學為躲避戰火而紛紛內遷的慘況與混亂,對國難日亟、民族存亡之危機有了更為直觀的體會。此次國難教育調研的經歷,為梁甌第在抗戰爆發后探討戰時教育問題埋下了伏筆。
其四,抗戰初期中大教研所開展的戰時教育實踐。抗戰爆發后,尚仲衣教授出任中大教研所代主任。在其組織下,中大教研所自發開展各種戰時教育實踐活動,配合抗戰需要,如舉辦戰時教育講座、教育進修班、特種訓練班;與嶺南大學、勷勤大學共建戰時教育研究會,在《中山日報》設置“戰時教育專欄”;成立抗戰教育實踐社,組織“抗戰教育服務團”,支持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的活動等等。中大教研所師生積極參戰、為國效力的戰時實踐活動,為梁甌第后來思考中國大學的戰時改進提供了靈感。
二、梁甌第戰時高等教育二書的主要內容
《戰時的大學》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歐戰時美國的大學》二書探討一戰時歐美大學是如何調整、改進,為國家效力的。
首先,在教學教育方面,各國大學針對戰時需要調整課程。課程的調整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停授部分原有課程,二是增設新課程,或改變原課程的內容,使其偏重于戰爭問題,以切合戰時需要。如英、法、德三國大學增設了動員法令、國際法與戰爭、戰事外科、戰時特種講座等課程,又改變了哲學、神學、法學課程的內容,以戰爭局勢為中心。在美國大學,化學系設“燃料、火藥及軍需品”、數學系設“炮彈發射”“方向窺測”、英語系設“戰爭文學”、政治學設“戰爭外交”、歷史系和國際法系設“軍事史”“現代戰爭史”、經濟學系和社會學系設“戰時財政”“戰時勞動”、護理系設“戰時護理”、心理學系設“戰爭心理”“戰事服務的心理測驗”等課。
除課程調整外,各國大學還與政府密切合作,開展軍事教育訓練。如美國大學于1918年秋全面實施大學軍事訓練計劃,成立“學生軍訓練營”。據此計劃,聯邦政府向各大高校委派軍官指導軍事訓練,并提供軍訓所需設施。學生入學即為新兵入營,成為一名陸軍士兵,接受軍事管理和教育訓練。從1918年10月1日成立至11月26日遣散,美國共有516所大學成立了學生軍訓練營,總計約14萬人完成軍事教育訓練。
其次,在學術研究方面,四國大學通過軍事科技研發為戰爭服務。例如德國大學對化學武器、戰時糧食問題、軍事裝備發明與制造進行了研究,英國大學為政府和軍方所開展的研究更為豐富,包括“爆炸藥的試驗;爆炸藥優廉制造法之研究;特種炸彈的制造與掘壕具的發明;軍用皮布之準備及試驗;飛機飛艇所用布、麻的研究;炸彈發射計的構造;飛機測量計的試驗;海陸空用無線電通信問題的研究;特種地圖之制作;絕氣瓦斯的制造及發明;海陸空軍用鋼鐵的試驗;秘密通訊方法的研究;新式射程指導鏡的制造”。在美國,大學所從事的戰時研究覆蓋到化學、物理工程學、細菌學、生物學、心理學、植物學、數學、藥劑和有毒物質研究等各個領域[9]。
最后,在社會服務方面,四國大學在戰時均響應國家動員,將教學、科研設施交付國家,作軍事之用。例如,法國大學“教室講堂不改軍營,即改為病院”,英國牛津大學各學院變成“兵營和招募的陣地”。在美國,100多所高校將校舍交付戰爭部使用,改作訓練所、兵營、軍用實驗室等[9]。
大學師生則踴躍參軍,為國效力。例如1915年夏季學期時,德國大學共有34386名大學生參戰,占大學生總數的64.2%。至1915—1916年冬季學期,德國大學教師中有1111人參戰,占教師總數的30%。“不少著名的專家或國際學者,都在前線上,……寧愿拋下書本,遺棄了實驗室,到炮火的陣地上像常人一樣的工作”[10]。“英國的牛津大學參戰的人數達1500人,劍橋大學應征者有735人入新兵伍。”[9]在美國,共計180所大學的男學生棄學從軍,其中6所大學離校參軍學生的比例超過50%[9]。
通過對一戰時期歐美四國大學的研究,梁甌第得出結論:“教育跟軍事、經濟、政治一樣,亦同為戰爭之一重要工具。”[9]一戰期間,四國大學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三大職能上積極調整,應對戰爭之需,既實現了大學的教育職能,也凸顯了教育為國家服務的功用。
三、梁甌第對抗戰前期中國高等教育的批評與建議
通過比照一戰中的歐美四國大學,梁甌第對抗戰爆發后中國大學的表現感到不滿,從大學師生、辦學政策、教育方針三個方面予以了批評。
首先,他批評了抗戰爆發之初大學師生的表現。梁甌第指責許多學生不知亡國之危,未能積極動員,共赴國難。他質問:“試問抗戰至今,學生軍已有組織與訓練的有哪幾校!曾已出發前線的學生又有多少?戰區或后方的服務團、慰勞隊、救護隊等,雖也有學生參加,但是踴躍工作的倒底又有幾人?”[10]梁甌第對大學教師的批評更加猛烈,理由有三:1. 知識陳舊,不符抗戰之需;2. 囿于書齋,不擔抗戰之責;3. 故步自封,抵制戰時教育變革。他指責許多大學教師是“學究式的教育者”,做的是“書蟲工作”,結果成立“空頭主義者”“既無身臨前敵,執戈衛國的勇行,更未將研究與教學改弦更張,以適合戰時的需要”[10]。
其次,他批評大學的教育管理政策。一方面,他指責大學仍舊恪守原有課程,不做變通和調整,“念文學的只要研讀李杜詩、韓蘇文、春秋楚辭、米爾頓詩、伊麗莎白時代文學、莎士比亞喜劇、史前社會史、說文解字;念科學的只要修習日月蝕專論、化妝品化學制造、古生物學、北美洲地志、歐幾里得數學、加利幾何學、切腺位標”;另一方面,他不滿于大學陷入停辦、停課、遷移的被動狀態,缺乏積極、主動的改進姿態,“警報一來,逃之夭夭,警報一弛,零零落落”[10]。
最后,他反駁了一些大學管理者所主張的維持原有教育模式的理念。例如梁甌第批評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危城講學“最后一課”“抗賽論”等觀點。他指責“危城講學”是“濫竽充數的教授先生們”敷衍了事、逃避救亡天職的借口[10],宣稱“在國家興亡間不容發的最后關頭”“教育者們卻沾沾自喜的勸人模仿印度的太戈爾,倡敵我學生抗賽論,叫人埋歌苦讀”,實際上是為了抵制“戰時教育”[10]。
梁甌第對大學師生、辦學政策、教育理念的激烈抨擊,直指抗戰爆發前后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病。因此,梁甌第引一戰中歐美四國大學的具體作為,作為抗戰后的中國大學提供“糾正時下一部分謬誤的觀念與行動”的參照,并就中國高等教育如何改進提供了建議。
首先,他強調中國大學應革除舊弊,掃蕩舊習,結合抗戰現實,為國效力。梁甌第認為,戰時的中國大學應舍棄“學用相違”的舊弊,師生亦應摒絕“知行不一”的舊習。中國大學應轉向“武裝頭腦與武裝手足”“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的“國防教育這一健全的道路”。他寫道:“我們所需要的大學不是要空洞的、抽象的研究干枯的條文定律,而是要實際地、具體地學習抗戰的事業。”[10]
其次,他主張中國大學在戰時應改變消極、被動的態度,積極、主動地投身于抗戰之中。為此,梁甌第列舉了一些具體措施,如在前線成立設立戰地大學、發揮教師的表率作用、加強集體實踐教學、大學管理“軍營化”、課程設置“戰爭化”、修建臨時校舍以使原校舍“貢獻國家作為軍營或醫院之用”[10]。
最后,他呼吁中國高等教育應以“民族主義教育”為最高理念。梁甌第認為,奉行“民族主義教育”,可使中國大學在戰時成為訓練抗戰干部的陣營,在戰后成為“發揚民族所有的遺產,以與西方學術文化相溝”[9]的機構,從而將“戰時與平時,學術與實用,前方與后方,非常急變與遠大理想”有機結合、協調起來”[9]。
四、梁甌第戰時高等教育研究的意義
抗戰爆發后,梁甌第并未投筆從戎,而是轉向研究一戰時期歐美四國高等教育。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研究,傾注了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關懷,也流露出對中國高等教育于火中涅槃、勇擔抗戰新使命的期盼。盡管梁甌第在批評中國高等教育和大學師生時常有過激之論,但這出自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情。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讀到梁甌第之書后認為,他對當時大學的批評“亦極中肯,綮目前大學之保守舊有政策,固不相宜也”[11]。
從抗戰前期國內知識界的思想走向來看,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教育論并非難鳴之孤掌。一方面,抗戰爆發后,眾多愛國師生表達了投筆從戎的志愿,但各校對師生離校從軍政策不一,引起了部分師生的不滿;另一方面,抗戰初期,國內知識界圍繞“要不要戰時教育”“如何實施戰時教育”等問題掀起了一場影響廣泛的教育論爭,由此涌現出一股主張各級教育“戰時化”的戰時教育思潮。在基礎和中等教育層面,陶行知及其所領導的生活教育社是這股戰時教育思潮的重要主張者。
在大學教育層面,梁甌第是戰時教育思潮的代表之一。因此,梁甌第的戰時大學教育論不僅反映了當時廣大愛國師生要求參加抗戰、救亡報國的訴求,而且與陶行知等進步人士的教育主張相一致。
大學教育,或曰高等教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來源。梁甌第著眼于抗戰中中國大學的戰時改進,立足于抗戰建國雙重使命下中國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可謂用心良苦。時至今日,戰火與硝煙雖已遠去,但梁甌第的戰時高等教育研究闡明了“大學興廢關系國家存亡”的道理,對當今中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 張學強,李東東. 梁甌第的西南邊疆教育研究及其價值[J]. 民族教育研究,2016,27(01):13-17.
[2] 曲士培. 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31-338.
[3] 莊澤宣. 各國教育比較論[M]. 廣州: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出版部,1929:1-2.
[4] 崔載陽. 世界戰時的學校動員[M]. 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5] 崔載陽. 今后教育應以明恥教戰為根本要義[A]//陳彩鳳,黃秀華,農莉民. 廣州民國日報青運資料選輯(1923-1929)[C]. 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1992:365-369.
[6] 吳冬梅,楊林. 20世紀30年代崔載陽的民族中心教育理論研究[J]. 教育學報,2015,11(02):93-103.
[7]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同人. 戰時教育工作計劃(三) [N]. 申報,1935-12-28 (第22514號).
[8] 梁甌第,富伯寧. 上中學生國難教育意見調查[A]//李文海. 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814-872.
[9] 梁甌第.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歐戰時美國的大學[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1+13-14+17+40-42+105-106+111-113.
[10] 梁甌第. 戰時的大學[M]. 重慶:戰時文化出版社,1938:7-8+46-47+69-70+89-112.
[11] 竺可楨. 竺可楨日記(第一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32.
(責任編輯:鄒宇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