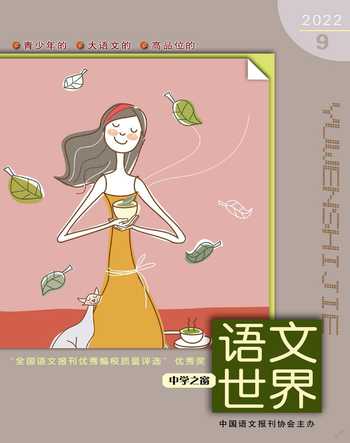閑人與看客
馮曉晶
《阿Q正傳》是魯迅先生的經(jīng)典作品之一,被收錄于部編版高中語(yǔ)文教材選擇性必修下冊(cè)。通常情況下,人們解讀這篇課文中的主角——阿Q,往往都是從批判的角度進(jìn)行的,這符合魯迅先生的初衷,也符合主流價(jià)值觀的認(rèn)識(shí)。畢竟,魯迅先生所創(chuàng)作的阿Q,其身上所存在的“阿Q精神”,也就是“精神勝利法”,確實(shí)表現(xiàn)著人性中的“小”。通常情況下,阿Q精神也就是精神勝利法的主要表現(xiàn),就是妄自尊大,自輕自賤,欺軟怕硬,麻木健忘;而進(jìn)一步解析,其實(shí)質(zhì)是“弱者無(wú)力反抗,只好在精神上求得安慰”,所以人們常常認(rèn)為“精神勝利法”就是“自暴自棄的弱者的哲學(xué)”。
應(yīng)當(dāng)說(shuō)這樣的分析非常有道理,也應(yīng)當(dāng)說(shuō)這樣的分析結(jié)果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基本的共識(shí)。在批判阿Q精神的同時(shí),筆者以為文中還有一類角色也值得細(xì)細(xì)研究,這就是課文當(dāng)中不時(shí)提到的閑人與看客。相對(duì)于阿Q這個(gè)角色而言,閑人與看客顯然沒有那么重要,其更多的是一個(gè)配角角色;但這種角色所代表的意義卻是不可忽視的,無(wú)論是魯迅先生所處的那個(gè)社會(huì),又或者是任何一個(gè)社會(huì)當(dāng)中,總難免會(huì)出現(xiàn)閑人與看客,對(duì)于這樣一個(gè)群體及其角色而言,應(yīng)當(dāng)建立一個(gè)怎樣的認(rèn)知,非常值得思考。
一、閑人與看客的普遍存在
通讀《阿Q正傳》這篇課文可以發(fā)現(xiàn),阿Q這個(gè)角色是有些特立獨(dú)行的,當(dāng)然這也是作者魯迅創(chuàng)作的重點(diǎn)人物,因此其獲得人們的普遍關(guān)注也是必然的。相比較而言,閑人與看客屬于大多數(shù),盡管這樣的人物人數(shù)眾多,卻容易被忽視。那么為什么筆者又想對(duì)閑人與看客進(jìn)行解析呢?其中一個(g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對(duì)于絕大多數(shù)的讀者而言,其身上不可能存在阿Q這樣的特點(diǎn),或者說(shuō)即使每一個(gè)人身上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阿Q精神,在某一些場(chǎng)合也可能會(huì)表現(xiàn)出一些精神勝利法,但是至少來(lái)說(shuō),其不可能成為一個(gè)人的主要特征,因此對(duì)于絕大多數(shù)讀者而言,是不可能成為阿Q的。但不可否認(rèn)的一個(gè)事實(shí)是,卻很有可能成為閑人與看客。
從文本中的描述來(lái)看,閑人與看客在文中的表現(xiàn)有“普通”且“普遍”的一面。文中說(shuō),“未莊的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幫忙,只拿他玩笑”——在這里,未莊的人們就是閑人,就是看客,他們?cè)诿鎸?duì)阿Q的時(shí)候,“只拿他玩笑”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這實(shí)際上是必須批判的(具體原因下一點(diǎn)再闡述)!問(wèn)題的關(guān)鍵在于,假如在我們的身邊也有一個(gè)類似于阿Q這樣的人,那我們是不是也會(huì)有“只拿他玩笑”的語(yǔ)言或者行為呢?如果有,那又說(shuō)明了什么呢?
將研究的視角回歸到作者,筆者以為魯迅先生在創(chuàng)作的時(shí)候,閑人與看客并不是一個(gè)可有可無(wú)的角色,甚至可以認(rèn)為,在魯迅先生的眼中,閑人與看客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一些人性,也是魯迅先生批判的對(duì)象。認(rèn)同這一點(diǎn)并不是對(duì)作為讀者的自己的否定,恰恰相反,正是因?yàn)殚e人與看客普遍存在,所以在解析這一類對(duì)象的時(shí)候,更有助于讀者的我們?nèi)シ此甲约骸徱曌陨怼?/p>
綜合來(lái)看,對(duì)文中的閑人、看客等其他人——這些在文中一閃而過(guò)的次要人物作深入分析,就能更加全面地理解魯迅思想的深刻性。
二、閑人與看客的警示價(jià)值
所以,基于上述分析,筆者想亮明的一個(gè)基本觀點(diǎn)就是:閑人與看客也是具有價(jià)值的,批判阿Q精神的同時(shí),也要批判閑人與看客身上更具共性的不足。
實(shí)際上,魯迅先生對(duì)閑人與看客也是深惡痛絕的,這種觀點(diǎn)在魯迅先生的作品當(dāng)中可以說(shuō)是非常常見,而在《阿Q正傳》通篇中尤其眾多。在《阿Q正傳》中,除了典型人物阿Q之外,未莊的閑人、酒店的人、看阿Q槍斃的城里人,甚至是趙太太,在他們的身上都表現(xiàn)出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那就是閑人與看客的身份,所以從某些方面來(lái)說(shuō),他們實(shí)際上都是同類人。這些人雖互為形影,卻不自知,更不互憐,他們絲毫不認(rèn)為自己身上也存在著他人的缺點(diǎn),更不認(rèn)為自己身上存在阿Q那樣的特點(diǎn),他們麻木地以對(duì)方的尷尬和悲慘境地作為緩解自身壓抑或苦悶的憑借,顯得可憐又可恨。可以肯定的講,在魯迅先生的眼里,或者說(shuō)在魯迅先生的筆下,這些人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特點(diǎn),無(wú)論是被動(dòng)的盲目,還是主動(dòng)的自欺,本質(zhì)上都是病態(tài)的心理,是可悲的國(guó)民性弱點(diǎn),都應(yīng)當(dāng)是被批判的對(duì)象。
因此,閑人與看客的警示價(jià)值,在課文解讀的時(shí)候不可忽視。這里不妨從課文中挑一處描寫來(lái)說(shuō)明:“或者因?yàn)榘說(shuō)是趙太爺?shù)谋炯遥m然挨了打,大家也還怕有些真,總不如尊敬一些穩(wěn)當(dāng)。否則,也如孔廟里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jīng)圣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dòng)了……”
在這段描寫當(dāng)中沒有明確提及閑人與看客,但也正是因?yàn)槿绱耍鸥@得閑人與看客更具普遍性,甚至更具隱秘性。趙太爺原本看不起阿Q,阿Q也只能用精神勝利法去對(duì)待趙太爺和他那一巴掌,然而吊詭的是,卻因?yàn)榘和趙太爺是本家,所以“大家”居然“也還怕有些真”——這里的“大家”是誰(shuí)呢?除了閑人與看客又有可能是誰(shuí)呢?那此時(shí)閑人與看客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特點(diǎn)與阿Q又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呢?還不一樣應(yīng)當(dāng)是被批判的對(duì)象嗎?此處魯迅先生所寫的另一個(gè)角色也是如此,這就是“先儒”。按理說(shuō)先儒應(yīng)當(dāng)是學(xué)問(wèn)大家,他們的思想境界應(yīng)當(dāng)超過(guò)一般人,可惜的是在面對(duì)“孔廟里的太牢”的時(shí)候,依然會(huì)因?yàn)椤笆ト讼麦纭保浴氨悴桓彝齽?dòng)了”。這樣的先儒與一般人又有何區(qū)別?與閑人和看客又有什么區(qū)別呢?
所以,閱讀這些文字并且思考這些問(wèn)題,就可以發(fā)現(xiàn)體現(xiàn)在閑人與看客身上的這些人性的不足,確實(shí)也應(yīng)當(dāng)是被批判的對(duì)象。如果只是因?yàn)榘吸引了批判的火力,而忽視了這些閑人與看客身上所暴露出來(lái)的不足,那即使讀者能夠回避阿Q的精神勝利法,也未必就能走向一個(gè)更高的境界。
三、走出閑人與看客的窠臼
從上面的分析來(lái)看,無(wú)論是作為課文解讀者的高中語(yǔ)文教師,還是作為教師的教學(xué)對(duì)象,也就是學(xué)生,在解讀《阿Q正傳》,在解讀阿Q精神、精神勝利法的時(shí)候,要堅(jiān)持整體和系統(tǒng)的思路,在關(guān)注阿Q的同時(shí)也關(guān)注閑人與看客,只有這樣,才能走出閑人與看客的窠臼。
應(yīng)當(dāng)說(shuō),閑人與看客的窠臼是明顯的:在面對(duì)阿Q的時(shí)候,他們只是將阿Q作為嘲笑的對(duì)象,極少有批判并改變自身的意識(shí);在面對(duì)自己的時(shí)候,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不足,自然也沒有批判的意識(shí)。其實(shí)無(wú)論是面對(duì)生活中的經(jīng)驗(yàn)積累,又或者是面對(duì)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角色,當(dāng)解讀者不能真正面對(duì)自己的時(shí)候,那么課文解讀的意義是有限的。
在筆者看來(lái),不能面對(duì)自己,也就意味著沒有走出閑人與看客的窠臼。這也就意味著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小”。如果是這樣,那么在面對(duì)魯迅先生所創(chuàng)作的這些作品的時(shí)候,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收獲呢?要知道,阿Q的性格本質(zhì)是由“奴隸意識(shí)”和“帝王意識(shí)”構(gòu)成的。無(wú)論是在魯迅先生的筆下,還是在更多的解讀者心中,阿Q應(yīng)當(dāng)是作為一個(gè)象征符號(hào)而存在的,他是對(duì)中國(guó)人的高度的精神本質(zhì)的象征,而且未莊的所有人都與阿Q在精神本質(zhì)上一脈相承。坦率地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并且在課文解讀的時(shí)候留一只眼睛給自己,不讓自己成為閑人與看客,那么才算是準(zhǔn)確地把握了課文的脈搏,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學(xué)有效的認(rèn)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