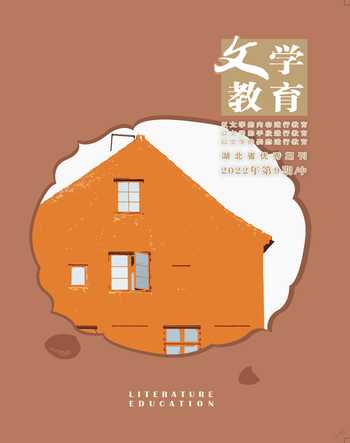簡(jiǎn)論董立勃軍墾小說(shuō)中的兵團(tuán)精神
劉蒙蒙 李瑞敏
內(nèi)容摘要:董立勃的軍墾小說(shuō)以“下野地”農(nóng)場(chǎng)為舞臺(tái),敘述了發(fā)生在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的傳奇故事。女性形象在董立勃的軍墾小說(shuō)尤為突出,她們?cè)谄D苦的條件下為兵團(tuán)的屯墾戍邊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董立勃的軍墾小說(shuō)通過(guò)藝術(shù)的形式呈現(xiàn)了“熱愛(ài)祖國(guó)、無(wú)私奉獻(xiàn)、艱苦奮斗、開(kāi)拓進(jìn)取”的兵團(tuán)精神。
關(guān)鍵詞:董立勃 軍墾小說(shuō) 女性形象 兵團(tuán)精神
學(xué)界對(duì)董立勃小說(shuō)研究較為深入,通常以他的“下野地”系列小說(shuō)為對(duì)象,在賞讀作品的同時(shí)研究其語(yǔ)言風(fēng)格與藝術(shù)特色。有的學(xué)者則是通過(guò)特殊視角研究董立勃小說(shuō)中的個(gè)性展現(xiàn)。本文主要探討董立勃軍墾小說(shuō)與時(shí)代的關(guān)系,力求在文化潤(rùn)疆視野下發(fā)掘其作品的新內(nèi)涵并為弘揚(yáng)兵團(tuán)精神和推動(dòng)文化潤(rùn)疆工程進(jìn)行有益探索。
一.“下野地”的傳奇
1954年隨著“駐疆官兵集體就地轉(zhuǎn)業(yè)”的指令下發(fā),大部分的官兵“脫離國(guó)防部隊(duì)序列”[1]投入到組建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的行列中去。此后內(nèi)地支援邊疆的知識(shí)分子和有志青年積極響應(yīng)國(guó)家號(hào)召,自發(fā)地來(lái)到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參與建設(shè),組成了一支“不穿軍裝、不拿軍餉、永不復(fù)員的特殊部隊(duì)”[2]。這支部隊(duì)“執(zhí)行著國(guó)家賦予的屯墾戍邊神圣使命”[3],他們分布于新疆每一寸荒蕪的土地。在建設(shè)新疆的同時(shí)這支部隊(duì)也保留了軍隊(duì)體制,在發(fā)展?jié)摿^大的墾區(qū)設(shè)立若干個(gè)團(tuán)場(chǎng)。“下野地”系列作品中故事發(fā)生的地點(diǎn)下野地便是特殊條件下的產(chǎn)物,是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眾多團(tuán)場(chǎng)中的一個(gè)。
作為新疆極具代表的鄉(xiāng)土文學(xué)作家,董立勃的創(chuàng)作根植于與他有千絲萬(wàn)縷聯(lián)系的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他的系列作品多以下野地為舞臺(tái),飽蘸真摯,盡情地將內(nèi)心積蓄的對(duì)于新疆土地的熱愛(ài)揮灑而出。
“下野地”是毗鄰天山北麓,隸屬于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134團(tuán)場(chǎng)”的一片區(qū)域。降水量少,氣候干旱,戈壁遍布,在未開(kāi)發(fā)前生存條件極為惡劣。“下野地,不是個(gè)村子,也不是一個(gè)鎮(zhèn),更不是一座城。它只是一片荒原。”[4]從作家根據(jù)實(shí)地情況進(jìn)行創(chuàng)作這一行為來(lái)看,能夠激發(fā)作家創(chuàng)作激情為其提供文學(xué)素材的多半是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和生活體驗(yàn)。“人都有一個(gè)根。……不管你怎么寫(xiě),寫(xiě)到最后,你肯定要寫(xiě)你回憶最深處的那個(gè)東西。那個(gè)東西,別的地方?jīng)]有,就在生你養(yǎng)你的那個(gè)地方。”[5]“下野地”農(nóng)場(chǎng)在新疆看似普遍,但作為董立勃的家鄉(xiāng)的客觀現(xiàn)實(shí),它為董立勃?dú)v經(jīng)商海浮沉、沉積人生經(jīng)歷后以游子返鄉(xiāng)身份理性反思自己的前半生提供了可能性,同時(shí)也為董立勃?jiǎng)?chuàng)作“下野地”軍墾小說(shuō),呈現(xiàn)兵團(tuán)軍墾故事提供了原型。
“下野地”系列小說(shuō)講述的是發(fā)生在以荒漠戈壁為底色的新疆建設(shè)兵團(tuán)團(tuán)場(chǎng)上的墾荒故事,這些故事不僅為讀者描繪了風(fēng)沙彌漫、戈壁遍布的惡劣環(huán)境,呈現(xiàn)了艱苦的墾荒生活,也展現(xiàn)了兵團(tuán)戰(zhàn)士不怕吃苦、拼搏向上的人格魅力,塑造了鏗鏘屹立的兵團(tuán)人形象。
“董立勃在不同的場(chǎng)合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小說(shuō)要有好故事。”[6]董立勃精通于講故事,但他卻化繁為簡(jiǎn)力求將自己的敘述簡(jiǎn)單化,從而將重心轉(zhuǎn)移到故事情節(jié)的傳奇性,以保證自己的文學(xué)作品充滿浪漫與傳奇性質(zhì)。如其代表作《白豆》,開(kāi)篇即設(shè)置懸念:“這一年的夏天,在下野地,先是有兩個(gè)男人想娶白豆當(dāng)老婆,后來(lái)又有一個(gè)男人也想娶白豆當(dāng)老婆。”[7]誰(shuí)是白豆?那兩個(gè)男人又是誰(shuí)?這種敘述手法使讀者閱讀興趣大大提升,同時(shí)也使該作品趣味橫生,可讀性增強(qiáng)。在小說(shuō)第六章《玉米地青紗帳》中的“下野地”“不再像一座兵營(yíng)”“正在變成一座大村莊”,故事達(dá)到新的高潮。白豆與馬營(yíng)長(zhǎng)結(jié)婚已成定數(shù),但就在初秋的一天晚上,白豆被黑影像老鷹捉小雞一樣地剝?nèi)チ松砩系囊路_@個(gè)黑影是誰(shuí)?白豆和馬營(yíng)長(zhǎng)還能結(jié)婚嗎?愛(ài)慕白豆的那兩個(gè)男人又該如何?無(wú)獨(dú)有偶,故事的結(jié)尾,胡鐵以暴力為手段證明了自己的清白,正當(dāng)他為了自己重獲自由欣喜若狂之時(shí),老羅的話“像一串雷,從遙遠(yuǎn)的天邊滾過(guò)來(lái)。……你還是要回到勞改隊(duì)去……你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革命罪。”[8]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難以接受現(xiàn)實(shí)的胡鐵在陽(yáng)光刺入雙眼時(shí)發(fā)出嚎叫,嚎叫化成了沙暴,“他和那場(chǎng)龍一樣卷過(guò)的沙暴一塊消失了。”[9]他會(huì)不會(huì)再回來(lái)?回來(lái)不會(huì)發(fā)生什么?小說(shuō)故事波瀾起伏、張弛相間,結(jié)局令人回味無(wú)窮,引人遐想。董立勃憑借自己嫻熟的敘述技巧不僅合理地推動(dòng)了故事情節(jié)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更使多樣、鮮明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打破常規(guī)、超越表面,加強(qiáng)了故事的戲劇性效果,體現(xiàn)其作品之“奇”。
二.屯墾戍邊中的女性
屯墾戍邊是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的重要使命。1954年,集體轉(zhuǎn)業(yè)的官兵們?yōu)榻ㄔO(shè)新疆拋灑汗水,創(chuàng)造了新政權(quán)建立以后的新輝煌。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這些兵團(tuán)戰(zhàn)士們的情感需求和對(duì)婚姻的渴望愈發(fā)地強(qiáng)烈,兵團(tuán)墾區(qū)男多女少的現(xiàn)狀使屯墾官兵對(duì)婚姻的渴求變成了嚴(yán)峻的社會(huì)問(wèn)題。為了滿足人們的需求、平衡男女比例失衡問(wèn)題并保證屯墾戍邊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央加大宣傳力度,不斷地在報(bào)紙上刊登“到新疆后可以進(jìn)俄文學(xué)校,可以當(dāng)紡織女工,當(dāng)拖拉機(jī)手”[10]之類(lèi)的新聞報(bào)道。
藍(lán)圖已繪就,正當(dāng)揚(yáng)帆起航,兵團(tuán)如愿地從河南、山東、湖南、上海等地招收了大量女兵,急迫的婚姻問(wèn)題得以解決。同時(shí)這些女兵也成為了建設(shè)新疆、屯墾戍邊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女兵不僅從事著和男人一樣的工作,她們之中有一些人甚至為了集體,無(wú)私地犧牲了個(gè)人的青春和幸福。“地里干活的,女人多,男人少。……新疆開(kāi)發(fā)了好多荒原,灑在上面的汗水,有一大半是女人的。”[11]董立勃的母親和小姨就是荒野戈壁上最早的一批女兵,她們本是山東人,但是她們?yōu)榱酥г陆ㄔO(shè),艱苦奮斗,任勞任怨。董立勃敏銳的目光觀察到了這些女性前輩的堅(jiān)韌,他在訪談中毫不吝嗇地稱(chēng)贊他的母親:“所有人類(lèi)優(yōu)秀的品質(zhì),我在我母親身上全看到了。”[12]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多以女性為主角并以她們的名字來(lái)命名小說(shuō),如《白豆》《米香》《青樹(shù)》等。董立勃關(guān)注女性為墾荒所作出的貢獻(xiàn)并“不由自主地把美好的東西通過(guò)女性表現(xiàn)出來(lái)”[13]。
作為以前輩故事為原材料,重新講述兵團(tuán)故事的“說(shuō)書(shū)人”,董立勃對(duì)兵團(tuán)墾荒生活有著充分的認(rèn)識(shí)。在以旁觀者的視角講述先輩的故事、展現(xiàn)女性墾荒經(jīng)歷的同時(shí),董立勃有意識(shí)地塑造因國(guó)家招收女性進(jìn)疆政策而來(lái)到新疆的“外來(lái)人”形象,并通過(guò)這一類(lèi)游離在兵團(tuán)的外來(lái)人的獨(dú)特眼光審視兵團(tuán)內(nèi)部建構(gòu)和兵團(tuán)文化。外來(lái)文化與兵團(tuán)文化碰撞,為客觀審視兵團(tuán)和兵團(tuán)文化提供了途徑,也為敏銳感知事物、理性呈現(xiàn)故事、多維反思?xì)v史提供了可能性。董立勃結(jié)合自身的兵團(tuán)生活體驗(yàn),力圖在其小說(shuō)中再現(xiàn)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兵團(tuán)人真實(shí)的屯墾生活,并通過(guò)知青宋蘭、支邊女兵白豆等“外來(lái)人”的故事,縱向展示了被塵封的歷史。
《白豆》問(wèn)世之后,董立勃形成了自己的敘事策略,擁有自己獨(dú)特的故事切入口,在敘述墾荒故事的同時(shí)也展示了人民真實(shí)的屯墾生活。“下野地,不是個(gè)村子……也不是一個(gè)鎮(zhèn),更不是一座城。它只是一片荒原。五十年前,下野地也有人,可很少。少得可以用荒無(wú)人煙來(lái)形容。沒(méi)有人的地方,沒(méi)有歷史。”[14]屯墾官兵響應(yīng)黨的號(hào)召,在塔克拉瑪干、古爾班通特兩大沙漠邊線上開(kāi)荒造田,貧瘠的荒土到處長(zhǎng)著不大的梭梭樹(shù),“荒野全是野草野樹(shù)。要把荒野變成莊稼地,就得先把這些草和樹(shù)摘掉。草太多,樹(shù)太密。要用刀砍,不知要砍多久。”[15]未開(kāi)發(fā)的荒地只得用“燒荒”的方式鏟除礙事的雜草,燒了荒,這樣的地依然無(wú)法種植,還叫荒地,得用專(zhuān)為開(kāi)荒發(fā)明的“坎土曼”進(jìn)行翻曬。當(dāng)時(shí)的墾荒條件有限,機(jī)械化尚未普及,荒原上的拉犁隊(duì)在沒(méi)有拖拉機(jī)的情況下,人承擔(dān)起了一切勞動(dòng)。“揀起雜草灌木的根須,用齒耙收拾出松軟平整的新田塊”[16]已經(jīng)稱(chēng)得上是女性在墾荒過(guò)程中最簡(jiǎn)單的開(kāi)荒活動(dòng),但面對(duì)需要開(kāi)墾上萬(wàn)畝良田的墾荒任務(wù),以及不惜一切修建水利工程、建立防風(fēng)固沙森林的美好展望,兵團(tuán)建設(shè)的客觀現(xiàn)實(shí)要求女性必須克服一切困難,摒棄男女意識(shí)之分,從事和男性一樣的勞動(dòng),自覺(jué)加入到開(kāi)荒建設(shè)中去。“中午的太陽(yáng)像個(gè)烈焰熊熊的火盆,把人捂在里面沒(méi)有同情地烘烤。”[17]高溫炙烤著大地,突擊性的開(kāi)荒使得午飯后二十分鐘的休息時(shí)間如金子一般寶貴。沾滿淡黃色汗斑的白襯衫用力一擰汗液就滴落下來(lái)“觸到曬焦的土地發(fā)出吱吱的聲響,并升起一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瞬即逝的霧氣。”[18]炎熱的天氣改變不了她們建設(shè)新疆的意志,她們與男性一樣憑借自己的氣力和不服輸?shù)木衽c一片廣闊無(wú)邊的荒野進(jìn)行著一場(chǎng)大廝殺。她們干著和男人一樣的活兒,像男人一樣用肩膀拉起沉重的犁頭,加入了用人力犁地的活動(dòng),她們?yōu)榱硕嗬鐜追值夭活櫱度爰绨虻睦K索,頭也不回地在未開(kāi)墾的荒地上翻出泥浪,使得荒野上的田地面積逐日增加。她們是保障墾荒戰(zhàn)士生活堅(jiān)強(qiáng)后盾,也是沖在農(nóng)業(yè)建設(shè)發(fā)展第一線的軍墾女兵。董立勃在描繪墾荒生活、訴述女性墾荒經(jīng)歷的同時(shí)也展現(xiàn)出了兵團(tuán)女兵任勞任怨、不畏艱辛,用自己的青春建設(shè)新疆的奉獻(xiàn)精神。
三.兵團(tuán)精神的呈現(xiàn)
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在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xiāng)”活動(dòng)背景下,知識(shí)青年懷著對(duì)祖國(guó)的熱愛(ài)、對(duì)新疆美好未來(lái)的憧憬,積極響應(yīng)號(hào)召來(lái)新疆支邊,其中就包含大量女青年。《米香》中的上海學(xué)生宋蘭就是其中之一。她們高唱著“祖國(guó)哪里需要我們,我們就到哪里去”[19]而來(lái)到了風(fēng)沙凜冽,條件艱苦的新疆。一些青年在兵團(tuán)精神的影響下最終選擇留在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成為了“兵團(tuán)人”。
自然環(huán)境的艱苦并未使女性屯墾開(kāi)荒、建設(shè)新疆的意識(shí)完全消弭,也未使女性為新疆發(fā)展貢獻(xiàn)自己青春的話語(yǔ)徹底沉沒(méi),她們以自己堅(jiān)毅的精神抵擋著風(fēng)雨的侵蝕,仍抱有為邊疆建設(shè)奉獻(xiàn)自我的熱忱。她們靈活運(yùn)用自己的知識(shí),改革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教授當(dāng)?shù)厝宿r(nóng)業(yè)知識(shí)。她們?cè)r(nóng)村,在戰(zhàn)勝艱苦自然條件的同時(shí)也加強(qiáng)著自己的思想建設(shè),力求將自己的力量轉(zhuǎn)化為建設(shè)新疆的一磚一瓦,這是“熱愛(ài)祖國(guó)”的體現(xiàn),更是對(duì)“無(wú)私奉獻(xiàn)”精神的弘揚(yáng)。
《靜靜的下野地》中,知識(shí)分子周青追逐愛(ài)情跟隨馮其來(lái)到了下野地這個(gè)“在地圖上找不到標(biāo)示的地方”[20],她不畏風(fēng)沙,在投身墾荒事業(yè)的同時(shí)為水渠的修建、新疆農(nóng)業(yè)技術(shù)進(jìn)步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白豆》中山東十九歲的女兵為了軍墾大渠的挖掘,不顧嚴(yán)寒冰雪,但卻被凍土石塊砸倒,以身殉職,將自己的生命奉獻(xiàn)給了新疆屯墾事業(yè)。《米香》中為了堵住被堆積的雨水沖開(kāi)的大壩水柱,會(huì)游泳的米香將個(gè)人放在國(guó)家之后,毅然跳下堤壩以身?yè)跛H说虊我脖Wo(hù)了國(guó)家的財(cái)產(chǎn)。《米香》中宋蘭為響應(yīng)號(hào)召,解決屯墾老兵的單身問(wèn)題,在復(fù)雜的思想斗爭(zhēng)之后選擇與放羊老兵老謝結(jié)婚,但她并未喪失追求個(gè)人幸福的能力,她積極進(jìn)行個(gè)人思想調(diào)整并對(duì)老謝的不合適性要求進(jìn)行反抗,這是女性意識(shí)覺(jué)醒的象征,也是女性個(gè)人與墾荒事業(yè)的高度結(jié)合的標(biāo)志,最終她與老謝成為“支邊青年嫁給放羊老兵,扎根荒野譜寫(xiě)時(shí)代愛(ài)情曲”[21]的婚姻典范。自然條件的惡劣無(wú)法消磨的是宋蘭建設(shè)邊疆的意志,“青年返城”政策出臺(tái)后,宋蘭卻更堅(jiān)定了留在邊疆的心意,“說(shuō)真的,當(dāng)年從上海走出來(lái),就沒(méi)有再想著回去。”[22]她將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獻(xiàn)給了邊疆的發(fā)展建設(shè),真正發(fā)揚(yáng)了“無(wú)私奉獻(xiàn)”的兵團(tuán)精神!
沙漠、草灘、戈壁、沼澤地,棲息于此的“兵團(tuán)人”以卓絕的精神應(yīng)對(duì)大自然的挑戰(zhàn)。一畝畝被開(kāi)墾過(guò)的良田、一條條通達(dá)的溝渠、一捧捧浸潤(rùn)著汗水的糧食、一寸寸被他們守護(hù)著的土地,這就是對(duì)“開(kāi)拓進(jìn)取、艱苦奮斗”精神的動(dòng)人書(shū)寫(xiě)。她們用自己的歲月與生命譜寫(xiě)建設(shè)新疆的動(dòng)人故事,在熾熱的燃燒過(guò)自己之后達(dá)到個(gè)人生命的升華,這也是對(duì)新疆精神、兵團(tuán)精神最好的闡釋。
董立勃以“說(shuō)書(shū)人”身份解讀兵團(tuán),客觀敘述歷史,并通過(guò)可貴的自省精神,以豐富的題材、各式各樣的人物故事為我們展現(xiàn)了塵封多年的兵團(tuán)歷史,也找尋到了那些失去的歲月。“下野地”軍墾小說(shuō)中的眾多女性,在從“外來(lái)人”到“兵團(tuán)人”身份的轉(zhuǎn)變過(guò)程中展現(xiàn)了她們“熱愛(ài)祖國(guó)、無(wú)私奉獻(xiàn)、艱苦奮斗、開(kāi)拓進(jìn)取”的兵團(tuán)精神。探討董立勃軍墾小說(shuō)中兵團(tuán)精神的呈現(xiàn),也是對(duì)“文化潤(rùn)疆”的有益探索,更是對(duì)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的歷史詮釋。
參考文獻(xiàn)
[1]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新聞辦公室編.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M].烏魯木齊: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出版社,2009:21.
[2][3]馬大正.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發(fā)展的歷程[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12.
[4][14]董立勃.騷動(dòng)的下野地[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1、1.
[5][6]李從云.論董立勃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文體[J].小說(shuō)評(píng)論,2006(05):35-39.
[7][8][9]董立勃.白豆[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3:1、280、284.
[10]盧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18.
[11]董立勃,李海諾.對(duì)話作家董立勃[J].西部,2006(12):94-96.
[12][13]李從云,董立勃.我相信命運(yùn)的力量——董立勃訪談錄[J].小說(shuō)評(píng)論,2006(05):24-31.
[15][16][17][18]董立勃著.遠(yuǎn)荒[M].濟(jì)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26、28、93、94.
[19][21][22]董立勃.米香[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4:41、124、283.
[20]董立勃著.靜靜的下野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96.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級(jí)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訓(xùn)練項(xiàng)目《文化潤(rùn)疆視野下新疆鄉(xiāng)土文學(xué)研究——以董立勃等作家為例》(202110757 061)
(作者單位:塔里木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