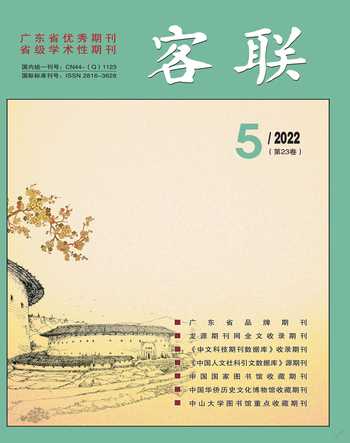以人民為中心: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邏輯進路與實踐
劉振源
摘 要:革命時期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涉及宗教、民族、外交等多方面關系,情況復雜。如何對寺院土地所有權進行改造,是土地改革中一個特殊問題。基于認識和實踐,黨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以人民為中心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根據革命實際需要,調整和完善寺院土地政策,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改造道路。回溯黨的寺院土地政策的演進,能汲取經驗啟示,為當前實踐提供借鑒。
關鍵詞:寺院土地政策;歷史回溯;演進邏輯;以人民為中心
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是中國革命的內容之一。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相較于地主土地所有權的改造,具有特殊性,涉及宗教、民族、外交等多方面關系,對其研究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學術界對黨在革命時期各個階段寺院土地所有權的具體改造政策進行了研究,學者們的研究為我們理清了黨在革命時期各個階段的寺院土地政策的背景及發展脈絡,使得深入探討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制定和調整的邏輯成為可能本文希望對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進行綜述,以探尋其制定和調整的邏輯,總結其經驗啟示。
一、對寺院土地所有權進行改造的必然性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1],這句話鮮明指出了宗教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中國封建時代,宗教往往能獲得封建政權的支持,各類寺院借此通過各種手段,占有大量耕地,乃至近代這種現象仍然存在。如民國4年前,江西玉山縣瀛山寺原有田租1100余石[2];類似的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也普遍存在,如“四川藏族地區德格八邦寺,土地多達2000多畝。”[3]。
近代西方教會利用傳教特權,通過租買、教徒捐獻、巧取豪奪等方式,各類教堂在中國各地也占有大量田地。如1900年前的二十五年,僅僅河套地區,洋教堂所霸占的土地面積達到四、五百頃以上[4];1899年在河北獻縣,天主教堂占有土地2184畝[5]。
綜上,寺院土地所有權主要包含了兩部分,國內原有寺院土地所有權和西方教會土地所有權。
中國的寺院土地所有權在表現形式上與地主土地所有權有所不同,但是從本質上來看兩者沒有區別,都是封建土地剝削制度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寺院占有田地之后,僧侶直接參與耕作的田地所占比例較小,大部分田地被用來出租進行封建剝削。如玉山縣瀛山寺每年光田租收入就有1100余石[6];德格八邦寺約有400戶科巴(農奴)為其耕種[7];近代蒙古地區喇嘛教寺廟也普遍存在“雇工種地、雇工放牧”[8]的現象。另一方面,寺院除了出租田地進行封建剝削,還利用租佃關系,時常向佃農攤派勞役,甚至放高利貸成為解放前四川藏區許多寺院重要的經濟來源[9],可見其對農民或農奴的剝削和壓榨,在手段和性質上,跟普通地主沒有差別,這充分說明近代中國的寺院土地所有權具有封建剝削性。
不同于國內原有寺院主要靠統治者封賞、信徒捐贈來獲得土地,近代西方教會在中國租買田地的權利,來自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誕生之時便帶有濃厚的殖民色彩。西方教會在中國獲得田地的過程,同樣充斥著殖民者的橫征暴斂,巧取豪奪取代了正常的租買。如寧夏教區主教王守禮(C.Van Malckebeke,比利時人)便在著作中記載,1930年在華購置荒地,普通每畝只給價一元[10]。這現象在近代中國各地多有發生,傳教士及不法教徒強占土地,成為近代各地發生“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與國內原有寺院以封建剝削為主要目的不同,近代西方教會占有田地,不僅僅利用租佃關系剝削教民,還以此為根據地,開展殖民活動。“凡是教堂的佃戶都得信奉天主教”[11]這一句話,揭露了西方教會利用租佃關系開展文化侵略的本質。這種文化侵略危害極大,導致了部分教民“知有教堂,而不知有民族國家,知有羅馬教皇,而不知有中央政府”[12]。由此可見,對近代西方教會在中國各地所占有的田地進行改造,不僅具有反封建性,還包含著反侵略因素,也是革命時期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內容之一。
二、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演進的歷史回溯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大宗教在國內都有不少信眾。在近代社會生活中,宗教影響著很多民眾的日常生活,在部分少數民族中影響力較大,信教群眾較多,因此對國內原有寺院土地所有權進行改造,事先要考慮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問題;另一方面,深入內地活動的西方教會,有著帝國主義勢力撐腰,對其占有的土地進行改造,必然要建立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基礎上。
綜上,相較于地主土地所有權,近代中國寺院土地所有權具有其特殊性,情況較為復雜,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認識和改造,伴隨著革命實踐發展變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經歷了一個發展和提升的過程。
(一)建黨初期及國民大革命時期(1921年-1927年)
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宗教及宗教問題的認識,還處于深化過程中。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宗教總體上持強烈批判的傾向,揭露了西方教會是侵略者的幫兇和馬前卒的本質,但對寺院土地所有權問題鮮有提及。1923年5月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及了“沒收寺廟土地將其無償交給農民”[13],但這一時期,黨的當時工作主要聚焦工人運動上,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未成為黨的實踐主張。
農民運動是國民大革命重要組成部分,但國民大革命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形式來開展的,農民運動的斗爭策略要考慮到統一戰線的團結,在這時期的農民運動是以“減租減息”和“限制田租”為主要斗爭目標。隨著農民運動的發展和革命的深入,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問題的認識不斷地深入,大革命后期召開的黨的五大通過了“土地問題議決案”,指出了“然寺廟、祠堂等所屬之地,占有耕地之數目,亦實有可觀。”進而提出了“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及農業公司的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14]。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1937年)
土地改革是土地革命戰爭的重要內容,伴隨著紅軍軍事斗爭的勝利,“沒收寺廟、教堂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15]的主張在蘇區得到執行。在執行過程中,一方面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是“以不妨礙他們宗教情感為原則”[16]采取謹慎靈活的方式進行的;另一方面改造寺院土地所有權與改造部分宗教從業者同時并舉,在消滅寺院土地所有權的封建剝削屬性同時,也將部分宗教從業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土地革命戰爭的后期,紅軍在長征途中經過了不少少數民族聚居區,這些少數民族地區的宗教信仰情況比蘇區,更為特殊和敏感。因應形勢的變化,黨也對寺院土地政策進行了及時的調整,如紅軍在康北建立的波巴自治政權頒布的《土地暫行條例》規定:“喇嘛寺的廟地不沒收,可以租給波巴人民耕種,但須減輕地租”[17]。長征時期黨在少數民族聚集區的寺院土地政策,反映了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問題認識的深化,為后面在少數民族聚居區進行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積累了實踐經驗。
(三)全面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945年)
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抗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推動者。為了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社會各階層抗戰,黨對土地政策進行了調整,在此背景下,黨的寺院土地政策也進行了調整,政策更為靈活,如1942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決定的附件》中關于“特殊土地”的處理,就規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變動”[18]。對于西方教會土地問題,黨也制定了新政策,1941年制定的《晉冀魯豫邊區土地使用暫行條例》就規定:“外國宣教士以私人購置或捐募之土地,改為有關教堂或教會學校所公有”、“天主教和耶穌會經依法取得所有權之土地有契約證明者,為教會所公有”[19]。
(四)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1949年)
為了支援人民解放戰爭和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完成,黨及時對土地政策進行調整,其中包括對寺院土地政策的調整和完善。1947年9月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了“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20],明確了對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的目標。但是由于寺院土地所有權問題,涉及民族、宗教、外交問題,因此對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各地的新生人民政權在黨中央的政策指導下,考慮信教群眾的宗教情感以及宗教從業者的生計問題,結合當時當地實際情況,秉持謹慎的態度,采取了多種改造形式,來推動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
因改造條件相對成熟,漢族地區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在解放戰爭期間就基本完成了。對內蒙古、西藏等民族地區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黨和各民族地區人民政府采取了“慎重穩進”的改造方針,根據各民族地區實際的情況和革命的發展形勢,有先有后,逐步開展改造工作。1947年10月,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和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制定的《內蒙古土地制定改革法令》便規定:“廢除一切舊王公貴族、地主、喇嘛寺院等占有的土地所有權”[21],而藏區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到1958年才徹底完成。對于西方教會土地所有權的改造,各解放區根據當地教會獲得土地途徑是否合法等具體情況及與教會所屬國外交情況,結合黨當時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有的如陜甘寧邊區“用公債合法征購”;有的如太行區“對于教堂像對于地主一樣地清算了”;部分新解放區由于改造條件不足,對教會土地所有權的改造采取了“暫停土改,實行減租減息”,為建國后教會土地所有權改造最終完成做準備[22]。
三、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演進邏輯
(一)馬克思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演進的核心立場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體現了黨在寺院土地所有權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在革命時期,中國革命形勢不斷發展變化,黨的寺院土地政策也隨之不斷調整完善,但是這種調整和完善是改造方式、手法的調整和完善,并不是目標的調整,實現對所有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始終是黨的寺院土地政策的目標,即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看法和政策,始終貫徹和執行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基本立場。
(二)中國革命的現實需要: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演進的直接原因
通過對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的綜述,我們可以看到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在不同階段其內容是有所差別,是一個不斷調整和完善的演進過程。這種動態演進,不管是長征途中黨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寺院土地政策的調整,還是全面抗戰時期黨因應抗日統一戰線建設的需要而進行寺院土地政策的調整,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當地革命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是推動了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不斷演進的直接原因。
(三)實踐和認識的深化: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演進的內在動力
黨對中國近代寺院土地所有權最初的認識是來自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蘇俄革命經驗等的間接認識。隨著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的深入,黨對中國近代寺院土地所有權復雜性、特殊性有了直接認識,進而推動了革命實踐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黨對中國近代寺院土地所有權的科學認識。正是基于實踐和認識的深化,推動了黨將認識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實現創造性轉化,開辟了中國特色的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道路。
(四)以人民為中心: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演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從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來看,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目標是實現對寺院所有權的改造,一方面消滅國內寺院土地所有權,另一方面解決西方教會占有土地的問題清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從根本上維護了人民利益。從政策調整的演進邏輯來看,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的演進結合了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長征時期的調整、抗戰時期的調整、解放戰爭時期的調整,無不以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為導向。從政策執行的方式來看,革命時期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采取相對溫和、靈活、謹慎地政策,考慮民族間的差異,照顧了信教群眾的情感,避免了改造運動給社會帶來的強烈沖擊,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四、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演進的經驗啟示
從實踐結果來看,革命時期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是成功的,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又能夠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具有中國特色,為今天正確認識和處理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帶來以下啟示。
第一,政治地看問題。講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突出的特點和優勢,革命時期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正是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出發,從政治上看待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的必然性,從政治上分析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的特殊性,從政治上處理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的復雜性,既正確地把握了寺院土地政策的政治方向,又注意到寺院土地所有權問題改造過程中的政治影響,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應用典范。
第二,全局地看問題。一方面,革命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兩對矛盾相互交織在一起,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特點,它們的存在和發展規定和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這要求黨在不同時期工作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對寺院土地政策進行相應的調整;另一方面,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不能簡單地、孤立地看成宗教問題,還要看到其背后,牽涉到民族、外交等問題,要全面地對其進行分析,結合其他工作來開展。故而黨在革命時期不同階段制定寺院土地政策時,既要將其置于中國革命的整個大局之中,又要根據革命工作重心的發展變化來制定相應的政策,從而使之成為中國革命的推動者而非阻礙者。時至今日,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置于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大局中來解決,全局地看問題,仍然是解決此類問題的必然途徑。
第三,發展地看問題。任何事物都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革命時期中國革命的形勢呈現的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動態,這決定了黨制定的革命政策也要隨之進行動態調整,用發展地眼光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僵化思想,墨守成規,這是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
第四,實踐地看問題。實踐是認識的來源,也是認識深化的重要途徑。正是通過不斷深入的革命實踐,黨對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的認識不斷深化,從間接認識到直接認識,最終形成對其科學的認識,為推動實踐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認識的基礎,正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
第五,革命時期對寺院土地所有權的改造,面臨著錯綜復雜國內外形勢,困難重重,但是最終能夠勝利完成,離不開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推動,人民是革命時期對寺院土地所有權改造的最大推動力。而人民之所以支持革命時期黨的寺院土地政策,關鍵在于這些政策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這些政策體現了黨的人民利益至上觀。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我們的改革和發展,面臨著新形勢,迎接新挑戰,唯有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方能助力我們取得新勝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汪光華.民國時期江西寺產嬗變的研究[J].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3(31):26-33.
[3]谷千.民主改革前四川藏傳佛教的寺廟經濟[J].西藏研究.1998(2):85-87.
[4]戴學稷.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爾多斯等地的罪惡活動—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一個實例[J].歷史研究.1964(5-6):67-96.
[5]王中茂.近代西方教會在華購置地產的法律依據及特點[J].世界宗教研究.2004(1):69-76.
[6]汪光華.民國時期江西寺產嬗變的研究[J].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3(1): 26-33.
[7]谷千.民主改革前四川藏傳佛教的寺廟經濟[J].西藏研究.1998(2):85-87.
[8]湯曉方.論近代蒙古地區喇嘛教的寺廟經濟[J].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1):55-60.
[9]谷千.民主改革前四川藏傳佛教的寺廟經濟[J].西藏研究.1998(2):85-87.
[10]戴學稷.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爾多斯等地的罪惡活動—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一個實例[J].歷史研究. 1964(5-6):67-96.
[11]同上
[12]同上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1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7年)[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15]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0年)[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16]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 (下冊)[M].南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17]郎維偉,周錫銀.紅軍長征與藏區現代宗教、土地等法規的誕生[J].中國藏學.2006(3):65-71.
[18]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年)[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19]編寫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文獻選編(1927-1937年)[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
[20]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6-1947年)[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21]哈斯木仁.解放戰爭時期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土地政策與土地改革[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20-25.
[22]李傳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待教會地產的態度和政策[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3):10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