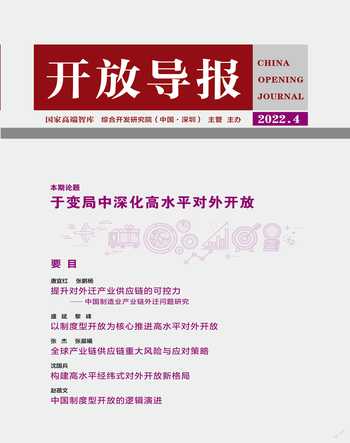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盛斌 黎峰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開放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面對以“邊境內”措施規制融合為特征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中國的對外開放重點已由強調市場準入的市場型開放,轉變為重視國內制度改革創新的制度型開放。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有利于深化國內市場化改革,增強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參與全球經貿新規則制定。中國應積極參與高標準經貿協定與談判,推進貿易與投資自主創新制度改革,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制度集成創新建設,積極參與全球經貿治理,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關鍵詞] 制度型開放? ?國際經貿規則? ? 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圖分類號]? F125.1?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4-6623(2022)04-0015-06
[基金項目]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全球經濟治理、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與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研究(20JJD790003);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自主選題項目:全球價值鏈背景下國際經濟規則的重構及中國的角色。
[作者簡介] 盛斌,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國際經濟理論與政策、國際貿易、國際政治經濟學、區域經濟合作;黎峰,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全球價值鏈分工與中國開放型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快速增長,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開放型經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之處。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美英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全球范圍內掀起逆全球化浪潮,以對華貿易摩擦和技術封鎖打壓中國技術創新,以國際經貿規則重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邊緣化中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要求中國加快開放型經濟轉型,進一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加快國內制度建設,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型開放轉變。
一、從市場型開放到制度型開放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新中國第一輪對外開放呈現以下幾個特征:一是“飛地”經濟,即通過打造各類經濟特區、開發區等開放載體,實施稅收、土地優惠,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產業集聚發展;二是單向流動,即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為載體,資本、人才、技術、管理等高級生產要素向中國沿海地區集聚,大力承接跨國公司的產業梯度轉移,發展以“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三是市場開放,即在GATT/WTO規則框架下,大幅降低關稅及各類非關稅壁壘,提升市場準入水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演變,支撐傳統對外開放模式的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其中最為關鍵的當屬國內體制機制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之間的“制度沖突”。
第一代國際經貿規則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憑借著超強的綜合國力構建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組建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三大國際組織,從而建立起以其為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其中,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以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成為構建戰后國際經貿規則的主體。第一代國際經貿規則主要強調市場型開放,體現出邊界措施自由化與便利化的突出特征,如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簡化海關程序、提高貿易政策透明度、對商業存在形式的服務貿易給予投資市場準入并實施國民待遇。
在以邊界措施自由化為特征的國際經貿規則條件下,中國不斷加快國內市場化進程以及貿易自由化進程。1994年,中國頒布《對外貿易法》,強調透明度及非歧視原則,并促使貿易政策取向由貿易保護向“貿易中性”轉變。2000年7月,中國修訂《海關法》,并逐步在各行業和部門展開實質性關稅削減。根據世界銀行和WTO的統計,中國的平均實施關稅水平由1992年的43%降至2001年的15.6%,入世后到2005年進一步下降為9.7%①。在非關稅壁壘方面,中國逐步取消了進口調節稅、出口補貼、進口配額以及進口替代等措施,簡化了進口許可證的管理流程及手續。在技術標準、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等管理措施上,到2005年實現32%的國內標準基于國際標準制定,44%的標準依照國際標準進行修訂,同時廢除12%與國際標準不符的國內標準②。在投資自由化方面,中國逐步由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資管理體系,轉化為市場經濟體制下投資主體多元化、資金來源多渠道、投資形式多樣化、投資范圍和領域擴大化的新模式。同時,逐步取消了對外匯平衡要求、本地含量要求和出口績效要求等限制。
中國的市場型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中國全面深度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開放型經濟也隨之出現井噴式增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等發達國家積極鼓吹和倡導以“邊境內”措施及規制融合為特征的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試圖以公平貿易為由強化自身競爭力,并推動發展中國家實施有利于發達國家擴張全球價值鏈的國內規制改革。為此,美國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③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談判,進而將北美自由貿易區升級為標準更高的《美加墨貿易協定》(USMCA)。在發達國家的推動下,“邊境內”措施規制融合已成為當前區域與雙邊國際經貿協定與談判的核心議題,也將成為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的核心內容。
與市場準入的邊境措施自由化相比,“邊境內”措施規制融合更加強調標準的統一、競爭規則及市場監管的一致。具體而言,標準一致化包括工業技術標準與動植物衛生檢疫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環境及勞工標準。競爭一致化包括投資管理體制、競爭政策、政府采購、國有企業等。監管一致化包括法治、反腐敗以及各國監管協同。發達國家之所以強調“邊境內”措施的規制融合,一方面是因為在“全球生產、全球銷售”的新型國際分工生產模式下,東道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競爭政策、環境及勞工標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逐漸成為產品成本差別的主要來源,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需要各國在標準、規則及監管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在標準制定、公平競爭、市場監管等方面擁有一整套更加完善的制度體系,一旦其國內制度安排升級成為各國一致認同的國際經貿規則,毫無疑問將獲得制度層面的“先發優勢”。
二、制度型開放為什么重要?
加快制度型開放,是黨中央、國務院應對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適時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三個主要支柱,其中第一個支柱就是制度型開放。2015年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涉及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構建外貿可持續發展新機制、建設若干自由貿易試驗園區等制度型開放相關內容。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在2020年11月召開的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創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那么,制度型開放為何顯得如此重要?
1. 制度型開放是國內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需要
經過40多年來不斷的改革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著一些“深水區”改革,如進一步加快轉變與優化政府職能、消除區域間市場壁壘、破除行政與行業壟斷等問題。制度型開放無疑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又一次“以開放倒逼改革”的歷史契機。如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取代外資審批制度,對國有企業及政府采購的競爭中性要求,將有利于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推動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此外,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對產權保護國民待遇、工業技術標準一致、市場競爭及監管規則一致的要求,將有效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2. 制度型開放是增創國際合作與競爭新優勢的需要
在市場型開放階段,中國充分發揮低成本優勢及政策激勵作用,通過促進國外高級生產要素與國內低成本要素的充分結合,進而釋放出巨大的生產能力和出口規模。然而,隨著國內經濟快速發展及要素成本不斷提高,加之后崛起的發展中經濟體的低成本競爭,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生產成本優勢難以維系,急需從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完善的供應鏈體系等方面著手,增強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在貿易自由化與便利化、信息公開透明、投資者權益保護、公平競爭等方面的高標準,將有利于加快營造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透明高效的政務環境、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和合作共贏的人文環境,創造新型制度性紅利,降低交易成本、商務成本等制度性成本。
3. 制度型開放是全球經貿新規則競爭的需要
以深層經濟制度融合為特征的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已逐漸成為高水平貿易與投資協定及談判的特征。以被譽為“21世紀的貿易協定”的CPTPP為例,它為以全球價值鏈為基礎的新商業規則與紀律設立了一個更高的基準,如“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方式的市場準入、投資領域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中立而透明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特別是為應對創新、供應鏈貿易、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小企業等新挑戰與新議題,引入了擴展的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環境、勞動、反腐敗等“規制融合”類的新條款與規則,以促進成員之間國內監管的協調與一致性。中國積極主動對接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才有可能參與高標準FTAs網絡建設,將高水平開放與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進而在國際經貿規則乃至全球經濟治理中反映發展中國家的愿望和訴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宣布,中國將積極推進加入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表明了中國通過深化制度型開放參與全球經貿新規則競爭的決心。
三、如何推進制度型開放?
面對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及“邊境內”措施規制融合要求,中國應從三個方面著手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一是積極參與并簽署高標準的雙邊及多邊國際經貿協定,通過對其中高標準條款的承諾履行倒逼國內制度改革;二是以國內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建設為抓手,對照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與國內體制機制的“制度沖突”,有針對性地進行體制機制創新;三是在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重點領域加緊制定統一規則,在國際經貿合作中大力實施并積極推廣“中國標準”,為全球經濟治理及國際經貿新規則提供“中國方案”。
(一)積極參與高標準經貿協定與談判
近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區域、雙邊、諸邊及多邊經貿談判。根據WTO官網統計數據,截至2022年3月,中國簽署并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共19個,其中與發達國家及亞太新興經濟體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及升級版有8個,包括:東盟、瑞士、冰島、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韓國。此外,中國成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并已生效。中國還與挪威、以色列等發達國家開展雙邊自由貿易談判,與韓國開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升級版洽談。同時,中國積極申請加入CPTPP和DEPA。中國可借助高標準FTAs和BITs的談判、簽署及履約,不斷推進國內制度型開放。
與傳統WTO框架下的國際經貿協定相比,高標準國際經貿協定的簽署及生效,對國內體制機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利于加快制度型開放步伐。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例,RCEP以建成全面、現代、普惠和高質量的自貿協定為目標,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自然人流動等領域的自由化承諾,形成了區域內更加透明、開放、包容的經貿規則。從內容來看,RCEP不僅覆蓋了與市場準入和開放有關的“邊界”措施,還納入與“邊界內”措施相關的諸多新規則,包括投資、知識產權、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中小企業與經濟技術合作等議題。這些規則絕大多數超越了WTO管轄范疇,體現了規制融合的要求。加入RCEP并履行協定承諾,將倒逼中國加快相關領域的制度型開放步伐,如遵照協定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優化創新法治環境;競爭政策條款的實施將不斷改善市場競爭環境,充分發揮市場競爭要素優化配置的關鍵作用,規范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程序。
(二)推進貿易與投資自主創新制度改革
為更好應對以“邊境內”措施規制融合為特征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中國以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信息公開透明、程序簡化公正等領域為重點,積極推進國內體制機制自主創新改革,以立法形式對制度創新成果加以鞏固,2019年3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我國在《外商投資法》制定之前沒有一部統一管理外資的法律,而是以改革開放之初分別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三部法律并輔以其他國務院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來進行管轄。后者不但體系分散,而且由于制定時間較早,未能反映出國際上關于外資政策變化的新理念、新趨勢與新模式,與全面深化改革戰略、高水平對外開放目標以及市場主體期待存在較大差距。
鑒于此,《外商投資法》整合了我國目前關于外商投資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形成一套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包括投資定義、投資促進、投資保護、投資管理、法律責任等,結束了我國對外商投資與企業的“碎片化”管理。同時,《外商投資法》吸收了國際目前通行的先進外資政策理念與模式,按照內外資一致原則,實現了更高水平的投資權益保護與投資自由化,亮點包括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以及負面清單制度;編制和公布外商投資指引;建立健全外商投資服務體系;保障外商企業平等參與標準制定和政府采購活動;保護外商知識產權(尤其是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建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等。此外,《外商投資法》強調了各級政府和部門踐行守約的“政策誠信”,包括制定涉及外商投資的規范性文件必須符合規定;執行中不得減損外商的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必須履行向外商投資企業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以及訂立的各類合同。
然而,我國的體制機制創新及制度型開放仍有待進一步深入。仍以《外商投資法》為例,對外商投資實施的準入特別管理措施(即“負面清單”)需要隨后發布并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動態調整;需要以《外商投資法》為依據,對現有涉及外商投資的各級政府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進行清理,根據實踐需要做出必要修訂甚至廢止。此外,《外商投資法》實施中與其他法律法規如《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還有一個恰當銜接問題,需要適時跟進。
(三)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制度集成創新建設
面對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國際經貿規則的重構,我國于2013年開始,先后分6批在21個省市設立了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成為改革開放前沿和第一方陣。就功能定位而言,自貿試驗區/自貿港的對外功能是集商貿物流、高端制造、現代服務于一體的綜合型對外開放平臺,以及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的離岸金融市場(中心);對內功能則是充當國內改革“試驗田”與制度創新示范區,以及大力培育新產業、新模式和新動能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心。
自貿試驗區/自貿港以深化國內體制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目標,對照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有針對性地推進各項體制機制改革,形成了一整套自主和集成制度創新體系。一是開放公平、安全高效的市場準入管理制度系統,主要包括: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核心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以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為核心的貿易便利化管理制度;以自由貿易(FT)賬戶分賬核算體系為核心的金融創新及監管制度;國際航運開放監管服務。二是以“放管服”(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重心的政府職能轉變制度創新體系,包括以先照后證、多證合一、審批注冊單一窗口、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極簡審批等為特征的現代商事登記制度;以信用風險分類為依托的市場監管制度、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經營異常名錄和嚴重違法企業名單制度、“雙隨機一公開”抽查制度等為重點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以市場主體首負責任為機制的綜合監管制度等。三是與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相適應的法律保障制度,包括調整國家層面的相關法律法規,如頒行《外商投資法》;建立國際商事仲裁中心、知識產權法庭等形式的地方性司法保障及權益保護制度;發展創新人才服務體系和國際人才流動通行制度,如人才“綠卡”制度、“雙創”特區等。
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我國自貿試驗區/自貿港仍需進一步加大體制機制創新力度,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核心進行壓力測試與風險測試,創造出更多可復制推廣的經驗及最佳實踐案例。首先,建立與實施高標準和法治化的市場監管體制。應進一步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建立健全公平競爭制度,確保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享受平等待遇;政府采購應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加強和優化《反壟斷執法》;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加大知識產權侵權懲罰力度;保障投資者權益,加強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等。其次,積極加快服務業對外開放。應大力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取消服務供應商數量限制、服務交易或資產總金額限制、服務業務地域限制、雇傭人數限制、特定類型的法律實體或合營企業限制;建立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快金融、電信、專業服務等市場開放與可競爭性;進一步促進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大力發展便利數字貿易與電子商務,推動跨境數據流動;促進自然人流動,優先給予高級商務人士及其配偶、特定高技能專業人士和技術人員、投資者以及提供售后服務、租賃服務、安裝與維修服務的商務訪客簽證和流動性便利等。再次,通過立法賦予自貿區/港更大改革自主權。支持自貿區行使地方立法權,如制定與實施自由貿易港法;建立司法保障和權益保護制度;促進訴訟、仲裁、調解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建立多元化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等。
(四)積極參與全球經貿治理
近年來,在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推進國內制度建設的同時,中國基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愿望和訴求,以更加主動與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中國作為東道主在2016年杭州峰會上首次將貿易與投資議題引入G20議程,并達成全球首份《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為營造開放、透明、可持續的全球投資政策環境制定了九項非約束性原則,成為指導成員國制定投資政策的綱領性多邊文件,為未來達成多邊投資協定或制定全球投資規則邁出了關鍵性一步。中國將“互聯互通”元素注入APEC合作框架,倡導以APEC為基礎推進亞太自貿區(FTAAP)建設,實現亞太區域經貿規則的整合。2014年11月的APEC北京峰會通過了《APEC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和《APEC開展基礎設施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實施路線圖》,使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成為APEC框架下合作的優先領域。此外,中國支持東盟十國發起的RCEP談判,推動協定在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政府采購、電子商務等規則領域較WTO標準的廣度與深度有所提高,并在經濟技術合作、中小企業、發展中成員差別與特殊待遇等領域體現了包容性發展的特色,為探索建立高水平開放共贏的FTA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嘗試。中國發起并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金磚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上合組織銀行,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新型制度性公共產品。以上事實表明,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已充分認識到制定與把握國際經貿規則是一國在國際社會中“軟實力”與“巧實力”的體現,正日益加快由國際規則接受者到國際規則參與者的歷史性轉變。
當前,數字貿易規則是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一個重要議題。美日等發達國家主張跨境數據自由流動,歐盟倡導以保障安全為前提的跨境數據流動。在電子傳輸永久免征關稅議題上,美國、歐盟、日本等多數發達經濟體認為,WTO現有的關稅削減承諾已為依托有形介質為載體的實物貿易(如CD存儲器)提供了自由貿易的規制框架,以數字形式傳輸的數字內容產品應享有同等的自由貿易權利,因此主張對通過電子方式傳輸的內容給予免征關稅的非歧視待遇。中國應重點挑選一些比較優勢明顯、實施基礎較好且具有一定國際影響的標準、規則領域深入推進,為全球經濟治理及國際經貿新規則提供“中國方案”。中國可以跨境電子商務的物流服務、數字支付服務、5G標準、5G產品和服務等領域為重點,在加快國內標準及規制的制定與完善的基礎上,積極借助“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加快推進以貨物訂購為核心、以數字服務為重點的“中國版”數字經濟國際規則體系向周邊國家或地區、新興市場、發展中大國和部分發達經濟體輸出。同時,根據貿易伙伴國數字基礎設施水平、國內監管規則完備程度以及數字產業鏈發展程度采取不同的推進思路。選擇數字經濟基礎較好并且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的經濟體達成“中國版”數字經濟協定。此外,應鞏固并發揮APEC成員經濟體“最佳實踐”模式,通過“非約束性原則”,實施“探路者行動”,為APEC經濟體提供數字基礎設施能力建設援助和技術支持,推動中國5G技術率先在亞太地區實現規則、技術、標準的輸出,為全球數字貿易新規則提供“中國方案”。
[參考文獻]
[1] 裴長洪,彭磊.中國開放型經濟治理體系的建立與完善[J].改革,2021(4):1-14.
[2] 盛斌,高疆.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從規則接受者到規則參與者[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5):18-27.
[3] 盛斌,黎峰.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在哪里?[J].國際經濟評論,2017(1):129-140+7.
[4] 張二震,戴翔.更高水平開放的內涵、邏輯及路徑[J].開放導報,2021(1):7-14.
Advance High-level Opening-up with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s the Core
Sheng Bin,Li Fe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0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open economy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face of high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in-border” measures and regulations, Chinas opening-up focus has shifted from market-based opening-up with market access to institution-based opening-up with emphasis on domestic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Accelerating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will help deepen domestic market-oriented reform, enhance new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high-standard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and negotiations,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ystem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e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free trade por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governance, and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with institution-oriented opening-up as the cor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Ope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High-level Opening-up
(收稿日期:2022-06-21? 責任編輯:羅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