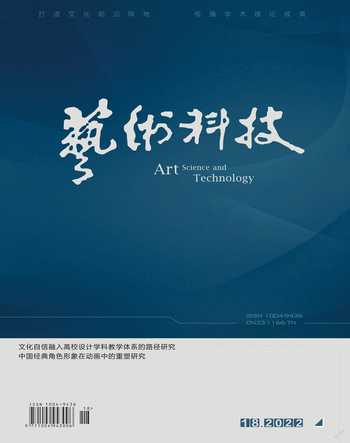論《激情》中的危機敘事
摘要:當代英國著名女作家珍妮特·溫特森的小說《激情》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小說以拿破侖戰爭為歷史背景,講述了主人公亨利和維拉內拉逐漸理解愛情和自我的故事。在此過程中,溫特森解構了以重要歷史人物和戰爭為代表的宏大敘事,將筆觸集中于主人公作為普通人所經歷的起伏,以此突出戰爭的殘酷和主人公的重生。文章通過分析小說中體現出的戰爭危機、自我身份危機、情愛危機以及它們與小說中兩位主人公成長之間的關聯,論證小說中的后現代主義色彩,為人們如何走出生存困境、獲得自由提供啟示。
關鍵詞:珍妮特·溫特森;《激情》;危機;敘事
中圖分類號:I561.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18-0-03
珍妮特·溫特森是當代英國著名女作家,她鐘情于愛情、性別、自我身份等主題,作品既反映社會現實,又體現自身的理想追求,獲獎無數。其作品語言簡練而優美,意義深刻且豐富,一個個奇妙的故事充分體現了她對語言非凡的掌控力。對希臘神話、童話故事、《圣經》等西方經典文學作品的改寫及重組,使她的作品充滿了想象力和無限的解讀空間。
《激情》出版于1987年,采取回憶與現實穿插、歷史與虛構結合的非線性敘事策略,充滿了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小說以19世紀初拿破侖征戰為歷史背景,以“激情”為大框架統一多個獨立章節。第一章節“皇帝”以亨利的口吻講述了自己背井離鄉,狂熱追隨拿破侖四處打仗的故事;第二章節“黑桃皇后”以維拉內拉的身份記錄了自己在威尼斯的“自由”生活;第三章節“零度寒天”再次以亨利的口吻記述他與維拉內拉相遇并逃離戰場,歷經千難萬險回到威尼斯的故事;第四章節“巖石”是亨利和維拉內拉的復調敘述:亨利為了愛情殺死維拉內拉的丈夫,后被囚至瘋人院且拒絕出逃,而維拉內拉拒絕與亨利的婚姻,生下亨利的女兒后,仍選擇在水上漂泊度日。
基于此,本文試圖分析小說中的危機敘事以及它們與小說中兩位主人公成長之間的關聯。通過文本細讀,筆者認為《激情》中的危機敘事分為三方面,一是戰爭危機,二是自我身份危機,三是情愛危機。在溫特森筆下,深度刻畫了各種形態的“戰爭人性”,她將筆觸集中于主人公作為普通人所經歷的起伏和傷害,表達了人類為維護自身生存的精神訴求。最終,兩人走出困境,走向成熟。
1 《激情》中的戰爭危機
溫特森解構了法蘭西第一帝國締造者——拿破侖·波拿巴的形象,以此突出戰爭的殘酷及其帶給人們的傷害。在《激情》中,拿破侖不再是擁有輝煌戰績的英雄,而是自大虛榮的偏執狂。溫特森通過拿破侖因身材矮小,鐘愛并重用矮小的仆人和高大的馬匹這一事實,諷刺了拿破侖的虛榮心。同時,拿破侖對雞肉有著近乎瘋狂的偏執,他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但也是一個徹底受控于食欲的瘋子,廚房里“到處都是被拔光了毛的雞”[1]。這一戲劇化的場景和拿破侖形象使讀者發笑。在溫特森筆下,他自私自利,不顧將士們死活,野心勃勃地追逐著權力和自己的利益。書中寫道:“波拿巴要把他的國家攥在手里,像擠壓一塊海綿那樣擠壓著它,直到擠出最后一滴水。”[1]他仿佛是殺紅了眼的怪獸,心中只有戰爭和敵人,犧牲別人的利益來換取勝利。“他的欲望之火燃燒得比我們持久,因為他永遠不會以生命的代價來換取。”[1]他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拒絕別人建議。此時的拿破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專制獨裁者和利己主義者,這也為他最終的失敗和眾叛親離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
在領袖的帶領下,亨利背井離鄉,他最初憑借著對拿破侖的崇敬,熬過了酷寒天氣和各種艱苦惡劣的條件。在他心中,拿破侖是生活的焦點,“是他在混沌中創造出了意義”[1]。但士兵們在這無盡的戰爭中經歷的只有痛苦和絕望,“我們是鼻子凍得通紅、手指凍得青紫的白種人。三色人”[1]。“三色人”這簡單的三個字,道出了士兵的心酸。“我們穿著夏季的外套,進入了俄國的冬天。我們蹬著膠合的靴子,踩進了雪地。”[1]有人將腿塞進已凍死戰馬的內臟里取暖,第二天早上卻發現自己的腿腳被凍其中,可其余的士兵們無能為力。此刻的拿破侖給國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痛苦,他在歷史上的戰斗英雄形象徹底被顛覆,而這也印證了戰爭帶給人類的負面影響。溫特森立體地塑造了人物,“讓人們以辯證的思維去思考人性更深刻的內涵,以人道主義去拷問與審判那些戰爭的發動者與制造者”[2]。
此外,溫特森沒有直接描寫金戈鐵馬、血流成河的宏大場面,而是細膩刻畫將士們的心理活動,或著眼于微小畫面突出戰爭的殘酷以及戰爭背景下的“非人”狀態。正如肖向東所說,“注重客觀的戰爭在人物主觀心靈上的投射與反映,或大膽直接地揭示個體人物對于戰爭的精神體驗和情感經歷”[2]。在《激情》中,眾多普通人同偉大人物一樣登上舞臺,不僅有征服者拿破侖、名將奧什將軍、約瑟芬王后,更有亨利、維拉內拉這樣的小人物和數以萬計的普通將士。溫特森引導讀者關注這些“小寫的、復數的”個人命運,以此展現“多聲部的、復調的”社會。
溫特森以普通人的視角看待這場影響了歐洲歷史進程的大戰,再一次解構了宏大敘事。亨利看著朋友們失蹤、身受重傷,甚至離世,對人性有了深刻的透視。亨利說到一個石匠被炮彈炸成了兩半,他想把石匠僅剩的身體從戰場上帶回來,但“他的腿已經和其他人的腿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了”[1]。此處第一人稱敘述手法的運用拉近了小說與讀者的距離,使讀者通過亨利的眼睛看到了戰爭的殘酷,感受到戰爭給人們帶來了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創傷。戰爭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人們,而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在一定文化范疇上,又承載著整個民族的歷史,讓人們在渴望和平的同時深入思考如何解決危機。
2 《激情》中的自我身份危機
在《激情》中,殘酷的軍旅生活使以亨利為代表的年輕士兵們的心理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離開自己的母親和愛人來到戰場,變成了艾略特筆下的“空心人”。他們在戰爭中感受不到自我,冷酷淡漠,“沒什么能打動我們,盡管我們都期待著被觸動”[1]。無數幸福家庭破碎了,年輕的士兵困惑不安,在死神的威脅下,無助地找尋生命的意義。“為了在這零度寒天與戰爭中活下來,我們火葬了自己的心,把它們永遠擱置。”[1]他們只有對傷痛保持麻木才可以存活下來,而這心一旦喪失,就很難再找回。溫特森對此描述到,“世上并無一家當鋪可以將心典當。你不能將它拿了進去,包塊干凈的布暫時寄存,待到手頭寬裕時再去贖回來”[1]。總之,溫特森突破了以戰爭英雄為中心的傳統創作形式,而“格外凸顯出對處于戰爭環境中的‘普通人的精神世界與心靈表現的藝術掘進”[2]。
當亨利目睹戰友為了生存付出的努力時,他又一次對戰爭和所謂的戰爭領袖產生了懷疑。那些饑寒交迫的士兵“剁下自己的手臂,放進鍋里煮。身體上的片片血肉。你可以一直這樣剁下去,直到心臟在它被洗劫一空的宮殿里獨自跳動”;“有些人被陽光灼傷后卻長出了新皮,又厚又黑,活像燒煳了的麥片粥”[1]。這一切傷痛都是戰爭帶來的,八年過去,亨利終于明白,拯救人們的不是拿破侖也不是上帝,而是他們自己。正如學者尹星所提到的,“作為背景的戰爭不僅為小說講述的背叛、危機、身份意識等主題提供了戲劇性的環境,也強化了人物的個體選擇和意識視角,因此是不可或缺的”[3]。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下,亨利必須為自己的命運負責。面對同伴的犧牲,亨利開始通過日記思索自己生命的意義,具有私密性的日記“將小說的公共空間轉化為私密空間,從而真實地營造故事發生的場景,詳細描述故事中的事件,細膩地傳達當事人的行為、心理感受與體驗”[4]。亨利不愿再做拿破侖帝國的犧牲品,“就算犯錯我也想自己來。丟了性命也是為自己”[1]。于是他決定逃離戰場,并堅守自己的尊嚴。
在溫特森筆下,維拉內拉是復雜卻充滿魅力的矛盾體。她天生擁有蹼足,渴望成為船夫,卻因性別限制無法如愿,也因這雙蹼足無法成為舞者。她愛上“黑桃皇后”,也因對自我身份的困惑而感到腦袋空白。她已經“忘記了自己要去哪里”[1]。她嫁給一個并不愛的男人,用終身幸福做賭注來緩解找不到“黑桃皇后”的痛苦。“我沒什么可失去的,我早就在更歡樂的時光里失去了所有”[1]。她將一切看做不值一提的游戲,她的心一層一層“把它自己給藏起來了”[1]。當維拉內拉坦白自己是“無心之人”,并希望亨利把她的心從丈夫那里偷回時,溫特森“把這些不可理解的事件嵌入環境之網而使它們現實起來”[5],現實和想象交融,小說的敘事力量由此形成。
此外,維拉內拉主動放棄了“家中天使”的身份。作為女性,她承擔了社會工作,活動領域從家居空間轉移到賭場里、河道上,女扮男裝穿梭于人群中。之前精神上的錯位和迷失感再一次打破始終占主導地位的男性注視。她與亨利一起穿越莫斯科的冬天,死里逃生,讓亨利有了家的歸屬感。像弗吉尼亞·伍爾夫夸贊伊麗莎白一樣,“事實上,她是個開拓的先鋒、迷途的羔羊,富于冒險精神”[6]。伊麗莎白與維拉內拉一樣,不甘當蕓蕓眾生中的隱形人。她們都是不拘小節、勇敢堅毅的女性,一個在變幻萬千的倫敦街頭,一個在迷宮般的威尼斯水城,以高度的自我精神,甚至不顧一切的冒險精神沖破扼殺女性自我身份的父權社會,開拓了自由的天地。
3 《激情》中的情愛危機
在小說結尾,亨利和維拉內拉并未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經歷了炮火和苦難,亨利渴望愛情,相信愛情永恒。他愛上維拉內拉,渴望與她組建家庭,但維拉內拉卻不愛他,并表示“他永遠也無法偷走我的心”[1]。在這一危機下,亨利為維拉內拉殺了她的丈夫,并偷回被藏在那的維拉內拉的心,之后被終身囚禁在瘋人院,且拒絕出逃。直至結局,兩人走向成熟,這一情愛危機才得以解除。對亨利來說,愛情像覆盆子,這些脆弱的生命“不論天氣如何,也不管前景怎樣。沒人知道為什么,在松樹已從根部開始枯萎,野羊都被蓄養在室內的時節,這種溫房植物仍然在難以置信地生長”[1]。亨利渴望擁有這樣的愛情,“像那些回游的鮭魚一樣堅定,尋找愛的蹤跡”[1]。是維拉內拉讓他向曾經的一切作別,那屬于拿破侖的八年軍旅生涯,那喪失自我、喪失心和情感的麻木生涯。亨利義無反顧,最終他卻明白自由不是權力、財富或名譽,而是愛,“哪怕僅僅只有一瞬間,忘我地去深愛一個人,那就是自由”[1]。雖然他終身被囚,也沒有得到維拉內拉對他的愛,但他擁有這珍貴的自由。在小說結尾,他說自己仍愛著維拉內拉,“即使她永遠無法回報,也告訴了我創造出一個愛人與墜入愛河的區別。前者是關于你的,后者則關于他人”[1]。此刻的他明白了,真正的愛情不是靠投射自己的幻想來構建人物,他依舊寫著日記,但幸存、破碎的心已經逐漸愈合。
維拉內拉不僅拒絕了亨利對她的愛,也放棄了對“黑桃皇后”的激情。她開始正視自己的未來,思考自我應如何存在。她帶著女兒平靜度日,“冬天仍去教堂曬太陽,夏天則在溫暖的墻上感受陽光”[1],但開發出了自我的無限可能。她不再女扮男裝,因為她的心、她的自我現在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后現代時期重視個人化故事的講述,將歷史、哲學、現實、心理等問題納入其中,進而解構了宏大敘事。溫特森通過對傳統寫作方式的顛覆,通過一個個講述自我的故事,使讀者可以憑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對其進行填補。此時,小說結構是流動的、不固定的。如同維拉內拉正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她帶著溫柔寬厚的母性,帶著自己的心和自我,走出過去的創傷重新開始生活,做到了危中見機。溫特森在采訪中提到:“我們不斷忙碌地去解決的只是人生的一個過程,因為沒有最終的答案,而你又必須去尋找,必須不斷前行,不斷地在尋找中發現真正的自己,然后不斷地適應或者改變。”[7]如同中國文化中的循環論提到的那樣,結束意味著開始。正是遇到的危機導致了新的循環,《易經》講求既濟未濟,人應該保持不停過河的人生態度。
4 結語
在珍妮特·溫特森的想象與現實的融合敘事中,關于戰爭、自我身份和情愛的危機持續困擾著小說中的主人公,但溫特森的創作意圖絕不僅僅局限在危機本身。小說中的這三類危機均指涉現實,讓讀者冷靜過后對所面臨的生存困境進行思考。溫特森通過解構宏大敘事揭示戰爭的非人道,直接諷刺戰爭帶給人們的身體傷害和心靈傷害,同時聚焦于兩位主人公作為普通人在戰爭背景下經歷的自我身份困惑和情愛焦慮,在生命認知層面開拓意義,即只有努力解除自我所面臨的各種危機,人類才能更好地生存,才能更加和諧地與社會共處。
參考文獻:
[1] 珍妮特·溫特森.激情[M].李玉瑤,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3-219.
[2] 肖向東.戰爭·人性·和平:論戰爭文學主題的文化蘊含與啟蒙意義[J].懷化學院學報,2013(10):47-50.
[3] 尹星.女性城市書寫:20世紀英國女性小說中的現代性經驗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159.
[4] 陳博.西方后現代小說敘事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49.
[5] 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M].伍曉明,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67.
[6] 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衛夫人[M].孫梁,蘇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140.
[7] 珍妮特·溫特森,奧黛麗·拜爾格,蒲火.寫作就是高空走鋼絲:珍妮特·溫特森訪談[J].延河,2016(5):84-103.
作者簡介:劉路兒(1997—),女,河北武安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英美文學。